精神碎片与文化理想
——关于《大十字架》系列及文化意义的对话
张强
张强:我认为你们近期创作的“大十字架”系列对原本的“装置”概念有了很大的突破。这不仅体现在经过重新配置的物品材料能指关系的转变和作品所显示出来的文化营造上,更重要的是这种文化情境的产生是非一般意义上“装置”起来的。而且经过主体严格设计、修正之后打造出来的。打制的过程是一个手工的过程,这对原有的装置概念是一种改变。选择打造而非完全直接挪用对创作者是一种设定的限制。同时也给创作者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和自由度。在《大十字架》系列中,现成物品的配置和选择是慎重的,相对于“打造”是一种从属的方式。整个实施打造的过程可视为一个哲学化的过程。一种由精神而物质、由物质而精神的辩证还原。这种还原从多方位多层面上向艺术的本真状态逼近,进而强化了其哲学性的思考,我认为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这首先从精神和艺术本体两个层面判定了《大十字架》系列的独立品性,同时从根本上将其从流行的装置族类中剥离出来给《大十字架》系列以存在的理由。

高兟:在我们看来,流行装置存在一个问题:作品和作品、艺术家和艺术家之间可相互替代,对现成品放任的堆积和挪用,使作品生产过剩、泛滥和真伪难辨,这将导致装置艺术从本质上对自身的否定。这可能是装置艺术的鼻祖杜尚所始料不及的。当他将小便池搬进博物馆,除去对艺术的揶揄之外,也解放了艺术并给装置艺术下了一个定义:现成品转换情境后所指产生变化即为艺术。这种创造性的观念在批量生产和相互的模仿中失去了创造的意义成为观念的垃圾。面对如此现状,我们决定“打造”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装置”,这在艺术本质上实际是一种“反装置”的实验。
高强:实际上十字架从根本上是无法挪用的。在我们这个无神论的国度,连接人与上帝的十字架从来就没有获得“在场”的身份,我们只能从零开始。我们更像一个木工而非艺术家,我们设计好图纸、丈量好尺寸、解开木头拖入到这个长期工作中去,完全像做一个工程。最终打制成的“十字架”是否还应称之为十字架是一个问题。《大十字架》已从元十字架的语境中解放出来变成了某种“十字架”。
张强:我觉得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十字架是个先在于你们作品的约定俗成的东西。事实上你们打造出的仍然是个十字架,但这并不妨碍从这些作品中读解出更深的含意。我的一篇评论你们作品的文章的题目称为《十字架下飞舞的精神碎片》就是如此。精神的“飞舞”是我从《大十字架》系列面前得到的总体感觉。
高兟:如此静态——甚至可以说是庄严静穆的“十字架”何以会有如此“飞舞”的感觉呢?
张强:面对重构后的“十字架”首先感到的不是宗教殿堂里的神圣与庄严,而恰恰是你们被“物化”的精神碎片在貌似神圣庄严的“十字架”下盘旋飞舞。强调这一点是想说明作品表达的是对此在现实的关注,是把“十字架”精神平面化和哲学意义上现代化的过程。你们所欲强调的神圣性和所谓的理想主义在这里是不存在的,“元十字架”的神圣属性已经在你们的制作过程中被拆散了,实际上已经走向了你们所希望的反面,貌和神离,甚至存在着某种“渎神”的成份。
高强:你的读解是有意思的,这说明《大十字架》系列所包含的意象是复杂的,一些人得出的结论和你是相反的。
高兟:对《大十字架》的不同解读意味着解读者与《大十字架》相互间的创造。解读的过程是其价值意义的生成过程。
张强:我之所以指出你们作品中的“渎神”的成份是有根据的。记得1990年在撰写《山东美术史》当代部分时我曾考察过你们在“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引起广泛关注的《充气主义》系列作品。我觉得从《充气主义》一直到1992年——1993年带有波普倾向的《复印机艺术》、乃至于近期的《大十字架》系列,实际上有一条潜隐的“渎神”线索,贯穿在你们多年的创作行为之中。其中,如果说《充气主义》的“渎神”是外向的、扩张的,《复印机艺术》的“渎神”却是现实的、夸张的,而《大十字架》系列的“渎神”与前两者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是直接借助了一个“圣体”。在对“圣体”的打制复原过程中,“渎神”的欲望与意志得到昭显。那就是最终的十字架已经成为一个面目全非的“物性质料”之物。
高强:在《充气主义》中确实存在过一个“渎神”问题,那更多针对的是传统文化而非指超自然的上帝。《复印机艺术》也可以说有某种“渎神”成份,它所针对的是人造的神、与其说是“渎神”不如称之为批判。而《大十字架》系列若言“渎神”未免武断,至少“渎神”不是《大十字架》系列的根本属性。
张强:我所指的“渎神”实际上是很宽泛的。
高兟: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讲“渎神”和“敬神”是一回事,不然临终的尼采怎么会既称自己为凯撒又称自己是“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呢?我想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权利剥夺你对《大十字架》系列的“渎神”解读,其实你的解读是有共鸣的。彭德曾来信言称:十字架在欧美的地位比国徽还要神圣,将十字架作如此结构处理,对欧美观众来说,无异于当着中国人的面拆天安门城楼。彭德先生的话或许严重了,但他也道出了《大十字架》系列的“渎神”性质。
张强: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问题,彭德所言属道德判断范畴。仅从这个层面上解读《大十字架》系列,从根本上失去了作为艺术存在的理由和价值。那太简单,和一幅政治漫画没有区别。我认为《大十字架》所呈现出的是一种深刻的“文化渎神”,这根本上不同于伦理意义上的“渎神”。
高兟:我更觉得《大十字架》系列中的所谓“渎神”和“敬神”品性是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因而使复杂难以言说。这体现在一个“飞舞”的“精神碎片”物化在一个同构的“形体”之中。精神语言转化为能指肌体之后,你无法剥离出其中一块称之为“渎神”的、也无法剥离出另一块称之为“敬神”的,“渎神”与“敬神”的感受因人而已。它实际上是观者自己所持有的观念与其相互投射的感觉。不然就不存在着王林感觉中的“崇高”、“壮丽”和“令人敬仰”;黄专称之的“宗教救世的方案”;岛子所言的“对人类的精神处境的异化深怀关切”以及你所说的“飞舞的精神碎片”以及彭德的“《大十字架》所蕴含的永恒与理想,有着超越具体宗教的启示性”等不同的解读和论断了。
张强:作品从艺术家手中完成之后滑向一个更广阔的空间隧道,成为一个“自在之物”。任何对它的阐释都是合理的,从这个角度看,艺术家自己的宣言和理论往往是靠不住,甚至是脱节的。艺术家的理性把握常常在感觉创造之中被自我颠覆了,《大十字架》系列也存在着这种颠覆,正是由于这种颠覆使得作品脱离了你们本来所持有的“理想主义”和“崇高”以及“庄严伟大”的设定,走向了反面——“碎片”与“渎神”。当然这种“渎神”是属深层的、文化的,所以在我看来是深刻和真实的。
高强:假如这种理论是成立的,意味着创造者在作品“自在”之后也可以站在一个解读者阐释者的立场发言。这种发言与非创作者的发言不同之处是:前者与作品存在有着某种“血缘”关系,即他的阐释不可能完全切断创作过程中所持有的理念,而后者则是自由的。尽管如此我仍愿站在创作者的立场表达一种元艺术原则而非仅仅阐释它。
张强:从你们为《大十字架》系列作品的命名来看,你们选择了《世界之夜》、《世界黄昏》、《黎明的弥撒》、《人类的忧虑》这些神圣庄严的名称是否想表达某种你们持有的人文主义或理想主义和你们所言称的“人类主义”信念呢?
高兟:可以这样讲。我们主观上希望我们是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甚至站在“后人类”的立场反观人类的历史,从人性中向善的原则度量、审视人与上帝、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以及历史自身发展的纬度。在视觉文化的历史这个层面,我们尽可能把握一种“原创”的“临界思维”、以及“临界状态”和“临界创作”。
张强:这未免有些虚妄。请解释一下何为“临界”!?
高兟:这有些虚妄吗?但我认为我们作为跨世纪人类中的一员应当持有一种批判的文化理想主义的信念,不然就有滑向世俗的犬儒主义或物质主义等庸俗文化泥沼的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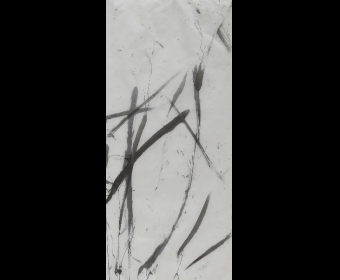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