蓑衣何处太荒唐
——朱东润的乐山武大
龚静染/文
一
朱东润到达乐山的时间是1939年1月13日,更准确的时间是当天下午一点钟。
这个时间很重要,因为武汉大学要求返校必须在1月15日前,过时不候。也就是说超过了这个时间,你就可以不用再来了,只能另谋出路。但是朱东润居然提前了两天从几千里以外赶到了,在一路上仿佛有贵人相助,眼看就到不了校了,但很快就出现了转机。比如到了重庆后,根本就买不到去乐山的汽车票,到乐山要等一、两个月,如此这般到了乐山,事情早黄了。但就在这时,他居然神奇地买到了一张飞机票,搭上了刚刚开通的“水上飞机”,这种飞机只能载几十个人,飞行高度也不高,但几个小时就顺利到了乐山。为此,他难掩欣喜之情,把第一次坐飞机的感受写成了一首赋:“于是翱翔徘徊,从容天半;架飞机而西行,望万象之弥漫;初敛翼而低昂,忽奋迅而泮涣……”
朱东润就这样“意外”地来到了乐山。
他到的当天就找到他的泰兴老乡戴凝之,戴也在武汉大学供职,热情地招待他吃饭,并把他安排在了乐山府街的“安居旅馆”里住下。但这看似简单的住宿,其实后面有不同寻常的含义,但朱东润刚来人生地不熟的,也就只好听从别人的安排。但住了一段时间后,他发现了这个安排的“妙处”。当时,武汉大学的教授们分成了两营,一边是以安徽藉为主的“淮军”,其主要人物是校长王星拱;一边是以湖南藉为主的“湘军”,主要人物是教务长周鲠生。这两营的人一直暗中争斗,到了乐山后矛盾日趋表面化。当时,“淮军”的人到了乐山后主要住在鼓楼街、半边街,而“湘军”主要住在玉堂街、丁冬街,而朱东润则住在不偏不倚的中间,两边都不挨边。这点是他的老乡戴凝之早替他考虑周到了。
朱东润能够到武汉大学教书,主要是陈西滢的原因。他们是上海南阳公学时的同学,朱东润小时候家境贫寒,但后来有人看重他是块读书的料,便出资让他到上海读书,其实是把他当成了一桩生意来做(读书的钱是要还的),毕业后,朱东润在《公论报》做事,但报纸不久就解散了,暂时没有去处,他便去了英国,“那时出国的手续很简单,用不到护照,用不到签证,只要到外国轮船公司,花三二百元可以置票直达欧洲。日本船的三等舱更便宜,九十元可以到英国。”(《朱东润自传》),他到英国后是勤工俭学,但读了两年中途就回国了。
有了国外的这点经历,又懂些翻译,所以他便从南通师范学校到了武汉大学谋了个外语教席,当然收入也比过去好了不少。在到乐山之前,朱东润已经在武汉大学待了八年时间,即1929年到1937年,也算得是个老武大了,而抗战的到来,武汉大学被迫西迁大后方的乐山,教授们或去或留都有选择,但这也成为了武大内部帮派斗争的一个整合的机会,各派都拼命安插自己的嫡系,所以像朱东润这种无根无派的人,早早成了别人的眼中钉,想乘机将他除掉。
但幸好有陈西滢的帮助,朱东润才得以留任,陈西滢是文学院院长,说话管用。但朱东润对陈西滢并没有特别的感谢,只是君子之交而已。朱东润与陈西滢在上海做同学的时候,陈西滢还叫陈沅,后来改成了陈源,字通伯。当然,陈西滢的名字为世人熟悉,是因为他与鲁迅的一场笔仗,让他多少背负了不少骂名,我们这代人知道的陈西滢就是因为中学课本里的一篇文章,他同梁实秋、林语堂、邵洵美等一样,成了鲁迅的论敌。朱东润有远见,当时就认为此事“一定会在文学史里传下,可是不一定于陈源有利。”(《朱东润自传》)这算是替陈西滢说了句公道话。其实,其时武汉大学有两个人都同鲁迅有过节,一个是陈西滢,一个是苏雪林,前者主要为“女师大风波”的立场问题起争执,后者更多是因私,据说苏雪林在一次书局老板的私人聚会上对鲁迅的怠慢大为不满,从此结下怨恨,在长达几十年的岁月中不遗余力地骂鲁,一直骂到后来去了台湾。
朱东润很清高,不依傍,更不容忍沆瀣一气。他在早年曾经有做官的机会,但由于不喜欢官场的习气,很干脆地放弃了。那是在1927年,朱东润刚好三十岁,当时国民党南京政府正在组建阶段,吴稚辉去信叫朱东润到南京谋事,位置也不错,是担任南京中央政治会议秘书。朱东润在《公论报》时曾经做过吴稚辉的助手,吴稚辉非一般人,不仅是国民党元老,也是功底深厚的文化人,他觉得朱东润有才便有意让他去发展,但朱东润一到南京就水土不服。
他刚到南京的当天,吴稚辉正好出差去了外地,就叫他的一个亲戚去陪朱东润。当天,那个年青人请他到馆子里搓了一顿,就两个人,但要了“四大四小”(菜肴),这让朱东润惊讶于这“一桌不菲的席面”,其实,人家可能是一片好意,有接风洗尘的意思,但过惯了清贫生活的他如何习惯这般奢侈。饭后,那位青年又同他聊天,大概也没有什么好聊的,就聊起了南京的娱乐,“话题落到看戏。最后说到准备给一位女演员赋两首律诗,问我能不能和一下。也许我这个人有些大惊小怪,在革命中心,听到作诗去捧一个女演员,这还不稀奇吗?稀奇的事还多呢,不久以后,有人指给我看在那座接待室里,蒋介石招待电影女明星;又有人给我说狄秘书和秦淮歌妓小金凤怎样要好。革命就是这样的革法,我这个中学教师真是开了一番眼界。”(《朱东润自传》)
朱东润原以为到了南京是来革命的,为革命政府效力的,哪知道情况并不如他所想,他感到自己仿佛是局外人,对世事实在是有点不解风情。“这一年7月间,南京城里真是熙熙攘攘,过着太平的岁月……阴沟一样的秦淮河,在散文家朱自清的笔下是‘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一般的女士们,头发久已剪短了,脂粉还是不能没有的。尤其在政府机关,有了这样的女同事,那时粉香四溢,格里罗嗦的字句变得清真雅正,东倒西歪的书法也变得笔飞墨舞了。”(《朱东润自传》)
朱东润对这样的“太平的岁月”却是如坐针毡,他认为自己不是搞政治的料,而他的周围不过是“一批没有脊骨的政治贩子”,所以他在南京呆了八十天后便再也呆不下去了,他把刚刚领到不久的国民党党证“扔在转角楼对面的屋脊上,由它风吹雨打,作为我这八十日生活的见证。”
从此以后,朱东润再也没有跟政治打过交道,一心只做学问,安心当好教书匠。他后来在文革中经历了“非人磨难”,却在打到“四人帮”后以83岁高龄入党,但这跟政治没有什么关系,他只是想给过去的苦难正名,甚至这样的正名还多少有些天真的成分。
二
武汉大学到了乐山后,当地人把里面的人称为“中央人”。“中央人”包含了些特权的意思,这首先体现在经济收入上的优越,当时武汉大学的教授,男的每月拿一千元,女的拿八百,其他职员薪水也不菲。
乐山地处川南大后方,当时的生活水平是非常便宜的。叶圣陶是1938年10月29日到的乐山,与朱东润到的时间相差不过两个多月,他到了后发现此地生活舒适,“肉二角一斤,条炭二元一担,米七元余一担。……买小白鱼三条,价一角八分,在重庆须六角。大约吃食方面,一个月六十元绰绰有余矣。”(叶圣陶《嘉沪通信》)消费与收入的巨大差异,让人不得不费心思去为他们理财,所以上海的银行都跑到乐山来了,恨不得让钱多得在当地没法消受的“中央人”把钱都存在银行里。叶圣陶曾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大学教师任课之少,而取酬高出一般水准,实同劫掠。于往出纳课取钱时,弟颇有愧意,自思我何劳而受此也!”
当地人自然艳羡得不得了,殊不知物价也随之往上抬,其实是“中央人”打破了当地的生活秩序,对老百姓的消费形成了挤压。后来,乐山的物价高涨起来以后,通货膨胀,钱是真的不值钱了,教授们很快就感到了生活的压迫,但这是后话了。但对于高薪来说,朱东润显然还是看重的,尽管为了这份高薪他付出了妻离子别的代价,“自从二十七年离别家庭,到达乐山以来,二十八年的冬季泰兴便沦陷了,全家在沦亡的境地挣扎,只有我在这数千里外的大后方。路途是这样远,交通是这样不方便,一家八口谈不到挈同入川,自己也没有重回沦陷区的意志。有时通信都狠困难,甚至三两个月得不到一些音耗。”(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序)
朱东润与新到校任课的叶圣陶关系不错,也许是叶圣陶也没有什么特殊关系(也是陈西滢推荐来的),同他一样不介入任何内部斗争的缘故。但在大学里面,教授也是分成了三六九等的,一些学究们也是要讲出身与血统的,像叶圣陶这样的教授虽然在外面的名声很大,但进了学校就完全不同了,而有些人可能也并没有什么真本事,但他们认为写几本白话小说算不得什么,倘若没有些研究诸如经、史、子、集之类的东西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所以,叶圣陶在武汉大学多少被那些科班出身、沾过洋墨水的人瞧不起,出身低微常常为人诟病,连他在讲课时的“苏州腔”也常常被人调侃,被说成是“期期艾艾”,成为了别人打小报告的罪名。于是叶圣陶与朱东润便被调去完成“苦差事”:为新生开语文补习班,一人顶一班。不过,这般处境也成了两人做朋友的基础,朱东润心里是站在叶圣陶一边的,他觉得那些自命不凡的人其实不过是马粪皮面光,道貌岸然而已。
在乐山的一段时间里,朱东润与叶圣陶都住在乐山城北的竹公溪,他们两家对河而住,“水浅的时候,踏着河床乱石就可以过去了”。这条竹公溪其实只是穿过乐山城区的一条小河,唐代女诗人薛涛曾经盘桓在此,所以它并非纯粹是一条莽撞的野水,且两边也不乏美景入目,叶圣陶之子叶至诚就曾回忆道:
“一天,父亲和朱东润先生出去。通常的走法,总是出篱笆门左转,沿竹公溪边的小路到岔路口,下一个小土坡,从沙石条架成的张公桥跨过溪水,对岸不远的竹林间有个十来户人家的小镇,有茶馆可以歇脚。这一天,他们改变了路线,到岔路口不下土坡,傍着左手边的山脚,顺山路继续向前,乐山的山岩呈褚红色,山岩上矮树杂草野藤,一片青翠,父亲有过‘翠丹崖为近邻’的诗句。山路曲曲弯弯,略有起伏;经过一个河谷,也有石板小桥架在溪上,只因远离人家,桥下潺潺的溪水,仿佛分外清澈。望着这并非常见的景物,朱先生感叹地说:‘柳宗元在永州见到的,无非就是这般的景色吧!他观察细致又写得真切,成了千古流传的好文章!’父亲很赞赏朱先生这番话,将其写在他当天的日记里。”(叶至诚《旅伴》)
实际上,竹公溪虽然只有几米宽,却也有不少自然之趣,且不说它在四季中的喧嚣与静谧让人沉浸,就是过去在河里捞点小鱼小虾也应该不存问题,那绝对是佐餐下酒的好东西。王世襄当年曾写道:“瓜脆枣酡怀蓟国,橙黄橘绿数嘉州。”但王世襄的情趣不见得朱东润就有,他会不会扁着裤腿去汊水摸鱼就是个问号,因为朱东润当时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份闲情逸致,好在竹公溪与市尘隔绝,相比人际关系复杂的校园,这里不失为一个清净之地。
武汉大学的派系争斗是有渊源的,诸如“欧美系”“武高系”“东南系”“本地系”等,早年闻一多先生在武大短暂任教,并很快离去就是因为“沾不上边,应付不了”(《闻一多与武大》俞润泉/文)。当时武大虽然西迁到了偏于一隅的小地方,但里面的斗争从来没有中断过,朱东润与叶圣陶在乐山武汉大学同属被排挤的对象,但可能是由于两人的性格风格迥然有别,所以在对事的态度上也不尽相同。叶圣陶要散淡、洒脱一些,他认为大可不必在一个小塘里折腾,在乐山呆了两年多时间后便去了成都,告别了那些正斗得如火如荼的“湘军”和“淮军”。朱东润本来也可以走的,但他坚持留了下来,他仍然不甘离开这个勾心斗角之地,他甚至决断地认为“斗争就斗争吧。这虽然不是我的要求,但是我也无法拒绝。”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他当时的选择是很多的,比如可以到三台县的东北大学去,或者到贵阳师范学院去,也可以到西北大学去,都是去当系主任,比在武汉大学的待遇好。但他最终是哪里都没有去,由此看到一个人的执拗,但朱东润不无自嘲地说:“真想不到我把妻室和七个子女留在沦陷区,走到七千里外的武大中文系独力作战,对付这高高在上的‘金德孟’王星拱校长,和刘系主任。”(《朱东润自传》)当时,他也可以到南京的中央大学去,跟他颇为熟悉的陈柱尊在那里当校长,只要他愿意随时都可以去,只需一纸信函,况且南京离他的家乡泰兴非常近。但朱东润绝对是不会去的,因为他不可能去沦陷区做文化汉奸,被人唾骂。他非常明白,“无论如何,只要敌人和汉奸在南京和泰兴,我是不会回家的。一年、两年、三年,甚至更长更远的时间,我一定要坚持下去,也一定能够坚持下去。”朱东润做到了这点,直到抗战胜利后,他才到了南京去教书,而他整整在乐山呆了三年零七个月时间,说他坚守了知识分子的气节也好,说他愚古不化也好都能找到理由。但在乐山武汉大学的几年里,也让他感慨良多,毕竟那是他一生中难忘的地方,所以在他离开乐山的时候,专门写了一首诗:“披发只今多拓落,蓑衣何处太荒唐,风和帆饱樯乌动,剩与嘉州伴夕阳。”原来事情如此简单,所有的校园斗争都瞬间化解了,只余一声“太荒唐”。这首诗也看出朱东润的感慨很是伤神,与他初到乐山时的情形完全不同,知识分子大凡都有些迂腐,说起来满腹经纶,但就装不下退一步则海阔天空这个简单的道理。
三
通过那场旷日持久的校园斗争,也能够看到朱东润性格中的幽暗之处。他与他的那些上司和同事们不认同、不妥协、互不买账,从正面讲,是对某种理想情怀的坚守,从文化性格来讲,也是知识分子固有的“文人相轻”心理作祟。武汉大学素有“湘淮之争”,朱东润前面所讲的“刘系主任”就是指的刘博平,此人一生都在“小学”中苦下音韵词义的功夫,自视为国学门类中之正宗,所以在刘博平看来,朱东润的学问不过是“半壶水”“半路出家”,不值一提;当然,朱东润也不理会刘博平,特别是西学东渐的境况下,他们代表的是新学问,那些只会在故纸堆里洋洋自得的陈词滥调为新派学人不屑。
当时的文学院院长刘永济也是搞传统学术的,他是湖南人,自然是“湘军”中的一员大将,但刘永济的学问也非俗流,在词学研究方面功底深厚,在他留下的二百有余阕词当中,确实不乏佳作,如“等是虚空无著处,人生何必江南住”等,而刘永济与“寅恪(陈寅恪)、雨僧(吴宓)”二翁私交甚密,自然不把朱东润放在眼里。
1940年的一天,刘永济见到屋檐下的豆架初成,触景生情,写了一阕《鹧鸪天》:“岁序潜移悄自惊,江村物色又全更。蚕初作茧桑都老,豆欲行藤架已成。云易幻,水难停,百年销得几瞢腾。疏櫺小几茫茫坐,翻尽残书眼翳生。”词中的洒脱与性情,不见红尘中的蝇营狗苟,但生活并非如此,走出豆架便是另一番景象,乐山武大里明争暗斗从来没有间断过,哪怕是在最为艰苦的抗战时期。那时,由于生活的贫困,刘博平和刘永济还因为经济拮据在乐山大街上卖过字画。大家都过着苦日子,但就没有人愿意放下面子,以宽容的姿态对待周围的人和事,派别中的双方都在温文尔雅的面目之下,剑拔弩张地斗得你死我活,笔者不得不惊叹于人性的复杂。
当时还是武汉大学青年教师的程千帆曾回忆道:
“武汉大学才办的时候,文学院是闻一多当院长,后来他走了,就是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当院长。但中文系主任是刘博平先生,一来他是湖北人,二来他是黄季刚先生的大弟子,有学术地位。所以陈源尽管当院长,也不能动他。陈源是胡适他们一派的,中文系像刘永济先生、谭戒甫先生、徐天闵先生、刘异先生(他是王闿运的弟子,讲经学的),都是旧学一派。还有朱东润先生,和陈源是同学,他们一起到英国去留学。陈源大概有钱,就一直读完,朱先生比较穷,没有读完就回来了。后来还是陈源介绍他到武汉大学教书,他和刘博平先生、刘永济先生搞不好,并不是两位刘先生对朱东润先生有意见,主要是他们对陈源有意见。我到武大的时候是个年青人,我对朱先生还蛮尊敬,他对我也蛮好。”(程千帆《劳生志略》)
站在局外看人就不一样。在程千帆的眼里,刘博平和刘永济是值得尊敬的前辈,朱东润与他也过从无隙、心无芥蒂。他不参与,不介入,所以大家相安无事。其实这里面恐怕有个根本的问题,就是程千帆还是一个年轻人,疏于世故,当然也还不具备与他人平起平坐的资历。
当年的大学,在一般人的眼里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地方,大学教授也是饱有诗书之辈,但殊不知教授也是人,在很多时候同一般人没有区别,当然,普通人在勾心斗角上肯定是难以企及的,因为他们不懂皮里阳秋,更不懂春秋笔法。程千帆的回忆中就留下过当年的一段龌龊:
“后来我又认识了徐哲东(震)先生,是太炎先生的弟子,常州人,讲公羊学,又讲韩柳文。他先在中央大学当讲师,到武汉大学的时候已经升教授了。徐先生住在乐山的城外一个叫作王石碑的地方,离乐山嘉乐门外还有十五里路。有一次,日本人听说蒋介石要去乐山视察,便派飞机把整个城市都炸了,这情报是错误的,但城市给炸了。当时人能够在城外找到房子的,都在城外找了房子。我住在学地头,离嘉乐门外大概有几里地,到王石碑还有十五里,很远。徐先生是练过武功的人,走这点路不大在乎。他在中央大学当讲师的时候,有一次中文系开会,请哲东先生舞剑,他答应了,舞剑的时候长袍子全身都作响。朱东润先生当时在武汉大学,刘博平先生当系主任,朱先生教文学批评史,博平先生的学术思想比较守旧,认为文学批评可以不必修。徐哲东先生应聘到武大,人还没有来,要开学了,博平先生是系主任,就替徐先生开列了一些课,其中有一门课是传记文学研究,这是当时教育部选课的课程。徐先生到了以后,看到这个课表说,我以前没有教过这个课,是不是暂时开别的课代替。他同刘先生商量后,就决定开个韩柳文研究,因为他原先在中央大学教这个课,中央大学的《文艺丛刊》里面还有他的《韩集诠订》这样的专门著作发表。朱东润先生就开玩笑,写了一篇杂文,投到当时重庆的一个刊物叫作《星期评论》上发表,是国立编译馆馆长刘英士编的,刘同我也有点来往,我在那里投过稿。他后来在南京办《图书评论》,我也发表过文章。朱先生的杂文说,大学里面也很特殊,传记文学怎么开出韩柳文研究来了?是不是把讲《郭橐驼传》和《永州八记》变成了传记研究?徐先生看到后很生气,说:他的嘴巴很巧,我可不会讲,但是我会打。我要打他,我打的人不是我治还治不好。东润先生就很狼狈。那时教室旁边有个教员休息室,两课之间可以在里面休息。只要哲东先生在里面,东润先生就不敢进去。后来哲东先生有个比较熟的朋友,是法律系的教授,好像是叫刘经旺。他是湖南人,是个好先生,就劝徐先生。徐先生也就答应不打了。”(程千帆《劳生志略》)
程千帆还说了句“东润先生可不敢把这件事情写进他的《自传》里”,此话说得揶揄了点,但从文人相恶这件事情上看,武大的派别之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像朱东润这样的笨拙之举总会成为众人唾之的对象。在抗战艰苦的大时代氛围下,小环境的龌龊不断,大概是知识分子的通病,但在乐山期间,朱东润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著作,同时成为了中国传记文学经典、“二十世纪四大传记”之一的——《张居正大传》的写作。
1941年秋天,那是朱东润最为彷徨的一段日子,他就在这秘而不宣的岁月里开始了长达三年的艰苦写作,但他的内心装着一台大戏,他已经为里面的每一个人物画好了妆,准备粉墨登台,这时的朱东润在下笔的冲动中感到了灰暗生命里的一丝喧嚣。《张居正大传》的一开头,就我们拉开了一幅乱世的序幕:朝室倾轧,血光冲天,马蹄声急……而张居正便是在这样乱世中登场的:
居正出生的时候,明室已经中衰了:太祖、成祖的武功没有了,仁宗、宣宗的文治也没有了,接后便是正统十四年英宗出征,不幸恰被鞑靼人包围,大军数十万遇到歼灭的命运,连皇帝也成俘虏。在这个困难的阶段,幸亏于谦出来,拥立景帝,支持了当日的天下……(那个时代)整个政治的提示是偏执与专制,大臣常有的机遇是廷杖与杀戮。因此到处都是馅谀逢迎的风气。政治的措施只能加速全社会的腐化和动摇。这是张居正出生的时代。(朱东润《张居正大传》)
朱东润为什么要选张居正这样一个人物来作为传主呢?因为这是一个挽危于既倒的功臣,他整顿内政,抵抗外侮,让垂危的明王朝延长了七十二年。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正是抗战进入最为艰难的时期,这本书在出版后是起到了一定的现实作用的。另一方面,张居正在打击贪官污吏、刁生劣监上也显出了英雄本色,这是朱东润在借张居正表现自己的政治文化见解,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下,不难看出他在现实困境中的角色认同和理想主义情怀。对于这本书的写作动因,他自己也说得很明,“倘使大家记得一九四三年正是日寇深入中国,在侵占了东北四省,更占领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而后,他的魔掌准备一举打通平汉铁道、粤汉铁道,席卷广西、贵州,从而把整个中国扼杀在四川、云南和西北,那么对于内安中国、外攘强寇的张居正和他的时代,必然会有一个不同的看法。”(朱东润《遗远集叙录》)但除了现实意义以外,朱东润如此沉迷在历史中演绎跌宕起伏的斗争场面,是不是多少也在寻找逼仄环境下的精神突围?
朱东润在写书的过程中忍受着生活和精神的双重煎熬,其写作环境是相当艰苦的:“日减一日的是体重,日增一日的是白发。捉襟见肘、抉履穿踵的日子,总算及身体会到。住的是半间幽暗的斗室,下午四时以后便要焚膏继晷。偶然一阵暴雨,在北墙打开一个窟窿,光通一线,如获至宝,但是逢着寒风料峭、阴雨飞溅的时候,只得以围巾覆臂,对着昏昏欲睡的灯光,执笔疾书。这些只是物质的环境,对于精神,原算不到什么打击。然而也尽有康庄化为荆棘的时候,只得把一腔心绪,完全埋进故纸堆里去。这本书便是这种生活的成绩。”(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序)
笔者读过不少关于乐山武大时期(1938—1946)的回忆文章,作者如叶圣陶、袁昌英、苏雪林、凌叔华、钱歌川等,他们当时是乐山武大的教师或家属,文章中有不少关于乐山生活的片段,辛酸苦辣,林林总总,但都没有直接记录校园中勾心斗角的事情。客观讲,纷纭境中矛盾时时存在,文字中大可不必再去斤斤计较,人性的丑陋常常为人避之不及,在钱钟书的《围城》中,方鸿渐、赵辛楣、李梅亭、高松年等人在“三闾大学”中的明争暗斗,其实在乐山武大中也一样是存在的,可以说学校表面看上去平静,但人心的动荡远远难有凌叔华“看山终日不忧贫”的那份悠闲从容。在当年的武大学生留下的回忆录中,齐邦媛的《巨流河》、杨静远的《让庐日记》、吴鲁芹《暮云集》等中都留下了不少当年的记述,后来又看过很多期台湾武大同学会编的《珞珈》杂志,内容更多的是艰苦学生活中求知问学及青春岁月中的友情和爱情,总体来说他们对那段生活都是缅怀的、一往情深的。但在朱东润的回忆中则相反,可以说是苦涩的、不堪回首的,甚至还多少带着点憎恨和厌恶,让人容易对他产生某种阴暗的联想,最少会觉得他不是那么澹泊和镇定。
但朱东润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据他的亲友学生回忆,他确实是个非常固执的人,自信且自负到了无出其右者的地步,连郭沫若都曾挖苦过他是“资产阶级怪教授”。但是这怪中也有真,朱东润是个较真的人,他敢于揭开伤疤让脓液流出来,这自然会讨人嫌,但他是真实的,真实得有些小肚鸡肠,仿佛庸俗的处世之道他几乎全然不懂。另一方面,朱东润又自视甚高,非常看重自己的学问,认为的他的传记文学是开创性的。在乐山的三年多时间中,他笔耕不辍,完成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张居正大传》,并毫不客气地称之堪与《约翰逊传》和《贝多芬传》相提并论,这在其他人看来就是个自大狂,好在金子经得起时间的淬炼,真东西有时就是佶屈聱牙的异类。
其实,文学上的成就并没有为朱东润带来多少欣喜,有人会在大谈创作经验的时候或多或少去美化自己,他却不想在读者面前讨巧卖乖,他甚至认为“著书只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他说:“有的人底著作,充满愉快的情绪,我们谈到的时候,好像看见他那种悠然心得,挥洒自如的神态。对于我,便全然两样。我只觉得是一份繁重的工作……生活是不断地压迫着,工作也是不断地压迫着。”(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序)其实,在朱东润的心中有很多不乏温情的东西,比如他在后来写过一本叫《李方舟传》的书,这是他专门写给他妻子邹莲舫的。这是一部很特殊的书,李方舟就是邹莲舫的化名,丈夫写妻子的书在明清时期早有先例,但多是文人的风月之作,如冒辟疆《影梅庵忆语》笔下的董小宛,但朱东润的《李方舟传》是“中国传记史上少有的一部为中国普通家庭妇女著书立说的作品”。应该承认,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流淌的是真挚的爱,这跟其他人眼里一身傲骨的朱东润有很大的差异,朱东润破例地在传统中为自己开了回“小灶”,硬生生地在帝王将相的传记系列中挤进了一个小人物,为此他为自己辩解,“在下州小邑、穷乡僻壤中,田父野老、痴男怨女底生活,都是传叙文学底题目。”(朱东润《遗远集叙录》)其实,在笔者看来,《李方舟传》或许叫《李方舟忆语》更为适合,文章也要讲究量体裁衣,《李方舟传》显然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原因就在于朱东润把一个回忆录当成了传记,虽然我们可以将之视为创新尝试,但我更愿意把它看做是他任性和自负的再一次显现。对于处理传记题材轻车熟路的朱东润先生来讲,不至于不知道一部成功作品中所需要的写作元素,但他写了,没有任何顾忌,这又让我想起他那句“蓑衣何处太荒唐”的诗句。
朱东润说过,“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一生”,但传记是一回事,生活是另一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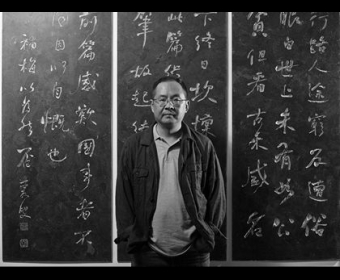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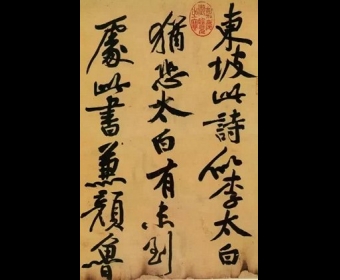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