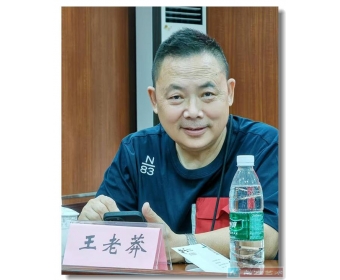川沙:物主义时代的隔海抒情诗观(4)
|
九 身处当代,我们的文学作品是当代的吗?我们的当代文学正处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景况。我们处在一个文学的断代史后的时期,我们处在一个反文学的时代。我们不仅是失去了传统文化,更毁坏了传统文化,我们不能够站在传统文化的肩膀上去承接现代文化。因此,我们的诗歌和小说,我们的文学作品真的是在浪费木材! 在这个“后”派盛行的“拿来主义”时代,如果我不能够消化,我更喜欢在古典主义的道路上裸体地缓慢爬行,而且,将身子更近地贴在普罗大众感情的土地上爬行,因为,如果我就是他人的话,我都不能感动,都不能诚实面对,在我自己面前都不能通过的东西,我怎么能够写给他人呢?就是说,我不喜欢毫无分析地将那些现代主义的新衣来绑缚在我的身上。
诚然,刚到英国的时候,在伦敦的大街小巷的老石头房子里穿行的时候,我也感受到一种古老陈旧的压抑,简直就像是时光倒流,回到了一派《大维。科波菲尔》那部黑白哑声电影里展现的狄更斯笔下19世纪中叶英国社会的老城风貌,那个时候,我才开始理解现代主义在欧洲的时代背景,才理解为什么在马里内蒂在他的那篇“未来主义”的宣言里,那么偏激地诅咒意大利说“博物馆就是坟墓,博物馆将无数的坟场墓地布满大地……博物馆就是屠杀画家和雕塑家的荒谬绝伦的屠宰场……”。(这有些象我感觉到比我大三十多岁的父亲在他生前总是在我面前念叨时的压力,更何况那些博物馆里从画布和雕塑身上探望出来的一双双几百上千岁的逼视着他们的眼睛。)理解为什么布勒东要和阿拉贡、艾吕雅、马里内蒂和恩斯特一帮人在他们的诗歌运动里搞风靡一时的什么“口述和写作的自动创作法”、未来主义的“自由辞藻”、“达达”派的“自发创作”、“文字游戏”、“语音秘方”、“禽鸟语言”、“词汇革命”和“字母主义”等等。但是,他们显然有些矫枉过正。作为超现实主义运动的掌们人,布勒东领导的运动在风行几十年后,随着他的死亡而宣告瓦解。在承认现代主义正面意义的同时,我们应该不违心地老实承认,现代主义运动最后还是成为了“博物馆”里传统文学主干的一个细小的旁支,并彻底地融汇进了主干并成其为中间的有机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体的实物你如果到了巴黎,可以在蓬皮杜艺术中心参观时看见。实在地说,除开他们的一些有积极意义的创意外,他们的部分粗劣的绘画和雕塑,到今天还是让大多数人不知所云满头雾水,很多就是无可争议的垃圾!而且,看不懂的主要就是亚洲人。 在自然科学领域内有时间和空间基准,例如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始建于1675年,位于英国首都伦敦的“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 (Royal Greenwich Observatory (RGO)),就规定了经过这个天文台的子午线被确定为全球的时间和经度计量的标准参考子午线,也称为本初子午线(Prim e Meridian)”,即零度经线。 在社会科学领域,如公元1901年在伊朗发现的《汉漠拉比法典》[10],1804年公布的《拿破伦法典》,1787年完成的《美国宪法》等等法典,属于社会科学领域的法的尺度的成文法典。 我们在19世纪下半叶俄国托尔斯泰、契柯夫和妥思托耶夫斯基等作家的作品里,都可以看见法院、陪审团、陪审员这些字眼和场景的描写,而且由此而产生“罪与罚”的系列详细法典、道德是非观念和相应的良心上的终极追问。这些,无疑是显然都还不太健全的沙皇俄国时期社会科学领域的法的尺度具体体现。考察上述几个作家的作品描绘的俄国社会场景同时期的中国,我们处在1851年至1909年的依次为咸丰、同治、光绪和宣统四个皇帝的统治,我们的法官是什么呢?文学方面,无论曾朴的《孽海花》,还是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九命奇冤》和《恨海》,都仰仗衙门里的“青天大老爷”包公包丞相了,衙门里没有什么“陪审团”,有的是脱了裤子打板子。 西方国家包括当时的还很封建的俄国、都还有在法之外的道德和良心的裁判所如教堂,涉及的是宗教领域内的舆论和忏悔等问题。我们也有佛、道教的一些道德的规范,但更多的 却是族法和家法伺候。在苏童的大概是描写民国时期的《妻妾成群 》里,唱京戏的梅珊就是朗朗乾坤下的家法伺候:让家仆处以投井——死刑!法官就是娶了五个姨太的家长老爷陈佐千,法警或刽子手就是家仆们。
亚里斯多德的悲剧理论强调故事情节的营构是悲剧的灵魂,黑格尔的悲剧理论强调伦理冲突结构是悲剧的中心。无论是悲剧人物的过失论,还是悲剧情节的有机整体论,抑或悲剧效果的净化说,在两者的深层,其旨归都体现出伦理的实质。而后来的无论是叔本化还是尼采,无论是现代悲剧里的象征主义悲剧、存在主义悲剧还是荒诞主义悲剧,所体现的真正的精神内核, 都没有脱离亚里斯多德、黑格尔等所确立的西方悲剧传统的伦理观念。一个社会,在它的灵魂深处,其伦理实质应该是属于文化范畴和更深处的宗教领域。法典是一个国家或社会伦理的具体的外化的相对恒长稳定尺度分明的律法体现,而相应的实施这些律法的则是国家机器的法院,法官,陪审团、律师及监狱等等。在悲剧的崇高之下,由这些来表达非崇高所受到的不等的惩罚、制裁。这些制裁和惩罚是基于律法——契约——的公正和公平。它触及灵魂或者叫良心之外的部分,而触及灵魂的部分属于文化和宗教范畴。前者由表,后者及里。我们时常看见,在一个表里都相对健康的社会里,一个人没有犯法,但是他因高尚的自律而导致内心的愧疚、会引发他因过失而辞职甚至极端到自杀身亡;相反的情况则可以在一个相对不健康或野蛮的社会里,一些人犯了法却致死不伏法,更谈不上什么忏悔不忏悔了。甚至更加本色和野蛮的人会说,“几十年以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 中国古典诗歌从《诗经》、《离骚》到唐诗、宋词、元散曲,及至艾青、冯至、穆旦等,都主要是在抒情;在古代,希伯来的《圣经·旧约》、埃及的《亡灵书》、印度的《吠陀经》、以及我们所熟悉的聂鲁达、佩斯、艾利迪斯、曼杰斯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塞佛尔特、狄兰。托马斯、奥登等等,也都是优秀的抒情诗人。 按照西方诗歌的理论,诗歌在本质上是Physical的而不是Mental的。就是说,诗歌在本质上是述诸于人的情感,而非理智。从我们的古代诗歌里,也同样地说明了这样的道理。
我认为,抒情诗所表达的人心中隐秘的浪漫冲动和对神圣的渴望,是人类心灵深处的终极理想境界情怀。诗歌是一种宗教,它的图腾是人类最原始的情感,因此,我愿意我的诗歌在本质上是接近古典主义的,或者说是传统的。之所以用“接近”两个字,因为在本质上,对于创作而言,它是一种回到自律的、孤独的“个人写作”,而这个“个人”是一个当代的人,因此,他是一个当代的具体的“个人”表达。另一方面,抒情在一首诗歌里,它不是唯一的,或从头至尾的,抒情式在一首抒情诗里占主导地位,同时可以含有“叙事”、“戏剧”等综合成分。我愿望的是一种广义的古典风格的现代抒情诗,而且,它具有一种世界性的趋向,例如,我身处加拿大,我的回忆(抒情的核心)是中国的,我的眼前,却是一个拥有一百多个种族和民族的多元文化的国度,她是一个真正的具有未来意义的“地球村”。“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钟书语)说的是一个道理。诗的灵魂深处的感情,应该是原始的。抒情是诗歌的核心,它是感动的源泉,我们无论是骑毛驴赶路还是乘飞机赶路,我们的情感还是人的情感,我们的灵魂深处,都有一种原始的“乌托邦的冲动”,那种冲动打动着我们,让我们充满了信心毫不怀疑地相信和感觉到生命的远方,除了遥远而外,还有可以期待的“乌托邦”,从而使我们的生命——特别在绝望时刻——得到救赎、超越和产生现实之外的纯精神意义——一种灵魂的提升。 共同的是一切[12]
一个既是我自己又是许多他人的复数的我,在黑夜里“纯净的荒谬空气中”,[13]拄着手杖,朝月亮的方向行进…… |
 南方论坛
南方论坛
 频道热门
频道热门
-
鬼金的小说与绘画
它们以慢的形式推进着,就像刀子,在某一个虚构的想象中,在推进,推进,直到划开皮肤,呈现出白色的茬,然后才是肉,才是红色,破裂的...[详情] -
刘川 译 | 弗兰克·比达特:夜的第四时辰(长诗)
弗兰克·比达特,1970年代出版的首部诗集《黄金州》与《身体之书》虽获评论界关注,但其作为不妥协的原创诗人之声誉真正确立于1983年问...[详情] -
清静 | 深入解读王老莽诗作《三元塔》
这种深度并非老莽刻意为之的深奥,而是源自诗人对生活的敏锐感知和对人性的深刻理解,让读者在阅读中能够获得启示和感悟。其洞察犹如一...[详情] -
美国当代诗人弗朗兹·赖特诗选
美国诗人弗朗兹·赖特,1953年生于维也纳,2015年因肺癌去世,2004年诗集《走向葡萄园岛》获得普利策诗歌奖。他父亲是著名诗人詹姆斯·...[详情] -
马嘶诗选:不与他人同巾器
马嘶,生于四川巴中,现居成都。著有诗集《万古与浮力》《热爱》《春山可望》《莫须有》。曾参加《诗刊》第三十三届青春诗会,获人民文...[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