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一个词语概括对卡尔维诺的整体印象,这个词语应该是“积淀深厚”。
的确是这样,无论是读他的经典著作《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还是读他的新书《论童话》,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卡尔维诺读过的书实在是多得恐怖。而这样的好处是,在一个个生动的文学案例和作者软磨硬泡的解说面前,你最终不得不承认,只要他说的就都是对的。
在他一系列非虚构作品中,《文学机器》广受赞誉,卡尔维诺把文学当作进程予以讨论,认为文学是宏大的叙述游戏,作者和读者在此过程中接受理解这个世界的挑战。正如他的文学创作,是一台复杂的文学机器,他一生的工作便是将与时代休戚相关的科学、哲学、政治学的零件置入这台文学机器中,不断地磨合,不断地调试。
今天推荐的是面对新媒体的多元丰富,他谈论身处危机的作家们该如何看待自己写作?
身处危机的作家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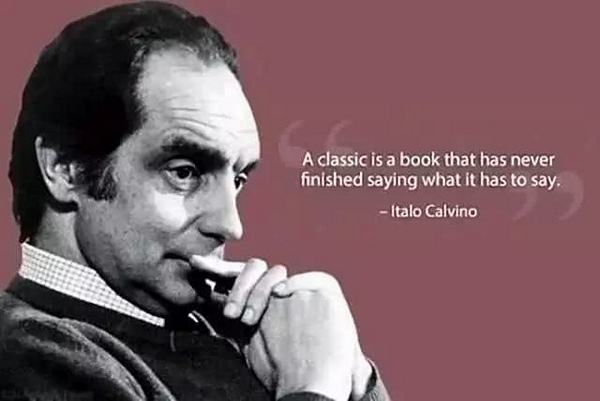
一位作家处于危机当中是唯一可以使他有所收获的状态,也使他能够接触到某种真实的东西并写出人们恰好需要阅读的东西。
几天以前,我遇到一位作家同行。他对我说:“我处于危机当中。”我回答说:“啊,你也是这样。我感到高兴。”
我和这位朋友很少见面,每年只有一次,或者连一次都没有,但我们会不时通信。无论是写信还是面谈,我们的想法总是彼此相反。他对我说,我们这个世纪的文学完全是错误的,是一种理智主义的、干巴巴的、从根本上来说是通过事先考虑好的指责为基础编造出来的文学。他对我说,应该回归情感,回到19世纪伟大作家那种直接贴近生活的做法。我反驳他说,文学应该表达现代的生活,它的严酷,它的节奏,也包括它的机械性和非人性,以便找到当今人类生活的真正的基础。
在讨论当中,我们都倾向于将自己的立场发展到极致:我坚持己见主要是为了让他发火,而且一定程度上也因为我相信自己所说的话;他更是坚持己见,尤其因为他相信自己所说的话,而且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让我发火。
所以,几天前见到我时,他说:“我处于危机当中。”然而我回答说:“噢,好啊,你也是这样!”我这样说,并非由于我残忍地享受他人的痛苦,而是因为一位作家处于危机当中(一位作家将自己的工作建立在与世界的一种特定关系的基础之上,而当这种关系显得并不合适时,就需要找到另外一种关系,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观察人和事物的真实情况,以及人类历史的逻辑)是唯一可以使他有所收获的状态,也使他能够接触到某种真实的东西并写出人们恰好需要阅读的东西,尽管他们并没有觉察到自己需要那些东西。
“创作的时候,我们会强行改变生活,无论是出于道德主义和理智主义,其结果都是一样的,”我的朋友说,“所有人,包括我在内,我们强迫自己书中的人物采取荒唐的举止。”这种话从我的对话者嘴里说出来,显得非常奇怪,因为他的作品正是以极端简单的内容,以及人物那些朴实、日常,从来不会受到强迫的情感而著称。
“你说过那些情感是荒唐的,但那才是正确的做法,”我回答说,“因为表现我们时代的生活,就意味着让其中没有明确表达的东西发展到极致的结果,使其中所有的戏剧性情节得到发展,或许直到创作出一部悲剧。”那位朋友斜眼看看我,而我也明白他在想什么:对于看到生活悲剧性的一面,我从未表现出兴趣,因为我的愿望更多的是对现实滑稽的或者是喜剧性的变形。
不过,他没有这样说,而是沿着另外一条线索继续说了下去。“要想创作出悲剧,”他说,“就只有完全贴近生活,贴近人类现实。这种贴近是快乐的,是没有保留的,也不包括我们知识分子进行的任何争论。没有幸福感,就不可能称之为悲剧。只有我们能够表达人类生活的快乐时,才能真正具有悲剧性。”我的对话者以他通常那种沉重的口吻,说出了对于生活的快乐的颂扬之词。他是一个阴郁、忧伤、不苟言笑的人。
“然而,生活是可怕的!”我抗议道,同时放声大笑。
我们环顾四周。我们见面的地方,无论他还是我都不常去。那是罗马威尼托大街的一间咖啡馆,它所在的那条街因费里尼的《甜蜜的生活》而世界闻名。在那里,一切都显得低能和无聊。轰动的丑闻彼此交织,一切都显得了无滋味和缺乏意义,像是处在地狱边缘的那个无辜而悲伤的地方,一个死人之乡,笼罩着幻觉般的快乐色彩。我们谈论悲剧与幸福,而我们周围是一处由虚假的愉悦生活、虚假的兴奋和虚假的财富构成的景象。
长龙般的汽车因为习惯性的交通堵塞而一动不动地停在那里,车主们疯狂地踩刹车,还演奏起汽车喇叭的大合唱。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正在奔赴愚蠢的爱情,橱窗里展示着完美而无用的商品。
为了表达现代生活节奏,除了描述查理曼大帝卫兵们的战争和决斗,我找不到更好的故事。
我们下面是一个敞开的空洞洞的深渊。那个下午,在罗马,我和这位叫作卡尔洛·卡索拉的作家坐在一起,他是《法乌斯塔和安娜》和《布贝的女友》的作者。在我们这个欢乐和现代化爆发的意大利,这位作家还在创作那些带着淡淡忧伤,发生在外省的简单而朴实的故事。
“在我们这个时代……假如谁能够无视我们这个时代,去寻找那些深层的东西,而非表面现象,寻找那些会流传下去的东西,而不是短暂的特征……他就能真正地表现我们这个时代。”卡索拉说。
“不过,需要去经历这个时代,投身其中,经受它的折磨……”我说。
“不,要拒绝它,不接受它提出的那些理由,甚至不去读报纸。”卡索拉说。
接着,我说:“明天的文学将在我们身上诞生,我们始终精神涣散,焦虑,如饥似渴地吞噬那些印刷品,并且因为道路的拥堵而神经紧张……”
卡索拉说:“我们能够通过其作品见到那个时代真正景象的所有作家,都被同时代的人认为是不合时宜的作家,而这仅仅因为他们不符合潮流……”
就这样,我们缓慢而又固执地继续争论下去。我是为了让卡索拉发火,不过一定程度上也相信我所说的话;卡索拉相信他所说的话,但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让我生气。然后,我们就分开了。他回到小城托斯卡纳做他的教师,过着他那平静、孤独、专心致志的生活,把那些古典作品一读再读。我回到自己就职的意大利北部那家大出版社,去吞噬世界上那些被印刷出来的、汪洋大海般的、无用的纸张。我回到始终处于运动当中的生活,回到工业运动中紧张的神经,它们没有一分钟停歇和聚精会神。为了达到人类永恒的真理,卡索拉又回去讲述那些农村姑娘在家中度过的漫长下午。而为了表达现代生活节奏,除了描述查理曼大帝卫兵们的战争和决斗,我找不到更好的故事。
每天和每周出版的印刷品,日复一日地跟踪和记录风俗现象,解除了文学所承担的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进行细致反映的任务。
我们中哪一个更超脱于现实之外呢?或许我们两个都是?或者两个都不是?意大利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家,意大利是一个千面之国,它具备作为明日小说诞生之地的所有条件。然而关于这一点,如今我们能说的也只有:明日的小说,恰恰是我们今日最无法预料的小说。现在的意大利,一方面是一个非常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国家,社会福利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另一方面,又是一个老派、一成不变、非常贫穷的国家。要想获得对世界的完整想法,哪一种情形更好呢?我们既有底特律,也有加尔各答,如今一切都混杂在一起,北方与南方,先进科技和贫困地区,不同的思想意识彼此共存,相互影响,紧紧缠绕在一起。假如一个小说家希望从整体上对这个世纪的痛苦进行概括和表现的话,这种情形或许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尽管如此,就在此时此地,我们的问题是:还有必要写小说吗?
假如需要讲述代表我们这个社会的状况、风俗的变迁,并对社会问题进行梳理的那些故事,那么借助电影、新闻,还有社会学论文,就已经足够了,而且还有富余。
如今,电影非常善于讲故事,懂得如何捕捉社会关系中的精髓,描绘环境,提出和解决日常行为、情感和道德方面的问题。当然,我们应该说,电影看似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通过面孔和环境来表现的明显真理,其实是一种幻觉。在电影放映机下,每个真理都会变成一种手法、修辞和谎言。假如说电影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小说的范围,那并非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具有重要的价值,而是因为电影经过的地方,寸草不生。很多作家仍旧在进行小说创作,以便与电影竞争,然而,他们也仅仅是在诗歌上获得了很少的结果。电影所占据的环境、人物和情景,文学再也无法靠近,因为它们的内部好像受到了白蚁的啃食,手一旦靠近,立刻就会化作灰尘。
每天和每周出版的印刷品,日复一日地跟踪和记录风俗现象,解除了文学所承担的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进行细致反映的任务,而在19世纪,这正是它的义务与快乐所在。然而,每天紧张而不停地翻阅那些墨迹新鲜的报纸,我们又得到了什么呢?仅仅是获悉所有那些不重要的信息。假如仍有很多小说家与这种对事实进行诠释的方法进行竞争,希望能够写出某种更加深刻的东西,试图在他们的小说中记录下风俗的变化、时尚和谈话、上流社会的生活,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他们不会超出一个时期报纸上的新闻,以及几乎是用录音机记录下来的一些表达方式,他们也不能超出一种模棱两可的道德主义,因为这种道德主义已经成为它奢望惩罚的那个世界的亲密同谋。在世界文学当中,就在我们这个世纪,描述上流社会和搬弄是非的著名小说变成杰出诗歌作品的例子并不少见。但是,即使在这片土地上,好像也无法再长出任何青草。
小说必须而且能够发现方法,几千种、几十万种新方法,这些方法体现了我们如何加入这个世界,并逐渐对新的生存状况进行表现。
即使是关于社会问题的“谴责性小说”,也时日无多。如今,政治和经济需要以资料为根据的调查和以数据与数字为基础的分析,而不是情感和情绪上的反映。作家借助文学近似性去应对亟须以完全不同类型的知识和研究来解决的问题的奢望,越来越像是一种肤浅的自负。不过,我们也要说,以科学方法理解社会现实的这些道路,假如单独去考量,也是非常有限和令人失望的。社会学或者局限于像大山一样庞大而无法统计的数据,在纸上复制那些它无法破解的人类错综复杂的问题;又或者,当社会学提出一些概括性的定义时,它会强行修改现实,排除验证自己的观点时所有不必要的东西,但这种做法与文学的手法一样武断。然而,世界上亟须解决的社会问题,又在不断要求文化的干预和引导。撰写一篇关于社会问题的杂文或者调查性或者批评性文章,就是赋予自己的作品以实践性,并且立刻对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小说的创作就如同不合时宜的重负,并不会考虑到历史任务,以及能源经济本身的紧迫性。在可能采取行动之处,一种真正的社会激情就会在行动当中,或者在直接与行动相关的创作和研究上面表现出来。为何我们还要拖延,而不马上去创作一部小说呢?
总之,即使大部分好像是专属小说的题材,如今也已经被其他认知工具所拥有,在这些工具中,也并没有哪一种能够提供以前文学所能提供的东西。小说是一种无法在已经开垦的土地上生长的植物,它必须找到一块处女地来扎根。小说已经不能再奢望为我们提供关于这个世界的信息。然而,它必须而且能够发现方法,几千种、几十万种新方法,这些方法体现了我们如何加入这个世界,并逐渐对新的生存状况进行表现。
或许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确认,那种作为获得自我意识并带着生存在这个世界的惊恐环顾四周之人的第一个行为——诗歌永远不会终止,那种我们称之为小说的特殊的诗歌形式也是一样。
摘录《文学机器》[意]伊塔洛·卡尔维诺/著 魏怡/译 译林出版社2018年5月版
转自文学报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