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让意义的光,照亮这个世界
作者=景凯旋
来源=2019年2月《经济观察报·书评》
2018年6月,我应移居捷克的朋友徐晖、韩葵夫妇的邀请,在布拉格住了一个月,其间我曾两次与捷克著名作家伊凡·克里玛见面交谈。克里玛的作品大都已在国内出版,如《我快乐的早晨》、《我的疯狂世纪》、《我的金饭碗》、《终极亲密》、《等待黑暗,等待光明》和《没有圣人,没有天使》、《布拉格精神》等。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布拉格老城区的捷克笔会所在地,克里玛现在是捷克笔会的名誉主席,在座还有几个捷克作家;第二次见面是在布拉格近郊克里玛的家里,他的妻子海伦也在,但没有参加我们的谈话。
克里玛已经87岁,身体看上去很健康,眼睛炯炯有神。每逢有笔会活动,他都会独自乘有轨电车去老城。尽管他已搁笔,但思维仍然很敏捷,回忆往事,他显得温和、平静,有时还会流露出幽默的神情,这是一个对人生已经有了自己的定论,宽厚地看待世界的老人。我们的谈话算不上采访,而是很随意地聊天,我觉得这也是克里玛现在喜欢的谈话方式。
两次见面交谈都由徐晖夫妇引荐和陪同,精通中文的捷克翻译家李素做我们的翻译,目前她已经将许多当代中国文学作品译成了捷克文。以下的对话根据录音整理,对于徐晖夫妇和李素的帮助,在此谨表谢意。
|对话|
2018年6月4日,布拉格老城区捷克笔会
除了写作,别的事我都不会
景凯旋:非常高兴今天看到了许多捷克作家,看到了克里玛先生,我一直都很喜欢捷克文学。这次一到布拉格,我们就去看了哈谢克的墓地。中国读者熟悉卡夫卡、里尔克、哈谢克、卡佩克等作家、诗人。1980年代,中国读者又开始知道了塞弗尔特、昆德拉、赫拉巴尔和你。今天终于见到了你本人。你的作品大都已在中国翻译出版了,我也曾译过你的《我快乐的早晨》和《布拉格精神》。
伊凡·克里玛:翻译我的作品很难吗?
景凯旋:不是太难,你的作品故事性很强,写得很有趣,并且让人思考生活。
伊凡·克里玛:我非常高兴,我的作品会在这么遥远的国家出版,而且读者那么多。
景凯旋:我很想知道,你当时怎么能够坚持二十年的地下写作,是完全出于对文学的热爱?
伊凡·克里玛:我当时也有许多烦恼,我知道我要继续写作,因为除了写作,别的事我都不会。当然,也是因为我在国外有出版代理人,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我的作品,美国、英国、德国的出版社,所以我知道我的作品会出版,我不会面对完全沉默、完全被遗忘的那种状态。
景凯旋:不过,当时你和许多捷克作家都失去了工作,如果无法在国内出版作品,是否在生活上会发生困难?
伊凡·克里玛:我们当时的写作处境其实并不是很糟,有很多国外的出版社,把我们的作品翻译成德文或英文,也有国外的出版社出版捷文的作品,然后运送到捷克。虽然在捷克出版不了我们的作品。
景凯旋:国外好像有很多出版社出版捷克文的作品。
伊凡·克里玛:对,德国、奥地利都有加拿大也有一个专门出版捷克文学作品的出版社。
景凯旋:我觉得萨米亚特是20世纪世界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文学现象。
伊凡·克里玛:我们当时的萨米亚特的印刷量有好几百册。事实上,我的作品一直都能在国外出版,所以基本生活并没有很大问题。最初,当局会扣除国外寄来的大半稿费,后来我就托别人将稿费带回国,这些稿费足够维持日常生活了。
无论什么处境,都要真诚的热爱生活
景凯旋:在“布拉格之春”之后,你当时在国外,完全可以留在美国,但是你却选择回国。在你的一篇小说《我快乐的早晨》里,一个女的出国了,她回国后见到她的男朋友,就劝男朋友出国,但是她的男朋友认为,在两种坏的选择中,他选择一个最不坏的,就是留在自己的国家。那么,在你看来,生活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伊凡·克里玛: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唯一的回答,我相信每个人都应该寻找自己生活的意义。这个意义可以意味着好多的事情,每个人都不同,每个人都必须找到自己的回答。比如说,当一个好父亲或者当一个好公民,都是很有意义的。
景凯旋:“生活在真实中”曾构成捷克作家的精神力量,您是如何理解这个短语的?它与文学有何关系?

访问者景凯旋与克里玛
伊凡·克里玛:我想,“生活在真实中”就是,无论在什么处境下,都要真诚地热爱生活,爱自己的亲人、朋友和情人。对于文学来说,应当是一种自由的写作。在全权社会,文学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反抗公共领域的谎言、尽量去寻找真正有人生意义的那些主题。
景凯旋:捷克当代文学中有许多性爱关系的描写,这与现代西方文学通过性爱表现孤独的个人性有什么不同?
伊凡·克里玛:性爱是人与人最亲密关系的体现,我们的生活和人性曾遭到扭曲,甚至人最亲密的关系也是不可靠的,可能捷克作家的作品更注重社会的层面吧——维护人的尊严、承担社会责任,一直是捷克文学的传统。
景凯旋:你的小说中好像都是在思考什么是生活的意义。在你的作品中,总是表现现代人的精神虚无。你后期的作品都写到了宗教的作用,写到了人和人的亲密关系,终极的亲密。你似乎在追寻这个问题。但是,你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没有圣人,没有天使,但仍然还存在终极亲密。
伊凡·克里玛:说的非常对。
景凯旋:西欧作家描写性爱关系,这种关系往往是一个失败。在你的作品中,性爱最后往往也是失败的结局。但是,你的人物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即这种亲密关系有没有一个更好的结论,而西欧作家不思考这个,只是告诉读者,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伊凡·克里玛:西欧作家其实也在寻找他们的答案,不是完全虚无的。
景凯旋:我觉得加缪就是这样,我觉得你俩有相同的思考。
伊凡·克里玛:我很喜欢加缪,可能也受到他的影响。我也喜欢萨特,法国的那些作家我都喜欢。
景凯旋:法国的作家,尤其是存在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本质上也是在思考人生的意义。
伊凡·克里玛:我见过萨特。
景凯旋:我记得你在回忆录中写道,萨特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访问布拉格时告诉你们,虽然斯大林犯了错误,但苏联还是对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题还是对的,因为西方已经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了,你当时在旁边说了一句:的确是这样,尤其当人不必生活在其中时。这是一句讽刺的话,对吗?
伊凡·克里玛:有可能。
景凯旋:美国作家菲里普·罗斯上个月去世了,你知道这个消息了吗?
伊凡·克里玛:我和罗斯是很好的朋友,他是个真正的作家。他去世以后,我和我夫人都写了很长的文章悼念他。罗斯也是捷克笔会的成员,他生前曾获得一个捷克的国家荣誉奖,表彰他对捷克文学的推广,颁奖仪式上他还邀请我陪他去。
景凯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罗斯曾经访问布拉格,并同你有一个对话。他说,西方作家什么都可以写,但所有事情都不重要;捷克作家什么都不被允许,但所有事情都很重要。他担心捷克作家也将面临西方作家的困境,再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可写,他说得对吗?
伊凡·克里玛:当时他确实是这么说的。其实,我当时也不是完全赞同他的这种说法。
景凯旋:就是说现在捷克已经是民主国家,但仍然有许多东西可以写。
伊凡·克里玛:一个作家什么题材都可以写,人与人的关系是那么复杂、那么重要、那么丰富的一个领域,所有的社会体制下都可以去写这个题材,只不过在全权国家,人们经常会面对一些非常的危机,所以对文学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题材。一个人会经常面对危机,必须做出重要的选择。你不能很舒服地去生活,你要每时每刻做一些选择。好的文学可能也是这样的。目前捷克有许多杰出的青年作家,我相信他们面临新的时代,一定会写出非常优秀的作品。
2018年6月11日,布拉格近郊克里玛家客厅
我在集中营学会了偷东西
景凯旋:我是在1997年第一次读到你的小说《我快乐的早晨》,那时候中国还没有译介你的作品。我在八十年代曾翻译过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昆德拉和你的小说都很幽默,这大概是捷克文学的传统,但昆德拉是对生活进行解构,那时候由于中国经历了文革,人们感觉理想幻灭了,有一种“逃避崇高”的说法,这使得昆德拉在中国很走红。因此,当我读到你的作品,读到瓦楚里克和哈维尔的作品时,感觉与昆德拉不一样,你们反对犬儒精神,充满道德情怀。于是我知道,捷克实际上有两类不同的作家,而许多中国读者更喜欢像哈维尔、瓦楚里克和你这样的作家。前几天,我们还特地去参观了特雷津集中营,因为我知道你10岁时就被关进了这个集中营。
伊凡·克里玛:是的,我在那里被关了三年半。我是第一批被送到那里的捷克犹太人,那是在1941年12月10号,一直到战争结束。但特雷津的环境并不是最差的,关在里面的人还是可以活下来,因为特雷津是纳粹的一个对外宣传工具,允许国际代表团参观,纳粹想让外界知道,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也不是像人们说的那样悲惨。特雷津有商店,有乐队,有洗澡间,但没有毒气室。如果被关进奥斯维辛,我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和你们谈话了。
景凯旋:就是说,那时候大家已经知道毒气室的事了。
伊凡·克里玛:可能不是所有人都听说过,那时有许多捷克人移民到国外,从广播中知道了毒气室的事,但是当时捷克国内并没有多少人知道。我记得很清楚,大概在1945年,有一批孩子被关进来,纳粹要把他们送到洗澡室,那些孩子就大哭起来,因为他们已经听说,送去洗澡室就是要被杀死。
景凯旋:我们看到特雷津集中营里有洗脸池、抽水马桶,还有烤火的炉子。
伊凡·克里玛:在过道里有共用的洗脸池,房间里没有,只能用铁桶把水带进房间。冬天会供应一点煤,但是很少,所以还是很冷。我们最难过的是饥饿,我在那里学会了偷东西,偷了好多东西。偷煤块、偷土豆,有人被送到别的地方后,他们的东西都存放在一个仓库中,我们就让一个人放哨,其他人溜进去拿东西,我从集中营出来时,还带着一件偷来的睡衣。
景凯旋:我很喜欢你的回忆录《我的疯狂世纪》,这部书就像一部捷克的当代史。捷克当代文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很大。你知道,中国有非常多的读者。
伊凡·克里玛:那我太高兴了,我想中国可能也是全世界读者最多的国家。
景凯旋:而且,捷克作家思考的往往也是现代世界很重要的问题。
伊凡·克里玛:全世界最好的作家应当都在思考一些相同的问题。
景凯旋:可能我们和捷克人曾经有过相似的经历,所以更加走心,读西方现代作家的作品,还是有不一样的感觉。
伊凡·克里玛:那是因为我们都有过共同的经验,当然捷克现在已经发生了改变。中国这个国家这么大,从自然和历史的环境来说,是不是需要有某种共同的文化意识?
景凯旋:的确如此。不过,所有民族对自由的渴望都是一样的。我读你的作品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捷克现代历史的变化,在1948年人民是追求社会平等,而到了1968年和1989年则是追求自由。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
伊凡·克里玛:也不完全是这样,二战后捷克人包括知识分子都很信奉苏联的计划经济,认为共同劳动、共同分享是很美好的理想,所以在1948年大家都拥护苏联式的制度,但后来发现这种经济体制没有效率,不如西方资本主义的效率高。所以,到了1989年,人们终于不能忍受了,因为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大家都渴望提高物质生活水平。
景凯旋:这是人对生活的正常追求。
伊凡·克里玛:苏联式制度的最大问题是,把人性看得太理想,低估了人性对财产权、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但人性从来都不是理想的,如果反对追求个人利益,一个人就会没有工作的动力,劳动就没有效率。在这方面,资本主义做得要好一些,一个人只要努力工作,就会获得个人利益。捷克就是这样,1989年以后,个人利益有了保障,全社会的生活水平马上就提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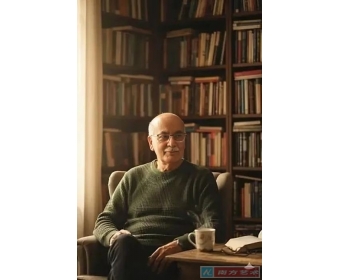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