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当代诗的新范型
——李建春《大红勾》阅读札记
刘年久

刘年久,1990年生,陕西商洛人。文学携带者,写诗,也写评论。
《大红勾》是一次高保真、高纯度、全景式的诗歌写作。因为诗的主题是诗人的整个读书时代,所以自传性很强。大量的本事记忆细节、戏剧化情节与个人议评圆融无间,道气充盈,流露出诗人独特的人格魅力。故阅读时总能直入诗人的心性脉络,逍遥、悠游、无碍。
按照李建春《诗意来自与真实的较劲》这篇创作谈中的说法,本诗是“通过打捞记忆的碎片,使之成为当代诗的文化重建”(注:本文的相关引用皆出自此文)。这里,我感兴趣的是“当代诗的文化重建”这一命题/任务,究竟何谓?在文章里,李建春表达了对中国诗人迷执现代主义诗学传统的强烈不满,认为现代诗歌“虚伪的玄学化使当代汉语失去了统摄本土经验的根基,使心性的圆融、完整变得破碎”,更糟糕的是它的抽象“普世性”目标扼杀了“地方性经验”,从而使“地点性”在诗歌中完全丧失。这种“个人化的玄学范型”或者说“风格典范”的源头来自对西方现代派诗人作品的长期阅读和吸收,从而形成了一种占据意识形态地位的强势美学趣味。他认为当代汉语诗的这种“抽象化”趋势,“既偏离了《诗经》以来的诗教传统,也与当代史的实际经验脱节”。因此,他写作《大红勾》可视为矫正/反拨这一正统诗学而重建本土人文诗学的尝试。
那么,他的反拨策略是什么呢?他说:“我个人能够做的,就是一方面既内化上述西方大师(即艾略特、庞德等)的风格影响,另一方面,又从心性上修复被虚伪的个人化玄学前提、思想基础所击碎、替代的一个朴素中国人感知世界的完整感,使那些被个人主义屏蔽的本土经验和社会情景重新进入诗歌”。显然,诗人是想为现代诗贫乏的社会性和本地性注入社会学、伦理学内涵,重新恢复“我”的肉身性、历史的可视化特征和地方经验的生命力。他的写作要处理的是“个人心性、当代史经验、中国文化记忆、当代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意在通过诗歌这一特殊的形式载体/媒介接通中国传统的“诗教”“道统”,从而使湮没的传统在当下重获新生与活力。他以读经入门代替读诗,历经数年从个人体悟和修身功夫两个层面接引传统中国文化精神的源头活水,将儒释道经典文本义理内化于日常生活和精神境界的呼吸运转之中,运用自己的空性和道心使其在心灵内部融会贯通互相激发,故而能够提振自我日益成长为一个勇猛雄健、自足丰赡的现代个体。他能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中国文化,完成心性的修炼、文化的归属、历史的再认识、现实生活的批判性反思,因而他像一个马上得道的人,可以凭精纯的个人努力在心灵史和精神史的双重意义上为当代汉语诗歌构建一个完整的新人文诗学样本。
《大红勾》在文本形态上兼有“诗史”和“史诗”的双重特征。前者可以理解为“以诗记史”,即将诗歌作为记录个人求学历史的载体,突出的是“史”的方面;后者可以理解为“化史为诗”,即将个人求学的历史写成个人的诗,突出的是“诗”的维度。尽管如此,诗人更为看重的则是借由对个人求学历史的过程性描述,来重构和彰显地方性经验、时代情景和文化记忆这些具体时空里变迁的事物,其中融入了理性的审视、感性的审美以及贯穿全诗的史诗视野,故这首诗具有极强的综合性气质,体现了牟宗三先生所谓的“综合之尽理精神”“综合之尽气精神”。“尽理”与“尽气”,正是李建春诗歌浑然天成的独特艺术气息。
在语言上,李建春在上述创作谈中自述,“我的诗是一种综合的诗。通过综合观照的语言‘理解’自己,而不是表达自己”。这里又引出两个新命题,一是“综合”,一是“理解”。“综合”是创造行为,是诗歌的组织形式,也是诗意的提炼和凝聚;“理解”是认识行为,是区别于直接表达的慧悟和观照,也是主体回忆和思考时存在真理的自行展开。综合性与理解性,相互支撑,相互依存,共同建构起完整的诗歌形式和丰赡的诗意内核,在不失表达精确性的同时又指明了一种现代诗歌语言探索的新方向。
我们确实能从本诗的语感上感受到一种心性的圆融,细节、情景、心迹,片段式的、意识流的、戏剧化的图景合理分布在个人成长史的长河上,本土经验、时代情景、传统文化和个人思索交织化合在一起,以及那些一气呵成饱含势能而跨行不断句的淋漓生气,常带给人一种恣肆愉悦的诗性经验。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从文体上说,我总感觉《大红勾》的散文性极强,其语感语势尤其与鹿桥的《未央歌》有形神相通之处(凑巧的是,《未央歌》正是一本写西南联大时期大学生活回忆的小说,与本诗所写诗人读书时代主题接近)。它有些偏离我们通常认为的长诗印象,而尽显跳脱、生机、朴真、活泼的品质。我猜想,如果不是诗人在时间维度上采用了随时与当下切换的处理手法,在空间维度上采用了大量的分号将不同方向和层次的内容组团式拼接在一起,而在总体的时间结构上造成一定的间离和律动效果的话,那么,诗歌的这种大散文性将更为凸显。诗歌的散文化一直是个问题,但文体之间的界限,原本并非泾渭分明。于是,我们又要回到那个始终困扰我们的问题:一首诗之成其为诗的条件是什么?诗的本质规定性是什么?毋庸置疑的是,诗歌自有诗歌的纪律。但也许,我们更应从诗歌内容对形式的特殊要求和规定性上来思考,毕竟我们在这里遭遇的是一位“与真实较劲”的诗人。
李建春的诗歌写作为我们提供了当代汉语诗歌的一种新范型——“当代诗的文化重建”。这是一条有待开掘的新路。“中国文化”在他这里是核心词。这条“返本”的路同时肩负着“开新”的使命。他的“新人文”诗学重建之路,既面向纵深的历史记忆和人文传统,又凝视广阔的现代处境和日常生活,旨在两者之间建立起一种与生活本质的连续性等同的历史纵深联系,使这一话题具有无限的阐释空间和内在对话性。须警醒的是,我们的全部努力旨在与解决现实生活的困境和发展出一种完善的人性与伦理相联系,我们的工作归根结底应体现为一种新生活的建设和创造。“新人文”如何与当下的现实生活接榫,如何将传统智慧的朴素自然性延续到日常生活的复杂性深处,如何刻画现实的具体困境并使诗歌引领人的精神而不是沉迷于描画既有的经验世界,这些问题与诗歌的存在根本地联系在一起,仍待我们在诗人的实践中觅寻的答案。
《大红勾》延续了《幼年文献》的诗学理念,两首诗在时间范围上有重叠之处,而表达内容则各有侧重点,概括起来前者侧重个人,后者偏重时代。《大红勾》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幼年文献》的时代见证和文献保存意义,因而更具个人化、自传性的魅力。我喜爱的布罗茨基说,生活是光的残渣;而基尔恺郭尔说,不能变成礼物的过去,不值得记忆。李建春则通过为记忆赋形,将他的过去生活作为珍贵的礼物馈赠给了我们。他对语言和风格的多样化诉求,对开掘自我潜能永不满足的抱负,对探索精湛诗艺刻苦顽强的训练,都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坚强、完美的诗人榜样。此刻,我想引用《大红勾》的结尾来结束这篇短文:
我的诗寻找格律
寻找空气中的枷锁,我听到铁链
抽打流水,过时的人民在大地上奔忙
而向日葵走向末日,向日葵
在黑暗中扭头,我们的爱情才开始
2018年12月22日一稿
12月28日修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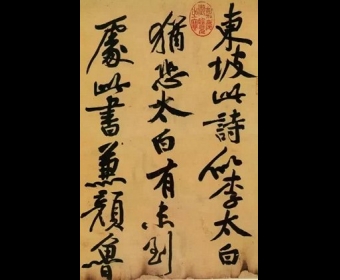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