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渔访谈录
不要输掉一颗心,这是为诗人的本分
访问者:南方都市报记者
个人情感与千秋风云结合
南方都市报:这次获奖的诗歌中,《高启武传》是很受关注的一首诗。它非常新颖地尝试了以诗的形式写史,为什么这样写?
朵渔:我就是想尝试一下,能否将历史容纳进诗歌里,以史入诗。我是痛感当代诗歌太无力了,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哼哼唧唧的小诗与之完全不搭调。中国文化自古就有一种对史和诗的信仰,我就想从历史中寻找一些坚实的东西来,《高启武传》就是这种实验品。这首诗我大概酝酿了两三年,主要是苦于没有一个好的形式。我觉得每一首诗都应该有它不同的形式,就像每个美女都有她不同的身段。当代诗歌这双小脚实在太秀气了,稍有越轨就是冒犯。诗人必须抛弃那双自恋的鞋子,给诗以自由的成长空间。但是自由也有其限度,比如,诗最终还是一种“心灵的虚构”,而史是实的,如何化实为虚,虚实转寰,最需要功夫。我为此考虑了很久,并在阅读《史记》的过程中得到启发。将个人情感与千秋风云结合得如此完美,太史公堪称大诗人。情感的出口一旦清晰,完成它只需要两个小时。
为什么要写我爷爷?我想我不可能脱离开自身经验去写史,我必须从自我的经验中找到一个合适的入口。我的出生地和童年经验奠定了我的情感基础,以及写作伦理。我出生在山东农村,是共和国的最底层,当地的生存状况、儒教传统、人伦情怀,对我的塑造是决定性的。同时,我爷爷本身就是一部当代史:1949年前他是最穷苦的孩子,1949年后他是最底层的农民;曾经翻身做过主人,随后又被历史所裹挟,做了一辈子饲养员。这样一个经历了底层生活的小人物,其一生渗透了共和国的全部历史。有人关注过这些人的命运吗?他是一个政权的悲惨倒影,一种历史的小隐喻,他早已死去,我如果不为他立传,他这一生就彻底默默无闻了。他没有好好活过,我把他从墓中唤醒,希望他能再活一次。
南方都市报:有论者认为“耻辱感”是你写作的动力之一。这种耻辱究竟是什么?你的对手是什么?
朵渔:“耻感”是儒家文化的传统,就像基督世界的“罪感”。孔子讲:“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那意思是,做人要懂得礼义廉耻,要有羞耻之心,要对自己有一个不妥协的标准,如此方可为士。孟子称“无羞恶之心,非人也”,话说得非常狠。为什么要强调“知耻”?因为“知耻”才能有个底线,如果你连羞耻都不在乎的话,那你作起恶来就轻而易举了。《中庸》还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耻方能改过,这就近乎勇了,百毒不侵。“知耻”是修身之道,首先是针对自己的,因此最大的对手就是你自己。有时这耻感也来自外界,比如人权不彰,普世价值屡受侵犯,一个现代为士者就必须“行己有耻”“不辱使命”。
南方都市报:你这些年辞职回家,埋头作诗,处境应该很不容易?一个诗人,仅仅靠写诗能养活自己吗?
朵渔:也没有那么严重,这其实是一个不断自我调适的过程。当你发现自己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有尊严的人的时候,你与时代、体制之间的紧张关系就确立了。这种紧张关系积累到一定程度,最终会自行断裂,因此选择回家是一个主动选择。“选择”本身就是一个本质性的问题,所谓“存在先于本质”,就是这意思。我把自己的饭碗打破之后,谋生总是个问题,但养活自己总是容易的,不容易的是你还要承担起对其他人的义务,这时常让我颇感内疚。其实生活并不需要很多物质的东西,你努力去追求物质,必然会失去些别的。鱼与熊掌的事情,古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当我想明白这一点之后,我的焦虑感在慢慢消失。我觉得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已经很不错了,能够按自己的选择去做就更幸福。写诗当然养不活自己,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上帝会赐给诗人一个饭碗。有不少诗人因生活的压力暂时放弃了写作,想先发财再写诗,内心其实很纠结。你写作的热情也许能够重燃,但你最美妙的那几年光阴、创造力最旺盛的那段时光却永远失去了。很多时候,选择其实并不难,无非是取与舍。
南方都市报:独坐书斋,不参与现实生活,是否会缺乏现实感?
朵渔:古人动不动就隐居,现在哪那么容易将自己隐藏起来?一张小官吏的脸上都写满了现实,你出去打趟酱油都可能遭遇不测。我天天在窗户里面读书,窗外每天都在发生事故。我心知肚明。我的意思是,“现实感”是一种经验,更是一种态度。我从来不担心经验的匮乏,我只担心自己走着走着就萎了。
南方都市报:这次获奖的诗歌中,也有两首诗是写到朋友的。在《复脸》和《感怀》中,你都写到志同道合的朋友离散“我们在哪个岔路上匆匆别过”、“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这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朵渔:人总是离不开朋友的,隐居很深的人也会为朋友留一道入山的小径。我的很多诗属于赠答之类的,或有一个很明确的书写对象。《复脸》、《感怀》也是有感而发。很多当年一起写诗的朋友,开始有一种青梅竹马的感觉,对诗歌都是半斤八两的狂热。但在最初的游戏结束之后,大家突然间四散了,选择了不同的路向。我的很多朋友都非常有才华,无论是写诗、拍电影还是做生意,都能做得很出色。我还留在这条路上,是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很笨,做不了其他的东西。我对诗看得很大,很清楚自己的才能,也有一种对自我的期许。但是,期许往往都是空自许,谁知道呢。
解放个人,必须先解放身体
南方都市报:你是“下半身诗歌”的发起人之一。但你的诗却和人们印象中的“下半身诗歌”不搭界,你如何看自己与这个流派的关系?
朵渔:2000年提出“下半身诗歌”这一概念时,我并不认为“下半身”仅仅就是一个“性”的概念。如果下半身就是指性的话,我的确是“最不下半身”的。在我的诗歌写作中,对性涉及不是很多,也不是很直接,这是我的风格。但并非说我没有下半身的立场。在我这里,它更包含有一种自我解放的意义。我们这个国家,很久以来已经没有身体了,或身体被层层包裹,变成了无性的、体制化的、统一的、僵尸化的了。要解放个人,必须先解放身体。这也是我参与“下半身”诗歌运动的初衷,它一开始就带有解放的、对抗的、冒犯的含义。“下半身”现在影响比较大,有人觉得很下作无聊,但你会发现它既有一种破坏性,同时也具有建构力。它在破坏、冒犯、顶撞、反抗的同时,也建构了一个自由、活泼、欢快、湿润的个人空间。它破坏的是小家碧玉般的小脚诗,冒犯的是虚伪的、中产的、平庸的道德,它顶撞权威,反抗束缚,探索“人性的、更人性的”自由边界。
南方都市报:这些年你编《诗歌现场》,对诗歌与现实间的关系你是怎么看的?
朵渔:我和朋友们编《诗歌现场》,最初的用心,就是看到诸多同代人在燃烧了自己的青春激情之后,已渐渐陷溺于世道人心,烂在时代的泥泞里,“求仁得仁,求道得道”,讨生活养家糊口去了。我们想重新寻找,重新发出兄弟般的呼唤,希望昔日的伙伴能够互相听到,共同创造一个自由、灿烂的诗歌场域。这当然是有些理想主义的一厢情愿。诗人都是很有个性的动物,你这么高蹈,他以为你在装。现在,轻飘飘的事物满天飞,沾点“个性”的东西就是牛逼,而庄重、严肃的东西总是最容易引起质疑。这都是很无所谓的事情。我从最笨拙的地方入手,一首诗的“言之有物”、“有感而发”、“切己及物”被我看做最基本的诗歌伦理。你当然可以在诗里玩很好的花活儿,但我最终还要看你这首诗里到底有没有一颗怦怦跳动的心,有没有人的体温。一味的冷酷、炫技,强调“诗是一门语言艺术”,其实相声也号称是一门“语言艺术”,而且还讲究说学逗唱……北岛老师去年在获得中坤诗歌奖时,有感于“词与物的分离”,曾大发感慨:“诗歌与世界无关,与人类的苦难经验无关,因而失去命名的功能及精神向度。”这确是很可怕的。诗人一旦失去了言说现实的能力,他被现实所抛弃就是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在我们的诗学道统里,往往不归李,便归杜。杜诗被称为“诗史”,是为“诗与现实”的最伟大的撑腰者。熊十力有一个说法:“工部才逊太白远甚,而后世宗杜不宗太白者,杜公一段真精诚千万不可磨耳。”也就是说,杜胜在有“心”,本真本诚,方与大才李白打个平手。你那点小才哪能跟李白比?老老实实,不要输掉一颗心,我觉得这是为诗人的本分。
南方都市报:所以有论者认为,你不仅是诗人,而且过于强烈的道德感让你具有公共知识分子的特点。你怎么看这种说法?你愿意自己是诗人,还是知识分子?你对诗人的“思想性”好像很看重?
朵渔:我乐于承认自己是个“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与“民间”最为对立的那几年,有人问我属于哪一派,我说我是“民间知识分子写作”。其实我离一个 “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准还很远,比如我的行动力就很差。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诗人不应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对现代汉语诗人的身份危机做一番自我辩驳——— 对诗人在现代日常生活世界、现代社会文化结构中的合法性问题进一步追问:你在现代社会中到底是一个什么身份?你说你在创造,那么你到底创造了些什么?你有没有自知之明?人只有认清他自己所处的真实境况,他的状况才是一种真正的“精神状况”。辨清自我的实存与时代的精神状况之间的关系,日常生活的世界才会逐渐清晰起来。很多人说诗人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人”,哎哟,你能走在这个时代中间就不错了。我们很多诗人很有才华,文本做得也漂亮,但往往写到中年就写不下去了。为什么写不下去,我觉得还是自我启蒙、自我完善的持续性不够,在文化视野、精神底蕴上输了。年轻时当然可以逞一技之快,但你不可能永远年轻。说“诗人永远都年轻”,很扯淡。诗人也是人。
南方都市报:你曾说要“以一种有节制的绝望和充分的耐力与时代对峙,并从最基本的人性中寻找拯救心灵的力量”。而今天,人们对文学的作用并不抱那么大的希望。尤其诗歌失去了它的多数读者。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朵渔:我承认这个现实,诗人的确失去了他的大多数读者。这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诗歌教育问题、文化转型问题、资讯变革问题等等。但我也有一个朴素的信念:只要你写得足够好,你就会拥有自己的读者。失去读者,诗人自身是有责任的。你写得轻飘飘的,不痛不痒的,打情骂俏的,没人围观是很正常的。还有一些形式上的实验,据说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那点小热闹是不可能有什么影响力的。有人说被冷落是先锋诗歌的宿命,这话在理。但集体被冷落就不正常了。你想想,集体先锋那是个什么阵势?我依然对文学抱有理想,我依然认为诗歌会是一种拯救心灵的力量。
做诗人本身是幸福的事
南方都市报:那你觉得这个时代对于诗歌是一个好的时代还是不好的时代?
朵渔:其实对诗歌而言,每个时代都是好时代。做诗人本身就是件幸福的事情,他有一根敏感的神经,可以选择最自由的言说。比如当下,我就觉得是一个“幸福的时代”,当我确立了与时代的紧张关系,仿佛为自己套上了一副轭,每向前一步都有一种痛苦的重负。你说是好还是不好?诗人的牛逼之处在于,他可以在痛苦中炼就黄金。有一次我跟几位西方诗人讲述我的遭遇,他们听后兴奋异常,说,我们一起去战斗吧。他们大概是太安逸了,没有了对手和愤怒,这是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南方都市报:你的诗歌风格似乎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朵渔:说实话我很羡慕那些早熟的才子,但我本人却是一个成熟很慢的诗人,很愚笨。这也使我偏信,诗人应该有一个不断生长的过程,他不应该一下子就熟透了。早熟往往意味着早夭。一个诗人如果一开始就确立了自己的口气、风格,往往到了一定程度就很难再往前走了。我自己的诗歌风格往往两三年就有一个变化。如果没有变化我会恐慌,觉得自己难以为继。其实很多变化是自然而然的,自我怀疑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必然带来改变。一成不变地写十年,在我看来就是件恐怖的事情。
南方都市报:作为70后诗人中的一员,你怎么看待70后的诗歌?
朵渔:70后本身就很分裂,风格、路径、精神追求多元。一个感觉是,70后稍显犹疑,他们既没有老第三代们的快活与灿烂,也没有80后的自然与放松。这代人走走停停,聚聚散散,耽误了太多功夫。一竿子插到底的人物太少了。一以贯之,确乎其不可拔,如此才会有大诗人。这可能也是70后经典化迟缓的自身原因。另外一个感受就是,现在很多诗和人,其实就是无“心”,写出来的东西或冷或怪,或炫或恶,逞一点小才。整体而言,这是普遍晚熟的一代,浪费了多年光阴,专心致志者、特立独行者还是少了。
南方都市报:你现在日常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一般情况下,灵感从何而来?
朵渔:我的日常生活就是大部分时间阅读,发呆,然后写作。从2005年开始,我有意识地把西方的哲学补了一下,这两年在看中国古典的东西,我觉得这一课早晚都要补上。我的写作习惯一般是这样:每天在发呆时,忽然想到什么,就把它记下来,一段话或一个词。积累了一段时间,就有了写作的感觉,然后将精神调整到最好,将一段时间的所思所想写下来。很多诗通常是在一种“失神”的状态下完成的,写完放在抽屉里,隔几天再拿出来看。这样子每个月能写几首小诗,一年大概能留下三四十首。这种状态我已经很满意了,仿佛一首诗就是一坨金子。
南方都市报:你说写得如何自己也不知道,那么诗的好坏到底要靠谁来评判呢?
朵渔:诗最终还是要交由读者评判。从诗人的角度而言,自己是第一个评判者,但会有偏差,比如喜新厌旧、自我怀疑。批评家往往限于风格、意义上的评论,对一首诗的生成秘密并不精通,因此很难给诗人一个心心相印的评价。同行之间的批评,则往往不知道对方说的到底是真话,还是溢美之词。因此,我很感谢那些多年来对我的诗歌不吝批评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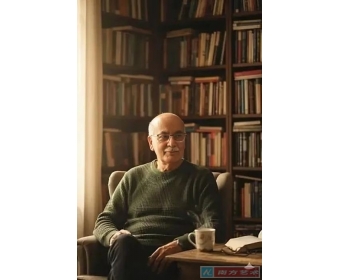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