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在举荐一线实力诗人和发现诗歌新人方面,你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比如2017年新出版的评论集《神的家里全是人》,推荐了40位全国范围内影响力不太大但踏实写作的一线实力诗人,一个个为他们写评论。还有你最近在个人微信公众号“撞身取暖”里推出的湖北60后、70后诗人,很多诗人我还是第一次读。这些推荐和评论,会浪费你不少时间和精力。如果对诗歌没有公益心和大格局的诗人,不会去做这些对自己没利的事。请谈谈你做这些事的真实意愿?
张执浩:文学存在的终极意义,除了我们众所周知的那些东西外,还有一点就是能够不断地推陈出新,写作者自己不断推出新品,同时又要不断有新生的写作者参与到这项事业中来,只有这样,文学才有长期存在的必要和可能。或许是因为编辑职业的缘故吧,我对新人新作总是充满渴望,乐见他人写得好,也乐于推荐那些特立独行、令人耳目一新的新人新作。《神的家里全是人》就是在这样一种心境之下诞生的,从这本书里你可以看到,我是一个杂食主义者,入选的40位诗人都是面孔清晰但又各有特点的汉诗诗歌现场“第一线”的写作者,我真心认为,他们的出现才真正构成了目前汉语诗歌的繁盛或多样性。随后,我在个人公号中连续推出的湖北60后、70后诗歌展,是缘于我今年参与的“湖北百年新诗选”这个项目,编委会在讨论入选名单和作品时,业已醒目的诗人大多入选了,但还有些我个人认为写的不错的诗人没有入选,为了弥补这个缺憾,我决定利用这个时机将湖北省内的诗人队伍按我的视野,分年龄段重新梳理一遍,于是就有了“荐读”系列。这个栏目现在影响逐渐大了起来,想加入的诗人越来越多,至今已过百人。诗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群体,除了显性诗人外,还有许多隐性和潜在的写作者,我不可能有精力一一“荐读”下去,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何况这也仅仅是一个展示平台,写作者自身的造化才是关键。接下来,我计划将湖北80后、90后甚至更年轻的诗人也梳理一遍,权且当作我个人的一个资料库吧。做这种推荐工作固然耽误精力,但“日拱一卒”,眼见诗人们的队伍越来越大,也挺有乐趣的。
9、在我的阅读视野内,感到你是个有抱负、有自己明确写作方向的诗人,这缘于你有清晰的写作理念,其中“强调诗歌的‘唤醒’与‘复活’功能,在写作中尽可能追求语言带来的画面感和声音”是你近几年提出的。语言带来的画面感和声音,古诗也不缺乏,而且古诗中的画面感和声音尤其清晰和立体,比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都是极有画面感和声音的诗句。这样的诗句也有‘唤醒’与‘复活’的功能,现代人读过也能感同身受。你所说的现代诗歌中画面感和声音提供的‘唤醒’与‘复活’功能,与古诗提供的有无区别?如果有,区别在哪里?
张执浩:抱负真谈不上,我说过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这种悲观不同于厌世,相反是基于“人生不值得一过”前提下的积极的生活态度,有点近乎于及时行乐的味道吧,所以你才看到,我是多么热衷于俗世,热衷于饲养我们的肉体。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谈到我看见那些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时的恐慌感,从这些人的脸上你能看见人类真正的绝望,不是贫穷或其他,而是那种深深的无底的空洞感。所以,我一直将写作当作是反抗遗忘的重要手段。“唤醒”与“复活”的启示就是从这里来的。如果我们的写作不能将沉睡在记忆里的那些东西,那些人与事,那些丰沛的情感唤醒,我就觉得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如何唤醒,落实在诗歌写作上,就应该用声音和画面去谋篇布局,让沉睡的苏醒过来,让淹没在尘埃中的重新闪亮,一如智者所言:“如谜忽觉,如梦忽醒,如仆者之起,如病者之苏”(马一浮),惟有如此,诗歌才能产生活灵活现的效果。我们日常生活里的大多数语言都是昏昏沉沉含混不清的,只有诗歌的语言具备澄清往事反观自省的功效。这方面中国古典诗歌已经做到了极致,但新诗写作长期处于主观性表达的模式中,吁求远大于内视,我倒觉得适当地校正一下我们写作的视角是有必要的,那种隐忍,含蓄,并能在一再地退守中恪守人之本分的力量,我觉得更应该得到彰显。
10、在你的诗歌创作中,最丰富的资源都来自那些方面?
张执浩:简而言之是日常生活,但并非是日常生活素材,而是你对待日常生活的态度,即,敢于趋近琐碎和闲杂的耐心。当然,这也是我个人的成长经验历练出来的,强求不得。有时候状态好,我感觉什么都可以入诗。但这种时候并不多。所以,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怎样调整好自己的精神状态,包括身体状态,牢牢守住自己的精气神,少一点耗散,就可能多写一首好诗。
11、对于诗歌语言的运用,我感到你越来越自由和放松,甚至网络语言也拿来用,比如“酱紫、酱紫”,还有自创的词“骨灰脸”等等。你这样运用是偶尔拿来作为对规范语言的调剂,增加趣味,还是觉得用在此诗中恰如其分?网络语言入诗,是否会给读者带来困惑?
张执浩:几年前我在回答《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曾说,我是用“日常生活用语”在写诗,这种语言更倾向于口语,但有时候也不全是口语,主要看言说场合或对象。通常是,我感觉怎么舒服准确,就怎么写,没有那么多的限定。“酱紫”虽说是网络语言,但放在《蘑菇说木耳听》这首诗里时,有一种恰如其分的声、色味道,如果你曾经泡发过蘑菇、木耳的话,你就有这样的体验。但在别的场所,你将“这样”换成“酱紫”就显得轻佻了。所以说,究竟该怎样灵活地运用我们的语言,一定是不能墨守成规的。我有一个童年伙伴,搞了一辈子的数学,最近突然迷恋起诗歌了,他不久前告诉我,现在他才发现诗歌有趣的很。我告诉他,诗歌与数学差不多是一样的。词与词的组合,数字与数字的组合,产生出种种意想不到的结果,写诗的最大乐趣不过于此了。我的书桌前平时总是摊放着两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如同摩尔密码一样的词语,它们都是突然出现在我脑海里的,有时候我会久久地盯着它们看,感觉它们就像山岗上的小哨兵似的,随时都在提醒着我。对意义的悬置,对趣味的寻找,尽可能多地发现我们生命中那些意味深长的东西,可能是我近些年写作的主要的特点之一吧。
12、多年来你一直保持旺盛的创作势头,有什么秘诀吗?
张执浩:除了专注,还是专注吧。就像我在前面说到的,这个时代过于丰富了,写作者得守护好自己的精气神。
13、你主张让诗歌与生活保持同步,不仅仅指用语言处理现实生活问题吧?这个同步还包含什么?
张执浩:每个写作者面对的无非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想写的东西,一个是能写的东西。往往是,想写的太多了,却又写不了;很多能写的却不愿写,或者是随便写写。如此一来,就使我们的写作就变成了一桩时时处处可疑的事。我主张的“同步”,是指写作者首先要对自己的生活状况、写作能力有一个基本的评估。先将那些能写的东西处理好,然后再用想的东西提升自我。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也是我反复强调的,要让我们的写作具有鲜活的现场感,不能仅仅词语在叠加,而是诗人在生活,在这样生活着。实际上,包括我本人在内,总会被枯燥的生活所困扰,觉得没有什么可写的必要。但真正的诗歌,往往就存活在我们以为它不可能在的地方,在毫无诗意的地方写出诗来,远比去“远方”寻找所谓的诗意更具创造力,也更有乐趣。
14、你认为已经写出了自己最满意或最重要的诗歌了吗?
张执浩:我肯定写出过自己满意的诗,但最重要的诗是什么样子的,什么时候出现,我并不清楚。譬如说,《高原上的野花》,于我而言肯定是阶段性重要的诗,但“最重要的诗”将以什么面貌出现,我真不知道。
15、请谈谈目前中国诗歌发展的生态如何?
张执浩:总体而言,我觉得挺好的。各种风格流派都出现了标志性的诗人,也留下了一批值得研究的文本。新诗人层出不穷地涌现。官方与民间的壁垒正在消弭。交流和传播的平台也越来越丰富……当然,最大的问题还是,整个诗坛给人的感觉太浮躁了,沉不住气的诗人太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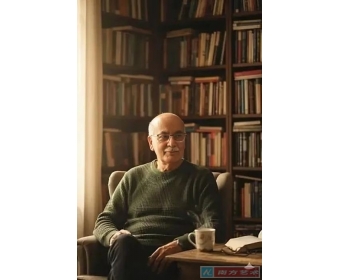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