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多年没听到唿哨声了。现在的孩子晚上秘密招呼同伴出去玩,用的是电话,撒的是“去对对计算步骤”的谎。可今天晚上,我突然听到了一声唿哨。我的心被拽了一下,忙奔到窗前,见前楼一鬼机灵的瘦男孩儿,把食指和中指钩在嘴里用力吹,边抬头望着楼上哪家窗户。
这声音这情景我太熟悉啦,它本是我少年时代呼朋引类时的“暗号”呀——一长声代表“快出来”,两短声代表“坏啦,我爸要修理我,出不去了。”
现在的孩子都不会打唿哨了。因此,我特别喜欢这个怀有绝技的小崽儿。他的一声唿哨,使我想起了自己的少年时代……
那年,我13岁。一天下午放学后,老师通知我们几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队员,说是区教革委(教育革命委员会)决定将各校宣传队的骨干集中到一所学校读书,为的是便于集中排练节目,并与其它区的宣传队抗衡。
第二天,十几所小学的宣传队员就都到市二校报到了。那年月,中国已不再鼓励读书,人心思乱,群盗蜂起。学校里漂亮聪明的孩子,大都被吸收入宣传队。在文艺上有一技之长,参军或招工就便当多了。
报到那天,大家都特别兴奋。如此多的“人精”被集中到一个班,自有一种恍惚和自豪。宣传队成员,大都是知识分子和干部家庭的孩子,虽然那时代流行“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但在我们心里,压根瞧不起“劳动人民”出身的孩子。在宣传队里,比的是机敏、淘气想象力,和气质、穿着,像是个小小而又顽固的“准越轨”社区,有着在禁欲时代难得的某种快活和自由。
新班主任讲完话,休息半小时。不同学校来的十几个男生不约而同地到了厕所,齐唰唰蹲了一大溜——抽烟。其实十几岁的孩子哪会抽烟,就是为了摹仿成年人的狠与粗,那是暴力时代的流行嘴脸。我记得我带的是“红玉”,八角五分一盒。我将它撕开分给我旁边蹲位的同学。在当时,“红玉”烟属于高档。我从父亲抽屉里偷出,为的是“镇住”其他学校来的男生。果然,他们带的是“战斗”,二角八分——
事情来了。等我拉完屎走出厕所,被一个铁小来的男孩子截住,他人高马大,是附近学校有名的唢呐手,外号“棒子”。他冲我很近猛一挥手,几乎刮着我的鼻子,然后佯装着整整军帽。这个动作,是当时很流行的“挑战”动作。如果对方没反应,就算“服了”,今后只能听其役使。还不待我做出反应,我的同学甘宏已飞快地贴于棒子身后,双膝顶双膝,棒子跪倒在地。我上去照他头部一阵猛打,棒子顶了一会儿,就求饶了。甘宏摘下棒子的军帽戴在自己头上。抢军帽,也是当时流行的“征服者”动作,算是一种象征性仪式吧。
从此,宣传队平安无事,大家已暗中认可了谁是“大爷”——通过初次交手定了“尊卑”。
宣传队队员,个个漂亮机灵。特别是几个跳舞的女生,袅娜的身条,一脸的狐媚,嗲拉吧唧,小小年纪学得格外矫情,比同龄的女孩“懂事儿”多了。在宣传队里,男女生界限几乎不明显,加上彼此帮着化妆,打打闹闹,一块跳舞,手足接触是常有的事。男生们常常私下给女生“打分”,起准确恰当的绰号,并认真地讨论谁谁可以做谁谁的“老婆”。后来,这种分配渐渐半公开,因为“搭配”得合适——到现在我仍然奇怪,我们那么小年龄,怎么有如此老练的“眼力”——女生也认同它。接着,几对小“恋人”表现出深深的(的确如此)依恋。化妆时固定相帮,一块儿打饭,寒暑假还偷偷见面。
我的“老婆”是乐队弹中阮的,很文静的一个女孩子。与舞蹈队的女孩不同,她总是悄悄的,学习也好。说实在话,我一入学就喜欢她。她也喜欢跟我说话,与我结伴来去。很奇怪,大家很少拿我们两个开玩笑。现在想来,恐怕是因为大家认为我们是“真的”。那时,十三四岁的孩子却有自己的言行准则,于今想来这一切仍令我感动。后来,她被南京军区歌舞团招小文艺兵入伍了,行前她赠我一块她用旧了的蓝手帕和一块她弹琴用的“指甲”。我们在轨枕厂的仓库后门告别,她的脸由红变白,嗫嚅着说她怕离家,让我最后抱抱她。我们抱在一起哭了。真的很心酸。我第一次体会“爱情”的滋味,心的滋味,也知道了什么叫走,而什么才称得上“别离”。两个少年,拥抱在一起一点儿身体的感觉都没有。我想,我这一生是在那天才第一次注意到落日这一自然现象的。
她走后没有给我写过信,那时我们还想不到写信。不久,听说她在部队和一个拉手风琴的人“早恋”,被劝退(伍)了。退伍后就到了临汾的叔叔家,她父母怕回来“丢人”呐。
宣传队的指导教师是某大厂派来的“工宣队”师傅,姓葛。他人生得极精神,白白净净,额阔眉长,北京人,能说会道,被我起了个外号:“京棍儿”。这位葛老师,一开始就令我们讨厌,他似乎也特别讨厌男生,说起话来急燥、不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相反,他特别喜欢女生,尤其是跳舞的那几位。京棍儿舞跳得好,也善于创造编排新节目,这为他创造了条件:在辅导女孩们动作时,他总是仿佛无意,实则有心地捏一把,揉搓一下,弄得她们又羞怯由兴奋。这一切,被我们几个男生看在眼里。特别是棒子,更是妒火中烧。因为他“老婆”赵晓舸常常被葛老师“个别辅导”。我们几个男生常常为了“报复”京棍儿,在演出时,不是故意忘词,就是装作下意识地提一下裤腰,引起台下一阵哄笑。有一次,弄假成真,在跳“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毛主席”时,我装生病跟不上拍子,后来真的崴了脚。这些报复虽有效,但终不解气。
终于,“解气”的机会来了。一天傍晚结束排练时,棒子找到我们四个人,说请我们每个人吃一个锅贴。食后,他说今天京棍有点不对劲儿,排练时他悄悄送给赵晓舸一副漂亮流行的尼龙护腿,六块二的那种。并让赵晓舸晚上到他宿舍(葛系两地分居)。我们一听,就预感到事儿不善了。不是出于气愤,更多是少年的冒险欲和捣蛋心理,使我们几个决定收拾一下这北京人。
天黑透了,我们叫开大门进了学校,并对传达室的师傅说稍等我们一下,拿好道具就出来。我们悄悄摸到京棍儿窗下,不敢往里看,再说也看不见——他屋里是黑的。……一会儿,我们听到屋里有桌椅撞动的声音。接着仿佛有人挣扎,还有赵晓舸(果然是赵晓舸!)的哭声。棒子一跃而起,哐哐踢开门,大叫一声“我操你妈——葛老师!”我们四个旋即而入,拉开灯,只见葛老师刚刚离开赵晓舸不远,强装镇定却张口结舌。赵晓舸的军绿上衣被揪掉一个扣子,白衬衣撕开了,露出了半只平平的小乳房。
葛老师见只有我们几个孩子,可能放下心来了。就说“正好,来电了。你们送晓舸回家吧,她不敢这么黑回家,非让我送她呢。”谁也没料到葛老师这么说,一下子都傻那儿了。怎么办呢?棒子望着我,我望着棒子。走毬吧,甘宏说,我妈还不知道我在哪儿呢。晓舸和我们一起回家了。在路上,我隐隐感到一阵激动,妈的,甚至还伴有生理上的反应;另外几个同学也与我一样,仿佛经历了一场大变故,大家兴奋地搭肩“支帐”走着,故意甩下后面的晓舸。
后来,事情的败露不是由于我们几个孩子,而是传达室的师傅找到了晓舸的父母(部队干部),晓舸父母审问孩子,一切昭然。京棍儿被调回厂批斗,又被晓舸的舅舅痛殴“封了”左眼。晓舸从此几乎不再露面,她家门口被孩子们用煤块写满了“大流氓”“大坏蛋”等秽语。我后来特别后悔听棒子的话去捉京棍儿,甘宏和豆健也有这种心理。我们都觉得特别对不起赵晓舸,是我们害了她。此后我们很少理睬棒子。
70年代中,宣传队又连锅端到了一所中学,宣传队已是名震晋阳大地。我们演出的节目已远远不同于文革早期的粗陋、蛮野,而是显得精致、抒情,甚至还可以说是“华丽”。样板戏已是整场的演,还出过三位省京剧团的实力演员。舞蹈就更棒啦,像《洗衣歌》、《雪里送炭》、《毛主席的光辉照祁连》、《亚非拉,人民要解放》、《赤道风雷》、《风雪小红花》、《丰收舞》等,无论是演员还是舞台布景服装道具,都称得上绚丽缤纷——可能那是个需要虚构莺歌燕舞,“就是好”的时代吧,文艺拨款几同于政治宣传般痛快。但十几岁的孩子可是不管什么“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不懂什么“纲”,什么“线”的。说实在话,那时我们排演《洗衣歌》,根本就不曾想什么“拥军爱民”。我们嘴上不说,心理感觉是一样的:“哎,这节目真来劲,一帮漂亮的小姑娘,在捉弄挑逗一位英俊的解放军班长!”就是这样,在那样一个压抑的年代,像《洗衣歌》、《雪里送炭》、《沙家浜·智斗》等节目,实际上曲折地传达了中国人对性爱的渴望。
也就是这期间,在我们宣传队里,已经不再仅以抽烟、打架、逃学、找女孩为乐。我们渐渐长大,脑子变得复杂些了,好朋友之间已开始交换各自控制手淫的经验。同时,在几个好朋友中形成了一个秘密交换“毒草”书籍的小圈子。因我们几个都喜欢穿白色圆领棉汗衫,被同学们称为“老头党”。“老头党”成员均系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各自家中均多少有些劫后幸存的文学读物。我们从家中偷出彼此交换,我记得当时“老头党”骨干读过多遍的书至少有:《青春之歌》,《迎春花》,《红楼梦》,《古文观止》,《沉船》(泰戈尔),《安娜·卡列尼娜》,《海上劳工》,《约翰·克利斯朵夫》,《静静的顿河》,《普希金抒情诗集》,《海涅诗选》,《牛虻》,《红与黑》,《契诃夫小说选》。此外,几本《巴金文集》虽然有“爱情”的地方多被扯去,但也被我们的想象力补上,反复传看。
阅读给我们开辟了一片新天地。我们知道,原来人可以而且应当有魅力地活。我们变得“文明”了,大家似乎又有了一个新的、潜在的对人评估认可的方式:谁读书多,“小资调”浓,理解得深,讲得清,人又仗义,谁就是“大爷”。就在这阶段,一向属于我的“跟帮”甘宏,越过我成了众望所归的大人物。我心服口服。
我记得我是用一本没有开头的《红与黑》竖排本,换来了甘宏的《普希金抒情诗集》。那是冬天,寒冷、干燥,演出后我们回到学生宿舍,暖气咝咝地将水漏了满地。我躺在上铺,翻开了这本诗集。一下子,我被这随意翻开的一页咬住了!——
一切是幻影、虚妄,
一切是污秽和垃圾;
只有酒杯和美色——
这才是生活的乐趣。
爱情和美酒,
我们同样需求;
若没有它们,人
一生都打欠伸。
我得再添上疏懒,
疏懒和它们一道;
我向它颂扬爱情,
它给我把酒倾倒。
当时我感到有点头晕,浑身轻松而乏力。这或许就是所谓“震颤心灵”吧?这样的阅读经历只有这一次,因为一首挺一般的诗。以后我阅读了数不清的杰作,但这种心的震颤永不再来了。当时我想,妈的,普希金厉害!他说的对我的胃口。他的思想可真颓废,可这颓废是多么亲切迷人。他只说实在话,我读他的诗,知道他爱谁恨谁;想干什么,不想干什么。这才是最地道的男人!这样写诗我也能写——当然,我写不了,更写不好。但的确,我是从那时开始写诗的。后来,我的写作一直有这种真切表达的特征,我想,这与我平生第一次受到的阅读感动有关。
大家都看了普希金的诗,但很奇怪,其反应程度与我相去甚远。在诗歌方面,我们彼此很少能交换阅读心得。此后,我的谈伴越来越少;我想,人世间注定有极多的聪明人,但就是与诗无缘。那时,普希金成了我唯一的偶像,谁他妈不喜欢顶了天的普希金,谁就是大傻瓜!唉,在那个闭塞的时代,我们能够读到的书,知道的作家诗人太少太少了。但恰因其少,反而超量地汲取了它们的营养。
现在,我常常怀恋在那懵懂岁月中度过的“宣传队”生涯。抽烟,打架,早恋,捉“奸”,演出,秘密阅读,旷课……呵,这一切都远去了。这是那个苍茫时代带给我们的丑陋和快乐,无耻和自由。它独有的时代魅力已构成我们这代人身上总体性格特征的一部分。良莠互渗。这代人的活力和局限,独立感和支配欲多半应源于此。
“弱不禁风呵”,我会望着今天不会打唿哨的独生“宝贝”们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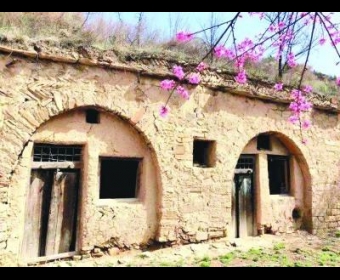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