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2018年11月《经济观察报·书评》
一
在《聂鲁达传:生命的热情》的译者序中,本书的译者杨震这样介绍这本传记:首先,在中文世界中,流传最广的当然是聂鲁达的自传《我坦言我曾历经沧桑》,但是因为自传往往具有“未必可信”之处,所以才需要传记作家这样的他者型传记,比如这本由英国传记作家亚当·费恩斯坦书写的《聂鲁达传》。相比自传,费恩斯坦的这本传记,“吸收了我们几乎能想到的全部聂鲁达著作、书信、文章、遗稿”,加上众多亲朋好友的回忆录、研究专家的专著等等,是迄今为止“资料最为翔实的一本”。
首先,作家的自传为什么总有“未必可信”之处?其次,资料翔实的传记是否意味着是一部好传记?要知道,文学史上大多数作家都不信任传记作者,究其原因,大概与传记作者对作家披露的事实有关。传记作家对作家本人和私生活的兴趣,大于对作家作品的兴趣。正如诗人奥登的名言,一本糟糕的传记会把传主所有的身世遭际告诉你。作家本人的生活需要曝光吗?米兰·昆德拉在《小说艺术》中写过一个“小说家”的词条,他先是借用了一堆名人名言,福楼拜、莫泊桑、纳博科夫、卡尔维诺,说来说去就是想说明一个真正小说家的特征是“不喜欢谈论自己”。
除了从个人隐私的角度考虑之外,作家不喜欢被传记作家曝光,大概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这就是乔治·奥威尔所说的,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如果从内部洞悉的话,都是一连串的失败。每个现代作家都禁不起传记作家的严格审视。作家其实比普通人对失败的体悟更加惨痛,因为在一个作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饱受冷眼和质疑,他的成功是偶然的,失败是常态。所以,诗人奥西普·曼德施塔姆才有这样的感喟,想要写作,至少你得有托尔斯泰的地产,要么就得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苦役。
二
《聂鲁达传》中,提到聂鲁达早年生活的一个细节。1921年,聂鲁达远离家乡到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读书,并开始写作诗歌,他写了一首诗《节日之歌》在学生联盟的竞赛中胜出,费恩斯坦评价说,这首诗“给他赢得了一定名声,但没有钱——这种情形日益成为他的命运,来日方长”。聂鲁达在自传中对早年读书时候的饥饿记忆和羞辱印象深刻,“当时我写的远比以前多,但吃食却少得多。那些日子我认识的某些诗人,因为穷,严格限制饮食,从而送了命”。他还回忆跟其他年轻诗人在节日期间去附近的城镇朗诵,被观众喝倒彩,轰下台,他们大喊着:“饿鬼诗人,滚吧!别来搅了我们的欢乐节日。”
聂鲁达总结自己的一生说,我的一生乃是漫长的漂泊。不过就算是漂泊、旅行、流亡,这些前半生的艰难历险都是后半生功成名就的衬托。这种回忆经过了漫长岁月的渲染,已经蒙上的怀旧的光环。他在自传中评价世人对诗人的苛刻时说:“有许多人不能容忍一个诗人享有一切作家、音乐家、画家应得的舒适的物质条件,不能将其看作诗人在世界各地出版作品所获得的成果。那些落伍的保守文人时时刻刻要求尊敬歌德,却不让当今的诗人有生活的权利。我有一辆汽车这件事尤其令他们恼火。在他们看来,汽车应该是买卖人、投机商、妓院经理、高利贷者和无赖的专属。”这段话中,有句话是点睛之笔,世人会尊敬歌德,因为他已经死去,而对于那些活着的作家,世人只会用更加苛刻和恶毒的言语去造谣、中伤和评价他。
这涉及到文学史上如何评价一个仍然在世的作家的问题。聂鲁达的自传,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澄清。对那些少数活着,但是取得了世俗和文学意义上的成功的作家,他们为什么会反对传记作家呢?纳博科夫就担心,传记作家根本做不到理解他的一生,“我讨厌肆意对待伟大作家的珍贵生活,我讨厌挖空心思打探那些的生活隐私——没有传记作家会看到我的私生活。”因为对传记作家的不信任,他才完成了自传《说吧,记忆》,主要集中他俄罗斯时期,他的晚年还打算完成一部自传《说下去,记忆》聚焦于他的美国时期。在他看来,一个作家留下的书面文字就足够了,他的日记、书信和闲谈不是公共资产。但是他的晚年充斥着无穷无尽的工作,已经没有足够的经历完成美国时期的自传,他才授权另外一位传记作家安德鲁·费尔得。纳博科夫认为在生前完成的传记,至少是可以操控的,费尔得已经向纳博科夫保证“该删什么,最终由您定夺”,正是有这种理解,纳博科夫才放心地把很多东西袒露给费尔得。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费尔得已经逐渐偏离的他的写作方向,他以为他的著作已经足以构成了他艺术生命的历史,他的私生活与任何人无关,但费尔得偏偏对他的家族的逸事和传闻充满了猜测的兴趣,更为要命的是,把他的私生活与他小说中的人物进行弗洛伊德式的联想,并随意判断点评他的人生。
三
在纳博科夫的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传记作家书写传记的矛盾心态:如何才能平衡作家的自传与传记之间的关系?这大概是每个传记作家都需要面对的问题: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利用一个作者已经发表的文本作为其传记的材料,同时避免对这些文本进行过度或草率的阐释?事实证明,作家的自传很多地方都是靠不住的,在《聂鲁达传》中,费恩斯坦直接点评说:“聂鲁达的回忆录是世上所有回忆录中最诱惑人的,但你在其字里行间找不到稳定的真实性——或任何诸如完整的故事这样的东西。”这个点评至少有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个层面,聂鲁达生前写作的时候,已经对自己的过往进行了修饰,这是每个作家在写作自传的时候都免不了的行为,我们的记忆都是选择性的。第二个层面,因为聂鲁达去世后,他的第三任妻子玛蒂尔德对聂鲁达的自传进行了重新编辑,我们无法得知她是否对其中的章节进行了修补或者删节——费恩斯坦就怀疑,玛蒂尔德删去了聂鲁达自传中对第二任妻子迪莉娅的部分论述。法国作家加缪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以为作家必定会写与自己有关的事情并在书中描写自己,那是浪漫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一种幼稚想法。一个人在作品里讲述的往往是其怀旧的历史或者愿望的历史,几乎从来都不是他本人的历史。”

《聂鲁达传》
(英)亚当·费恩斯坦/著
杨震/译
启真馆·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年7月
如果作家的自传都是不靠谱的,传记作家的传记是不是就可靠了呢?或者说,好的传记的标准是什么?批评家詹姆斯·伍德对号称写下了最完整的契诃夫传的传记作家雷菲尔德批评到,“令人咋舌的是,契诃夫最完整的传记作者几乎没有在契诃夫的作品上花什么时间。这本传记丰富得很苍白:一大堆旅行日记、信件和聚会。关于作家,他几乎什么都没说,并在很多地方把事实刨去了文学的背景。总的来说,他还不如完全不提契诃夫的作品,因为他简短的评论似乎诠释照本宣科、例行公事罢了。他似乎要建一座围墙,一砖一石都是生平的’事实’。”事实当然很重要,但是如果作家传记中如果堆满了事实,无穷无尽的细节,并没有对其做有机的遴选,传记就变成了人物年谱和大事记。
对一本作家传记来说,是作家的生活重要,还是作家的作品更重要?大多数人会说是作家的作品重要,但是对传记作家来说,作家的生活同样重要,尤其对那些一生都过得十分丰富多彩的作家而言。比如像聂鲁达这样的作家:诗人、外交官、旅行家、收藏家、参议员、工人运动的支持者、共产党员、被通缉的要犯、总统候选人、诺奖获得者,三任妻子,无数情人,早年以华丽之笔写情欲之歌,中年之后写人民、领袖、政治,日常生活。这样跌宕起伏的一生,很难让传记作家甘心放弃书写他的生活。二十世纪的作家——聂鲁达、海明威、奥威尔,他们的生活与二十世纪广阔的历史融合在了一起,他们参与了历史的创造,见证了众多关键的时刻,他们的写作与时代紧密相连。他们都是社会活动家,一生的漂泊和动荡,虽然未免苦涩,但是对作家的写作来说都是难得的经验。
一部出色的作家传记,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要避免“过度”用作家的生活来解读作品。但是想要做到“适度”,又谈何容易?割裂生活和作品,用詹姆斯·伍德的比喻,“如同屠夫用不同的刀子去切生肉和熟肉,未免不开化”,但如果只用从作家的生活中找寻出各种细节和暗示,用弗洛伊德式的揣测来分析作品基本等于瞎人摸象的行为,同样不可取。所以,“适度”是对传记做的真正考验。占据大量的一首资料,当然是好事,但是如果陷入资料当中,对事实和细节过于纠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作家无法做到化整为零,化资料为写作的经验,这样拿出来的传记同样缺乏观感。按照我的理解,好的传记应该像非虚构写作,即要在占有大量事实的基础上,像作家那样写作。但像聂鲁达、纳博科夫这样的作家,自身鲜明的特色也会无形中让传记作家产生崇拜心理。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就警告批评家,尤其是传记作者,“在论述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时,不管多么无意识地,都会采用他们的批评对象或传主的表达方式。简单地说,你会被你所爱的东西改变,有时候达到失去自己全部身份的程度”。这种适度的分寸把握是传记作者成败的关键。
四
读《聂鲁达传》的时候,我注意到了费恩斯坦提及到的几个细节,比如“聂鲁达”的笔名的由来,之所以注意到这个细节,是因为聂鲁达在自传中提及到,他小时候因为父母反对他从事文学,成为诗人,为了不让家人看到他发表诗歌,他在杂志上看到一个捷克人的名字,扬·聂鲁达,就借用了这个笔名。这本来是个无足轻重的细节,但是费恩斯坦还是补充了不少材料,比如推测笔名源自《福尔摩斯的探案集》,或者来自一个女提琴家等等。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聂鲁达到底是不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众所周知,他写过《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和《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新情歌》,他多次访问苏联,但是对俄罗斯人诗人被迫害的事实保持了沉默,他获得过斯大林国际和平奖,等等。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震惊了全世界,但是聂鲁达依然保持了沉默。在晚年的自传中,他提及到这一事件,仍然称赞斯大林“一个和善的、有原则的人,像隐士一样清醒,一个俄国革命的泰坦式的保卫者”。费恩斯坦分析这种心态时评价说,这种固执的信念源于一种观念“一堵墙只有两面”,如果你收回对一方面的忠诚,你就陷入了另一个阵营。这种对共产主义的忠诚是聂鲁达后半生写作的激情。尽管苏联失败了,但是聂鲁达在自己国家的同志身上找到了新的信仰寄托和情感安慰。
从这些细节的铺陈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传记作家费恩斯坦对聂鲁达的一生进行了理性的审视。他做到了一个一个好的传记作家的本分,即把聂鲁达的生活和他创作的诗歌进行了适度的对照,大多数结论也都是审慎而可靠,并没有精神分析似的揣测。但是,不得不承认,这本传记仍然像大部分作家传记一样,对作家的生活的兴趣大于对他作品的兴趣。或许这跟传记作家本人的能力有很大关系,如果你不是一个合格批评家,很难对聂鲁达的诗歌进行更加深入的解读和分析。传记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文学批评。只不过这种文学批评是建立在对作家一生的总结之上,所以要求传记作家具备全局的视野,批评家的灵敏嗅觉,还要具备作家的同理心,才可能写出一本优秀的传记。
阿伦特有个观点我很认同,她说传记其实是一种特定的历史。她的《黑暗时代的人们》是黑暗时代一幅幅肖像画,书中写到了很多她的朋友,比如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文学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等等,但是她的写作不会让人察觉她在写的人是她的朋友,她很少用那种“现实主义”的细节来描慕和揣测他们的生活,她把他们隐藏在作品中,给他们分别塑造了一幅幅思想的肖像。用她的学生和传记作家扬·布鲁尔话说,“在地点、人物和时段上追求出新的描述性传记,对于阿伦特这样的人来说并不合适。我们要展示的是她思想的历史基础,是激发她进行思考的待定经验,是濡养她的友谊与爱,如有可能,还要展示她的思维方式或思想风格”。这才是好的传记,也就是兼顾了思想性和文学性,把趣味性减到最低——,趣味性不是不重要,我们要警惕的是趣味性遮掩了真正想表达的东西,因为只有趣味性的传记无一例外,全部都是津津乐道描述作家的私生活,挖掘他们的各种八卦,反而让我们忘记了一个真正的作家的传记,只有他的作品。
诗人切斯沃夫·米沃什有一个观点,他说传记的价值只在于它能使人多多少少地重构传主曾经生活过的时代。好的传记不会只把焦点停留在传主身上,它会分散精力描慕一个时代的群像。大时代才是传记的主角,而那些只对传主本人的生活感兴趣的传记,只能沦为三流的谈资,注定烟消云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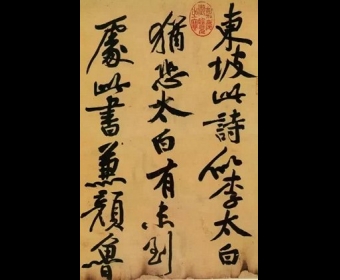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