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致的诗、“轻”之美与审美现代性的追求
——柏桦诗歌的诗学、社会学讨论
李商雨
柏桦,1956年1月生于重庆。现为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出版诗集及学术著作多种。最新出版的有:英文诗集Wind Says(《风在说》)。《在清朝》(法语诗集)。《为你消得万古愁》(诗集)。《革命要诗与学问》(诗集)。《秋变与春乐》(诗集)。《惟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诗集)。《蜡灯红》(随笔集)。《白小集》(随笔集)。《水绘仙侣:冒辟疆与董小宛——1642-1651》(诗集)。《竹笑:同芥川龙之介东游》(诗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出版。
曾获安高(Anne Kao)诗歌奖、《上海文学》诗歌奖、柔刚诗歌奖、重庆“红岩文学奖”。羊城晚报“花地文学奖”。首届东吴文学奖。
柏桦的诗歌让人瞩目的特点之一就是精致。这种精致,源于他诗歌的艺术自主性和他对艺术本位主义的态度,是对美的孜孜以求,而非历史或伦理。这种态度,可以视为柏桦写作的元语言,具有很强的后设意味。他对精致的追求,大致来自几个层面:首先是语言和修辞的层面;其次是一种精致的文化;再次就是精致的生活风格。在当今时代大语境下,他的写作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启蒙现代性的反拨,是纯粹的审美现代性或文学现代性的追求。将这种对审美现代性的追求放在时代语境中,可以见到它的“不合时宜”:从总体上讲,这是一个批评和写作的伦理化与历史化并存,却唯独不能容纳纯粹审美形式的时代。如何认识柏桦诗歌在时代中突显的差异性,是一个不太容易破解的难题。
一、精致的诗
柏桦的诗歌写作的分期很明显。前期主要是80年代;第二个时期,主要就是近十年来。1989年,柏桦的写作有个明显的中断,虽然此后他依然断续写了少量的诗歌,但仍应以那年为他写作的重要时间节点。①第二个时期,最明显的时间节点是张枣的病逝,即2010年3月。在此之前,柏桦也写了不少诗歌,但从写作的持续性看,以张枣病逝作为时间节点更为妥帖,尽管他已经出版了《水绘仙侣》。②
柏桦写出成名作是在1981年,③直到1988年,诗集《表达》出版,这期间他凭借诗集中的仅仅几十首诗歌成了中国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也是第三代诗歌的代表性诗人之一。如果可以将诗人的重要性量化成数字的话,拿这个数字去除他发表的诗歌的总数,所得的商,柏桦可能是最大的。这其中当然有和张枣的比较。因为同样作为80年代著名诗人之一,张枣也是那种以少量的诗,获取大的诗名的诗人。
柏桦第二个阶段的写作,在诗歌的数量上,呈现出和第一阶段不同的另一个极端:近十年来,他可能是中国重要诗人里写诗数量最多的。与早期的诗歌数量非常少,到这一时期的非常多,形成鲜明对比。从诗歌的美学对照,两个时期既一以贯之,又显示出很大的差异。后一时期,柏桦在诗的技艺、诗的美学的成熟度、诗歌背后显出的对汉语诗歌现代性思考的深度方面,都见出他较之第一时期的发展变化。以至于激赏者认为,柏桦近几年的诗歌,几乎每一首诗都在刷新汉语诗歌语言的高度。④这似乎是在说,作为整体的使用汉语写作的诗人,集中在一起进行一场语言的跳高比赛。但是,笔者以为,柏桦的写作还不仅是一次“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⑤除了语言以外,他在诗歌元语言以及日常生活风格上都有追求。不过,柏桦的追求,如果与维多利亚时代的王尔德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区别。为了自己的美学理想,王尔德与现实的世俗世界秩序发生了决裂,而柏桦虽然也将写作的美学落入实践理性层面,也将艺术与生活风格之间有明显对接,但他并不是去颠覆现世秩序,而是采取了一种较为温和的方式。
笔者讨论柏桦的诗歌写作引入王尔德文学事件看似有些突兀,其实不然。柏桦的诗歌,在某种意义上说,有一种美学上的孤军深入意味。他的诗歌的精致,肯定来自他对诗歌精益求精的追求,这种追求与欧洲那个时代的唯美主义运动相比,颇有几分相似。⑥尤其是,柏桦将艺术和生活密切联系起来,这很能让人联想到唯美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和“生活的艺术化”。对于柏桦来说,写诗与生活具有同一性,⑦这从他对饮酒的波西米亚式生活风格的热爱、他对丰子恺文人画的赞叹,⑧以及他诗中常常把饮酒作为一种美的追求来写来看,三者之间高度同一。三者之间的关系,由一个美的信条维系:对“平凡”的热爱。这显然是由柏桦改造——甚至可以说发明——的一种当代中国诗歌之美⑨。在王尔德的时代,由于中产阶级(其实就是资产阶级)尚未真正壮大到培养出他们的贵族趣味,他们对王尔德耽于审美形式的贵族趣味,怀着“既恨又爱”的感情,⑩所以,王尔德小说中的同性恋题材,深深冒犯了当时的中产阶级。11
柏桦的诗歌,与王尔德的美学相似点在于,他们都将纯粹的审美形式当做诗歌的第一要义置于诗歌的功能之前。在柏桦而言,他的诗歌就是精致。这种精致,首先表现在语言上。这是基于这样的观念:第一是表达的准确性;其次,是对语言——诗歌的声音、诗歌的用词、造句——本身的追求,由此而生成的诗的神秘感,让语言指向自身,让诗成为诗。以柏桦对声音的追求为例,他写于2014年的一首诗《鲜宅,1967》的第一节如下:
有些白发漂亮似青春
有些白发揪心如灰烬
有些回忆漫长而享受
有些回忆一瞥便惊心
更阴天你就一春多病
更念死她就活了下来
欧阳海,母亲,特园……
红箭、黑箭、孔雀……
这节诗歌每一行里的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在这首诗里,他每一行结尾的方式:均以双音节词结尾,这可以视为柏桦对诗的声音的一次实验,也体现出了他对新诗现代性的追求。他的这种实验,来自诗人卞之琳。
卞之琳在诗集《雕虫纪历》的序言里谈到诗歌的声音时认为,旧体诗是“较近哼或吟咏的调子”,而白话新诗则“较合说话的调子”。12他发现,旧体诗,以七言诗为例,往往是三个顿或节拍,最后一个顿,一般是三个音节,读起来是所谓“吟咏调”。而现代汉语以双音节词占主导,如果一句诗的结尾由三音节变为双音节,则诗歌由“吟咏调”变为“说话调”。
这二者的差异,并非单是调式差异,它其实回答了一个现代性问题,也是卞之琳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观念之下的发现。13之所以我们说这是现代性问题,是因为卞之琳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真正是立足于现代汉语的,这个发现,既有现代汉语区别于古代汉语的地方,也有区别于欧洲语言的地方。柏桦对诗歌语言的追求,也如卞之琳一样,“小处敏感”,从词法开始,扩展到句法、章法,做一个语言的“匠人”,让诗歌回到技艺的最初含义。14
二、平凡的“轻”
柏桦对诗歌审美形式的追求,是基于中国新诗的现代性前提下的审美现代性的追求。他的这种追求,笔者不过是从他在一首诗中对声音追求的举例说明。实际上他诗歌语言的精致,并不仅仅体现在这种卞之琳发明的说话调方面,甚至也远不止在对诗歌声音的追求方面,比如说,他对冲破裹挟权力意志的意识形态化了的普通话对现代汉语的禁锢方面的追求,同样让他的诗歌极为精致。15具体说,柏桦在写作中有意识地以日常口语为基础,加入了大量的文言词、外来语、英文以及方言词,呈现一种类似罗兰·巴特描述的“文之悦”效果,在各种不同性质的词语之间形成一道道快乐边线,从而对文本中包含的政治权力构成逃逸。16这样做,是对五四以来白话文屡次运动造成的恶果的反对,也瓦解了诗歌中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主体。这意味着,他的诗歌需要重建汉语诗歌新的主体性。
柏桦对诗歌语言精致的追求,是以《易传》所说“修辞立其诚”为出发点。此处之“诚”,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真诚、灵魂之类的含义,显然是指一种对诗艺精诚如一的态度。在柏桦看来,“用灵魂写”的真诚,容易在诗中流于不必要的道德化。他在诗集《竹笑》的“缘起”中引来芥川龙之介的话足以见出他的意思。17那么,所谓对诗艺的精诚如一,就是对艺术、美、修辞(能指)的“诚”,是对技术的严苛,让诗歌回到“诗艺”的起点。
然而,柏桦诗歌的精致,不仅是在语言,而且还在元语言的层面展开。很明显,他的写作并非仅仅耽于语言的精致,他对诗歌语言和声音的追求,其实既是纯诗的,又超越了纯诗,进而深入到古典文化与文学传统之中。他对白居易诗歌的关切和研读,是对白居易“讽喻诗”之外的诗歌的诗学认可。白居易的诗有两套相对独立的诗学系统,一套是政治正确的诗学系统,白居易将之集中表述于《与元九书》一文;另一套诗学见于他具体的闲适类的诗作,这类诗作显然和《与元九书》中表达的诗学观念不同。柏桦认可的,即是这后一种诗学。具体说就是,诗要从“平凡”的生活写起,写“平凡”的美。这种“平凡”的美,如果放在百年来的新诗史里,很容易看出它的意指:它是对主流话语的挑衅和逃逸,对五四以来文学的启蒙现代性的反拨,也是在实践一种审美的现代性。与之相对应,是柏桦对《枕草子》这一文本的发现。这部产生于日本平安时代的文学作品所包含的全部诗学,几乎都是来自白居易,它是白居易诗歌之美的域外之花。这部由周作人翻译的作品,被柏桦视为是白居易诗学的现代形态的圣经。在这部作品中,更加具体地体现了中国古代以来以“言志”“载道”为主流的美学之外的另一种美。“言志”“载道”可以视为文学中的“重”,而后者则是“轻”。
众所周知,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先是以“启蒙”,继之又以“救亡”为主流,这些都与古代诗歌的“言志”“载道”传统有所暗合。按照詹姆逊(Fredric R. Jameson)的说法,中国现代文学,是相对于第一世界的具有“民族寓言”特征的第三世界文学。如果必须与“言志”“载道”传统有相似性,那就是中国现代文学言的是启蒙的“志”,救亡的“志”,以及后来的诸如朦胧诗对抗专制制度的“志”,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写作”批判社会的介入的“志”,甚至,也包括在21世纪以来以伦理路线的诗人写作的道德伦理的“志”,它们载的也是这样的“道”。但终归这一切在索绪尔的“能指-所指”系统中,都是过于注重“所指”的文学,因而它们是“重”的。落实到百年新诗的写作实践,它们是启蒙的现代性,而不是审美的现代性。审美的现代性,必定以审美形式作为写作的起点和重点。据卡尔维诺的看法,现在,以及未来千年的文学应该具有的最优良的品质,就是轻逸。18卡尔维诺的意思是,文学惟有从沉重的意识形态中逃逸出来才可能获得艺术的美和自由。
依詹姆逊之说,任何文学都不可能摆脱“政治无意识”。但我们不应忘记,如果以詹姆逊“政治无意识”在文学中的普遍性作为借口来夸大文学的施加于现实的功能,这就已经是有意地偏离了文学作为文学的自身逻辑,进而成为文学生产场中的一种权力话语。笔者赞同竹内好在讨论鲁迅时得出的结论:“鲁迅看到,文学对此(政治)是无力的,至少看到有力的文学是无力的。”“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文学代替不了“一炮”。如果文学中的政治是普遍的,那也是如鲁迅说的,是政治的“余裕的产物”。文学的无力,是对政治的无力。19所以在《呐喊》时期过去之后,鲁迅进入了以审美为突出特征的《彷徨》时期。有论者认为,詹姆逊所谓的“政治无意识”,只不过是第一世界学者对第三世界文学的窄化和征用。20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是以西方作为参照,这势必落入到所谓的“与国际接轨”的路上去。须知,这种做法,极有可能会让某些汉语写作者生出一种优越感,但这种优越感,只不过是“与劣等感并存的缺乏主体性的奴隶的感情”。21
以上关于中国新诗在现代性语境下以“重”为特征的讨论,也映衬出柏桦诗歌之“轻”的价值所在。如果我们的讨论放在柏桦的整个写作生涯来看,他写作早期经历的80年代,也是写下诗集《表达》中那些名篇的年代。那个年代在1989后被人称为以“青春写作”和非历史化写作的年代,诗歌写作的不及物性是那个年代的特征。进入90年代以后,“中年写作”进入了公众视野,“历史意识”“及物性”“知识分子”“九十年代诗歌”等成了时髦的词汇。其实这批诗人,早在80年代甚至更早即已开始写作,只不过相对于当时的诗歌主流,他们显得泯然众人。这些诗人在90年代的咸鱼翻身,有诸多政治和社会学因素。
而21世纪以来,“911事件”、伊拉克战争、“次贷危机”等全球性大事,都直接间接与中国发生关联。全球化加速了中国进入消费社会——它不可避免的副作用是让每个人都参与到道德思考。所以,无论从批评还是写作的实践来看,新世纪以来的诗歌中除了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历史意识”之外,还加强了道德伦理因素。一些批评家对“打工诗歌”“底层写作”的鼓吹,也更进一步弱化了以审美形式为特征的诗歌写作。基于这种情况,王光明认为,流派概念上的“90年代诗歌”不过是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中,“既有历史的相对性又有时代的具体性,既是当代诗歌运动的某种合情合理的结果,又是一种矛盾重重的探索。”22至于新世纪以来新诗的伦理化路径,当然是这种历史“语境”的延续。
2010年左右,柏桦真正迎来了他写作的第二个时期。相对于他的早期诗作,他的诗中明显强化了“轻”的因素。“轻”,让他的诗歌更加精致,更加注重审美形式,因而相较于前期,他的诗在形式上更加考究。前文已经分析,这体现在两点:第一,通过以日常口语为主的各种词语的“杂于一”,从语言上摆脱普通话的意识形态控制;第二,通过偏离传统诗学,偏离百年新诗里包含的启蒙现代性的新诗主流诗学,尤其是避开90年代以来甚嚣尘上的“知识分子写作”的诗学。客观上说,这两点使他的写作在元语言的层面获得了美的自由。
这固然可以被反对者指责为是另一种“政治无意识”,但它其实已经最大化地稀释了诗歌文本的对现实的指称性功能作用,从而突显和强化诗的审美形式。可以说,这是一种对百年新诗的启蒙现代性的反拨,它明显是为了要强化诗歌的审美现代性因素。柏桦借力古典文学和古代传统文化的做法,是为实现现代汉语诗歌的审美现代性的追求;同时,也最大限度体现了柏桦的写作在这个时代的差异性——读者注意到,不但与“知识分子写作”形成差异,也与“民间写作”差异巨大。总归一点,精致,是柏桦诗歌在这个时代的差异性的外在表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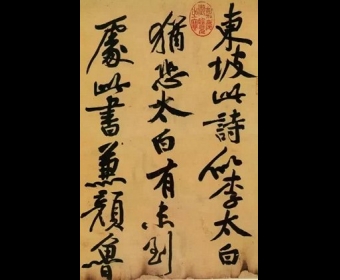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