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黎至仍给我留下最初的印象:个子不高,身体很胖有一张看上去像孩子一样的圆脸?但当他爽快的大笑起来时又有一种夸大了的成年人的感觉;他是一个很快乐的人(快乐消除了权势;):不轻意流露他的敏感;我仿佛对这个形象一见如故,的确后来证明如此,他在生活中有一种魏尔伦式的反抗天性,完全游离于这个制度之外(他六岁时玩结婚游戏;九岁时对女性完全入迷,十二岁时尝试文字创作,十五岁时与同学魏国安等成立“草堂”诗社并沉入课外阅读,学业荒废而主攻小说;十八岁时恋爱、同居、写诗轮番不停,在银行干部学校印地下诗刊《鼠疫》,受公安部门追察;二十一岁时向往“走”,失望笼罩一切——哲学,诗、人生,摇晃在神、仙、巫术、气功和宗教之中,在一个冬天学习太极拳;二十二岁写出《怪客》,无端端出走重庆朝天门码头,又在彻底绝望中返家;开始接识万夏、周伦佑,辞去银行的工作,放纵于酒、色、诗;二十二岁时从糊涂生活中苏醒,深入川西,川南乡下,心境渐趋明朗,进入诗创作第一个高峰,写出《街景》等作品,并通过万夏了解到“他们”“海上”诗人;二十四岁时围绕“非非”从事大型诗歌活动,想办宗教性组织诗歌教;并继续非非之行,写出《高处》;二十五岁时同蓝马、吉木郎格深交并和李亚伟去海南;同年与小安结婚;二十六岁流浪全国,为生活而生活;九二年与蓝马、吉木郎格,何小竹创办成都广达软工程公司,涉入广告、策划及信息等经济领域,一九九三年十月公司解体,非非消失)。而这个“魏尔伦”并未写过一行感伤的诗;他曾告诉一位诗人:“如果你要写好诗,首先不要写痛苦。”就这样,这个快乐的诗人在一九八六年九月的某个向晚时份来到了四川大学我那建筑工地式的学生宿舍,他系着一条狭长而晦涩的丝巾,这丝巾确立了一个标新立异的诗人形象(丝巾与他矮胖的身体构成一个特殊的诗人才有的不协感),生活中可能伤痛的唯一证据。那丝巾在幕色中零乱地捆(不是系!)在脖子上,似乎要像魏尔伦一样绞死雄辩;他的诗正在绞死雄辩,但不像魏尔伦用歌,而是用一长串矛盾、更替、中断、任意、短路的带有非非式“还原”论的名词。
他当时正以非非第一诗人的身份登上诗坛,继漂浮不定的《怪客》之后,写出扑朔迷离的《冷风景》。就像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小说《窥视者》或《橡皮》,这些作品本身就是一座没有出口的迷宫,是有意送给读者的一个悬在半空的安慰的虚构,“物”在“冷风景”中排列着,全然不顾意义的摆布(他妄图在此收回诗丧失绐小说的地盘,为“怪客”或“冷风景”向小说索赔,一个有待分析的诗歌案例)。我们永远无法弄清贝克特的《莫洛伊》中莫兰碰见的那个穿厚大衣、戴厚帽子、拿着根粗重的手仗的男人究竟是什么人,无法弄清《去年在马里安巴》那些静止不动的画面中让人费解的男人或女人,我们也无法弄清杨黎《高处》中的“A或是B,看猫、火山、一条路、还是夜晚、还是陌生人、彷佛B或是A。”这些A或B把中国诗歌的试验从某个方面推向极端。这些诗行不仅在当时,即使在现在,在无数学者和诗人热衷于西方后现代理论研究、引进、传播、实践的今天也属惊世骇俗的了。这种远离现实的四大皆空的语言还原论、这种完全彻底的乌托邦式的价值观在诗歌界内部引起了一阵震惊、愤怒、骚乱和蔑视。非非写作是不可理喻的,正如德国学者顾彬在《今天》一九九三年第二期《预言家的终结》一文中指出的一样:“因为非非派更属一种国际现象,对普通中国读者来说,它只能是阳春白雪。”非非对于当时的我同样也是阳春白雪。我很长一段时间困惑于他们为什么这么写?为什么要消解现实、抒情、经验,甚至一首诗的基本点——感受,我第一次真正目睹了什么是彻底反传统的诗歌:我保持着沉默,仅对孙文波、欧阳江河说:“非非诗的语言很有特色。”他们诗歌中(主要是杨黎的诗)的实验性、先锋性、拒绝性引起了我抒情般的好奇:就像一九六六年夏天傍晚我曾对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好奇一样,童年的第一次“先锋”体验又来到今天的“非非”体验。“莽汉”、“他们”“非非”、美丽的红卫兵、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我在想着。
“非非”,我初次听到这个名字是八六年五月,当时西南师大美术系的一个学生王洪志告诉我周伦佑邀他加入非非。“哦,非非,这是什么意思……”我在想,我想到周伦佑,一个有综合才能和有抱负的文人,一个不知疲倦的激昂的演说家,他就是非非主编,内心装满支配性里必多(Libido)的抒情权势。我在一九八五年见过他,他当时正在全国进行漫游和演讲,他来到西南师范大学接近尾声的浪漫的一站。在一个月夜,在一间灯火通明的阶梯教室,黑压压的学生抬起苍白、焦渴的脸朝向一个很有经验的雄浑的声音,他正讲到“象征”或“超现实”。一个热血汹涌的抒情战士现在驾驶着非非的梦船起航了。这行动(卓有成效的集体行动)本身就满含激烈的抒情力量。尽管他们在诗歌中有意反对抒情:但却从反面走向了抒情,正如T.S.艾略特所说:“向上的道路就是向下的道路。”一极必达另一极。
我和杨黎的交谈一直与诗无关系。我对他谈到了毛泽东,他后来也津津乐道于毛泽东及他的一句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条座右铭是一个启示:它启示了一种杨黎式简洁、朴实、“还原”的话语,他是否决定了在毛文体的基础上继续从事语言革命?他后来告诉李亚伟:文化革命曾带来一个口语彻底书面化的时代。废除古文以来,中国一直没有出现成熟的现代汉语文本。鲁迅的语言不是完全的现代汉语,沈从文也不是?只有到了《毛泽东选集》才形成真正的现代汉语;这堪称现代汉语的一个里程碑,统一了新社会的口径、约定了口气和表达感情的方位,新一代人民用起来极为方便,报纸、电影和讲话,甚至恋爱部采用这种语法和修辞。这使我想起胡适说过的一句话:毛泽东是我的学生,他的白话文是写得最好的。
是的,中国的长城在当时正有效地阻挡着西方资产阶级的话语入侵,而如今城门一开,人们就争先恐后要丢掉“毛泽东语言”这个传统(其实丢掉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延安整风运动,政冶学习形成了一个极好的毛话语普及模式。毛泽东依靠这个有效的模式在四九年以后通过报纸(最好的手段)、杂志、政治学习(这最厉害的形式),思想总结建立了一整套更完美的学习制度。我们在这个学习制度日复一日的训导下,从小就自然而然培养了毛话语的思维习惯。而早年奔赴延安的青年俊才何其芳,卞之琳、艾青、冯至几乎是一夜之间放弃了自己早巳形成的话语进入毛话语体系,心甘情愿脱抬换骨,这的确是一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或许是“毛文体有一个优势——他的话语从根本上是一种现代话语——一种和西方话语有密切关系,却被深刻地中国化了的中国现代性话语。”(李陀语)或许是某种天意的力量而非毛话语本身。谁说得清呢?据说爱走偏锋的法国怪才福科(MichelFoucault)晚年也被毛话语所吸引。但毛主席人很清楚,为了转变意识形态必须改变语言和写作;语言是意识形态和政治的一个最基本的因素。正如毛泽东很早就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说过:“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只要他不是哑巴,他就总有几句话要讲的。所以我们的同志都非学习语言不可。”这就是毛泽东的力量之所在,他倡导的简洁文体有一种朴实的权势(一种现代文本的快乐?),这种语言权势犹如一股道德威力的确深入人心,诗歌界的叶文福不是就以这种道德权势进行现实主义的漫骂吗?骆耕野不是也以这种道德权势写《不满》吗?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偏离——摆脱权势的基本程序(“今天”作了一次可贵的偏离;但又堕入另一种“今天”式的话语权势。)而偏离在一般情况下却是相当困难的。我有一位研究音乐学的明友付显舟(与我同年),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研究生,他有一次对我说:“很奇怪,我一写文章很自然地就是毛文体所规定的那一套话语:我老想偏离但做不列,毛文体用起来就是得心应手:我甚至尝试西方现代批评话语或五四时期的话语但文章就写不动了,语言也不灵了,还出现词不达意的情况。我明显感到毛文体话语的强大。他自叹恐怕这一辈子只能在毛话语体系下生活,工作、写作。我同样也感到偏离的困难。写诗碰巧能作出有效偏离,但一写文章就有种文字恐惧症,对所谓时代语言害怕、对中国传统语言害怕、也对车尔尼雪夫式、黑格尔式、别林斯基式、列宁式(许多人在背离毛文体时采用这类文体)害怕。言说如此困难?我将如何开口?我感到一种与我相隔离的话语权势高高在上、我处在它无形的监狱里。
我开始追踪非非的创作及理论。
如果说“今天”是对毛话语体系作出的第一次偏离(对所指的偏离),那么非非对毛话语体系作出了第二次偏离(对能指的解放)。杨黎曾告诉我:“诗是能指对所指的独立宣言。”就这样,非非突破了文字的恐惧症,获得了全面的身心自由。放开手脚、颠覆中心,走出文字的禁忌。他们首先集中火力歼灭诗歌中法西斯般的文学独裁——形容词,清除语言的道德含义;他们以最大的可能让名词、动词获得它们的最初存在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出现了杨黎先验的“无意义”声音:
下面/请跟我念:安。安(多么动听)/麻。麻(多么动听)力。力(多么动听)八。八(多么动听)/米。米(多么动听)牛。牛(也依然多么动听)或者/这样念:安麻。安麻(多么动听)力八。力八(多么动听)米牛。米牛(也多么动听)/一片片长在地上/长在天上……/
这声音出现在《A之三》。他试图在原语言基础上建立一个庞大的能指系统;推翻所指的长期“暴政”,让能指脱颖而出,姿意漫游。纯声音,纯书写、纯发现、纯还原、纯“不在”或纯引领——向高处,没有知觉的高处,本来的高处(这是一次更彻底的虚无主义的不可能胜利的努力)。这里,在“安、麻、力、八、米、牛”的世界里,没有悲观、没有时间、没有意义,也没有形容词带来的等级化或失语症,只有“最初的”极简单的声音的再现和词语的碎片。杨黎曾满怀这种创造了“简单”的奇迹之情告诉我:“一九八六年非非创刊意味着第三代人的纶争结束。第三代人其实质是用一个数词来指三种创作倾向:北岛式、杨炼式、万夏杨黎式,特别以第三种区别北岛的朦胧和杨炼的史诗,并不是断代的意思。所以今后不再会有什么第四代、第五代之类了。”
接着非非主义理论家蓝马在一个十月的黄昏被敬晓东介绍给我。我知道他是“非非”的命名人。他的《前文化导言》试图为人们的头脑打开一扇可怕的窗户;他层出不穷的非非理论被认为是一个超越了德里达的狂想;他最初的诗作《沉论》就已表现出反文化的坚决倾向。按照他的理论:“先有奔月的艺术,才有登月的技术。”而非非所进行的正是无迹可寻、需要承担最大风险的奔月的艺术。从“行”到“知”,一个率先迷失者,一个没有座标的探险者,一个对非非命题命名的感兴趣的人(他在1993年对我谈起于坚正在对一只乌鸦进行非非式命名),他日继夜以非非的名义对世界命名:“指船/指帆/指鸽/指鸥/指海……/水与水一位一体/手与水二位一体/走船/走水/走鸽子……/指远/指近/指周围……”在这首他所写的《世的界》中,他实践其“还原”理论,履行其“走向迷失”的诺言,破坏世界的基础形容词、破坏世界的结构动词、破坏世界的元素名词、破坏世界的绵延和场所数词、副词、度量词,总之破坏世界一切的语言制度,破坏所有对语言的记忆制度,从这些制度中把一切解放出来,解放从“世的界”开始,从其中的“的”字开始,世界再不是世界而是“世的界”,这个小小的“的”字在此起到了一个革命性的作用,世界的面貌由此改观。从此地出发,从“的”字出发,蓝马退出了世界!退出了价值!退出了语言!退出了文化!退出了人!同时又把语言、把人,把世界引入对语言的绝望境地,蓝马从不说开始说:“在沉默中坚持一片喧哗。”“能说的,都是不必说的,必须说的,恰恰是无法说的。”(维持根斯垣语)
世界在“世的界”形成了非非的世界。
而一九八五年底另一名号称“鬼才”的非非诗人何小竹正坐在涪陵暗淡的家中写《牌局》、《大红袍》、《葬仪上看见红公鸡的安》,他雅致的面部流露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感情——对自身写出的文字的惊恐。他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表情将导致什么?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这些已经写出的《鬼城》组诗(这些诗共十首被非非命名为鬼城,发表于非非创刊号上)已将他置于一个无法评说的境地,他感到恐惧似乎在抓住他的头发叫他离开地面,返回已不可能了。这时的何小竹正在不自觉的进入非非冥想。紧接其后,在蓝马《前文化导言》的冲击下,他开始自觉地、有意识地进入非非。他以盲人摸象这一成语对非非作出自己的解释:“非非是几个盲人模的那个大象。我、蓝马、杨黎,吉木郎格等人就是模像的盲人。我们写出的诗各不相同,但组合起来就是一头“非非大象”。其中有沉思的蓝马或奔放的杨黎。
一九八八年初,何小竹完成了极有争议的《组诗》并将它题献给蓝马,以表对这位“前文化”理论家的敬意(一个题辞的插曲:《组诗》在《非非》未刊发前,周伦佑曾建议作者删掉这个献辞。理由是,这个献辞会给《组诗》造成误读,以为《组诗》即是“前文化”理论的注脚,作者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作者认为能够读《组诗》的人,就不会误读,假如误读了,也是一种美妙的误读。最后题辞完成了它自身的工作)。在《组诗》“太阳的太”的章节中,何小竹开始了这样的“造句”:
1.阳光普照大地。
2.高一、二班有个谢晓阳:
3.今天,物理老师在物理课上叫我们打开上册第23页第二章第一节:预习:“阳离子。”
4.我舅舅在“红阳”三号当水手。
5.星期三,我没去夜自习,偷偷去“向阳”电影院看了电影《阳光下的罪恶》,这是不对的。
6.大扫除,我主动要求和班长去打扫又脏又臭的阳沟。
7.农忙假;我在家帮母办阳春。
8.阳雀喳喳叫。
9.阳萎……
这是一种典型非非式有趣的、局部的字的练习,一种对可能出现的“阳”字的美的反复认识。在此,阳字的宁静来到这个宁静的少年的一张白纸上,他发觉了一个平凡的“阳”字的本来目的!如最初仓颉造字,感天地泣鬼神,这个“阳”终于回到阳自身,回到蓝马式前文化(还原)的理想。中国的像形文字通过“阳”字带绐我们一种初逢的惊奇。“一个点是非非,一个面是非非,一种滋味还是非非,天也是非非,地也是非非,一个月亮非非,两个月亮更非非,而宝石特别非非,不过挑子也同样非非……一切皆非非,直觉亦非非,宇宙之谜被还原。”(蓝马《非非主义宣言》)太阳的太或者阳当然也就是非非之阳。
《组诗》企图努力告诉我们一种语言的自在,字呈现实际本身的样子,字与时代、处境、理论、价值,甚至对像全无关系。在这里,字仅仅是“张大嘴巴”开始言说,仅仅是一个通过诗的形式解构诗歌的文本。相当虚无!相当飘渺!
当蓝马突然在《日以继夜》、《九月的情绪》中偏离他的非非理论时(他转入带有象征意味的抒情),吉木郎格,这位腼腆而温柔的非非诗人(但他酒后的举止让人吃惊、整个眼神判若两人)正带着他那一贯克制的忧伤进入出奇不意的“很短”的非非,他写出一批很短的诗,被非非同人认为妙不可言。杨黎绐我背诵了吉木郎格的《消息》,我记住其中这样的一些句子:
6月6日是一个普通的日子
早上下雪
中午出太阳
晚上有风……
在另一首《妙》中,他用一种典型后现代的直陈式书写关于看了一本书的情况,大约是“我看了—本书,一本关于进攻和防守的书,看完后什么也没记住,只记住一个妙”。
这位曾写过许多关于动物的诗歌的诗人在《消息》或《妙》中更关心语言的去向(暂时忘记了心爱的动物),而不是语言的意义或象征,让语言流露它自己的“六月六日”一个普通的“纯在”状态。就像他日常生活中不带危险的形象一样,他也不带任何要求“伟大”的妄想念头在平凡的“字”里进行字本身的探索。这探索从两个方面进入诗中:一是生存体验,二是语言体验,就像经历对人来说也有生活经历和心理经历两个方面一样。作为诗人,他认为只有被他深深体会过的语言才与他息息相关,并通过对语言的“发现”才会让诗在文字中发光。
在他的诗歌中同样删去了痛苦,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早巳把自己的全部献给了诗歌中舒服的一面。”即使他在生活中痛苦着,愤怒看、感动着(甚至对感动时所说的话后悔),即使他在十月,在一个视线最佳的山坡上独自坐下点燃一支香烟,观看收割后的田野里静静的谷桩或一些积水的小坑倒映出秋天的天空,即使三两白鹤临空飞过、此起彼落,他好像若有所失,有某种来自外部的寄托。但他最终拒绝了这些情绪进入他的诗歌。只是在诗以外,他感叹过“一年又要过去了”,在那个山坡上他一次又一次感伤地观看着并点燃生活中的第二支香烟,因为非非诗歌是反对在诗歌中点燃抒情的香烟的。
罗兰•巴尔特(RolandBarthes)与非非的契合。
“文学中的自由力量并不取决于作家的儒雅风度,也不取决于他的政治承诺,甚至也不取决于他作品的思想内容,而是取决于他封语言所做的改变。”(罗兰、巴尔特语)非非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做出了对语言的改变;物质力量正消解着这个时代的激情,从风景到地貌毛泽东时代的影响已一天天荡然无存了,典型的社会主义式大楼已被西洋式宾馆所替代,精美的资产阶级生活改造着我们的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正在对中国社会进行它全面的“时代整容术”。当遗留下来的计划经济时代的诗人们还在坚持唱着怀旧之歌时,市场经济已开始了它不可阻挡的长征。如果说“今天”、“莽汉”反抗了毛文体的激情,那也是在激情范围内迎战了现存的道德观念,并以一种新的道德歌唱(仍是主体性的)在当时的青年心中达到如痴如醉。非非则超越了激情、消解了激情,与时代合拍了。在非非中,他们通过“还原”的语言把物质还给了物质,甚至延绵了物质的直立意义,斗争的矛头在这里不是指向道德,而是指向任何一种道德语言施以他们的“暴力”——抒情暴力。为此他们大刀阔斧消解现代主义的精英意积,大一体性、消解超现实主义发明的专利——神经分裂症式的话语模式——这种模式的首创是兰波;在此他们进而力图消解兰波式智慧中的混沌白热以及后来狄兰•托马斯式的“个人情结”的烦热眩晕。从这个意义上说非非所做的对语言的改变也是国际改变语言运动的一部份。五○年代的英国诗人拉金早就开始用简练、表意直截而无惊人妙语的娴熟技巧消解词义晦涩、歪曲句法、故弄玄虚而又浪漫狂热的狄兰•托马斯了。他使用不加渲染的,克制而稍稍压抑的文体、平易的朴素语气及日常性题材。拉金曾说过:“对我来说,整个古老世界、整个古典的圣经的神话都没有什么意思。我认为在今天再去搬用这类东西只能使诗充斥让人费解的陈词滥调,阻碍作者去发挥独创性”。(《第四次交谈》《伦敦期刊》1964,第四卷第八期)
“接照一种现存的美学和一种现存的伦理去行事要容易得多了。”(巴兰•巴尔特语)而非非必须忍受“发明”的痛苦,对于现实无用的痛苦,他们的痛苦来自于蓝马的首先“走向迷失”。迷失之后,他们想通过语言的“还原”来获得一种超越诗界的涵盖整个中国社会生活更广大的话语体系——非非式的话语帝国。但他们所作的是一场前途未卜的较量,他们或许最终将输给“传统力量”,即:人们从道德的优势上可以承认“今天”甚至“莽汉”但很难承认非非,因非非是反传统、反道德的,他们的“还原”长征也是虚无主义的长征,虽然何小竹曾自信地说:“非非诱人的近乎神话般的诗歌理想可以实现,为此我们对一切有关非非的误解和非议不想有太多的申辩。”可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语言理想是否真能实现?非非本身也进入了一个当代的“西西弗斯”神话。
“风格是一种行动性而非一种意图性的产物,它含有某种粗糙的东西,这是一个无目标的形式,它是一种个人的封闭的过程,决非进行选择和对文学进行反省的结果。风格仅仅是一种盲目的和固执的变化的结果,一个本能与世界交界处滋生的“亚语言”部份。风格其实是一种发生学现象,是一种性情的蜕变,风格位于艺术之外。”(罗兰•巴尔特语)而非非属于那种无风格的诗人,他们以自己的技巧方式探讨了从某种古典超然气质中引发的现代性愉悦,非非回到语言结构本身,而风格则在非非之外。
“马克思主义式写作和一种行为结合起来后,实际上立刻就变成了一种价值语言。例如工人阶级一词替换了“人民”一词。(罗兰•巴尔特语)蓝马的前文化(还原)理论已排斥了语言中这一故意的含混性、即排斥了价值语言,
“在现代诗中,名词被引向一种零状态,同时,其中充满着过去和未未的一切规定性。在这里,字词具有一种一般形式,它是一个“类”。诗的每一个字词因此就是一个无法预期的客体,一个潘多拉的魔盒,从中可以飞出语言潜在的一切可能性。现代诗把话语变成了字词的一些静止的聚集段。现代诗是一种客观的诗。在现代诗中,自然变成了一些由孤单的和令人无法忍受的客体组成的非连续体。(罗兰•巴尔特语)杨黎在他《十九个名词》或《十九个名词上与下》中实现了这种名词的“零”状态。这些陡然直立的互不相关的名词是一种令人不安的话语,这名词以“静”的聚集摧毁了一切伦理的意义并彻底吸收掉了风格。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教义必然导致一种规约性写作,这种写作应该十分清楚地指明一种应予表达的内容,却没有一种与该内容认同的形式。(巴兰•巴尔特语)非非通过他的“还原”把形式和内容结合在一起并反对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硬化症。
“这种中性的新写作是种毫不动心的写作,或者说一种纯洁的写作。(巴兰•巴尔特语)非非就像最早在《局外人》中运用这种透明语言的法国作家加缪一样,完成了一种“不在”的中性写作风格,语言的社会性或神化性在非非的诗中被消除了并获得一种理想风格——“不在”即在、空即实,无个性即个性的最高实现。非非就是以这种“不在”征服了写作中的意识形态,放弃了对一贯典雅或华丽风格的传统文学的依赖,达到了一种纯语言(或纯方程)的状态。诗歌(传统意义上的)被非非克服了,诗人的问题被重新追认了,诗失去了色彩,诗人成为一个诚实的人。在非非诗中,词语获得了自由,语言恢复了最初的新鲜(虽然这新鲜是没有意义的),非非变成了传达原语言的信息行为。一切祈祷式或命令式的语势(诗歌传统意义上的抒情话语权势)被一种直陈式写作所替代(或消解),被巴尔特式的“纯洁写作”所替代。诗歌达到了一个要求——形式就是文学责任最初和最后的要求。
一九九三年,非非诗人将非非语言引进市场经济发展轨道,提出中国首次语言大拍卖方案,接着,他们还评选中国最佳梦孩,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梦文,寻觅梦友。他们还身体力行创立中国第一个左派小区——即共产主义村。他们的非非之梦指向了共产主义之梦。但同年十月非非作为一个集体形象最终又被后现代(另一种权势?)所消解除,如杨黎所说“非非在坚决与温柔中解体了。”
文学走到了尽头,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迅速完成了它自身的—埸集体退出行动!拒绝行动!自杀行动!非非也以它“中性”般的“纯洁”姿态完成了这一最后的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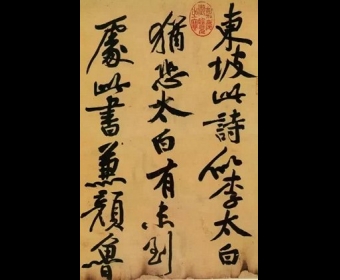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