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如上有关伦理陈述或伦理语言的悖论性看法,亦适用于宗教陈述或宗教语言。在“关于伦理学的讲演”中,维特根斯坦说:“我们并没有发现我们所谓的伦理说法和宗教说法的正确的逻辑分析。”[76]这实际上是说,伦理或宗教陈述,在根本上有别于科学命题。因为,按照维也纳学派的观点,哲学是对科学命题的逻辑分析;说没有发现对于伦理或宗教陈述的“正确的逻辑分析”,即表明伦理或宗教陈述不同于科学命题。伦理或宗教语言之不同于科学语言,亦可从另一方面看出。维特根斯坦说,“在伦理学和宗教语言中,我们似乎经常使用明喻。”[77]比如,将至善或上帝比作太阳或光照,等等。这样一来,伦理或宗教的语言,就常常是带有奇迹色彩的。但科学的语言,正如弗雷格所说,是干巴巴、无个性的东西。而且,以科学的眼光所看到的世界,是无奇迹可言的;或者不如说,所谓科学,即是用一种非奇迹的方式去看。
维特根斯坦认为伦理学是对绝对价值的探索以及绝对价值之不可描述所构成的悖论,表明此种意义上的伦理学探索在根本上是不可能的。维特根斯坦本人的探索,也没有为解开这一悖论提供任何有效的方法。因此,维特根斯坦对伦理学的最终看法,是将其视为人们冲撞语言界限的一种冲动,他说:“这种对语言的冲撞表明了伦理学的特征。”[78]毫无疑问,在维特根斯坦本人的思想框架内,“这种对语言的冲撞”必定是无果的。
下面我们讨论伦理学是否为科学的问题。有关这一问题,单从逻辑上讲,即有两种回答:伦理学是科学或伦理学不是科学。事实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在历史上均有其不同的支持者。
在本文的第二节中,我们已简要提及石里克对伦理学的看法,他认为伦理学应当是心理学的一部分。因此,在伦理学是否为科学的问题上,石里克当然认为是的,他在《伦理学问题》一书中说:“[……]即使伦理学是一门规范科学,它也不会因此就不再是一门关于事实的科学。”[79]石里克坚持认为作为科学的伦理学,一定与事实有关,他这样写道:“伦理学完全是与实际的东西打交道的。在我看来,这一点是确定伦理学任务的诸原理中最重要的一条原理。有些哲学家认为,伦理学的问题是最高尚、最崇高的问题,就因为这些问题与一般的现实无关,而是关乎纯粹的‘应当’的问题,他们的这种骄矜自大同我们是格格不入的。”[80]非常清楚,石里克此处的观点,对康德伦理学提出了挑战。
与石里克的观点不同,伦理学家摩尔认为伦理学不是科学。有研究者介绍说,“[……]穆尔(即摩尔——引者注)反对把伦理学理论的研究降低为一种自然科学或者一种社会学。伦理学是关于评价,关于鉴别行为好与坏的理论。科学事实能告诉我们实际上人们是怎样采取行动的,但却不能真正解决‘我应当做什么?’和‘什么是真正的善?’这样的问题。”[81]
非常明显,维特根斯坦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接近于摩尔,而与石里克相反对。维特根斯坦认为伦理学是对绝对价值的探索,因此与事实无关,他说:“对我来说,事实一点儿也不重要。”[82]而且,他还认为伦理学既然不可能是科学,因此,“它所说的东西对我们任何意义上的知识都没有增加任何新的内容。”[83]这即是说,伦理学陈述没有认知意义,也就不存在任何所谓的伦理学知识。维特根斯坦不认为伦理学是科学,因此,在他看来,伦理学也就不可能如石里克所认为的那样,是作为科学的心理学研究的一部分。有关维特根斯坦的反心理主义观点,在本文的第二节中,我们已简要提到过。在“关于伦理学的讲演”中,维特根斯坦通过对哈姆雷特一句话的分析,指出心灵意义上的好的与坏的属于“事实描述的范围”,因此而“并不是伦理意义上的好与坏的。”[84]这就再一次清楚地表明,维特根斯坦认为伦理学并非建基于心理学之上。
我们知道,维特根斯坦在总体上反对哲学模仿科学以建构某种理论的做法,因为在他看来,这一做法的实质是对概念与事实的混淆。从这一角度看,伦理学作为整体哲学之探讨的一部分,它不是科学,自然亦无需建构任何理论。维特根斯坦说:“如果只有通过某种理论才能解释伦理学的本质,那么伦理学的东西根本就是毫无价值的。”[85]伦理学的本质是对人生意义、绝对价值的探讨,在这样一种理解中,伦理学的东西没有认知意义,如此,建构某种所谓的伦理学理论,则必定是毫无价值的。美国当代哲学家诺奇克也说:“对人生的哲学沉思所展示的是一幅肖像,而非一种理论。”[86]
进一步说,伦理学之无需理论,根本上在于伦理学的归宿不像科学的归宿在于某种知识体系一样,它的归宿在于实践着的个体。维特根斯坦说:“关于伦理学,我们不需要为其构造一个理论,或有更多的陈述,‘所有我能做的只是作为一个个体前行,并且用第一人称说话。’”[87]这里的讨论涉及一个区别,即理论知识与实践之知,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根本不同的东西。陈嘉映对此有很清楚的阐述,他说:“理论之知以明述的、公共的知识系统为归宿,在这个系统中,各个道理通过互相可推导的关系组织起来。近代科学是这类公共知识系统的样板。与理论知识不同,实践之知的归宿不在一个知识系统,而在每一个行动者。”[88]
伦理学之为实践之知,这是否意味着,伦理学有指导实践的责任呢?如果有,它将如何指导?如果没有,那是否又意味着,伦理学是无用的?维特根斯坦说:“伦理学的东西是不能被讲授的。”[89]这就是说,有关人生意义、绝对价值的东西,是不可教的;而对于不可教的东西,亦即意味着是不可学的。这样一来,伦理学就不仅没有指导实践的责任,而且事实上即使想指导也是不可能的。
古往今来的许多哲学家,对此都持同样的观点。叔本华说:“伦理学能够重新培养一个硬心肠的人么,使他变成有同情心,因而成为公正的和仁慈的人?当然不能。”[90]陈嘉映也说:“指望伦理学来指导伦理生活,指望‘道德哲学’来提高‘道德水平’,这些都是错误的想法,因为‘理论’做不到这一点而责备它无能则是错置的责备。”[91]
石里克则更加直截了当地说:“伦理学本身除了真理而外并无其他目的。”[92]此外,在石里克看来,伦理学不仅不能而且也不应该介入实践,他说:“对一个伦理学家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从伦理学家变成道德家,从研究者变成说教者。”[93]而这样做的后果,则必定是将严肃的学术研究,变成了一己之私见的贩卖。就笔者所见,石里克的这一警告,直到今天仍十分重要。我们看到,在今天中国的思想界,一些原本可能并不一定是伦理学家但曾是学者的人,在功成名就之后,放弃了严肃的学术研究,热衷于在公共领域贩卖某种自以为绝对正确的道德观点,由此而变成了一个狂热的道德说教者。但这样做的后果,无论是对学术、还是对当代中国的道德状况而言,都不可能做出任何有益的改进,反而有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对青年学者和公众造成可怕的误导。我这样说,并非是对言论自由权的反对,而只不过是想表明,学者最重要的工作应当在学术领域进行,而不是时时以某种道德正确的姿态冒充先知。
是与应当的关系,是伦理学的核心问题。在以上的考察中,我们已经看到,维特根斯坦所理解的伦理学,与事实或如其所“是”的东西无关,或者说,真正意义上的伦理学不在世界之内。那么,维特根斯坦又如何理解应当/应该呢?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认为,前后期维特根斯坦对此有不同的理解。我们先来看他在《逻辑哲学论》中的一段话,即第6.422节:
在建立一个具有“你应当……”形式的伦理学规律时人们首先会想到:如果我不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但是,显然,伦理学与通常意义上的惩罚和奖赏没有任何关系。因此,这个有关行动的后果的问题必然是不重要的。——至少这样的后果不应该是发生于世界中的事情。因为在这种提问方式中的确含有某种正确的成分。尽管必然存在着某种伦理学的奖赏和伦理学的惩罚,但是它们必然是存在于行动本身之中的。
(而且如下之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奖赏必是某种令人舒服的东西,而惩罚则必是某种令人不舒服的东西。)[94]
在传统的伦理学中,有两大相互竞争的伦理学理论,即义务论和功效论。义务论更关注一个人做事的动机,并认为只有那些没有功利考量的行为,才具有道德意义。康德的伦理学,常被视为义务论的代表。以此观点来看,陈光标为出名或炫富而所做的所有“慈善”行为,哪怕可能惠及了一小部分弱势群体,但仍没有任何道德意义,无所谓善与不善。与义务论相反,功效论更看重某种行为的结果,认为只要造成了好的结果,那么此种行为就是善的。边沁和密尔,常被视为功效论的代表人物。而以功效论的观点看,同样以陈光标为例,人们认为只要陈光标是真拿钱给弱势群体,无论他的动机如何,他的行为就是善的、他所做的就是善事。从以上的理论背景出发,我们即可清楚地看到,维特根斯坦在上引段落之中,更偏向于某种义务论的主张,也就是说,前期维特根斯坦的伦理学观点,与康德更为接近。因此,维特根斯坦明确指出,当我们在谈论“应当”时,与其可能造成的后果没有关系,与某种令人舒服的奖赏或某种令人不舒服的惩罚也没有关系。简而言之,伦理学是某种在世界之外的、超验的东西。
如我们以上所引用和分析的,前期维特根斯坦对“应当”的看法,明显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解。在这样一种理解中,是与应当的关系是截然两分的,因此,当我们在谈及“应当”时,就与任何意义上的“是”或事实无关。但对于这样一种理解,随着维特根斯坦本人哲学观念的转变,他越来越持一种反对的立场。有关这一点,我们能在他1930年对“应该”的谈论中清楚地看到,他说:“‘应该’是什么意思?一个小孩应该做某某事意味着:如果他没有做这件事,那么某些不愉快的事将会发生。奖励和惩罚。关于这个问题,重要的是,其他的人被驱使去做某事。只有当存在着某种东西,它能给予支持和约束力——一种惩罚和奖励的力量时,‘应该’才是有意义的。应该本身则是无意义的。”[95]
与在《逻辑哲学论》中对同一问题的讨论相比较,1930年的维特根斯坦,对其前期思想即一种绝对义务论的观点,持一种尖锐的批判立场。众多周知,在对语言的看法上,后期维特根斯坦倡导,我们对某一语词意义的考察,应从其形而上学的用法中解放出来,回到日常语言的使用中来。从这一角度看,前后期维特根斯坦对应当/应该问题的不同理解,其实即是他前后期不同哲学观点的一种应用而已。在具体的分析中,后期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对“应该”这一概念的理解,应更多从其日常使用出发,来寻求一种常识的理解。在一种常识的理解中,“应该”的观念与具体的奖励和惩罚有关,而不再是某种形而上学的东西。由此,维特根斯坦说,“应该本身”是无意义的。
从一种更偏向于后期维特根斯坦、即带有更多经验色彩的角度出发,有论者指出,“我们的社会正处于这种恶性循环之中:一部分人违反大体上公正的规范但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或惩罚,于是更多的人争相效仿,造成规模越来越大的恶性循环而不得休止。”[96]这即是说,如果没有或缺乏一种制度上的约束或惩罚机制,那么就无异于“鼓励”社会成员竞相比坏,如此,则整个社会陷入罪恶的深渊而无法自拔。这就表明,一种正义的制度即某种惩罚机制的存在,对于一个良善社会的形成,是不可或缺的。毕竟,人既可能是天使,亦有可能是魔鬼。从这一角度看,后期维特根斯坦对应当/应该的理解,虽少了某种他前期思想中所具有的崇高之感,但其对人性的理解无疑更为成熟。
回顾维特根斯坦对是与应当这一问题的看法,我们大致可以说,在前期维特根斯坦那里,他认为是与应当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是截然两分的;是与应当,分属世界之内与世界之外。而在其后期的理解中,维特根斯坦放弃了形而上学这一维度,认为在是与应当之间并无清楚的界线;指明在某些情况下,二者之间有所纠缠,但又不能简单混同。在是与应当的问题上,有学者从实践的角度出发,认为二者是可以融合的,比如陈嘉映说:“有德之人融合了是与应当。”[97]这即是说,在“榜样”的身上,实然与应然融合无间。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维特根斯坦对石里克伦理学的评论。在以上的讨论中,我们已或多或少谈到,在对伦理学的理解上,维特根斯坦与石里克存在若干根本性的差异。比如石里克认为伦理学是科学、以心理学的研究为基础,并且无法摆脱与事实的关系。但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他认为伦理学是对生活的意义、绝对价值等问题的探讨,因此不可能是科学,也就与事实无关。
在这样一些原则性的分歧之外,1930年12月17日,维特根斯坦在诺伊瓦尔德克的“家”中,对石里克的伦理学进行了专门的评论。在评论中,维特根斯坦指出,关于“善的本质”,石里克认为有这样两种看法,一是“善之为善是因为它是神所需的”[98],二是“神需要善是因为它是善。”[99]在这两种看法中,石里克认为前一种解释是浅薄的,而后一种则较为深刻。但维特根斯坦对此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前者深刻而后者浅薄。理由在于,前一种解释清楚地表明“善的本质与事实没有任何关系”[100],因此“神”即为解释的终点;但后一种解释则不然,它似乎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探究来弄清善是什么——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这样一种思路,不过是一般理性主义者的浅薄之见。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维特根斯坦在对石里克伦理学的评论中,其所涉及的核心问题,仍是如何理解伦理学与科学或事实的关系,或者不如说,即如何理解“伦理学是什么”这一最具根本性的问题。
注释:
[1]黄敏:《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文本疏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530页。
[2][90][德]叔本华:《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任立、孟庆时译,商务印书馆,1996,第139、278页。
[3][4][英]西蒙·布莱克本:《我们时代的伦理学》,梁曼莉译,译林出版社,2009,第73、71页。
[5]周濂:《正义的可能》,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第253页。
[6][7][10][11][13][14][15][16][18][19][20][21][22][23][24][26][27][32][33][35][36][39][40][41][43][45][49][51][52][53][54][55][57][62][63][64][65][奥]维特根斯坦:《战时笔记(1914-1917)》,韩林合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18、129、115—116、116、117、118、117、122、123、123、124、124、125、125、125、125、128、127、127、128、130、126、126、127、127、127、122、122、138、139、139、141、141、126、126、126、126页。
[8][38][88][91][97]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行之于途而应于心》,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第197、5、147、167、252页。
[9][34][42][44][47][48][56][71][94][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韩林合译,商务印书馆,2013,第117、93、93、93、117、117、114、116、116—117页。
[12][86][美]罗伯特·诺奇克:《被检验的人生》,姚大志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第80、2页。
[17]关于维特根斯坦对死亡问题的讨论,参见李文倩:《维特根斯坦与自杀问题》,张庆熊、徐以骅主编:《基督教学术(第十二辑)》,上海三联书店,2015,第143—147页。
[25]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对金钱本身持有任何意义上的偏见,更不意味着我们认同某种将金钱视为所有罪恶之源的激进观念。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金钱是对那些为社会做出贡献之人的奖赏,也是他们所应得的。
[28][37][46][61]韩林合:《<逻辑哲学论>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第659、646、703、30页。
[29]关于“物自身”的系统研究,参见韩水法:《康德物自身学说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
[30][80][92][93]石里克:《伦理学的目的是什么?》,陈启伟译,洪谦校,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册)》,商务印书馆,1993,第457、452、439、439页。
[31][奥地利]奥托·魏宁格:《性与性格》,肖聿译,译林出版社,2011,第159页。
[50]参见甘绍平:《意志自由与神经科学的挑战》,《哲学研究》2013年第8期,第84-94页。该文作者不认同所谓自由意志不存在的观点,并针对神经科学提出的挑战,为自由意志做了辩护。
[58]韩林合编:《洪谦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第367页。
[59]这一研究趋势,亦逐步波及了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有关罗尔斯的《正义论》在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讨论情况,可参见李文倩:《政治哲学与当下思想界》,《读书》2013年第10期,第30—40页。
[60]不限于《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两书。
[66][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韩林合译,商务印书馆,2013,第115—116页。本文为讨论问题的方便,在引文的各小段之前,自行添加了编号。
[67][69][70][72][74][75][76][77][83][84][英]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论伦理学与哲学》,江怡译,张敦敏校,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第3、2、8、4、4—5、8、8、7、8、3—4页。
[68]维特根斯坦说,“善好在事实的空间之外。”参见[英]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读本》,陈嘉映编译,新世界出版社,2010,第274页。
[73]皮尔斯指出,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宗教、伦理和美学话语,“它们是无意义的,因为它们缺少事实的意义。”[英]大卫·皮尔斯:《维特根斯坦》,王成兵、吴绍金译,昆仑出版社,1999,第14页。
[78][79][82][85][87][89][95][98][99][100][奥]维特根斯坦著、[奥]弗里德里希·魏斯曼记录:《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徐为民、孙善春译,商务印书馆,2015,第73、106、108、107、107、107、109、105、105、105页。
[81][美]路德·宾克莱:《二十世纪伦理学》,孙彤、孙楠桦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第9页。
[96]慈继伟:《正义的两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修订本前言”,第7页。
本文发表于崔延强、甘绍平主编:《应用伦理研究》2017年第1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09~23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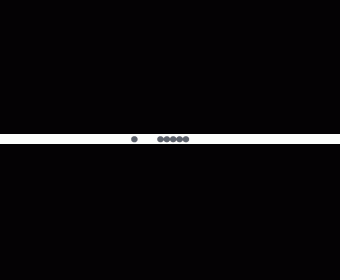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