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是为了每一个人》是一本极为通俗易懂的小书。根本上,这是一本用人人皆懂的语言写的一本女权主义宣传小册子。这本小书力图用直捷明了的方式把女权主义的、特别是激进女权主义的主要思想勾画出来,全面地阐释女权主义理论中最激进的思想的基本论点。
把这本小书翻译成中文,因为我希望能介绍女权主义中最激进的声音,让读者自己来判断,女权主义理论到底在哪些方面有合理性,在哪些方面有乌托邦的想象性。由于“女权主义”这个词在中国的政治社会语境中的负面意义,很多人提起女权主义而立刻面露拒绝之色,好像女权主义是洪水猛兽,让人恐惧和厌恶。[1]我完全理解这种情感性的反应,虽然我不得不说这种反应本身是因为对女权主义缺乏了解。很多反对或厌恶女权主义的人,他们几乎没有读过任何女权主义的书或关于女权主义的书。他们“本能”地反对女权主义。这种“本能”,我只能善意地提醒有自我反思能力的读者,是一种社会和文化塑造的反应,并非任何人的生理本能。研究与事实都证明,我们对很多政治文化议题的“本能”反应,是我们所受到的教育和塑造的结果。比如,在疯狂革命的时代,听到“马列主义理论”,很多人会尊敬与崇拜,但是今天马列主义理论,只是众多理论中的一种,那种似乎本能的尊敬已消失。对女权主义的恐惧和厌恶,在中国的语境里,除了中国的两千多年的歧视女性文化的影响外――中国文化是一个患有强烈的“厌女症”(misogyny) 的文化,――还有对1949年以来的有组织的女性解放的政治宣传的反感和反动。这种对某种官方意识形态的反感,导致很多人对自己以女性解放为标准的女权主义的恐惧和厌恶。
贝尔·胡克斯是美国最著名的女权主义理论家之一。她的思想对美国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有重要的贡献。她同时也是一个卓有影响的文化批评家,作家和教育家。她著作等身,以对种族、性别、阶级和文化的关系分析著名。她不予余力地批判她所定义的美国“白种至上的资本主义父权文化”(1989年在其影响深远的著作《顶嘴:思考女权主义,思考黑人》中所提出),以独特的视角看待美国社会和文化,洞察美国社会和文化的本质,对认识美国社会和文化有深刻的影响。她也是二十世纪末美国跨越学院和公众两界都非常成功的学院-公众知识分子之一。她对美国社会种族、阶级的分析至今还是学院讨论的主要议题。她的小说、诗歌和其他以通俗的语言写的女权主义理论也广泛地被非学院读者阅读。
贝尔·胡克斯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在威斯康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又在加州大学圣·克卢斯分校获得博士学位。多年来她在多所大学执教,先后在南加州大学、欧柏林学院、耶鲁大学、纽约市立大学作教授,是纽约市立大学“杰出英文教授”。从2004年起她回到家乡,美国南部的肯塔基州的一个私立自由文理学院,博睿雅学院 (Berea College),作驻校作家,同时兼课,开始了她生命中的新的历程。
贝尔·胡克斯并不是她的真正的名字。她的真正的名字是葛劳瑞娅·晋·沃特金。她以她太祖母的名字贝尔·胡克斯为笔名,并且在写名字时不按通常的规则大写名字的头第一个字母,目的之一是表明她与先辈女性的本质联系,之二是“重要的是我的书的内容,而不是谁写的书”。以小写名字而表明自我的不重要,她的这种与主流文化抗拒的姿态受到很多人的尊敬,也遭到很多质疑。
到2007年,她已经出版了三十多本著作。主要的著作有《我不是个女人吗?:黑人女性与女权主义》(1981);《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1984);《渴望:种族、性别和文化政治》(1990);《教导逾越边界:教育作为自由的实践》(1994);《胶片与真实:电影中的种族、性和阶级》(1996);《女权主义是为了每一个人:激情的政治》(2000);《我们真酷:黑人男性与男性气质》(2004);《灵魂的姐妹:女性、友谊和实现的满足》(2005);以及《见证》(2006)。值得注意的是,在贝尔·胡克斯的著作中,有三本特地给孩子们写的书。她非常关注为青少年和一般读者写作,虽然她可以写非常理论化的学术著作,但是她也坚持写为大众阅读的理论书籍。她自觉地采取为非学院读者写作的立场,挑战美国女权主义主要发生在学院里的现实。她认为学院女权主义是女权主义的自杀之路。真正的女权主义必须加入改变社会现实的努力。她自己就是改变和参与现实的女权主义者之一。除此之外,她还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演讲者,在美国各地演讲,宣传女权主义思想。她同时还参与了很多纪录片的拍摄,在纪录片中分析美国社会和文化现象。
她的书和电影获得过很多文学奖励和提名。其中,《渴望:种族、性别和文化政治》获得美国图书奖(1991);《我不是个女人吗?: 黑人女性与女权主义》被1992年的《出版家周刊》评为“上二十年对美国最富有影响的女性写的二十本书之一”。她还被美国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杂志之一《大西洋月刊》评为“我们国家的主要公众知识分子之一。”
《女权主义是为了每一个人:激情的政治》这本书语言通俗,是给对女权主义理论所知不多的一般读者写的介绍性读物。书的主要理论因此都是框架性的,勾勒了女权主义理论的整体关注议题,特别是勾勒了最受争议的激进女权主义理论的主要立场和论点。书虽然不厚,内容却非常丰厚,美国女权主义关注的主要问题都面面俱到地涉及和讨论了,并有自己的建议和结论。这本书回答的一个总体问题是“什么是女权主义?”“怎样实践女权主义?”回答的方式是把女权主义理论分成具体的议题,以简洁的但不是过于简化的方式对每个议题进行考察,讨论。胡克斯认为女权主义运动的消沉很大原因在于女权主义的学院化,因此,她写了这样一本非学院写作的女权主义宣言。
由于她的激进的立场和不拒不挠的声音,她也倍受争议,遭到很多批评。她是美国最受争议的知识分子之一。下文中我将详细地介绍胡克斯的生平和著作,同时讨论她的理论的意义。
谁是贝尔·胡克斯?
葛劳瑞娅·晋·沃特金于1952年9月25日在南方肯塔基州一个乡村小镇里出生。她的童年和家庭对她成长为一个女权主义者有很强烈的影响。她是七个孩子之一:六个姐妹,一个弟弟。她的父亲是一个清洁工,母亲在白人家里当女佣。家中虽然女性占绝大多数,但是男性占绝对统治地位。这样的生活环境对她的性别意识觉醒有很大的作用。她的弟弟有自己的房间,有很多小葛劳瑞娅和姐妹们没有的特权和权力。在她的自传体小说《黑骨头:少女时代的回忆》(1996)里,她描写家里的生活,描述她成长的过程,描写那个黑白隔绝的社会时代。母亲忍辱负重,虽然母亲是家里的灵魂,但是父亲是家里的一家之长,统治一切。葛劳瑞娅的外祖母也住得不远,外祖母是一个坚毅的人。所以父亲常常在家里宣布自己决不会让自己的老婆像她的父亲那样让自己的老婆主事,他要好好地管教老婆。他有意无意地跟自己妻子娘家较量,担心自己失去权力。目睹家里的性别权力关系,在成长的时代,在她知道女权主义这个词之前,她就体验到了并质疑传统的性别权力的模式。成年后她这样回忆,“我不记得第一次听到女权主义这个词或理解这个词是什么时候了。我清楚地知道,就是在我的少年时代我就开始对性别角色感到怀疑,我开始看到被‘制造’成一个女性的经验与被‘制造’成男性的经验是不同的。也许我有极强的这种意识是因为我的弟弟是我的长期的玩伴。我用‘制造’这个词,因为在我们家里,性别角色非常明显地是构建的,那就是几乎人人都同意,很小的孩子几乎都是相似的,唯一不同的是身体。几乎人人都经历过用社会构建的不同把我们制造成小女孩小男孩的过程,小男人小女人的过程。”[2]
除了家庭之外,葛劳瑞娅生活的黑白隔绝的社会对她的女权主义思想也有决定性的影响。她出生的小镇那个时候还是黑白分隔的,她生活在一个全是黑人的社区里。白人只是一个标志着危险概念和符号,并不出现在街上,到了中小学的时代,她上的是全黑人学校。一群尽心尽力的老师们,大部分都是单身的黑人女性们,帮助塑造了她对有色人种的自我的认识。小葛劳瑞娅非常聪明,深受老师喜爱。一个老师在她上中学的时候就对她说,“你很有天分,你被放到这个地球上,是要用你的知识做点什么的。”这种对她的信心给了葛劳瑞娅很大的激励。由于黑白隔绝的生活环境,种族的概念并不强烈。这种种族概念的缺失到了高中的时候有了巨大的改变。六十年代末期,肯塔基州要求所有的学校都黑白混合。她离开小镇,到一个黑白混合的学校。对她来说,这是一个悲剧性的经验。与白人高中生们混在一起,对自己的身份感到格外敏感。因为是黑人,老师们不特别关注她的精神和智力成长。她感到丧失的痛苦,感到作为一个黑人的痛苦。多年后她继续回忆,“我对那段时间记得最深的是一种丧失的感觉。把记忆留在身后、把我们的学校留在身后、把我们热爱和珍惜的地方留在身后、把那给了我们荣誉的地方留在身后,是极为痛苦的。那是我成长所经历的第一个最大的悲剧。”
很幼小的时候,她就发现了诗歌。她自己回忆,这种对诗歌的热爱来自于童年在教堂里的体验。葛劳瑞娅生活的南方,宗教气氛非常浓厚。她从小就跟父母上教堂。在教堂里,她用韵律和诗歌的形式背诵《圣经》,唱圣歌。到十岁的时候,她已经开始写诗了,她朗诵诗歌的能力在小镇上几乎人人皆知。她这样描述诗歌在她早期生活中的作用。“在我们这个劳动阶级的家庭里,诗歌是绝对受到尊重的一种文学表达。当停电的夜晚,当暴雨袭击的时刻,我们都坐在点燃着蜡烛的起居室里,进行才华表演。我背诵诗歌,华兹华斯、詹姆斯·维尔顿,兰斯顿·休斯,伊丽莎白·布朗宁,爱米丽·狄肯森,关德琳·布鲁克斯。白人作家的作品在学校和走门串户的推销员卖给我们的家里的书架上的伟大作品选集里到处都是,黑人的诗歌则需要找才能找到。”对诗歌的热爱给了她一个声音,也给了她对语言的敏感。贝尔·胡克斯的语言简洁、直捷、美丽、富有表达力。
她写诗,发表诗歌,同时写分析文章。上大学之后,在发表她的第一本小诗集《我从不哭泣》的时候,她决定采用一个笔名。一个原因是因为本镇也有一个女性名字与她重名,她不想引起误解。另一个是她的个性使她与众不同。很小的时候她喜欢说话带脏字,喜欢骂人。一次她在街头的小店里买泡泡糖。她跟一个大人顶嘴。“我还记得那种惊讶的表情。一个嘲笑的声音告诉我,我一定与贝尔·胡克斯有亲戚关系,贝尔·胡克斯是一个伶牙俐齿的女人,一个心直口快的女人,一个不怕跟别人顶嘴的女人。”这个女人是葛劳瑞娅的母系的太祖母。在一篇谈及自己笔名的文章《给葛劳瑞娅,她是谁?:关于用假名字》里,她这样写道,“葛劳瑞娅本是要成为一个甜蜜的南方女孩子,安静,服从,招人喜欢。她不该有我母亲家中的女人的野性的特点。”但是葛劳瑞娅决定继承贝尔·胡克斯的拒绝服从、意志顽强、勇敢无畏的传统。以笔名“肯定我与我的敢说敢做的女性先辈的联系。”从此,葛劳瑞娅自觉地成为了贝尔·胡克斯。“我用笔名的多种原因之一也是为了构建一个作家身份。这个作家将挑战和压倒要把我从说话引向沉默的种种冲动。”要发出声音,要说话,要顶嘴。这就是贝尔·胡克斯。
“顶嘴”:不屈不挠的声音
贝尔·胡克斯的所有著作都有这种“顶嘴”的特征:论战性的、挑战性的、激发起火花四溅的争论的立场和观点。但是当她离开南方的小镇第一次乘飞机飞往西部的加州,到斯坦福大学上学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害羞的不到十七岁的南方黑人女孩子。她获得了奖学金到这个白人占主导的常春藤学校上学。在这之前,她没有乘过电梯,没有乘过城市里的公共汽车,没有乘过飞机。
离开肯塔基熟悉而习惯的黑人社区来到一个学术圣地,贝尔·胡克斯极为激动,她热切积极地参与了当时席卷了美国校园的女权主义运动。她上课,开会,参加全是女性的晚会,但是,就是在这些活动中,女权主义运动的弱点和不足也暴露了出来。“就在我选的第一批妇女研究的的课程中,就是悌丽·奥尔森教授的课程之一,我开始注意到讨论中的关于黑人妇女材料的完全缺失,我感到与那些庆祝‘姐妹情谊’的巨大的白人女性群体的隔绝和陌生。”[3] 这种最初的失望变成了追求知识的努力,变成了贝尔·胡克斯对女权主义理论的主要贡献:把种族主义问题带进女权主义运动思想讨论之中。始终如一地批判种族主义。在女权主义运动中,她以“顶嘴”的方式,抵抗女权主义运动中的种族主义,以自己的独特的声音成为女权主义思考的声音之一。
这就是她写作她的第一本书《我不是一个女人吗?》的动机。那时她19岁,与男朋友住在一起。她在斯坦福大学上学,同时也在电话局里工作。她积极地参与女权主义运动,选学很多与女性有关的课程。在课堂上当学生和教授们讨论女性的问题的时候,她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和社会现实与白人为主的女权主义理论谈论的现实有很多不同之处。她试图找到谈论自己生活现实的理论,但是,讨论分析黑人女性生活现实的书少之又少。她的男朋友,一个黑人知识分子,鼓励她写出自己的书来。她开始动手写这本书。六年里这本书写过好几个草稿,她写来写去,并不是写作困难,而是找到自己的声音,找到自己可以跟女权主义理论“顶嘴”的方式,找到自己不屈不挠的声音。这是一本越写越短的书。贝尔·胡克斯后来回忆到,“最初的稿子非常长,十分重复。以批判性的眼光看,我看到我要与不同的读者说话――黑人男性,白人女性,白人男性等等。我的写出来的文字是在解释,在讨好,在宽慰。我的文字蕴涵着一种对说话的恐惧,这种恐惧好像是在等级制度里地位低的人对地位高的人的说话的方式。”最后,贝尔·胡克斯终于找到了自己说话的方式,“那些我直接与黑人女性说话的段落包含着我觉得最真实的我的声音。就是在这些段落里我的声音大胆,勇敢。”也就是在这样的声音里,葛劳瑞娅最终成为了贝尔·胡克斯。《我不是个女人吗?》这个题目是从十九世纪黑人女权主义者苏哲娜·楚思的一篇演讲中借用过来的。这个题目本身标志着胡克斯与黑人女权主义历史的关系。在这本书里,胡克斯向历史和现实中的、女权主义运动和黑人解放运动中所持的黑人女性的位置的观点挑战。她特别指出在黑人解放运动中,黑人男性领导们赤裸裸的对待女性的性别主义态度和立场。她同时也指出,这种性别主义的态度和立场与黑奴制度中黑人把美国父权制思想价值内在化有紧密的联系。她还批评某些社会学家的对黑人社会家庭文化的分析,特别是美国社会学家,纽约州参议员丹尼尔·帕特力克·莫伊尼罕的论点。莫伊尼罕曾在1965年提出了一个报告,分析黑人家庭状态《黑人家庭》,提出黑人男性由于经济机会的限制,心理上已经被损伤,导致很多黑人家庭是母系统治的状态。胡克斯反驳说,这个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母系统治”这个词中所含的权力,黑人女性,不管这些女性是不是家里的经济支柱,从来没有拥有过,因为黑人男性并不把经济能力看成是自己的男性气质的表现。在批评黑人男性和白人男性的同时,胡克斯也分析美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妇女权利运动中白人是怎样有意地把黑人女性关在这个运动之外的。她用历史事实揭示说,尽管有白人把黑人女性关在门外,黑人女权主义者们对这个运动还是做了杰出的贡献。同时她也批评当代的女权主义运动中的白人女性的傲慢。她指出,这些白人女性“邀请”黑人女性加入女权主义斗争,显示出她们认为女性这个词指的只是白人女性,其他种族的女性, 对白人女性来说,只是“他者”,好像不是人,不是女人。在结论里,贝尔·胡克斯激昂地号召黑人女性参与当代女权主义运动:“我们支持女权主义意识形态的黑人女性是先锋。我们在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姐妹开拓道路。”
这本书开始的时候很不容易找到出版社。有些出版社出版讨论种族议题的书。有些出版社出版反对性别主义的书,但是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冒险出版一本把两个议题放在一起讨论的书。最后,贝尔·胡克斯被介绍给南端出版社,这个出版社也是出版了这本《女权主义是为了每一个人》的出版社。1981年书一出版就成为讨论女权主义与种族主义的经典。十一年之后,出版家周刊还把《我不是一个女人吗?》列为“二十年内美国最有影响的女性写的书籍。”可是,贝尔·胡克斯的“顶嘴”当时招来的却是批判和抵触。特别是学院内,很多学院知识分子,特别是白人女性知识分子对贝尔·胡克斯强调女权主义运动中的种族主义不满,因为贝尔·胡克斯批判的就是她们的盲目和偏见。与此同时,一般读者,特别是黑人女性读者,对这本书却抱有很大热情,认为终于有人代表自己说话了。很多黑人女性给贝尔·胡克斯写信,感谢她的书改变了自己的生活。直到今天,这本书还在不停地再版。
这本书的出版使贝尔·胡克斯的名字成为女权主义争论中的一个提起来反应就激烈的名字。她的书往往引起很多争论。她的声音使很多人觉得不中听,很刺耳,因为书的声音是那个顶嘴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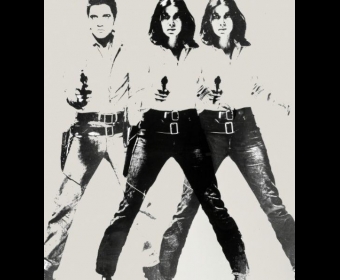

![作家专访丨熊焱: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视频]](/uploads/allimg/250606/0T124O47-0-lp.png)
![Liu Zongxuan 柳宗宣 | OUR BODIES AS RUINS 身体的遗址[视频]](/uploads/allimg/200606/1-200606111H3436-lp.jpg)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