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开腔的“说书人”
至此,朱朱的《清河县》两部曲无论在内容还是结构上,都已经相当完整自足。令人惊喜的是,八年后的朱朱又完成了《清河县》系列的第三部诗作,使整个作品的深度与复杂程度又向前推进一步。其中第一首诗的开篇这样写道:
一场暴雨移远了茶肆,
却也有那么多伞打着趔趄
翻过古桥头。雾岚林立于檐瓦,
积水没过了膝盖,街心,
青石板滑腻如群蛇。
这一天,说书人就要说到
你的死——开腔之前,
他一派监斩官的威仪,手中
轻摇的折扇,只待时辰一到,
就会变成掷落地面的火签。
“移远”,一个颇为醒目和打眼的动词,恰到好处地暗示了朱朱对镜头的调控。与《清河县Ⅰ》开场对卖梨小贩那“断了头的激情”的特写不一样,也与《清河县II》聚焦于潘金莲的舞台不同,在此处,既是暴雨造成视觉上的阻隔,使茶肆在雨中因朦胧而显得偏远,更是朱朱有意调节焦距,增加景深,为的是巧妙地完成转场,完成叙述层次的过渡和转换。与之相对应也相附和,“说书人”的出现,迅速地阻隔并打破上一部诗作中——由“我”的独白所引发的共鸣体验,造成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所说的“间离效果”。在更大的视角内,激情消弭,“我”不过是一个舞台上的角色、一个书中的人物而已。所谓“间离效果”,就是恢复观众对角色、读者对人物的距离感。得益于中国戏剧的启发,布莱希特坚持认为:在表演中,要“防止观众与剧中人物在感情上完全融合为一”,因为“接受或拒绝剧中的观点或情节应该是在观众的意识范围内进行,而不应是在沿袭至今的观众的下意识范围达到”[20]。这就是说,表演应为观众的思考与判断留有空间。朱朱将“说书人”安插在诗中,既是引入《清河县》组诗的前文本,也是引入写作主体、文本与读者间的复杂关系,正是在这个维度上,《清河县Ⅲ》才有其存在的必要和意义。
据格非考证,《金瓶梅》的故事虽然由《水浒传》的“武十回”敷衍而来,但将故事发生的地点由阳谷县改回到了清河县,还将原属于阳谷县的紫石街移至清河县中,在地理设置上多有悖谬,是一个经过虚构的“既是又非”的结构。《金瓶梅》的作者沿用此地名,既有叙事的需要,也有“俟河之清”这样的隐喻性暗示——与小说中纵情声色、人伦败亡的污浊构成一定意义上的反讽。[21]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认为,互文复写不是为了固化意义、限制理解,而是为了提供意义的更多可能性[22]160。朱朱直接以这个空间化的地理坐标作为诗题,并将发生在此处的故事搬上亦真亦幻的“舞台”,或许也隐藏着这样的暗示:如何能看得清混沌的历史呢?从对故事的处理方式来说,《清河县Ⅰ》是将不同视角的影像碎片重新组接为新的故事,具有一种电影般的视觉效果。在这里,朱朱所观看的《金瓶梅》电影同样是具有对话性的互文文本②。《清河县Ⅱ》则否定了《清河县Ⅰ》众目睽睽之下的潘金莲形象,更进一步地强化观看之谜局。与前两部诗作相比,《清河县Ⅲ》显得有些脱轨,但也因此具有超越性的价值。它不再以叙说或丰富故事、激荡文本间的意义为主要目标,转而关注故事的创作本身:不仅以“说书人”来提醒舞台的虚构性,提醒“列位看官”拉开与人物形象之间的距离,还以匿名之“我”在诗中置入了一个写作者的形象。事实上,这个形象又何尝不是曾经的说书人呢?
我的才能是阴性的?是的,
从一本书中刀戟蔽日的地平线
只捡拾起了一根晾衣杆,
穷我后半生要以另一本书
重现它立体主义的坠落。
在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看来,电影是“对单个形象和形象序列进行组合剪辑的一种产物”[23]25,“最具有可修正性”[23]26。立体主义的拼贴手法也与之类似,包含着解析与建构的过程,既富有秩序也充满创造力。“从一本书中刀戟蔽日的地平线/只捡拾起了一根晾衣杆”,似乎正对应着前两部诗作对历史故事的解构与重构,不管对所深入细部的表现多么精确,多么引人注目,也并非钩沉稽古,发微抉隐,而是注入了主观经验,充满刻意的引导。胡戈·弗里德里希(Hugo Friedrich)所言极是:现代诗人“不是作为私人化的人参与自己的构造物,而是作为进行诗歌创作的智慧、作为语言的操作者、作为艺术家来参与的,这样的艺术家在任意一个其自身已有意味的材料上验证着自己的改造力量”[8]3。借由“我”这个写作者的形象,朱朱也在诗中描述了这种尽情创造带来的书写快感——
墨在暝色中涨潮,窗纱
蘸取烛光勾画一个作者的身影——
狼毫笔蓄满了精液,以
雄性的自我分泌一个美人,
她已经情浓到浑身都是私处。
谁不曾体验过书写的自足
胜于现实中的搏击,谁就
无法操持这孤单的事业——
尘世是必经的但不是全部,
正如莲座之上,满眼多余的崇高。
对写作本身的注视,使这些诗行具有自述的意味。“成为他人”,以此脱离个体的躯壳,开始“第二人生”,以此参与平行世界,在面具之下保留抒情的可能。这正是朱朱所说的:“文学中的‘我’的使用即一种出自单方意愿的双向运动,在他者的面孔上激起一个属于我的涟漪。”[24]也是《清河县Ⅱ》中“我”幻化为潘金莲的叙述方式。在《清河县Ⅲ》中,诗人则化身为匿名的“说书人”、匿名的写作者,借此打量并道说书写的缘由、过程,以及弥散其间的火焰般自足的热情。仰仗语词的特殊创造力,诗人可以复活经验,再现形象,可以“让平地有了海,又干涸”,可以“亲手造就死亡”或者“煮沸悲剧的锅”(朱朱:《码头上》)。这就像马拉美所说的,诗歌的意义通过词语本身的内部照镜唤起,诗歌创作意味着极端地更新语言的原始创造行为[8]93。诗人既以语言的方式道说世界,更以语言的方式创造和发明世界。
五、修辞、历史与互文
朱朱深知语言魔术的魅力,他的诗的气质类似于庞德所说的“语词间的智慧之舞”[25],巧妙幻美,摇曳多姿。也很符合卡尔维诺对“精确”下的定义:作品构思明确;视觉形象清晰;词汇准确。其创作方式也与卡尔维诺相像,往往把幻想中的形象与语言思维中的意图统一起来,以视觉形象解决思维与语言不能解决的问题。[26]正如本雅明对电影意义作的剖析:“通过最强烈的机械手段,实现了现实中非机械的方面”[23]51,以此“建立人与机器间的平衡”[23]54。朱朱以数学般精密的思维组建诗歌的秩序,又以瞬间的、细致入微的视觉形象引起心灵的震颤和共鸣,从而达致理性与感性的平衡,充分释放汉语在隐喻层面上的能力。现代新诗乐于透视并深入事物的细部,以准确地揭示现代经验的复杂与含混为己任。只是视觉化汉语条分缕析的语言方式和词语的位移性能,也很容易导致词语流于语义的空转,陷入“词生词”的游戏局面。怀着对语言纯粹性的警惕与反拨之心,朱朱对写作本身的注视和打量最终落脚于语词的创造力量:
妄语在拔舌地狱的边沿,
就连乱云收后,阶前
点滴的雨也如磬板一声声
仍在历数我的修辞罪。
修辞虽然有助于将隐晦的经验细微地传达,有助于深入事物的内部,但词语的“纵欲过度”,也容易“导致语义超载”,“影响诗歌命名的有效兑现”[27]。“过度修辞的后果之一是将世界修辞化和文本化”[28],这并不意味着对世界的道说与创造更加丰沛、动人,反而意味着走向单调、贫瘠、狭窄和徒有其表。朱朱以视觉片段刻绘故事,虽有足够的惊颤效果,但也因为对历史维度多有回避,只剩下欲望和形象,当下和瞬间。从叙事的角度来说,故事内部的精妙构成是无限的,极尽修辞之能事的所得,大有可能只是一个封闭的语言游戏。因此,不同于前两部诗作热衷于构筑个体的精神剧场,执著于语言内部空间的开拓,《清河县Ⅲ》在虚构写作者的形象来打量写作本身的同时,也因为与文本拉开距离而获得一种新的时空维度。在朱朱将茶肆“移远”,将镜头转向远景时,诗歌也转向了更广阔的历史与现实语境。
在《清河县》之前,朱朱也有一些叙事诗从历史或文学文本中取材,比如叙说苏轼的《海岛》、叙说柳如是的《江南共和国》。但这些诗作大多聚焦个人的精神世界,意图以“纤微巧妙的词语”,以“展演”③的形式,重建“文明的七宝楼台”(朱朱:《江南共和国》),并无太大的历史视野。而在《清河县Ⅲ》中,“说书”“写作”制造了不同的时空段落,展演的部分丧失了直接性。命运反复,人物在纸面也在现实中穿梭,构成重重叠叠的镜像,读者可以在每一条街道找到王婆、潘金莲,也可以在其间找到自己。“向文字祈求/一把略长于人性的尺子吧,提灯/走进坏血统,而不是将毒液涂在纸页间。”(朱朱:《别院》)朱朱对个人精神世界的关注,逐渐拓展到了对人性的关注、对整个“尘世的奥秘”的关注;他对瞬间经验的展演,也逐渐偏移至对永恒性的沉思。
关于历史,赵汀阳的看法颇有道理。在他看来,历史是包含知识的叙事,另有在知识之外而且不能还原为知识的思想和精神;发现历史所蕴含的思想,关键在于为之建构贯穿历史的意义链和问题链,而不在于重演当时之心。[29]如何能企及历史的真相呢?像朱朱在诗中所写:“尘世那唯一的故事/从未被写就;他人也是/副本,述说着同样的不在场。”(朱朱:《码头上》)“互文性”赋予作者足够多想象的场域、修辞的空间,也同时“推翻了作者的权威”[22]161。历史题材的书写意义不在于求真,也不仅仅在于用文字重构其深邃迷人的内里,还在于与历史对话,在重生的镜像间一窥人性与自身。
多好的酬劳啊,经过一番深思,
除了人现在我什么都想冒充。
《清河县》的最后一首诗,是以瓦雷里和王小妮的诗句拼合而成,既暗含对生与死的思辨,与故事中人物的命运有关,也暗含对即将结束的写作本身与对自我的凝视。或许正如画布会暴露隐秘,词语中也隐藏着写作者的“自画像”。而此处创造性的互文,是朱朱对“清河县”故事的书写方式,也是语言向广阔历史空间与经验的多义性敞开的方式。《清河县》作为一首多视角、多声部、多层次的长诗,不仅对视觉想象与语词力量多有探索,还见证了朱朱在个人诗歌写作史上的突破。
注释:
① 程抱一认为,“木末芙蓉花”一句在汉字的排列上,具有“一种目睹一株树开花过程的印象”,正如刘长卿的“芳草闭闲门”(《寻南溪常山道人隐居》)一句,展现了一种“净化过程”。参阅程抱一:《中国诗画语言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14页。
② 克里斯蒂娃明确地将某一文本与此前文本乃至后文本之间的关系,即文本对话性称为“互文性”(in⁃tertextualite),并将语言及所有类型的“意义”实践,包括文学、艺术与影像,都纳入文本的历史。参阅茱莉娅·克里斯蒂娃:《主体·互文·精神分析——克里斯蒂娃复旦大学演讲集》,祝克懿、黄蓓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11页。
③ 胡续冬说得很有道理:朱朱的诗歌是非常标准的展演性诗歌,能把启示性的东西和展演性的东西糅到一个对阅读的状态有更直接的、更加全方位唤起的这样一种写作里去。参阅《“从不真的要一块土地”:当代江南诗歌的变迁朱朱讨论会实录》,《上海文化》,2018年第11期。
参考文献:
[1]叶维廉.中国诗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146.
[2] 葛兆光.汉字的魔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学札记[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59.
[3]敬文东.味,气象与诗[J].文艺争鸣,2021(1).
[4]敬文东.汉语与逻各斯[J].文艺争鸣,2019(3).
[5]敬文东.味与诗:兼论张枣[J].南方文坛,2018(5).
[6]马丁·杰伊.低垂之眼20世纪法国思想对视觉的贬损[M].孔锐才,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21.
[7]苏珊·桑塔格.论摄影[M].黄灿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8]胡戈·弗里德里希.现代诗歌的结构: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的抒情诗[M].李双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9] 帕特丽卡·劳伦斯.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M].万江波,韦晓保,陈荣枝,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546.
[10]李章斌,朱朱,刘立杆,等.落日、飞碟和时差:诗学对谈录[J].延河,2020(8).
[11]耿占春.观察者的幻象[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7.
[12]马贵.享乐、忍受抑或责任:当代诗歌中的身体伦理[J].江汉学术,2022(4).
[13]马小盐.《清河县》:朱朱所构筑的诗歌环型剧场[J].延河,2011(2).
[14]杉本博司.直到长出青苔[M].黄亚纪,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27.
[15]米歇尔·褔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20.
[16]伊塔洛·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M].张宓,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66.
[17]约翰·伯格.观看之道[M].戴行钺,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
[18]罗兰·巴特.明室·摄影札记[M].许绮玲,译.台北:台湾摄影工作室,1995:22-23.
[19]吴琼.视觉性与视觉文化:视觉文化研究的谱系[J].文艺研究,2006(1).
[20]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布莱希特论戏剧[M].丁扬忠,李健鸣,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191.
[21]格非.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2-5.
[22]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
[23]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王才勇,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24]朱朱,木朵.杜鹃的啼哭已经够久了:朱朱访谈录[J].诗探索,2004(Z2).
[25]伊兹拉·庞德.庞德诗选 比萨诗章[M].黄运特,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228.
[26]伊塔洛·卡尔维诺.卡尔维诺文集[M].吕同六,张洁,编.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367-381.
[27]颜炼军.“大国写作”或向往大是大非:以四个文本为例谈当代汉语长诗的写作困境[J].江汉学术,2015(2).
[28]吴晓东.后工业时代的全景式文化表征:评欧阳江河的《凤凰》[J].东吴学术,2013(3).
[29]赵汀阳.历史·山水·渔樵[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136,47.
(本文原刊于《江汉学术》2023年第1期“现当代诗学研究”名栏:第43-51页)





 在水一方 评论 夏至、敬文东:窥视者与说:好磅礴的文章
在水一方 评论 夏至、敬文东:窥视者与说:好磅礴的文章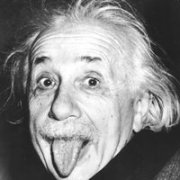 爱因斯坦的绵祆 评论 夏至、敬文东:窥视者与说:《清河县》三部曲是朱朱洞悉视觉复杂性与神秘性的经典之作,既呈现了传统叙事没落后讲故事的新可能,也打开了关于他者、关于作者与文本及阅读者间的,许多值得玩味细思的空间。
爱因斯坦的绵祆 评论 夏至、敬文东:窥视者与说:《清河县》三部曲是朱朱洞悉视觉复杂性与神秘性的经典之作,既呈现了传统叙事没落后讲故事的新可能,也打开了关于他者、关于作者与文本及阅读者间的,许多值得玩味细思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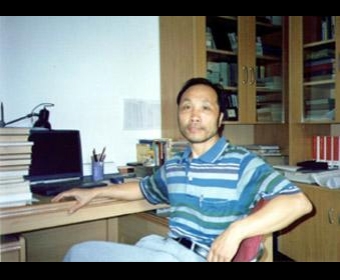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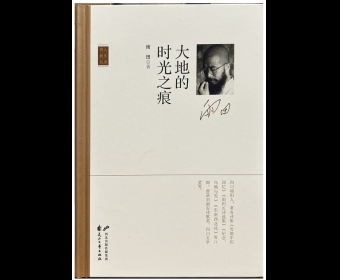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