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楚辞与遗承:调音师的远古形象
在通读余笑忠所有的重要诗歌作品之后,除了上文论述的“异乡人”之外,我还发现一批关键词,其中重要的如下:“红月亮”“废物”“小国家”“葬身之地”“扎根”“上游与下游”;“潜水者”“偷窥者”“旁观者”“梦游者”“邻人”;“幻肢”“迷雾”“晚景”;“暴雨”“沉冤之雪”“旧雨”“闪电”;“夕光”“微光”“阴影”“黑暗”“幽暗”;“托梦”“惊梦”“接梦”“旧梦”;“摇篮”“幼年”“天年”“老年”;“遗忘”“凝神”“孤寂”“悲欣”“哀鸣”“哭墙”;“屈死”“墓碑”“遗容”“醉生梦死”等。这是一些我们司空见惯的词,但是在余笑忠的诗歌中即成了重要的“灵魂之物”、“经验之物”与“想象之物”,诗人通过这些关键词,精心构筑他的灵魂世界中的“词”与“物”的关系,“思想”与“乡愁”的关系。余笑忠诗歌中“词”与“物”之间的本质关系,离不开“灵魂”、“经验”与“想象”的诗意表达与修辞诉求,甚至我们可深刻洞察精神语言的呈现形式,也是一种“物”。哲学家福柯说:“词把自己提供给人,恰如物被辨认一样。人们为了认识大自然而打开专业和阅读书本中的重大隐喻,相反的和看得见的方面,而且是更为深刻的方面,它迫使语言存在于世上,存在于植物、草木、石头和动物中间......因此语言本身必须作为大自然的一个物而被研究,同动物、植物或星星一样,语言的要素拥有他们自己的类似和适合的法则,他们自己的必然类推”。[8]透过这一些关键词,可以窥见余笑忠作为楚地出生的当代诗人与同样出生于楚地的古代诗人屈原(公元前340—公元前278)之间存在着“幽暗诗学”的渊源。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余笑忠曾经写过颇具影响长诗《九歌》,当下的诗人与读者基本上很难找到或读到这首长诗,此诗仅收录在他早年独立制作的诗集《九歌》中,而给我印象较深的就是诗人在诗中反复描述一条被鞭打的狗。多年后,他又据母亲的回忆,描述“他们这样屠杀一头耕牛”,可见这种内心古老的遗承——悲悯意识,在诗人的心中一直根深蒂固。另外,蕲春籍重要诗人耀旭十分喜爱这首长诗,于1994年将《九歌》连同他的评论一起寄至《作家》杂志,结果当年在《作家》第4期发表,此事亦可见证两位乡党之间真挚的诗歌情谊。尽管余笑忠并没有将这首长诗收入新世纪出版的三部诗集中,但不影响此诗是他早期较为重要的作品之一,同时此诗也可视为诗人青年时期向屈原致敬的虔诚赤子之心。诗人在90年代初创作的一批长诗标志着个体诗学态度的觉醒与确立,创作于1993年2月10日的《风中的八支蜡烛》即是余笑忠90年代诗歌创作的重要代表之一:
寒冬在加深。一群乡村小学的孩子
在墙角彼此撞来撞去
像一窝燕子,他们这样相互取暖
我,如何对他们谈起遥远的雪山
谈起孤独的斯堪迪纳维亚女儿
她远离亲人,与觅食的海鸟相遇
过冬的食物少而又少
四十天,或者更长,她要等待太阳反顾
雪峰,像一只静静的蜡烛
她的眼中是太阳的影子
是白夜十分绸缎一样的光
亲过她柔软的怀腹、跳动的乳房
如果有一群孩子,哪怕只有一个孩子
小熊那样拱着她的胸脯
她想,她一定不会这样死去
——摘自长诗《风中的八支蜡烛》第七节(1993)
余笑忠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最早引起诗坛关注的,应是他的长篇抒情诗在民间的影响力。关于余笑忠早期的诗学面貌,在我记忆中较为深刻的呈现,依然是他的长诗,除了上文提及的《风中的八支蜡烛》,还有《九歌》(1994)、《十年》(1997)、《我的身世》(2000)、《启蒙教育》(2001)、《俯首》(2002)、《喘息》(2003)、《秋日札记》(2004)、《春之歌》(2006)、《备忘录》(2006)等,余笑忠对长诗的创作停滞了一段时间,八年后又创作出长诗杰作《幻肢》(2013)。正是这一批长诗让我发现诗人与他心中的“远古形象”(雅克·朗西埃语)之间隐秘的呼应:屈原和杜甫。
法国当代哲学家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1940- )在《文学的政治》一书中论及法国诗人马拉美(Mallarmé,1842-1898)时,谈到一个概念,即诗人的“远古形象”[9](Ancient image)。我已经在多篇诗歌评论中,把它衍生为诗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诗学概念。在当下的汉语诗歌语境中,十分迫切地需要借鉴这些诗化哲学概念,从而有效地打开中西诗学之间的窄门。我已经从当代一些重要诗人的身上体察到了当代汉诗的“远古形象”在不断地复苏和隐现,比如欧阳江河、柏桦、杨键、沈方、杨典、育邦、苏野等,余笑忠也不例外。他们诗歌的精神行为与文化行为,他们正在试图借助诗歌内外的文化形象抵达这个“远古形象”。诗人余笑忠,还有一个专业的“朗读者”的身份:电台文艺主持人。他是中国著名的电台文艺主持人之一,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主持的电台文艺节目影响了几代人。“朗读者”的形象,同样可以追溯到古代,尤其是古代诗人墨客雅集时最为普遍的切磋诗艺文赋的交流方式,就是“吟诵”;甚至在古希腊,即有“诵诗人”这一古老的职业。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就记录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一说公元前470-公元前399)与“诵诗人”伊安(lon)之间的著名对话。古代的“吟诵”与今天的“朗读”、“朗诵”,是相似的发声艺术行为,因而我们可以认为余笑忠除了是一位诗人,还乐于为诗赋声,他的诗歌具有独特的乐调、语调与节奏。如果说,当代诗人中谁的语言节奏与乐感最为美妙,我首先想到的诗人中一定会有余笑忠。诗人一直在努力追寻汉语中被埋没的、幸存的“原音”,古老而伟大的“原音”:
在许多个日子
我有立下誓言的愿望,以挥别
我的过去。纵然只需
喃喃自语一番
但我是发过誓的,所以要么把誓言再背诵一遍
要么稍作修改,以适应今日之我,好使我继续玩弄
橡皮筋
我陷入犹疑,真的陷入犹疑
在这层意思和那层意思之间,摆下长沙发,以取代
从前的一块小布垫
“这正是你的可悲之处,”我对乐队某成员说
“你手中是一把好琴,只是琴弦松了。”
——《原音》(2009)
诗人在诗中留给读者两个重要的隐喻:“橡皮筯”和“琴弦”。两个词之间存在着强烈的诗义对抗,这种对抗我们可以视为一种“自我”的挣扎与觉醒,那个理想的“自我”究竟是伸缩自如、张弛有度的“橡皮筯”,还是直而美声、曲而音弱的“琴弦”呢?诗人给予的隐秘答案无疑是“琴弦”。但是,诗人又在诗中警戒“操琴者”,留下名句——“这正是你的可悲之处,你手中是一把好琴,只是琴弦松了”,这就是诗人在诗中结尾处道出极为震颤的“原音美学”的真相——“琴与弦的关系”:如何发现原音,演奏出原音。那么,什么是“原音”?我宁愿把诗人笔下的“原音”理解为“语言中的咒语”,或者是阿甘本所言的“声音的古老传统”。余笑忠诗中所言的“原音”,在我看来,又是一种最接近声音(语言)与抵达诗意的“召唤”与“还魂”之音。1936年,法国诗人瓦莱里(Paul Valery,1871—1945)在论述马拉美的诗句时,即写道:“对我来说——它应是——在声音之弦上——鲜活着的和思考着的存在(与此相对)——并将自我意识推向它的敏感性捕获——在情节、共鸣、对称性等等之中,发展着自我意识的特性。总之,语言出自于声音,而不是声音出自于语言”。[10]瓦莱里在其诗歌《皮提亚》中描述对一种声音的不可能追寻的悲剧,它既不是“我”的声音,也不是语言的声音,而是出自于身体深处的声音。从瓦莱里对声音的理解,我们亦可延伸一种新的诗学表达,当诗人识别出“原音”之后,也只是激活了源于自我的“他者”。因而我们对于“原音”的识别,超越了“我”,但是没有废除“我”。正如阿甘本所言:“如果诗歌的声音是人的声音,就不可能找到一个点:这个声音能即刻进入‘我’和‘身体’。然而正是存在着一个地方,在那儿,‘我’成功地自我超越,超越语言而抵达‘那个我们所是却毫不知情的晦涩实体’”。[11]而柏拉图更是惊心动魄地道出言说的力量:“一段话语,应该类似于一个活的造物”。余笑忠凭借他高超的诗歌技艺和影响力,成为当代诗坛的“调音师”。当代哲学家、批评家夏可君敏锐地发现余笑忠的这首寓意深长的《原音》,他说:
汉语就是这把好琴,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却把它演奏得走调了!单单这一句诗,已经足够让我们听到了对时代准确的诊断。我们的时代、我们的语言还没有被调校,它需要真正的诗歌来为这个时代调弦,诗人就是要为这个时代的语言调出它的准确音调。如果琴弦都没有调校到位,所有的演奏都显得滑稽可笑,只是一片混乱的噪音。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我们的汉语不就是混杂不堪的噪音?[12]
毋庸置疑,湖北诗人大都会从内心景仰古代伟大诗人屈原,甚至可以说屈原的影响,是世界级的。而古代诗人杜甫(712—770)同样也是一位世界级诗人。余笑忠在与我进行的访谈中即坦言,杜甫是他最喜欢的古代诗人之一。在我的阅读理解中,余笑忠的现代诗歌充满着一种“与古为徒”的人文气息,那就是温柔敦厚与悲悯情怀。这也是我时常反思的一个重要的诗学问题:诗人(余笑忠)与楚辞的关系,诗人与杜甫的关系。在诗人眼里,每一次反思,就是一次“回望”,正如诗人的佳句所言:“每一次回望有如托孤”。诗人的这种“托孤意识”,是一种诗学上的孤绝与惊醒,也是一种诗学的探险,进而有效地继承源自先贤的宝贵的诗学遗产:“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摘自屈原《离骚》);“悲愁回白首,倚杖背孤城”(摘自杜甫《独坐》)、“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摘自杜甫《春望》)、“百年歌者苦,未见有知音”(摘自杜甫:《南征》)。屈原是楚辞之祖,土生土长的楚国人,他对中国历代诗人的影响极为深远,甚至存在世界级影响,一直到今天。余笑忠在《有赠》中引用了屈原的诗句来聊赠友人:“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2016年10月某日,余笑忠拜谒屈子祠而赋诗一首:
大江东去。不乏众水西流
如屈子投江之汨罗
如苏子暂栖之兰溪
如我的母亲河:蕲河
我列举它并非为了比附
也并非暗藏勃勃野心
因为我想起了幼年时听说的事
发洪水时,思乡心切且异想天开的武汉知青
跳入蕲河,欲顺河而下
再逆流而上
一位朋友在诗里说,想到知青这个词
就感觉湿漉漉的
这一下子戳到了记忆中的痛处
而关于疼痛,又有什么比痛楚一词
更有份量?
——《谒屈子祠》(2016)
在我看来,当代诗人与古代诗人在诗性直觉上是相通的,阅读余笑忠的一些名作,我又会很快想到杜甫,想起杜甫的绝句与律诗。比如,《废物论》会让我想起杜甫的绝句《漫兴九首》之四:“二月已破三月来,渐老逢春能几回。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为蕲河而作》让我想起杜甫的《逃难》:“故国莽丘墟,邻里各分散。归路从此迷,涕尽湘江岸”;《哭墙》则让我想起杜甫的《哭长孙侍御》:“道为谋书重,名因赋颂雄。礼闱曾擢桂,宪府旧乘骢。流水生涯尽,浮云世事空。唯馀旧台柏,萧瑟九原中”;《正月初六,春光明媚,独坐偶成》让我想起杜甫的《宴胡侍御书堂》:“江湖春欲暮,墙宇日犹微。暗暗春籍满,轻轻花絮飞。翰林名有素,墨客兴无违。今夜文星动,吾侪醉不归”;……。同样,余笑忠也在自己的诗中引用杜甫的诗句,比如他在长诗《幻肢》中引用了杜甫的诗句:“瓢弃樽无绿,炉存火似红”。另外,一首《书事》在我看来,更是充满了杜甫的诗歌气息,夏可君称赞这是一首了不起的诗。可以说,这些诗歌气息的神似与贯通,让我惊叹不已。当然,我们不会说余笑忠的诗达到了杜甫的高度,而是意识到余笑忠的诗中存在杜诗气息,或者说有杜诗气韵。诗人之间的那种无师自通的诗学气息与精神血脉,大都是三观历练与诗性顿悟的结果,而不是蓄意而为,天然去雕饰,清水出芙蓉。我一直认为古代诗人的诗歌经典为何能够流传到今天,正是因为他们的诗歌具备“古典的现代性”(江弱水语),这种古典的现代性古诗经典所蕴藏的诗学魅力与秘密,从而促使它们依旧与今人产生共鸣,常读常新,经久不衰,焕发出既古老又恒常的生命力;甚至我们从现代诗的修辞理念出发,依然能够从古典诗歌中找出相互对应的现代性修辞。因而,我们发现在所有的文学门类中,唯有诗歌的修辞性是永远不过时的,唯有经历时间与空间双重洗礼的诗歌修辞具有永恒性,而我所发现的诗人的“远古形象”更加具有永恒性。
三、梦话与困境:诗学伦理构想
有一回,我居然梦见了慈禧太后
和她的长指甲
她的长指甲表明,她并不需要环握住什么东西
没有谁敢于动她一根指甲
她向我夸耀她的指甲还在生长
她俯身对我耳语:“我还有一颗妇人之心
妇人之痛,莫过于分娩死婴。”一股凉气
令我惊醒……我摸了摸我的脸
以确认它即使被抓挠过,也像新土豆一样
只是被蹭掉了一块皮
——《惊梦》(2014)
《接梦话》是余笑忠一部重要的诗集。余笑忠告诉我,诗集名称并不是他取的,而是出版社的朋友所取。从诗名来看,即易让人理解,诗的诗歌写作与梦境一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诗人与梦境的关系,犹如大地与月亮。杜甫在诗中有吟:“对酒都疑梦,吟诗正忆渠”,“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桃花气暖眼自醉,春渚日落梦相牵”。“接梦话”,在我们的乡下,是一种不吉的表现,但是诗人敢于把这种行为提升到一个精神层面来思考,突破世俗的禁忌,直接把它演变成诗歌写作的法器,因而他把“梦话叙事”引入诗歌,是重要的个体写作事件。我们清晰理解余笑忠“接梦话”的诗学隐喻的重要涵义,以及他在“梦话”与“诗话”之间的腾挪与转换。“接梦话”,是诗人进入现实与梦境的边缘状态下的精神臆想行为,是“生”与“死”的对话,是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的较量,是现实与历史的沉默对峙,因而“接梦话”在余笑忠的诗歌写作中生发为清醒而独特的梦想诗学,同时它也是一种在黑暗与沉默中冥想与对峙的诗学行为。余笑忠在《有人在传诵我的诗篇》一诗中写到“梦中之诗”这个词,我惊异于这个词,诗人道出“梦境中的诗境”,我认为这是完全是可能的,甚至我认为梦境中的抒情与叙事,依然是一种存在与真实,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在现实中,很多诗人常有在梦中作诗的习惯,时常会在梦中写出兴奋不已的好诗句,然后迅速从床上爬起来,记下那些佳句,我们可以视之为“梦中之诗”。
在余笑忠的诗歌中,大量穿插引用语,或是名人诗句、格言,或是他者言说、噫语、告诫,他在诗中用“”括起来的诗句,可以视为是诗人自我对话的方式,正如作者所言:“有所思的诗,不如若有所思的诗,无名天真状态的诗”。而诗人的这种“若有所思”其实已经无意识地构成了诗的“点睛之笔”,诗的灵魂包孕其中,可以极好地帮助读者理解他的诗,并且大大提升诗学情境的在场感,以及强烈的语言感染力,醒目而突兀。甚至我发现其中一部分引语,也可以视为“若有所思”的一部分。比如,《秘密》:“学会说再见并且终生牢记”;《痴人说梦》:“你在撒谎!”;《良人歌》:“击毙它,击毙它”;《原音》:“你手中是一把好琴,只是琴弦松了”;《一年之间》:“白鹭,你要回到我们的河边……”;《告诫》:“母亲叮嘱她的孩子:不管什么人盘问你/你说,我和你们是一个部分的”;《诱人的排比句》:“跟随我,我就是你的手杖”;《邱吉尔与熊十力》:“如果我受绞刑,观众还会多出一倍”;《为蕲河作》:“那么再说一次吧:如果我能乘坐一条小船/回到我的家乡多好/哪怕我不慎掉落水中,被河水/呛得泪流满面”;《凉台上》:“一个说:‘傻瓜,你怎么指望把生瓜煮成熟瓜。’”;《幻肢》:“你咬不动的石头,你就吻它”;《甘蔗田》:“如果我是一个地主……”;《清明日大雨》:“要回就回小国家”;《拧床单》:“你要跟我反着来”;《小刀万岁》:“小刀万岁!”;《炉边》:“我终于看清了某人的脸”;《诗人的甜言蜜语》:“如果你有了一辆自行车,你要学会给它打气”;《祭父辞》:“这回我死定了,儿”;《梦见父亲》:“那就再等等,也许明天/夜里,我还会来”;……。余笑忠在诗歌中的引语,像是“耳语”,又像是“自言自语”,它们是诗意的言说方式,它们是呼喊与细雨,言简意赅,或双关,或讽刺,或训诫,或揭露,或批判,或追问,或慨叹。余笑忠在访谈中这样谈及关于梦的书写:“其实并不是我多梦,只是偏爱梦的启示。在我看来,梦中出现的可能是我们在烦杂有日常中被忽略或遗忘的某种东西,或者是我们深思而意外获得的馈赠,就像我在一首诗中写过的:‘如今我相信,来到梦里的一切/ 都历经长途跋涉/ 偶尔,借我们的梦得以停歇’”。余笑忠创作于2014年的《惊梦》引起我习惯性的诗学警觉,诗人在诗中描述,梦见慈禧太后,梦见她的长指甲,以及慈禧对他的“耳语”:“我还有一颗妇人之心 / 妇人之痛,莫过于分娩死婴。”而诗人在另一首早写一年的《扰人之梦》(2013)中也写到“死婴”:
像生下死婴的
母亲
在她的暮年,一个永远未曾长大的孩子
喊她回去
她把雨夜的沟渠
看成坦途了
连惊叫都没有……
子夜,她湿漉漉地站在
我们面前。问我们
姓甚,名谁
我们用尽了所有的纱布、毛巾
直到她
迷迷糊糊地躺下,还不忘感激我们
替她腾出了一个地方
而谁又能回答?这里是
她的家
——《扰人之梦》(2013)
“死婴”又是余笑忠诗歌中一个沉痛的隐喻:被扼杀的人性,幼年之美善。“死婴”是很多中国母亲记忆中的一个痛点。《扰人之梦》道出了无数苦难母亲的生死悲凉和人间冤屈,诗人的心脆弱而疼痛至极,而只能在梦境中为这样的母亲祈福和救赎。诗人极为擅长把日常中的事物与历史细节进行奇妙关联、结合,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诗性话语空间,常常生发出令人惊叹的言说意象,而且极为自然地信手拈来,而又通过“诗话”、“梦话”的形式穿插在诗歌中,现实与梦想进行不断重叠,不断互构,从而营造出一种深刻而震颤的梦想诗学。正如诗人江离如此评价余笑忠诗歌中独特的“细节”抒写特征:“他的目光所及无非是莲子、艾蒿、樟树、剥豆荚、老母鸡等等生活细节里的寻常之物,不寻常的他通过对物的凝视以及娓娓道来的书写,把我们引到‘诗之思’……对‘无用之用’有了会心的一笑”,这“无用之用”,这“会心的一笑”,也可以是诗人笔下“庄子的苦笑”。
诗人沈苇(1965- )高度评价诗集《接梦话》的诗学意义:“‘惊梦’,可视为笑忠写作的原动力和内驱力之一,却每每呈现为对现实、对日常的‘释梦’,由此构成他三十年来诗歌创作的脉络、风貌和奇景。他将最新出版的诗集命名为《接梦话》,乍看令人感到不妙,因为我们知道接梦话是有风险的,民间认为容易引发梦中人的错乱甚至死亡。但与此同时,接梦话是超越时空的对话、交流,是一种‘象征交换’。在他的写作中,梦与现实的边界、梦与日常的边界、梦与自然的边界等等,一再被他突破了。到底是诗人接了梦中人的话,还是诗人作为梦中人接过了另一个清醒者的话?这是一个类似庄子与蝴蝶的问题。梦与现实(‘第二现实’与‘第一现实’)的互文与混溶,在诗人那里转化为一种清醒的自觉,一种‘精神的现实性’”。而著名音乐人、诗人李皖(1966- )对余笑忠诗集的评价,则让我感到有一些意外,李皖或许是因为对音乐的研究而更加突出地意识到了余笑忠诗歌的“声音”的敏感性,或许从音乐的角度来看,音乐人与诗人都是绝佳诗意的“调音师”(夏可君语):
读余笑忠诗集《接梦话》,虽然我有预料,但还是狠狠地把我震了一下,大量的优秀诗作——特别是他的一些很好的短诗——给我的感觉像是一块块黑色的煤块,擦根火柴就能着起来,而且能够烧得很久。他的诗写得非常简朴和朴实,修辞非常克制,那些短诗有着惊人的力量,这是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再一个就是“弱”的力量,他表达的情感有羞愧、惊恐,还有发自内心的慈悲,读起来惊心动魄。还有一个不得了的地方就是他的诗歌不是“发明”出来的,是“发现”,很多场景我们都见过,只是我们眼拙,而他敏锐地捕捉到了。还有一点就是,每个诗人都用身体里的另一个角色在写作,比方说张执浩是用他身体里的一个小男孩在写作,余笑忠的诗里也有一个农村小孩在说话,但从他现在越来越多的诗歌里看不出这个身份,我觉得这是他很了不起的一个变化,他现在的诗歌仿佛是一个不明的对象在写作,更像是这个世界本身的观照,这个世界本身的光照亮的东西。我曾经想写一个系列,叫“以事物本身的方式去认识事物”,我看他的诗里就有这个东西,那些事物在他的眼里焕发出了诗意的光亮,我读他的这本集子有非常好的感受。还有他的声音。一个诗人是有自己的声音的。笑忠的诗歌确实很像他自己的声音,就是黑色的、低沉的那种声音。这个“声音”是很耐读的,我特别喜欢他那些短诗。短诗其实很难写,但我看他大量的十行左右的诗歌都非常有力量。[14]
余笑忠对我讲,诗集原拟定的名称是“逆流而上”,后因出版方朋友的建议,把诗集名称换成了“接梦话”。在我看来,“逆流而上”与“接梦话”是两种不同的诗学表达方向,一个出世,一个入世,诗学表达的侧重点不一样。“逆流而上”更多呈现一种乡愁诗学,“接梦话”则是幽暗诗学与梦想诗学的混合体征象。“接梦话”,显然是一种偶然性的诗学契合与表达,不是诗人潜意识里沉积已久的诗学入口,而我个人更加倾向于他的诗集可命名为“凝神”。这不仅仅因为我最喜欢《凝神》的私心,更重要的是“凝神”既涵括了以上提出的三种诗学特质,又呈现了诗人自己特别强调的诗学态度——“专注”:诗学与立场的专注,人性与精神的专注,时代与乡愁的专注,温柔与敦厚的专注,古典与现代的专注。耀旭在评价《凝神》时,再次强调余笑忠的“发现”能力:“在我们视野之内的诗人中,同时具备良好的‘发现’能力又具备朴素诚恳的语言能力的人,其实是不多的,而毫无疑问,余笑忠就是这样的诗人”。一个没有专注精神的诗人,是很难具备卓越的诗意“发现”和“捕捉”的能力。诗人、批评家夏宏同样称赞余笑忠的“发现”能力:“余笑忠不仅敏锐的感应到存在者身上的灵光,且察觉到他的某种转渡。他似恐在诗中直接言明而丢失了它,转而在景、情、事、思的轮换中呈示出时隐时现的流殇曲水,乘用否定句、转折语,有时甚至一否再否、一转再折,将理智与情感、审美与道德、社会与自然之域相贯连。当你指认是它、是它们时,又像不是,似幻又似真,因为他们之间的障碍不知不觉的被诗(诗人)看透了”。[15]





 南方的南 评论 江雪:余笑忠论 | 风骨与:雄文
南方的南 评论 江雪:余笑忠论 | 风骨与:雄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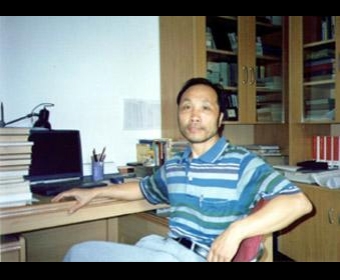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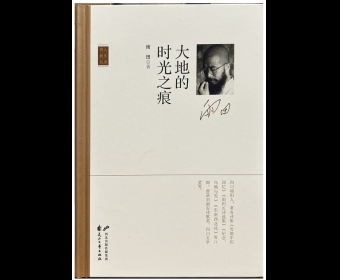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