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纪一个英国人赞美这种造诣高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躯体换了一个,而精魂依然故我。
*文章选自《七缀集》(钱锺书 著 三联书店2019-1)。
林纾的翻译
文 | 钱锺书
汉代文字学者许慎有一节关于翻译的训诂,义蕴颇为丰富。《说文解字》卷六《囗》部第二十六字:“囮,译也。从‘囗’, ‘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囮’,读若‘讹’。”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的引 “诱”,“讹”、“讹”、“化”和“囮”是同一个字。“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 “虚涵数意”(polysemy, manifold meaning),把翻译能起的作用(“诱”)、难于避免的毛病(“讹”)、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化”),彷佛一一透示出来了。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纪一个英国人赞美这种造诣高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躯体换了一个,而精魂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翻译出的东西。因此,意大利一位大诗人认为好翻译应备的条件看来是彼此不相容乃至相矛盾的(paiono discordanti e incompatibili e contraddittorie):译者得矫揉造作(ora il traduttore necessariamente affetta),对原文亦步亦趋,以求曲肖原著者的天然本来(inaffettato, naturale o spontaneo)的风格。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就文体或风格而论,也许会有希莱尔马诃区分的两种翻译法,譬如说:一种尽量“欧化”,尽可能让外国作家安居不动,而引导我国读者走向他们那里去,另一种尽量“汉化”,尽可能让我国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外国作家走向咱们这儿来(Entweder der Uebersetzer lasst den Schriftsteller moglichst in Ruhe und bewegt den Leser ihm entgegen, oder er lasst den Lesermoglichst in Ruhe und bewegt den Schriftsteller ihm entgegen)。然而“欧化”也好,“汉化”也好,翻译总是以原作的那一国语文为出发点而以译成的这一国语文为到达点。从最初出发以至终竟到达,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很贴合原文。那就是“讹”,西洋谚语所谓“翻译者即反逆者”(Traduttore traditore)。中国古人也说翻译的“翻”等于把绣花纺织品的正面翻过去的“翻”,展开了它的反面:“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皆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释赞宁《高僧传三集》卷三《译经篇·论》)。这个比喻使我们想起堂·吉诃德说阅读译本就像从反面来看花毯(es como quien mira los tapices flamencos por el reves)。“媒”和“诱”当然说明了翻译在文化交流里所起的作用。它是个居间者或联络员,介绍大家去认识外国作品,引诱大家去爱好外国作品,彷佛做媒似的,使国与国之间缔结了“文学因缘”,缔结了国与国之间唯一的较少反目、吵嘴、分手挥拳等危险的“因缘”。
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于是“媒”或“诱”产生了新的意义。翻译本来是要省人家的事,免得他们去学外文、读原作,却一变而为导诱一些人去学外文、读原作。它挑动了有些人的好奇心,惹得他们对原作无限向往,彷佛让他们尝到一点儿味道,引起了胃口,可是没有解馋过瘾。他们总觉得读翻译像隔雾赏花,不比读原作那么情景真切。歌德就有过这种看法;他很不礼貌地比翻译家为下流的职业媒人 (Uebersetzer sind als geschaftige Kuppler anzusehen)——中国旧名“牵马”,因为他们把原作半露半遮(eine halbverschleierte Schone),使读者心痒神驰,想象它不知多少美丽。要证实那个想象,要揭去那层遮遮掩掩的面纱,以求看个饱、看个着实,就得设法去读原作。这样说来,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到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自负好手的译者恰恰产生了失手自杀的译本,他满以为读了他的译本就无需去读原作,但是一般人能够欣赏货真价实的原作以后,常常薄情地抛弃了翻译家辛勤制造的代用品。倒是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功效。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者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这类翻译不是居间,而是离间,摧毁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扫尽读者的兴趣,同时也破坏原作的名誉。十七世纪法国的德·马罗勒神父(l'abbe de Marolles)就是一个经典的例证。他所译古罗马诗人《马夏尔的讽刺小诗集》(Epigrams of Martial)被时人称为《讽刺马夏尔的小诗集》(Epigrams against Martial);和他相识的作者说:这位神父的翻译简直是法国语文遭受的一个灾难(un de ces maux dont notre langue est affligee),他发愿把古罗马诗家统统译出来,桓吉尔、霍拉斯等人都没有蒙他开恩饶命(n'ayant pardonne),奥维德、太伦斯等人早晚会断送在他的毒手里(assassines)。不用说,马罗勒对他的翻译成绩还是沾沾自喜、津津乐道的。我们从亲身阅历里,找得到好多和这位神父可以作伴的人。
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公认的事实。他对若干读者,也一定有过歌德所说的“媒”的影响,引导他们去跟原作发生直接关系。我自己就是读了林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都觉得沉闷乏味。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我把林译哈葛德、迭更司、欧文、司各德、斯威佛特的作品反复不厌地阅览。假如我当时学习英语有什么自己意识到的动机,其中之一就是有一天能够痛痛快快地读遍哈葛德以及旁人的探险小说。四十年前,在我故乡那个县城里,小孩子既无野兽片电影可看,又无动物园可逛,只能见到“走江湖”的人耍猴儿把戏或者牵一头疥骆驼卖药。后来孩子们看野兽片、逛动物园所获得的娱乐,我只能向冒险小说里去找寻。我清楚记得这一回事。哈葛德《三千年艳尸记》第五章结尾刻意描写鳄鱼和狮子的搏斗;对小孩子说来,那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紧张得使他眼瞪口开、气儿也不敢透的。林纾译文的下半段是这样:
“然狮之后爪已及鳄鱼之颈,如人之脱手套,力拔而出之。少顷,狮首俯鳄鱼之身作异声,而鳄鱼亦侧其齿,尚陷入狮股,狮腹为鳄所咬亦几裂。如是战斗,为余生平所未睹者。”[照原句读,加新式标点]
狮子抓住鳄鱼的脖子,决不会整个爪子像陷进烂泥似的,为什么“如人之脱手套”?鳄鱼的牙齿既然“陷入狮股”,物理和生理上都不可能去“咬狮腹”。我无论如何想不明白,家里的大人也解答不来。而且这场恶狠狠的打架怎样了局? 谁输谁赢,还是同归于尽?鳄鱼和狮子的死活,比起男女主角的悲欢,是我更关怀的问题。书里并未明白交代,我真心痒难搔,恨不能知道原文是否照样胡涂了事。我开始能读原文,总先找林纾译过的小说来读。我渐渐听到和看到学者名流对林译的轻蔑和嗤笑,未免世态逐炎凉,就不再而也不屑再去看它,毫无恋惜地过河拔桥了!
最近,偶尔翻开一本林译小说,出于意外,它居然还有些吸引力。我不但把它看完,并且接二连三,重温了大部分的林译,发现许多都值得重读,尽管漏译误译触处皆是。我试找同一作品的后出的——无疑也是比较“忠实”的——译本来读,譬如孟德斯鸠和迭更司的小说,就觉得宁可读原文。这是一个颇耐玩味的事实。当然,一个人能读原文以后,再来看错误的译本,有时不失为一种消遣,还可以方便地增长自我优越的快感。一位文学史家曾说,译本愈糟糕愈有趣:我们对照着原本,看翻译者如何异想天开,把胡猜乱测来填补理解上的空白,无中生有,指鹿为马,简直像“超现实主义”诗人的作风。但是,我对林译的兴味,绝非想找些岔子,以资笑柄谈助,而林纾译本里不忠实或“讹”的地方也并不完全由于他的助手们外语程度低浅、不够了解原文。举一两个例来说明。
《滑稽外史》第一七章写时装店里女店员领班那格女士听见顾客说她是“老妪”,险些气破肚子,回到缝纫室里,披头散发,大吵大闹,把满腔妒愤都发泄在年轻貌美的加德身上,她手下一伙女孩子也附和着。林纾译文里有下面一节:
“那格……始笑而终哭,哭声似带讴歌。曰:‘嗟乎!吾来十五年,楼中咸谓我如名花之鲜妍’——歌时,顿其左足,曰:‘嗟夫天!’又顿其右足,曰:‘嗟夫天! 十五年中未被人轻贱。竟有骚狐奔我前,辱我令我肝肠颤!’”
这真是带唱带做的小丑戏,逗得读者都会发笑。我们忙翻开迭更司原书(第一八章)来看,颇为失望。略仿林纾的笔调译出来,大致如此:
“那格女士先狂笑而后嘤然以泣,为状至辛楚动人。疾呼曰:‘十五年来,吾为此楼上下增光匪少。邀天之祜’——言及此,力顿其左足,复力顿其右足,顿且言曰:‘吾未尝一日遭辱。胡意今日为此婢所卖!其用心诡鄙极矣!其行事实玷吾侪,知礼义者无勿耻之。吾憎之贱之,然而吾心伤矣!吾心滋伤矣!’”
那段“似带讴歌”的顺口溜是林纾对原文的加工改造,绝不会由于助手的误解或曲解。他一定觉得迭更司的描写还不够淋漓尽致,所以浓浓地渲染一下,增添了人物和情景的可笑。写作我国近代文学史的学者一般都未必读过迭更司原著,然而不犹豫地承认林纾颇能表迭更司的风趣。但从这个例子看来,林纾往往捐助自己的“谐谑”,为迭更司的幽默加油加酱。再从《滑稽外史》举一例,见于第三三章(迭更司原书第三四章):
“司圭尔先生……顾老而夫曰:‘此为吾子小瓦克福。……君但观其肥硕,至于莫能容其衣。其肥乃日甚,至于衣缝裂而铜钮断。’乃按其子之首,处处以指戟其身,曰:‘此肉也。’又戟之曰:‘此亦肉,肉韧而坚。今吾试引其皮,乃附肉不能起。’方司圭尔引皮时,而小瓦克福已大哭,摩其肌曰:‘翁乃苦我!’司圭尔先生曰:‘彼尚未饱。若饱食者,则力聚而气张,虽有瓦屋,乃不能閟其身。……君试观其泪中乃有牛羊之脂,由食足也。’”
这一节的译笔也很生动。不过,迭更司只写司圭尔“处处戟其身”,只写他说那胖小子吃饱了午饭,屋子就关不上门,只写他说儿子的眼泪有油脂 (oiliness);什么“按其子之首”、“力聚而气张”、“牛羊之脂,由食足也”等等都出于林纾的锦上添花。更值得注意的是,迭更司笔下的小瓦克福只 “大哭摩肌”,一句话没有说。“翁乃苦我”那句怨言是林纾凭空插进去了的,添个波折,使场面平衡;否则司圭尔一个人滔滔独白,说得热闹,儿子彷佛哑口畜生,他这一边太冷落了。换句话说,林纾认为原文美中不足,这里补充一下,那里润饰一下,因而语言更具体,情景更活泼,整个描述笔酣墨饱。不由我们不联想起他崇拜的司马迁《史记》里对过去记述的润色或增饰。林纾写过不少小说,并且要采用“西人哈葛德”和“迭更先生”的笔法来写小说。他在翻译时,碰到他认为是原作的弱笔或败笔,不免手痒难熬,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从翻译的角度判断,这当然也是“讹”。即使添改得很好,毕竟变换了本来面目,何况添改未必一一妥当。方才引的一节算是改得不差的,上面那格女士带哭带唱的一节就有问题。那格确是一个丑角,这场哭吵也确有装模作样的成分。但是,假如她有腔无调地“讴歌”起来,那显然是在做戏,表示她的哭泣压根儿是假的,她就制造不成紧张局面了,她的同伙和她的对头不会严肃对待她的发脾气了,不仅我们读着要笑,那些人当场也忍不住笑了。李贽评点《琵琶记》第八折《考试》批语:“太戏!不像!”“戏则戏矣,倒须似真,若真反不妨似戏也。”林纾的改笔过火得彷佛插科打诨,正所谓“太戏!不像!”了。
大家一向都知道林译删节原作,似乎没人注意它有时也像上面所说的增补原作。这类增补,在比较用心的前期林译里,尤其在迭更司和欧文作品的译本里,出现得很多。或则加一个比喻,使描叙愈有风趣,例如《拊掌录·睡洞》:
“而笨者读不上口,先生则以夏楚助之,使力跃字沟而过。”
原文只彷佛杜甫《漫成》诗所说“读书难字过”,并无“力跃字沟”这个新奇的形象。或则引申几句议论,使意义更显豁,例如《贼史》第二章:
“凡遇无名而死之儿,医生则曰:‘吾剖腹视之,其中殊无物。’外史氏曰:‘儿之死,正以腹中无物耳!有物又焉能死?’”
“外史氏曰”云云在原文是括号里的附属短句,译成文言只等于:“此语殆非妄”。作为翻译,这种增补是不足为训的,但从修辞学或文章作法的观点来说,它常常可以启发心思。林纾反复说外国小说“处处均得古文文法”,“天下文人之脑力,虽欧亚之隔,亦未有不同者”,又把《左传》、《史记》等和迭更司、森彼得的叙事来比拟,并不是空口说大话。他确按照他的了解,在译文里有节制地掺进评点家所谓“顿荡”、“波澜”、“画龙点睛”、“颊上添毫”之笔,使作品更符合“古文义法”。一个能写作或自信能写作的人从事文学翻译,难保不像林纾那样的手痒;他根据个人的写作标准和企图,要充当原作者的“诤友”,自信有点铁成金、以石攻玉或移橘为枳的义务和权利,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在各国翻译史里,尤其在早期,都找得着可和林纾作伴的人。像他的朋友严复的划时代译本《天演论》就把“元书所称西方”古书、古事“改为中国人语”,“用为主文谲谏之资”;当代法国诗人瓦勒利也坦白承认在翻译桓吉尔《牧歌》时,往往心痒痒地想修改原作(des envies de changer quelque chose dans le texte venerable)。正确认识翻译的性质,认真执行翻译的任务,能写作的翻译者就会有克己工夫,抑止不适当的写作冲动,也许还会鄙视林纾的经不起引诱。但是,正像背负着家庭重担和社会责任的成年人偶尔羡慕小孩子的放肆率真,某些翻译家有时会暗恨自己不能像林纾那样大胆放手的,我猜想。
上面所引司圭尔的话:“君但观其肥硕,至于莫能容其衣”,应该是“至于其衣莫能容”或“至莫能容于其衣”。这类文字上的颠倒讹脱在林译里相当普遍,看来不能一概归咎于排印的疏忽。林纾“译书”的速度是他引以自豪的,也实在是惊人的。不过,下笔如飞、文不加点,得付出代价。除了造句松懈、用字冗赘而外,字句的脱漏错误无疑是代价的一部分。就像前引《三千年艳尸记》那一节里:“而鳄鱼亦侧其齿,尚陷入狮股”(照原来断句),也很费解;根据原文推断,大约漏了一个“身”字:“鳄鱼亦侧其身,齿尚陷入狮股。”又像《巴黎茶花女遗事》:“余转觉忿怒马克揶揄之心,逐渐为欢爱之心渐推渐远”,赘余的是“逐渐”;似乎本来想写“逐渐为欢爱之心愈推愈远”,中途变计,而忘掉删除那两个字。至于不很——或很不——利落的句型,例子可以信手拈来:“然马克家日间谈宴,非十余人马克不适”(《巴黎茶花女遗事》);“我所求于兄者,不过求兄加礼此老”(《迦茵小传》第四章);“吾自思宜作何者,讵即久候于此,因思不如窃马而逃” (《大食故宫余载·记帅府之缚游兵》)。这些不能算是衍文,都属于刘知几所谓“省字”和“点烦”的范围了(《史通》内篇《叙事》、外篇《点烦》)。排印之误不会没有,但也许由于原稿的字迹潦草。最特出的例是《洪罕女郎传》男主角的姓(Quaritch),全部译本里出现几百次,都作“爪立支”;“爪”字准是“瓜”字,草书形近致误。这里不妨摘录民国元年至六年主编《小说月报》的恽树珏先生给我父亲的一封信,信是民国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写的:“近此公[指林纾]有《哀吹录》四篇,售与敝报。弟以其名足震俗,漫为登录[指《小说月报》第五卷七号]。就中杜撰字不少:‘翻筋斗’曰‘翻滚斗’,‘炊烟’曰‘丝烟’。弟不自量,妄为窜易。以我见侯官文字,此为劣矣!”这几句话不仅写出林纾匆忙草率,连稿子上显著的“杜撰字”或别字都没改正,而且无意中流露出刊物编者对名作家来稿常抱的典型的两面态度。
在“讹”字这个问题上,大家一向对林纾从宽发落,而严厉责备他的助手。林纾自己也早把责任推得干净:“鄙人不审西文,但能笔达,即有讹错,均出不知” (《西利亚郡主别传·序》)。这不等于开脱自己是“不知者无罪”么? 假如我上文没有讲错,那末林译的“讹”决不能全怪助手,而“讹”里最具特色的成分正出于林纾本人的明知故犯。也恰恰是这部分的“讹”能起一些抗腐作用,林译因此而可以免于全被淘汰。试看林纾的主要助手魏易单独翻译的迭更司《二城故事》(《庸言》第一卷十三号起连载),它就只有林、魏合作时那种删改的“讹”,却没有合作时那种增改的“讹”。林译有些地方,看来助手们不至于“讹错”,倒是“笔达”者“信笔行之”,不加思索,没体味出原话里的机锋。《滑稽外史》一四章(原书一五章)里番尼那封信是历来传诵的。林纾把第一句“笔达”如下,没有加上他惯用的密圈来表示欣赏和领会:
“先生足下:吾父命我以书与君。医生言吾父股必中断,腕不能书,故命我书之。”
无端添进一个“腕”字,真是画蛇添足! 对能读原文的人说来,迭更司这里的句法差不多防止了添进“腕”或“手”字的可能性(...the doctors considering it doubtful whether he will ever recover the use of his legs which prevents his holding a pen)。迭更司赏识的盖司吉尔夫人(Mrs. Gaskell)在她的小说里写了相类的话柄:一位老先生代他的妻子写信,说“她的脚脖子扭了筋,拿不起笔”(she being indisposed with sprained ankle, which quite incapacitated her from holding pen)。看来那是一个中西共有的套版笑话。《晋书》卷六八《贺循传》:“及陈敏之乱,诈称诏书,以循为丹杨内史。循辞从脚疾,手不制笔”;《太平广记》卷二五〇引《朝野佥载》:“李安期……看判曰:‘书稍弱。’选人对曰:‘昨坠马伤足。’安期曰:‘损足何废好书!’”林纾从容一些,即使记不得《晋书》的冷门典故,准会想起唐人笔记里的著名诙谐,也许就改译为“股必中断,不能作书”或“足胫难复原,不复能执笔”,不但加圈,并且加注了。当然,助手们的外文程度都很平常,事先准备也不一定充分,临时对本口述,又碰上这位应声直书的“笔达”者,不给与迟疑和考虑的间隙。忙中有错,口述者会看错说错,笔达者难保不听错写错;助手们事后显然也没有校核过林纾的稿子。在那些情况下,不犯“讹错”才真是奇迹。不过,苛责林纾助手们的人很容易忽视或忘记翻译这门艺业的特点。我们研究一部文学作品,事实上往往不能够而且不需要一字一句都透彻了解的。对有些字、词、句以至无关重要的章节,我们都可以“不求甚解”,一样写得出头头是道的论文,因而挂起研究某某专家的牌子,完全不必声明对某字、某句、某典故、某成语、某节等缺乏了解,以表示自己严肃诚实的学风。翻译可就不同,只彷佛教基本课老师的讲书,而不像大教授们的讲学。原作里没有一个字可以滑过溜过,没有一处困难可以支吾扯淡。一部作品读起来很顺利容易,译起来马上出现料想不到的疑难,而这种疑难并非翻翻字典、问问人就能解决。不能解决而回避,那就是任意删节的“讹”;不敢或不肯躲闪而强作解人,那更是胡猜乱测的“讹”。可怜翻译者给扣上“反逆者”的帽子,既制造不来烟幕,掩盖自己的无知和谬误,又常常缺乏足够厚的脸皮,不敢借用博尔赫斯(J. L. Borges)的话反咬一口,说那是原作对译本的不忠实(Eloriginal es infiel a la traduccion)。譬如《滑稽外史》原书第三五章说赤利伯尔弟兄是“German-merchants”,林译第三四章译为“德国巨商”。我们一般也是那样理解的,除非仔细再想一想。迭更司决不把德国人作为英国社会的救星;同时,在十九世纪描述本国生活的英国小说里,异言异服的外国角色只是笑柄,而赤利伯尔的姓氏和举止表示他是地道英国人。那个平常的称谓在这里有一个现代不常用的意义:不指“德国巨商”,而指和德国做进出口生意的英国商人。写文章评论《滑稽外史》或介绍迭更司的思想和艺术时,只要不推断他也像卡莱尔那样向往德国,我们的无知谬误大可免于暴露丢脸;翻译《滑稽外史》时,只怕不那么安全了。
所以,林纾助手的许多“讹错”,都还可以原谅。使我诧异的是他们教林纾加添的解释,那一定经过一番调查研究的。举两个我认为最离奇的例。《黑太子南征录》第五章:“彼马上呼我为‘乌弗黎’(注:法兰西语,犹言‘工人’),且作势,令我辟此双扉。我为之启关,彼则曰:‘懋尔西’(注:系不规则之英语)。” 《孝女耐儿传》第五一章:“白拉司曰:‘汝大能作雅谑,而又精于动物学,何也?汝殆为第一等之小丑!’”英文Buffoon、滑稽也,Bufon、癞蟆也;白拉司本称圭而伯为“滑稽”,音吐模糊,遂成“癞蟆”。把“开门”(ouvre)和“工人”(ouvrier)混为一字,不去说它,为什么把也是“法兰西语”的“谢谢”(merci)解释为“不规则之英语”呢?法国一位“动物学”家的姓和法语“小丑”那个字声音相近,雨果的诗里就叶韵打趣过;不知道布封这个人,不足为奇,为什么硬改了他的本姓(Buffon)去牵合拉丁语和意语的“癞蟆”(bufo,bufone),以致法国的“动物学”大家化为罗马的两栖小动物呢?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三幕第一景写一个角色遭魔术禁咒,变为驴首人身,他的伙伴惊叫说:“天呀!你是经过了翻译了!”(Thou art translated)。那句话可以应用在这个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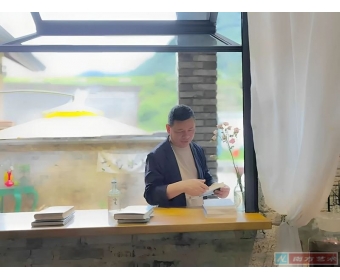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