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究竟心藏了大恶还是悲伤?
访谈者:张后

沈浩波
第一部分:关于北师大诗人群
张后:我访谈的伎俩,是先和被访谈人套交情,我从不掩耳盗铃,也不故做脸红,我实话实说,我和你有关过联系,是想在你的磨铁文化出我历史小说的三大霸主,后来没成,你好像是说不行,还是说什么来的?反正你没做,其实我那三霸,你根本没有看,或者没细看,是你手下人看的?他们未必能看明白……但话说到这里,我实际是2006年大场朗颂会那天见到你的,那天有食指、舒婷、陈仲义、胡续冬、杨黎、阿翔,我还照了几张你的相片,你当时还把一件白色T恤反穿了,我不知道你当时是不是故意穿反的?还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穿反了T恤?说不出的一种时尚味道?我回去偷偷也模仿了一次,却让小朵翻了我两天白眼,意思说我别出洋相了,我知道我永远穿不出沈浩波的那种精神和面貌?
沈浩波:那T恤啊,我有好几款都是那样的,看起来像是穿反了,其实是一种设计。这个冬天我穿的一件大衣也是这样的。这说明我喜欢略微的标新立异,和略微的追求时尚。只是略微,因为我知道,我骨子里有牢不可破的保守的一面。
张后:我在朵渔写你的随笔中,看到他称你“所谋乃大”,这是很高的激赏和赞誉?再这里谈谈你和朵渔和侯马、伊沙等等这些同学怎么样?你们的大学时代?你们的友谊令很多人津津乐道?放眼整座江湖,也没有几个群体如你等纯粹?和知名?
沈浩波:我和朵渔,伊沙,侯马什么时候成同学了?天。而且这个问题里居然落掉了徐江、南人还有宋晓贤。不应该呀(呵呵,只要在一个学校读书就可以是同学嘛,和多少届无关紧要——张后)。
的确,放眼整座江湖,也没有出现这样的奇迹,一个学校,一群顶尖的诗人,支撑了整个中国诗歌的天空!
但我们不是同学呀!伊沙、徐江、侯马、桑克是同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5级的,宋晓贤其实也可以算他们的同学,1984级中文系的,但上了5年,同时毕业。朵渔和南人是同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90级的。还有一些很好的诗人,比如张海峰,1986级的,李师江,1993级的。都是中文系。其实我是小师弟,比伊沙他们晚10年,北京师范大学1995级的。
我上大学那会儿,有一次,伊沙、徐江来北京,我们一起吃饭,席间有人问我是不是他们的同学,我心里很窘——难道我有那么显老?但残酷的事实告诉我,我20多岁时看起来像30多,30来岁的现在看起来像40多。天生一张老脸,想装嫩都不行。
所以,我们没有共同的大学时代,我和朵渔与伊沙、侯马之间更不可能有令人津津乐道的大学友谊。
我怀疑这个问题你不是问我的,是不是问错了,是问徐江的吧?他们在大学里的友谊到确实是一个令人津津乐道的传奇。可惜我晚生10年。
我们是很知名。但却不是一个纯粹的群体。也没有如你所言的那种纯粹的友谊。我与伊沙、侯马、徐江之间是有的,我与朵渔、南人也是有的。我是小师弟嘛,不敢造次,我这个人内心秩序感比较强。但是,我要揭发一下的是,朵渔和他的这三位师兄们之间是没有滴。彼此是不爽滴。友谊滴曾经有过现在不多了滴。但这个是没有关系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滴。每一个传奇都不可能真滴那么传奇滴。一定都要有无坚不摧滴友谊才能构成传奇吗——事实往往是恰恰相反。我也希望他们好啊,搞得我现在去天津都很尴尬,老徐和老朵同居一城,都是我师兄,你说咋弄?
朵渔说我“有谋乃大”,这不是激赏和夸赞,这是陈述客观事实。谋:追求的意思。我这个人确实立项远大,目标远大,对汉语诗歌所谋乃大,很大,非常大。
作为一个小师弟,1985级的几位师兄对我来说,在我的整个诗歌生涯中,意义重大。在我写作之初,他们三个之于我,如同指路之灯。你无法想象我和他们之间有多少次笔谈、面对面的长谈和交流。这3个人,一个比一个能言善辩,理论能力高超,聊天时更是妙语连珠,常常令人不觉东方既白。那时我还在上大学,侯马风度翩翩,言语坚定,理性与激情并存,令人神往,有时开车带我兜风,边聊天边用斩钉截铁的右手比划——“像我这么牛逼一人”,霍,那自信,那气象,令大学生如我心潮起伏,回到宿舍,我暗自在被窝里学着他的样子,把嘴一撇——“像我这么牛逼一人”,于是就觉得自己真的牛逼起来了。想起来了,后来我的那句名诗“通往牛逼的路上一路狂奔”,其牛逼一词之启蒙应该就来源于“像我这么牛逼一人”!徐江又和侯马不一样,我常去天津,在他家听他狂聊,此人目光如炬,眼光歹毒,言语尖锐,幽默犀利,听他讲天下诗人是一种享受,更是一种刺激,经常听得我汗流浃背。更要命的是,这个人渊博得过分,世上的书,仿佛没有他没读过的,聊天时从来都是手到擒来,那种对很多大师的不敬之辞啊,令我心中的叛逆之心如毒虫般昂起来头。我曾暗自发狠,回去要像老徐一样读万卷书,时光荏苒,10来年过去了,读得还是那么贫乏——原来读书,也是一种能力。伊沙出场时,别人基本上就没法说话了,嗓门太大,旁若无人,胖若无人,那时他真胖,被称为“吴胖子”,中气十足,慷慨激昂,往往在很多庞杂的话题中涉及诗歌最细微之处的秘密,不时令我心惊,我和伊沙有过不少通信,那时我还在写很学院的诗歌,在信中与伊沙据理力争,我很奇怪——伊沙哪有那么好的耐心陪我玩儿!这三个师兄,给了我诗歌现代性的最初启蒙,他们对现代性的那种深刻理解和追求,让我至今受教。我觉得他们是中国最早从骨子里理解现代性的几位诗人。
如今,十年已过。伊沙成就卓然,已成汉语诗歌长河中的巨石。徐江的写作,每每刷新我的诗歌认知,我以为,不知道徐江之杰出者,是无法理解汉语诗歌已经走到的深远之境的,那是超越语言、技法,超越一切陈词滥调,直抵诗歌最朴素内核的写作,看似简单,其实凝聚的是40多年的人生体验——汉语诗歌中最高级的人生体验。大巧若拙,绵里藏针。侯马的《他手记》和《进藏手记》堪称“绝代双璧”,他“这么牛逼一人”,想清楚了要写一首巨作时,那就一定是巨作,每读他的这两首巨作,我都会想起当年经常与他在一起时的体验,那种精妙的思辨,横溢的才华,饱满的情怀,融为一体后,竟能成就如此夺目之诗篇。当我去年仔细重读宋晓贤近年来的诗歌时,更是讶异的发现,当年天才的晓贤,竟然通过基督教,获得了强大沉厚的诗歌信念和诗歌力量,其诗歌之深沉、追问、拷打人性,均是在发时代之先音。我为我的这几位师兄倍觉自豪。
由于当年民间立场和知识分子写作的壁垒森严,我对被划到对头们那一堆儿里的桑克师兄的写作近年来关注不多。现在想来,其实也不应该。当年我上学时,其实桑克对我的鼓励很多。只是我们见面最晚,等到我们见面时,对不起,俺已经很“民间立场”了,呵呵。
伊沙、徐江和侯马是我的一个诗歌谱系,我很珍惜这种友谊。他们带给了我诗歌发端时的无限思考。
朵渔和南人则意味着我成长过程中的另一个谱系。对于我来说,他们作为我的师兄的存在,远不如作为我的“下半身”战友的存在那么强烈。他们是我一起写作的最亲密的朋友和战友,一起对陈旧的诗歌价值进行清理和挑战,一起抵挡各种污蔑和诽谤。2004年之后,我们各自走上了相对封闭的纯粹个人写作之途,朵渔的写作,有着越发强大的价值立场和由此带来的决绝内心,在“下半身”当年的战友中,朵渔是最重视技术的,当越来越精微的诗歌技艺与强大而孤绝的个人内心相融合的时候,朵渔的诗歌已经不可避免的成为独树一帜的诗歌风格,他将跨越他过去心中默认的前辈师承,走向个人内心锤炼的诗歌大道,作为他的朋友,我已不可能再提出什么有效的建议,只是去欣赏这孤绝中的诗歌力量。南人是个生命感觉极好的诗人,他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可以随手写作一首令人吃惊的诗歌,他有广阔的童心,世界是他的玩具,他可以像搭积木一样把世界随意组合,搭成他自己哈哈大笑的诗歌,他是智商太高的诗人,他的诗歌其实可以累积成一个巨大的讽刺意味十足的笑脸,真的是笑脸,但却充满荒诞和讽刺——世界,不过是我的玩具而已。谁干得过不以为然的他?我始终认为,如果南人再勤奋一点,他在未来会呈现出令后人惊讶不已的诗歌意义,呵呵,那时这个胖子可能已经是一堆化石了。我对南人心怀感激,我知道他对我的爱,几乎是无条件的,像爱着自己的小兄弟一样的爱,由于他的低调和与世无争,对于这样的爱,我的回报太少。
张后:我觉得在中国诗界,你的性格和伊沙最像,都有一种好斗?豪放不羁?敢硬碰硬的主儿?你对伊沙如何看?保括人和诗歌?我刚访谈过他,前不久(2009年初)你们一同在佛山亮相了?你俩的现身,佛山那地方一百年恐怕都没这般热闹了?我的意思是说,黄飞鸿之后那里就几乎消寂了,你和伊沙将佛山这两个字又锦上添了朵花?为此东道主老任还写了篇文章《“流氓先锋”的“胜利大逃亡”》?我没有看明白?谁是流氓先锋?谁又胜利大逃亡?
沈浩波:任意好的文章标题中,“流氓先锋”和“胜利大逃亡”都加上了重重的引号,这是作为评论者的任意好对这两个看法的否定。这也正是任意好长达6年对我的阅读后,真正知道了我的一个结果。他知道,我先锋得有来自生命自身的大道理,我当然不是“流氓先锋”,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流氓,但我很享受被别人视为“流氓”的感觉,那是一种阅读者被诗人伤害后的愤怒反应——你是一个流氓。哈哈哈哈,我不解释,你们说是那就是,生气去吧!现在觉得我不流氓了,又说我是胜利转身,哈哈哈,不用我解释,任意好眼尖,看得清楚,我从来都遵从着内心最高的价值指引,在生命意志的感召和强烈的个人独立道德的律令下写作,热爱生命,介入现实,笔底流淌的从来只有因这种生命感和情怀内化而成的浓烈情感。
我和伊沙确实有一些相似之处。我们偶然出于同一师门——北京师范大学,偶然都写诗,偶然又有了一些性格的相似之处,这很奇怪。好斗,确实。敢硬碰硬,确实。但说到豪放不羁,我觉得不是,至少我不是。我觉得伊沙也不是。我还是有很多羁的。在内心深处,我其实有很传统的一面。我并不是一个豪放的人。我可以不断打碎写作中的任何羁绊,但不断打碎羁绊本身,就意味着跟自己生命和身体里的众多羁绊在斗争。说明羁绊太多。我觉得伊沙的写作本身,正在越来越不羁,这里的不羁,指的是一种大自由。写作的自由,生命的自由。但我同时又相信,他一定有一种强大的东西“羁”着自己,因为真的毫无羁绊,其写作必然缺乏根本和厚重感,而我们看伊沙的诗,有很强的内心根基,写得很厚,那就是有所羁呀!不要相信任何不羁的东西——那会如浮云般瞎飘的。
很多人对伊沙有着诸多的道德非议。有时候甚至搞得我夹在里面也很头疼。因为我的很多朋友都跟伊沙有过剧烈的争吵。最近的一次是在佛山,阿斐是当年我们发起“下半身运动”时的最年轻的诗人,一直是我生命中重要的朋友之一。在会上,我指责了阿斐,因为我无法理解他们对伊沙、徐江的突然发难——毫无理由;上一次,是我的另外几个朋友方闲海、而戈、金轲、西风野渡,都是我私心认为非常优秀的诗人,但也是跟伊沙展开了规模堪称很大的交锋,人身攻击满天飞,我明白他们为什么愤怒,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德立场,但我无力说服他们,也无力去说服伊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德。所以我的理解是,我尊重他们每个人的立场,我只是他们的朋友,永远不应该也无法干涉各自的道德立场。那是一场看起来是纯道德立场的争吵,有着诗人生命中天然的纯粹感。但实际上,是一场诗人作为独立本体存在的那种巨大的生命独立性导致的生命体之间的对决。但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对于诗人而言,有比公共的道德更强大的内心立场。在我看来,伊沙是一个强大的生命巨兽,他有着很强大的充满欲望的生命感。在这里,欲望绝不是贬义词,欲望是生命的支撑点,我看伊沙,是一个生命意识极其强烈的诗人,是一个非常浓烈的生命体,这样的诗人,天然会遭遇到更多的道德质疑——因为他随时试图甩开道德的羁绊,或者说,他只想遵从自己内心的道德。所以,很多论争已经不是单纯的对错论战,更超越了道德范畴的简单立场,而完全变成了不同的生命体之间不兼容的战斗——一种天性嗜血的战斗。很多年前,我和韩东之间曾经爆发过一场长达七天七夜的网络论战,其实正是这种生命体之间的战争,别的,都是假的。生命体强大,生命意识浓烈的人,必然会深陷于这种战斗之中。生命感,是诗歌最顶峰的感受!可以感受,不可言说。
第二部分:关于“下半身”
张后:我最早知道你好像是你写的《谁在拿1990年代开涮》,后来得知你和你的朋友们在2000年的7月一同发起创办《下半身》同仁诗刊,并写作《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被喻为“在中国文化界引起了地震般的反响,彻底改变了中国先锋诗歌的走向”?当今口语诗的兴波作澜你说和你的网站“诗江湖”有没有相当的关系?
沈浩波:“当今口语诗的兴波作澜”和“诗江湖”,和“下半身”,关系大了去了。新世纪以来的最猛烈的诗歌旋风,就是从这儿刮起来的;新世纪以来口语诗歌的无限放大(遭了多少人的恨哪)甚至是无节制的泛滥,就是从这儿开始的;新世纪以来几乎所有重要的口语诗人,都是从“诗江湖”走出去的;新世纪最初涌现出来的大批1980后的年轻诗人,都曾经受过“下半身”的影响,其中的佼佼者们,几乎都是直接从“下半身”开始起步的,我说的是春树、阿斐、巫女琴丝、水晶珠链、土豆、鬼鬼、旋覆、小宽、溜溜、木桦们。在新世纪的前几年,“诗江湖”几乎就是“下半身”的同义词,而我和尹丽川、巫昂、朵渔、朱剑、盛兴、南人、李红旗、轩辕轼轲们就是从“诗江湖”开始冲上中国诗坛,在我们来到之前的中国诗坛是什么面貌?在我们来到之后的中国诗歌又是什么面貌?这就是历史!而紧接着在“诗江湖”出现的,是另一批年轻诗人,竖、乌青、晶晶白骨精们,后来他们与杨黎、何小竹们另外组建了“橡皮”论坛,当时在几乎所有从网络上起步的年轻诗人心中,都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下半身”还是“橡皮”,很多人是既爱此,又爱彼,难煞人也!再紧接着,一些不甘寂寞的中年诗人跳出来,取了“下半身”的最外在的皮毛,煞有介事的宣称:下半身再往下,就是垃圾,所以要搞“垃圾写作”,虽然这帮人是“下半身”的衍生品,但其实完全丢掉了“下半身”的精神内核,以生产口语废品为荣,成为无才华的口语写作者的集中营,后来又有人搞什么“低诗歌写作”,亦不过追风而已。至此,口语诗歌在网络上既有了大繁荣、大兴盛,同时又开始大泛滥、大口水——但我们不能取消无才华者写诗的天赋*,亦不可能去承担他们所带来的写作恶果,所以很多对口语泛滥、口水纵横的指控加在我身上的,对不起——跟我无关!大约在2005年前后,很多年轻的诗人开始面对他们越来越沉重的人生、生存等问题,同时也面临青春激情燃烧之后写作如何更深入的面对自我内心的问题,那种天才狂欢式的写作,那种一往无前的尖锐,那种“五花马、千金裘、与尔同销万古愁”的浪漫青春的集体酬唱式写作归于休止,“下半身”的那批诗人们几乎不约而同的开始陷入自我的沉思,有人选择了不再上网,比如盛兴;有人选择了不再在诗江湖展示诗歌,比如朵渔;有人选择了其他的艺术之路,比如尹丽川和李红旗;有人停止了写作,比如轩辕轼轲。但“诗江湖”仍然一如既往的担当着汉语诗歌生命现场的重担,这一阶段的中国诗歌的硕果依然凝结于此,中国最好的诗人如伊沙、徐江、侯马、唐欣、中岛、巫昂、君儿、南人、朱剑、马非等越来越饱满、丰富,将汉语诗歌的生命力拉向了灵魂的纵深,拉向了更综合更广阔的境界。当年从“下半身”时期一路杀将过来的诗人,比如巫昂,已经是这个时代最杰出的诗人,当年的青春战友,如今依然与我同行,一个时代造就的人物,岂会真的能被风吹雨打散?我和巫昂、朵渔、南人、朱剑、盛兴依然在中国诗歌的最前沿写作,而当年在“诗江湖”和“下半身”的氛围下涌现出来的中国诗歌的崭新面孔如小引、方闲海(口猪)、而戈、魏风华、金轲、唐煜然(花枪)们,经过长达10年的淬炼,已经成为中国诗歌新的中坚力量。“诗江湖”仍在继续着他的故事,“下半身”的那批诗人们仍在放大一代人的传奇,中国诗歌的先锋部队已经越走越远!作为这一切的亲历者、参与者、推动者、见证者——我深感荣幸!
张后:我读你的诗时,我总将它和金基德的电影某些画面联系起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你喜欢金基德的电影吗?如果用你诗歌中的部分情节让你拍部情感类型的电影,你愿意拍吗?尹丽川和李红旗都去拍电影了,我建议电影名字就叫《通往牛X的路上,一路狂奔》?
沈浩波:是啊,那俩拍电影去了。以前我觉得挺可惜。现在不觉得了。应该尊重朋友的追求。但我自己对电影真的没兴趣,金基德的电影,我都看过,当黄片看的。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黄片搞得太直接,看多了没意思,看金基德的电影,就像搞一个一开始穿了很多衣服的女人,但又一直在挑逗你,等你把她脱了,那就觉得比直接看一个光溜溜的女人有意思。所以金基德在那里绕来绕去,我只是饶有兴致的等着看属于把衣服脱掉后的那一部分,其他的——只是前戏。别说我不懂艺术,他那套我一看就明白,我不觉得有多高级。不就是挖掘内心的极致之狠嘛,相对于诗歌来说,算是艺术的童年期。
张后:我一直觉得你的诗歌也没有什么下半身的概念?我十岁就在胡同墙上写过类似这样的东西?王小丽你的乳房像宝塔,我要趁黑摸上你的宝塔……是不是我比较麻木?写点身体的特征和名称就下半身了?这不抬杠吗?那医院的妇科不是天天都下半身?也没什么大邪大恶的?我觉得你当年(2000年)抛出“下半身”这个概念,完全是故意和某些人或某些集团叫板或抗争?比如我们年轻时候,梳爆炸头穿喇叭裤,是和传统抗争?试问如果以现在的年龄,历史重新演过一回,你还倡导“下半身”写作吗?
沈浩波:你的这个问题,也是我想着力说的。本来,这几年,我几乎是在刻意回避关于“下半身”的各种问题。因为我始终觉得,“下半身”作为一个群体和一场诗歌运动,在2004年之后,随着当年参与者们个人命运的变迁,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史命。作为“下半身”的发起人,我有一种“好汉不提当年勇”的自矜。有什么可提的呢?历史是历史,行进中的我是行进中的我,现在的我不想去沾过去的那个我的光,一个像我这样的诗人,可以永远发出新的光彩,有什么问题呢?不光是我,这几乎是《下半身》杂志主要创始人的一种集体自矜,人生漫长,我们骄傲的内心不允许自己多谈那时的光荣。你什么时候听过巫昂、朵渔、南人、尹丽川、李红旗喋喋不休的谈论他们的“下半身年代”的?
但是现在,我却非谈不可了。因为历史太容易被抹杀。因为我看到了这种刻意抹杀的行为正在发生。我可不会天真的认为,这一场当年曾经摧枯拉朽的掀起中国诗坛集体“向下走”的,具有大拐弯意义的诗歌运动真的是抹杀不了的。真正的现实是,如果我们再绝口不提,你以为会有几个客观的人会面对自己的内心,会公平的表述?用鲁迅的话说,我向来不惮以最大的恶意去揣度中国人的内心。对于很多人来说,恨不得“下半身”从来没有存在过,他们希望自己遗忘掉这一切,也希望整个中国诗歌遗忘掉这一切。
但是,我在呢!我作为中国最好的诗人之一存在着。只要我没有失忆,你们一个也忘不了。很多人的方式是,说我的诗歌写作在“转变”,甚至说我现在的诗歌成就是因为对“下半身”的“转身”,呵呵,他们不知道的是,我是一个灵魂里的“下半身”。我不是说我要死死抱着这个词不放——我早已不需要。而是,我必须诚实的面对自己的青春,我的血液里流的就是这个东西,下半身时代的写作,已经成为我写作的根基。我现在的写作,只不过是在新的人生阶段,做到了内心和题材的更大丰富和写作的充分可能。也许在过去,你们看到的沈浩波,是个腰间挂着鸡巴写作的狂徒,但现在,鸡巴长在心里,长在了魂里。我的诗歌的每一行,每一句,都充溢着精液流淌的那种生命力,那种生机,那种饱满的创造情怀。
你的这个问题,暴露了你的狭隘和对“下半身”的属于集体无意识的那种无知。
什么是下半身?从来都不是“性诗”这么简单和无聊。当然不是,从来都不是。
“下半身”是一种方向,向着更具体、更现实、更有血肉的人生进发的写作方向。这样的写作方向,天然是向“下”的,不是凌空蹈虚,不是抽象的文学概念;天然是先锋的,是向前的,是对传统的不屈和对永远创造新美的坚持,是不做传统文学和诗歌之美的无条件服从的奴隶,是追求崭新的、当下的、现代的诗歌核心和价值。
“下半身”是一种精神,是一种追求生命内核的写作,是灵魂中有鸡巴的写作,是尖锐、反抗、挖掘、探索的写作,是永在拷问的写作。如果回到2004年之前的“诗江湖”网站,你会看到,在遮天蔽日的荷尔蒙之下,这种追求反叛和自由的写作精神,洋溢在每一个老诗人和新诗人的笔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创造体,可以混乱,可以粗糙,但却充满力量和生机。“下半身”使得中国诗歌拥有了身体,越来越多的年轻诗人在开始写作时,写的就是充满身体感的诗,打开身体,获得内心的自由,获得诗歌中的生命感。“下半身写作”,是为生命本身的尊严而写作,是找到自己生命本身价值的写作,是洞悉和了解生命的伟大和挣扎的写作,是拨开那些强加在个人生命上的一切腐烂的文化寄生物的写作。这么多年来,起码我本人,一直走在这一条直路上,从未拐弯。
“下半身”是一种价值,是追寻个人生命尊严的价值。是一种道德,一种新的道德,一种新的纯粹和干净的道德。那些“下半身运动”的创始诗人们,你什么时候看见他们蝇营狗苟?同流合污?从来也不会。他们甚至有着过高的道德优越感,这种道德,贯穿在他们的写作和人生中,从不妥协,对肮脏之物嫉恶如仇。当时在“诗江湖”写作的年轻诗人们,多少人是被这种气氛吸引而来的?我热爱这种道德,它对我的内心的坚定有很大帮助,但我同样不希望这种道德转变为一种精神的洁癖,我不希望我的朋友们成为道德清教徒。实际上这种分歧在我和尹丽川、朵渔们之间一直存在。“下半身”并不是一个整体,它是由一群完全不同的诗人组成的氛围,但我们每个人,都贡献着属于自己的精神和道德,我们有着很大的精神共通之处。直到今天,仍然如此。现在想来,当年的那场我和尹丽川、巫昂发动的“签名”事件,不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写作道德外化的结果吗?
“下半身”是一场反动和一次新生,更是一场巨大的催化。“下半身”反动了朦胧诗以降的种种趣味化的诗歌、概念化和文化化的诗歌,是对文人趣味、文化趣味、学院趣味和平面化的生活口语趣味的反动;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诗人从写作伊始就尊重个人生命体验,追求自由与反抗的写作,追求有身体的写作而不再去写内心浮夸的诗歌,它使中国诗歌开始获得了更新的和更现代的美学体验,催化了中国诗歌迈向更深刻的追求写作者个人生命核心的写作。
由于深刻的骄傲,当年“下半身”的参与者们都不再愿意提及当年之勇,有的诗人为了追求更独立的个人写作,甚至有意与当年“下半身”所追求的价值和方向拉开距离。我能理解这种写作的追求,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被局限在某一个群体中是不能被自己容忍的,尤其是“下半身”的那一群个人精神非常独立和强壮的诗人们,他们不能容忍“下半身”笼罩于自己的写作声名之上,不能容忍个人写作的独立性遭遇任何质疑。包括我自己在内,其实也有这样的心态。但我今天对此已深感无所谓,因为我知道,不会有任何东西,真的能够限制我的个人独立性,我已经天然是我,“下半身”也遮不住我,或者说,我已经足够充分和自信的可以重新面对这个我曾经以为会遮蔽我的强大诗歌词汇——“下半身”了。我还想说的是,当年受到“下半身”影响的一些诗人,这几年,由于这种骄傲的存在,刻意让自己与当年“下半身”的美学方向越拉越远,其实反而生硬的伤害了自己的诗歌,当年的那种生命感和身体感变得越发苍白,这是得不偿失的。其实,追求纯粹生命本体感受的诗歌体验,本来就是放大各人独立内心的,又岂会被区区一个名词遮蔽呢?
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其生命感都是不一样的,都是与其经历、感受、思考过的当下生命体验息息相关的,当我自觉已写出了匹配我当下生命价值的诗篇时,我并不敢去否定当年青春勃发时的生命体验,那些可不是什么“少作”,那是最年轻的生命,最激荡的精血凝聚成的生命勃发之诗。这么多年来,我私心最爱的诗歌,一直是《一把好乳》,那种语言的爆发,那种铿锵的生命感,融入了每一个字节和音符。《一把好乳》是我饱受骂名的诗歌,2006年,因为与畅销书作家韩寒在网络上争辩,而被这个浅薄的青年当做我的历史罪证贴到他的博客上,从而得到了第二次疯狂的流传,这个文学青年和他的更浅薄的粉丝们并不知道,他们口中诋毁不已视为我之不能见人的罪证的诗歌正是我自己心头的珍藏。我知道这首诗歌的意义,几乎可以这么说,这首诗的诞生和一诞生就遭到中国诗歌界口诛笔伐的命运,昭示着21世纪中国诗歌的开始。是的,新的写作开始了——当《一把好乳》这样强健的生命感直接爆发的诗歌被创造出来的时候。
张后:刚刚曲终人散的柏林电影节上,金熊奖颁给了秘鲁电影《伤心的奶水》,电影里讲述一个秘鲁少女法斯塔,恐惧一种在秘鲁恐怖统治时期下被强奸后易于感染的病“伤心的奶水“,为此她偷偷在自己的阴道里塞了一个土豆,以保护自己……如果这电影是在中国拍的,整不好就被说责成“下半身”电影?
沈浩波:你怎么这么爱看电影?阴道里塞土豆,这个情节基本上是满足艺术青年的心理需求的,不高级好不好?
张后:我一直对你的《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中的“从1980年代开始,追求先锋精神的诗人们一直在跟知识、文化进行着较量……这是通往诗歌本质的唯一道路,这是找回我们自己的身体的唯一道路,不了解这一点的诗人,根本没有资格来谈论现代诗歌”这一条目持有异议?假借访谈的机会,和你一辩,我们(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为什么非要较量呢?诗歌的呈现是为了不同风格和领域的较量吗?我们是不是都走进了一条误区?我自己写诗是因为我觉得诗歌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的初衷不必要去和谁较量而写的?也没人可以剥夺我的谈诗论诗的资格?你说呢?诗歌不是政治,不能将诗歌搞成诗政治?打倒不意味着毁灭,涅槃不意味着重生?
沈浩波:亲爱的提问者,您是在教育我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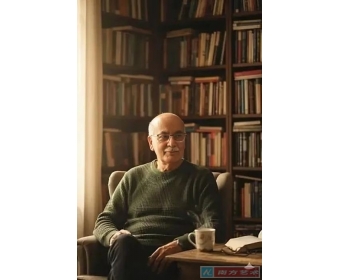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