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选刊》(下半月)第1期“作家班”谈话。
时间:2016年3月27日,地点:北京鸿翔酒店。
把世界流逝的每一分钟变成你自己
黑丰
今天我最想讲的一个话题,就是“把世界流逝的每一分钟,变成你自己的”。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应该把世界流逝的每一分钟,变成你自己。这是一个最关键的点。我跟大家一样,也是一个普通的写作者,今天来这里我就想,无能在任何地方,就是在我所在的杂志社也好,在其他杂志社或其他地方也好,我一定不能被麦克风、被这讲台、被周围的人群,把我蒸发掉,那就完蛋了。因为被麦克风、讲台等蒸发掉,我就不是我本人了。所以我要说一个人,活在这世上,就是要活得像他自己,也就是我刚才说的话题:把世界流逝的每一分钟变成你自己。今天我就从这个话题说起,其实这个话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思考了很久的一个话题,可以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它最初出现在我写的一个长篇艺术随笔里(叫《一个逐渐逼近天造的我的永梦》),(全文首发黄礼孩先生主编的《中西诗歌》2013年第4期),讲到这个笔记,多说两句,因为写这个笔记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因为当编辑很忙,事多,时间都是碎的。所以我只能断断续续的、一点一滴的地写,而且写了又改,改了又写。我常常是在半夜的时候爬起来写作。我的老婆就怕我写东西,因为我一写东西啊就睡不着,满脑子都它,走路吃饭上地铁散步上厕所睡觉都是它(都是要写的东西)。我喜欢把要写的东西带到林子间,带到睡眠里,然后又带到笔记里。我写东西晚上是不能开大灯的,也不开大灯。我习惯了一种刚好刚够写作光源的灯光,你说桔光也可。不开大灯再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怕影响老婆休息,我就只好准备了一个护眼灯,有时是手机灯,把被子盖在头上,勒紧被角(因为北方冷),悄悄地把夜里想到的东西记在本子上。我是喜欢记笔记的,信奉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的笔记本是随身带的,我今天带的是我的第77个笔记本。我觉得一个作家,你不能单靠聪明写作,因为任何人的聪明才智绝对是有限的,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时常带着笔记本,时常观察思考,时常把你的每时每刻观察到的东西,思考到的心得,闪烁出来的火花,写在笔记本上,然后在一个寂静的时光里,回到你的桌上,翻一翻,把它归类整理一下,然后你融进你的散文也可,融进你的小说也可,提炼成你的诗也可,重新在这些最原始的笔记上,在这些“速描”上面,再淬火,再创作。很多大师都是记笔记的,有素描本的。你像著名的画家克利,他就是记笔记的,他的用来素描和笔记的本子(他的日记本包罗万象)长期带在身上,并且一直探索。对艺术理论和各种各样的绘画媒材选择、试用、探索从未停止。他非常勤奋。他的画可以说都是汗水滴成的,是勤奋的结果(当然他很聪慧很有天赋)。在克利艺术生涯中,曾发生过的三次重大事件,第一次是 1901年10月,他访问了热那亚、比萨、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以及其他意大利城市,他观赏了皮罗·弗兰西斯加、乔托、西蒙·马提尼、保罗·乌切罗的作品;第二次,1914年春,北非之行,突尼斯东方文化让他大为倾倒;第三次,1928年,埃及之行,都有重要素描和笔记。作为一个写作者,跟大家交流,我就希望我交流的东西对大家有益。因为这是散文创作的一个笔会,我真想从我这里、从我的创作中,对大家有所启发;希望用我的这盏破“油灯”,把大家的那盏“灯”点燃。世界是混沌的也是黑暗的,大家都在黑暗中提着自己的那盏马灯,孤独地寻找另一盏马灯,寻找光源。然后点“灯”。互相点“灯”,大家都点“灯”,世界用来驱散黑暗的光亮就多了。但所有的“灯”都是有传承的,并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是从“前辈”那里,从我们的“父亲”那里,传承下来的。任何历史,任何文学史、艺术史,都是有传承的。这精神的东西就像火种,从我们的上辈那里借火把“灯”点燃,然后点燃下一盏,点燃无数盏,一盏一盏地传承下去,在传承中发展,在传承中创造,在传承中趋向完美。谁不敢说这东西是我独创的,从无到有的,都是在“父”(天父)的启迪下完成的。讲到这里,还是回到人的本体上来,我的最大的感触就是:我们必须把世界流逝的每一分钟,都变成我们自己,变成一个真实的个体,我们才能写出东西,才能把世界留住。
毫不隐讳地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吃素的基督信徒,我的父亲吃素,我也吃素。我这样说这样讲,把我的信仰把我的真实现状交给大家,把我的所有的东西都交给大家,就是想把大家当作老朋友,做一个真实的人,真实地在这里坐着,我不愿被世界的其他身份分割掉,不愿被诗人作家的名份分割掉,也不愿被《北京文学》的编辑身份分割掉。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昨晚赶到鸿翔酒店,蒋主编问我吃点什么,我说一碗面就行,他搞其他东西,我说不吃,一碗面条就可以了,吃完面条回来,就想今天要讲的东西,其实从前天接到通知就一直在想,因为我不能把大家糊弄过去呀,这么远跑到这里来。把世界流逝的每一分钟,变成你自己,就讲这个,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刚才讲,我不能被麦克风和讲台蒸发掉,还有,我们经常提到的所谓的人民、本土、民族、种族、国家、爱国等,还有机器啊商业化的东西啊,还有知识信息化时代到来的那种泡沫的东西,也不能把我们淹没掉,物化或异化掉,我们一定要回到我们生命的原体上来,感受这个充满生机的世界。人首先要回到原点,就像回到我们母亲的子宫里的那一刻,就像我们初次来到世界的那一刻,用一种涉世之初的陌生的目光来看待这个世界,我们时时刻刻的要用一种初生的目光、婴儿般的目光看待这个世界,我们才可能有真正的新鲜的东西可写。当然,这些话,在其他地方其他作家也说过,我们的前辈我们的父亲们也曾经说过,我就想通过我的嘴,通过我的生命体验,再把它说一遍。其实很多道理很多东西,包括我今天说的,都是“先父”说过的,没有新鲜的。但是我重新把它说出来,然后再通过你的耳朵,通过你的听小骨,然后传达到你的大脑中枢里面去,变成你的记忆,然后你去体会,体会之后你看是不是这么回事。任何时候任何知识只有体会和体认之后才能变成你自己的东西。所以我要说,大师的东西,你像鲁迅先生他所经历的时代,或者其他历史人物,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托尔斯泰,还有果戈里,他们所经历的时代,他们所经历的痛苦,不等于是你的痛苦,他所经历的东西,必须还要通过我们的身体再经历一次,这个时候才能变成你的东西,所以任何东西,它是没有捷径可走的。慢才是快,去认真地观察,去认真地感受,去实实在在地经历,看似很慢,但其实这是快的。
所以,人要是把世界流逝的每一分钟变成你自己,你就不会被蒸发掉。不会被那些大词,如人民的、民族的、种族的、国家的东西蒸发掉。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呢,新闻媒体经常宣传,要我们爱国,爱人民,爱我们这个民族,但是我觉得吧,人首先还是爱自己,爱自己的生命。如果我先成为祖国的,成为人民的东西,那就把我蒸发掉了,真的,因为一个世界上的人首先是一个人,世界首先是人的,然后才是社会的、民族的;首先是人的,然后才是国家的;不是先是国家的,不是这样的,这个东西我思考过了。你如果全部把我的人蒸发掉了,变成国家的东西,我一天到晚,就在搞这个东西,那我这个人全部就是空的,空洞的。所以,人首先要变成你自己,变成有血有肉有生命体征的人后,才是人民的东西,才是民族的东西。不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而是越是人的越是个体的就越是世界的。因为民族的东西它会在人的生命中沉淀下来的,民族的东西(比如文化)是通过个体生命来体现的。这里面是有很多话题可谈的,而且每一个之间都可以展开,但现在没有时间了,我就谈到这里。
所以,你就是你自己。
自己是什么?
你自己就是建立在一个有个体生命的基础上的,有个性,有棱角,不被时代所冲没,所冲刷,不被世俗化的东西把你湮没掉。……我们的东西不能写得像流水线上的那个工业产品,一模一样的东西,这是产业,我们不能把文学作品当产业。我有一个朋友,说他一天一首诗,我一听脑袋就疼。反正我是没有这种能力。我一年也写不了几首,有时一年一首也不首,我宁可写其他东西。有两首诗我写了很久,写猫的,题目叫啥呢?《猫的两个夜晚打开很缓慢》,这名字有点拗口吧,还有一首叫《猫归来》,这两首诗写的时间长。我觉得写一首诗有时并一定比写一篇小说容易。我的诗一般都要更动,写了又改,改了又写,所以这个作品啊,它是要反复进入的。你除非是天才莫扎特,他3岁时就开始弹钢琴,4岁时已经准确无误地弹奏短小乐曲,5岁能谱写小品,6岁开始进行旅行演出。但是贝多芬的作品是要修改的,巴赫的作品是要修改的,而且是反复修改,还有地中海的那个画家米罗的作品是修改的,还有著名的画家克利的作品是要修改的,还有俄罗斯的画家夏加尔的作品是要修改的,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要修改的,作品是修改出来的,不要太过相信一气呵成。李白写“床前明月光”,可能是一气呵成的,但是像李白这种天才是少见的,杜甫的作品是要修改的,所以杜甫的东西比李白的东西更耐读,更具有生命性和深刻性。所以那种一天一首诗,一天一篇作品,流水线上的那个东西,我是很反对的。修改,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信息,就是一部作品,是心跳的生命是汗水是人的血液浇灌出来的;还有一点,就是一部作品,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需要反复进入,需要精益求精。
……另外,我想说的,就是所有的知识,都是关于人的知识,所有的文化都是关于人的文化,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下史,所有的当下史都是人的历史。什么叫人?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了。就是知识的、历史的、文化的,都必须是人的,都必须对人充分尊重,都要体现这一点,也就是回到人的本体。我说要把世界流逝的每一分钟变成你自己,你不变成你自己,人家在那打牌,你在那里看牌,你像我们单位栅门前面的那一溜,天天坐一大圈人,里三层外三层,都在干啥?打扑克。他在看别人打扑克他在那里打哈哈,说你今天的时间和明天的时间一样吗?他就这么一模一样地过下去。这个时间还是你自己的时间吗?这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白白地流地逝掉了,所以这不是他自己的时间。他在那里打哈哈。他在哈哈中被蒸发掉了,他不是他自己,他是哈哈,是泡沫。打哈哈的时间,当然也是时间,时间也不会饶恕他,那个打哈哈的时间最后还是会很残酷很深刻地从你的脸部反映出来,他老了,他老了他有什么,他的人本价值何在?他是虚无的空洞的,他没有体现对他自己生命的充分的尊重。他没有把世界流逝的每一分钟变成他自己。所以知识的东西、历史的东西、文化的东西,最后要体现人体现人本,体现对人的充分尊重;知识的历史的文化的必须是肯定人的,必须是对人的人权的肯定、人的自由的肯定,必须对人的生命充满了挚爱,充满了悲悯,尤其是对苦众的悲悯。因为人的所谓人权,就是要活得像一个人。活得像个人的前提是自由。必须的自由。你说一只鸟,你把它关在笼子里,然后对它说我爱你,这不扯蛋。你把我关在铁笼里,然后爱我,这是我不能接受的。你说“文革”时期的“城乡户籍制”,一个户口本,就把你锁在那里,我听说河南有一个村闹饥荒,没饭吃,那人要出去讨米,但不行,说怎么就不行?他说你这是在丢丑,给党给社会主义的脸上抹黑。民兵在那里24小时站岗放哨,看你往哪跑?结果很多人都饿死在家里,一村一村的人饿死掉了,这还有自由吗?你说你爱人民,你爱的啥呢?爱是前提,是对人的生存权力充分尊重。因为生活的不适宜,人有迁徙和选择在新的地方生存的权力,这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力,是不能剥夺的。所以历史的、文化的、知识的东西,都要体现对人的充分尊重,都要体现对人的挚爱和宽容。对人爱的前提是自由。你说你爱我,但你不给我自由,你把我关在那个铁笼里,然后让我歌唱;你把一根铁链拴在我的腿上,然后让我跳舞,你说你爱我,这是爱吗?艺术创作也是这样,创作的前提就是对人的个性的充分尊重,就是对人的自由的充分尊重,没有自由就没有创作。这也不让写,那也不让写,还有艺术吗?比如我这两天补办护照,因为七月要去一趟罗马尼亚,参加一个“国际诗歌节”。你说我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公安局认可的身份证还不行,还要加上一个暂住证,因为我不是北京人啊,相对而言我是一个外省人,一个外省人在北京办一个暂住证有时比办一个身份证还要难。在通州区郊区,你得带上房东的身份证和户口本;在市区,你得带上房东的身份证和房产证,外加房东还要拿着自己的房产证到当地小区找街道办事处开证明。这就是说我的身份需要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证来证明,中国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证需要用暂住证来证明,暂信证需房东的身份证和户口本(房产证明书来证明,房东的身份证和户口本(房产证)需要街道小区负责人来证明。这样一溜下来,我的暂住证算是没有办成,首先,效区牌楼营村房东李大爷不肯出证,他说我马上要搬出去,不给。“不给就是不给!谁知道以后有啥事找到我头上。”他那白内障眼睛里透出一种非常凶狠的光芒。这几年算是在他这儿白住了。这样我就去找市内当地的朋友,在市里办,却又遇到街道办不给开证明,说这几天风声紧能办,说要是新疆的还要遣回原籍。你说痛苦不痛苦,我怎么才能证明自己洗刷自己,该怎么向祖国表忠诚表决心,祖国怎么就这么不信任我?我是一个清白的堂堂正正的公民啊,我到国外去是参加一个诗歌活动一个学术性交流活动啊,不是干别的。要这么多的证明还不给开证明你把我当什么了,当敌人啊?
不说这些了,说另一些话题吧。
2014年《山西文学》笔会,他们的主编鲁顺民给我出了一个题目《大视野下的本土写作》。我想顺便说说这个“本土写作”,跟现在讲的话题是一致的。前面讲了不被民族性的东西湮没,但也不能本土性的东西湮没掉。那么什么叫本土呢?就是写地方的那种地理和地貌,加上一点特别的民间方言、民歌民谣,就叫本土呢?这个我是不赞成的。……其实本土或本土的东西仍然有一个内在化的问题,要化为身体内部的本土。这个本土仍然需要我们通过人的生命感受,通过感觉、感触、感受、感悟,四个感。感受是核心。你对本土没有感觉,是惘然的。你说本土这东西,不是被感觉过的、感触过的,不是通过感受,到达你生命的体内,内化成你自己的东西,那个本土是表面化的。就跟我们提倡的民族性、人民性写作一样。你说你现在写东西,完全按照主旋的那一套,颂歌式的,稿子碰巧被我看到了,会丢到一边去的。这种东西,看两行就知道,因为在你的文字中我没有看到你的心跳,没有看到你内部的体温,你的东西完全是很表面的,没有进入事物的本质,这种东西我们肯定是不会发的,即使我提上去,主编也不会通过。所以,任何本土,一定要是通过人体通过生命的感受。
人的生命体是什么东西?
人的生命体啊,它是一种白金。一种可以变化的白金——人体白金。人体白金是个隐喻。世界是要通过人体白金,然后变成作品的,人体白金它是个凸透镜,通过这一特殊的凸透折射,把那个世界、那个现实社会,变成作品。所以,这个东西必须要经过生命过它一道,那才能变成作品的,不然的话,它是不行的。我这里有一个诗句,“蝴蝶是这个下午的一半,另一半我听见了落叶的叫喊”(这是安徽安庆的一个诗人写的,不是我的)。像这样的句子,是很典型化的,通过生命感悟过的,而且这里面涵蕴的东西很多。这里有生命体,人体白金的喻体。作品—人体—世界←→世界—人体—作品。人体是个啥呢?你以为那个血肉模糊的东西它是纯物质的吗?不,不是的,不能把它看成纯物质的,它也是精神的。人体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对此就是这么认为的。以前我只是怀疑人体不是纯物质的,但从他的著作中,我得到了确认。人体的神秘性,你从农村呈现出的一些现象就可知道,比如某家有一个死过失去了生命体征的尸体,如果吊唁中来了一个有例假人妇人,这时亡者会口鼻来血。还有人对灾难和危险的预感预知直觉等等。人有时是可以不需要通过思考直接预见事物的。眼皮跳肉体跳及人的某种不适,都在向人发送信号或拉警报。人有这种本能。人有无穷的未知和本能。因为上帝就在人的体内,换用东方人常说一句就是“佛就在我心中”。人是有良知的。人的良知谁给的?上帝给的。为什么我们犯了罪,害怕?恐惧?需要忏悔?就因为内心里有良知。良知是在你诞生之前上帝就给你植入到胚胎中了的,与生俱来。所以,我们要重视生命的感受,重视生命对世界的体认,然后变成作品。身体是一种特殊的神秘的土壤,什么土壤长什么庄稼。
除了生命体以外,再就是语言。语言是另一种现实。任何东西最终要变成语言。一个写作的人对语言没感觉是不行的。刚才讲的“蝴蝶是这个下午的一半,另一半我听见了落叶的叫喊”,这里面有一个隐喻的问题,隐喻是诗歌语言的一个最最重要特征。这里“蝴蝶”是一个重要隐喻。蝴蝶不仅意指下午的一半,也意指上午的一半,意指全天。蝴蝶不仅意指全天,蝴蝶意指蝴蝶;蝴蝶不仅意指蝴蝶,蝴蝶也意指一匹尖叫的落叶。从彩色的蝴蝶到秋天落叶的尖叫,从有机物到无机物,是残酷的。从第一句到第二句,不是平行滑动,是向深度发展的。这不是一种表面的物相。这里发生了一件事,一个生命事件。所以我有个问题,就是个人写作,不管你是写小说也好,写散文也好,诗也好,一定要向深度拓进,不要表面化。
去年有一个作者,是我的湖北老乡,他给我一部长篇小说,还有两个短篇。他说,我这个东西(指长篇)非常出色,可以算得上一流的作品,即使跟托尔斯泰的作品比也不会差。我说这个长篇我看不了,我们也用不了,先看看你的短篇你把短篇留给我看看吧!后来我在地铁里用汉王电子书看了他的一个短篇(是我叫他发的电子版),结果那个东西看了之后我很失望。首先语言也不行,他的语言是读到小说的中部以后感觉越来越不行。半文半白。该省的地方又没省,不省的地方又很啰嗦,拼命的议论发感慨。那议论感慨的东西如果是画龙点睛之笔也好,但不是。没有像深度化方向发展。材料越到后面越堆积。他写那个兄弟把哥哥老大杀死了,前面写得不错,因为那个哥哥老大有个水泥稻场。老二要借稻场堆谷脱谷,老爹、老二、老三那天没有跟老大商量,就把一担一担的稻谷挑到老大的稻场,不知道老大这一天也用稻场。老二、老三、老四把那个稻谷全部堆到老大的稻场上。他是被他的家庭赶出来的,或者排挤出来的。净身出户。但他很发奋,在外面打工,辛辛苦苦挣了一点钱,建了新瓦房,也建了一个稻场。这个稻场般不外租给别人用。刚好那一天他也要堆那收割的稻子,要知道稻子收割之后老放在田里就会生芽子,人偷或鸦雀老鼠吃。不赶紧挑回稻场是不行的。但是他的父亲和母亲没有经他的允许,就擅自把他老二的稻子全部堆在那里,老大当时就很生气,就把那稻子一捆捆地用冲担挑出来,堆在周围坟地里,坟地长满了草,那个稻谷都成熟了的,一丢下去,就全部撒落在草里无法收回。老父批评他,他反驳老父。后来他又推了他的父亲一掌,还把他母亲推了一掌。老三说,你赶紧向爸爸妈妈道歉,否则就没有好的。后来老三回家,回来了后见老大还没有道歉,还在扔那稻子。老三火了就用冲担,一冲担过去,就把老大穿透。致死。整个前面这部分写的很好,原因,发生发展高潮,但后面就不行了。后面写老三帮老大儿子读书考大学,写老大的儿子学木匠在深圳那边犯病,犯病以后进医院里没有钱等等,写老三的忏悔。老三用冲担把老大杀死的,个性已经出来了,后面进一步塑造也可,问题是后面的材料是一堆堆地往老三身上堆上去的。没有触及到灵魂深处的东西,也没写公安局怎么追究。后面就像一个好人好事的宣传材料。不能这样的。应该灵魂深处的忏悔才对。
任何东西要向深度拓进,不要表面化。你小说也好,散文也好,诗也要好,一定要向纵深发展。你的语言,包括你的所有的修辞,都是要向一个无限旋转的漩涡中心的秩序向内推进,垂直的一直深入下去。你不能一部作品有两个枪眼,两三个主题,那就乱套啦。两个枪眼(或两个主题)并不是巴赫金所说的那种复调小说。那说明你的不成功。复调是在主调突出鲜明的情况下显示出的复调。云南有个作家叫肖讧红,他以前的小说我总感觉有多个枪眼,他的那一只笔就像一杆老铳,一打就是多个枪眼。直到《悬棺》写得好,克服了这个问题。材料集中。当时我在外地,我把这个稿给二审的王虹艳,王虹艳也认为不错,但她因为请产假没开发稿会,这个稿子没排上……但不管怎样,这个写作,不能写分岔,不能写出的东西是这样又是那样,这是不很好的,一定要集中所有的笔墨,向深度推进,你说思想的深度、文学的深度、生命的深度、美学的深度都可以。所有的修辞都要向内,垂直,元点就是远点,近就是远,内就是外。
你用生命感受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变成了你自己。你感受这个杯子,这个杯子就变成了你的杯子啦。用存在主义学说,人不是以一个个体的形象出现在这里的,人是一种很广大的存在,周围的山、河流、树叶、草皮,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变成人的生命记忆的每一部分的。我们回忆的时候,是不是就回忆了过去记忆中的河流呀、树叶呀,沙洲呀、草房呀等一些东西呢?所以人与周围的事物是共在的。我与我小时候在冬天打猪草油菜叶共在,那蚀骨的风,那烫手的油菜叶的冷,冷冻到了人体的痛苦的记忆库里,所以我一看到那冬天的油菜,就直打哆嗦,很痛苦。那个记忆太深刻了。它已进入到我的有血有肉的生命体当中去。所以,把你观察到感受到的东西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再写出来就不是空洞的,就不是白开水。所以我要反复强调一定要用生命感受事物,不然,就变成白开水和表面化的东西。你东西写的好,让我感受到了你的心跳,感受到了你的体温、你的血液。你的作品就是有生命的,持久的。外面的世界都是通过人体变化的,人体不能被蒸发,不能被异化,不能变成机器上的螺丝钉、变成了工具、变成长城的一块砖、变成媒介语言、变成宣传机构只允许存在和定型化的那种东西,如果这样,那你这个人体就是非生命的了,人看世界,人讲话,就不是他自己,人写东西,就和这些异化你的东西一模一样了。那个东西就不是什么艺术品、文学作品了。文学作品和非虚构的东西还是不一样的。还有,我们和我们的这个世界,它是渐变的,一点一点的不动声色的,是从量变到质变的。我们只有跟着它一起渐变,“变成它本身”,或把它们变成我们。如果我们不“变成它本身”或把它们变成我们,我们是无法留住它们的。并且我们要把这种渐变贯彻到我们的作品中去。我们观察的时候,要注意这一点。那个画家塞尚,这是对艺术革命起了转折性作用的一个画家,正是他发现世界的这种渐变,刚才我说的,某些部分都是源于他的感受和思考。塞尚这个印象派画家,影响了立体派的毕加索,影响了一大批欧洲的绘画人士。
我有一个先锋小说《走入芈地》(中篇)(发在2008年《大家》第4期上),表现了这种可怕的渐变。文学并不是很广众的一个东西,不是毛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那种东西,那个喜闻乐见的东西是没有什么艺术价值的。文学就是小众的,中国有十三亿人口,但真正爱文学的并不多,它一定是少众的,只有故事才是大众化的。所以我们只能向文学性的方向发展,我们不能把文学葬送在我们手上。或通过我们这一代再下一代,变得越来越白开水化、越来越苍白,这样文学就会消失掉。去年6月《大家》笔会,他们提了这样一个问题,问文学会不会消失,我说文学决不会消失。只要人在,文学就不会消失。为什么?因为人,他需要虚构,需要白日梦,文学就是人的白日梦,如果人没有白日梦,是难存活的。想想从石头到石头、从残酷到残酷,多么痛苦。我的父亲母亲都是种田的,他们没有白日梦吗?有。我的父亲从早到晚就一直孤独地跟在牛屁股后面,耕地耕地,除了耕地还是耕地,没有梦,他们能行吗?那么,他们的梦想是什么?谷满仓稻满仓,金山银山,五子登科?除了这些还有什么?民歌民谣民间故事就是他们的梦。他们用以抵御现实的石头抵御现实的残酷性。可以说,人的绝大部分时光是生活在自己的梦想世界的,在梦的世界里疗伤、休息、休整、安眠,理想化。人是需要理想化的。——所以,只要人有梦想,文学就不灭。
时间是会流逝的,我们能把时间留下来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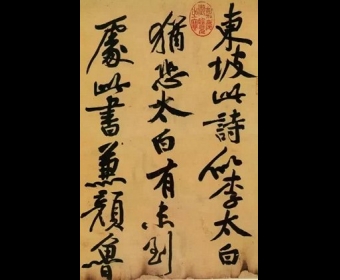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