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访谈①
◇翻译:孙玉莲、秦传安

本次访谈是1966年7月进行的,我和博尔赫斯之间的对话在阿根廷国立图书馆他的办公室里进行,他是那里的馆长。这间屋子使人想起更古老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实际上根本不是办公室,而是这个新近翻修过的图书馆里一间宽敞、华丽、高顶棚的房间。墙上挂着各种学术证书和文学嘉奖状——由于太高,不容易看清楚,仿佛是羞怯地挂在那里。还有几幅皮拉内西的蚀刻板画,使人想起噩梦般的皮拉内西在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永生》中的毁灭。壁炉上方有一幅巨大的肖像画,当我向博尔赫斯的秘书苏珊娜·奎因特罗斯小姐问起这幅肖像时,她的回答非常恰当地(即便并非故意地)回应了博尔赫斯的一个基本主题:“没啥,那是另一幅画的复制品。”
在房间斜对的角落里有两个巨大的旋转书架,苏珊娜小姐解释道:里面的书都是博尔赫斯经常查阅的,全都按一定的顺序摆放,从不改变,以便近乎失明的博尔赫斯能够根据书的位置和尺寸找到它们。比如字典放在一起,其中有一本很老的、重新装过坚硬背衬的、已经用旧的《韦氏英语百科辞典》,还有一本同样用旧的古英语词典。其他的书包括德语和英语的,范围从神学和哲学,到文学和历史,其中有全套的《塘鹅英国文学指南》,《培根现代图书馆》,霍兰德版的《诗体埃达》、《卡图卢斯诗集》,福赛斯版的《四维几何》,几卷哈拉普版的《英文经典》,帕克曼版的《庞蒂克的阴谋》,钱伯斯版的《贝奥武甫》。苏珊娜小姐说,博尔赫斯最近在读《美国内战图史》,而且,刚好在头天夜里,他回了自己的家,他90多岁的老母亲给他大声朗读华盛顿·欧文的《穆罕默德传》。
每天傍晚,博尔赫斯都到图书馆来,他如今习惯于在那里口授书信和诗歌,苏珊娜小姐把它们打出来,再读给他听。按照博尔赫斯的修改,她往往要打上两三遍,有时甚至是四遍,博尔赫斯才满意。有些下午,她读给博尔赫斯听,博尔赫斯仔细纠正她的英语发音。偶尔,当博尔赫斯想要思考的时候,他会离开自己的办公室,缓慢地绕着图书馆的圆形大厅兜圈子,楼下是埋头伏案的读者。但他并不总是一本正经,苏珊娜小姐强调道,这证实了你可能从他的作品中猜想到的:“总是有些玩笑,小小的恶作剧。”
当博尔赫斯走进图书馆的时候,头戴一顶贝雷帽,一套深灰色法兰绒西装松松垮垮地挂在他的肩膀上,下垂到鞋子上。顿时,每个人都停止了交谈,或许出于尊敬,或许出于对一位尚未全瞎之人的同情而犹豫迟疑。他的步伐是试探性的,拄着一根拐杖,使用起来倒像是根探测杖。他个子不高,头发看上去有点不真实地从他的头上竖起。他的面部特征有点模糊,由于年龄而变得柔和,部分程度上被他苍白的皮肤抹去了痕迹。他的声音也软弱无力,几乎就是嗡嗡声,可能是由于他那茫然的眼神,这声音听上去似乎来自于面孔背后的另一个人,他的手势和表情显得无精打采——典型的特征是一只眼睛不自觉地眼睑低垂。但是,当他笑的时候(他经常笑),脸上便堆满了皱纹,几乎像一个做鬼脸的问号。他习惯于用胳膊做出横扫或清除的手势,然后让手落在桌子上。他的大部分话都采用反问的形式,但是,当问到真正问题的时候,博尔赫斯就一会儿表现出一种若隐若现的好奇,一会儿表现出一种羞怯的、几乎是可怜巴巴的怀疑。
但最重要的是,博尔赫斯很害羞。有些孤僻,甚至是自我封闭,他尽可能地避免个人陈述,通过谈论其他作家,拐弯抹角地回答有关他自己的问题,使用其他作家的话、甚至是他们的书作为自己思想的象征。
这次采访中,我们试图保持博尔赫斯英语谈话的口语品质——这一品质和他的作品形成鲜明对照,透露出他对一门在其写作发展中扮演了如此重要角色的语言有多么精通。
记者:您不反对把我们的谈话录下来吧?
博尔赫斯:不反对。你把那些玩意儿装好吧。它们是个妨碍,但我会尽量假装像它们不在那儿一样谈话。敢问客从何来?
记者:来自纽约。
博尔赫斯:噢!纽约。我在那儿待过,我非常喜欢那里——我对自己说:“得了吧,既来之则安之,这是我的工作。”
记者:您指的是高楼大厦的墙壁,大街小巷的迷宫?
博尔赫斯:是的,我漫步街道——第五大道——结果迷了路,但那里的人始终很友善,我还记得我回答了几个高大、害羞的年轻人关于我的作品的很多问题。在德克萨斯,他们曾告诉我肯定会害怕纽约,但我喜欢那里。对了,你准备好了吗?
记者:好了,这机器已经在工作了。
博尔赫斯:那么,在我们开始之前,我可否知道都是些什么样的问题?
记者:大部分是关于您自己的作品,以及关于您感兴趣的英语作家。
博尔赫斯:哦,那就好。因为如果你问我关于当代年轻作家的问题,恐怕我对他们了解不多。因为在过去7年里,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了解古英语和古斯堪的那维亚语。因此,那对阿根廷人和阿根廷作家来说,在时间和空间上跨度都很大。但是,如果我不得不和你谈有关“芬斯堡之战”的片段、挽歌或者“布鲁南堡之战”什么的……
记者:您想谈那些么?
博尔赫斯:不想,尤其不想。
记者:是什么让您决定研究古英语和古斯堪的那维亚语?
博尔赫斯:刚开始我对隐喻很感兴趣。后来,在某本书中——我想是在安德鲁·朗格的《英国文学史》中吧——我读到了隐喻语,亦即古英语的隐喻,而在古斯堪的那维亚语诗歌中则是一种更加复杂的方式。然后,我便从事古英语的研究。现在,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今天,几年研究之后,我不再对隐喻感兴趣了。因为我想,对诗人自己来说,它们已经有点令人厌倦了——至少对古英语诗人是这样的。
记者:您的意思是在重复它们吗?
博尔赫斯:重复它们,一遍又一遍的使用它们,用“鲸鱼之路”代替“大海”,用“海木”或“海里的木头”代替“船”。所以,最后我决定不用它们了,也就是那些暗喻;但是,在此期间我已经开始研究这种语言,并且爱上了它。如今我组织了一个团体——大约有六七个学生——我们几乎每天都学习。我们阅读《贝奥武甫》最精彩的部分:“芬斯堡之战”片段和“十字架之梦”。我们还研究了阿尔佛雷德国王的散文。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学习古斯堪的那维亚语,它有点类似于古英语。我指的是词汇实际上并没有很大的不同:古英语有点像低地国家德语和斯堪地那维亚语之间的中途落脚点。
记者:您对史诗文学始终很感兴趣,不是么?
博尔赫斯:是的,始终感兴趣。例如,有很多人去电影院,并在那里暗自垂泪。这种事经常发生:在我身上也发生过。但我从不为感伤故事或悲惨情节而落泪。可是,例如当我看到斯滕伯格最早的强盗片时,我记得当时这些电影有很多史诗性的东西——我的意思是芝加哥强盗死得很勇敢——没错,我感觉到自己眼里盈满了泪水。我对史诗远比对抒情诗或挽歌更有感觉。我总是对史诗有感觉。那或许是由于我来自军人世家。我祖父博尔赫斯上校曾在边境战争中和印第安人打仗,他后来死于一场革命;我的曾祖父苏亚雷斯上校曾率领一支秘鲁骑兵,在对抗西班牙人的最后一场大战中冲锋陷阵;我另一个伟大的叔叔曾率领圣马丁部队的先锋队——就这么回事。而且,我的一个太祖母是罗萨斯的妹妹——我并不对这种关系感到自豪,因为我认为罗萨斯就是他那个时代的庇隆。但所有这些事情还是把我和阿根廷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也抱有男人得勇敢的想法,不是吗?
记者:但您挑选的那些作为您的史诗主人公的人物——比方说流氓歹徒——通常并不认为是史诗性的,不是吗?然而您似乎要从他们身上发现史诗性?
博尔赫斯:我想,他们身上大概有一种低级的史诗性吧——不是吗?
记者:您的意思是不是说,那种古老的史诗对于我们来说明显已不再可能,我们必须靠这种人物来充当我们的主人公?
博尔赫斯:我想,关于史诗,或者关于史诗文学,如果我们把某些作家(比如写《智慧七柱》的T.E.劳伦斯)和诗人(比如吉卜林,在他的《丹麦女人的竖琴歌》甚或短篇小说中)排除在外的话,我现在更加认为,尽管文人墨客似乎忽视了他们的史诗职责,但说来也怪,还是西部片为我们挽救了史诗。
记者:我听说您把电影《西区故事》看过很多遍。
博尔赫斯:是的,很多遍。当然,《西区故事》并不是一部西部片。
记者:的确不是,但对您来说,它是不是具有同样的史诗品质?
博尔赫斯:是的,我想是有的。在本世纪,正像我说的那样,那么多地方,偏偏是好莱坞为这个世界挽救了史诗传统。我去巴黎时,有人问我——他们知道我喜欢电影,或者说我曾经喜欢电影,因为我现在视力很弱——“您喜欢什么样的电影?”我觉得应当让他们震惊一下,于是说:“坦白说,我最喜欢的是西部片。”他们全是法国人,都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他们说:“当然,出于责任感,我们都看诸如《广岛之恋》或《去年在马里昂巴德》之类的电影,但是,当我们想自娱自乐时,当我们想让自己开心时,当我们想得到真正的刺激时,我们便看美国电影。”
记者:那么,你感兴趣的是不是内容,电影的“文学”内容,而不是电影的技术方面?
博尔赫斯:我对电影的技术方面知之甚少。
记者:请允许我把话题转到您自己的小说。我想问的是,您说过您刚开始写小说时胆子很小。
博尔赫斯:是的,我确实很胆小,因为年轻时我自认为是一个诗人。因此我想:如果我写小说,每个人都会知道我是个门外汉,我侵入了禁区。后来我出了一场意外。你可以感受到伤疤。如果你摸摸我头上这个地方,你就会看到。你是否感觉到了所有那些小山包,那些肿块?当时我在医院里待了两个星期。我做噩梦,睡不着觉——失眠。后来他们告诉我,我差点死掉了,手术成功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我开始担心我精神上的完整性——我说,“或许我再也不能写作了。”然后我的生命将会实际上完蛋,因为文学对我来说至关重要。这倒不是因为我认为自己写得特别棒,而是因为我知道,离开写作我无法生存。如果我不写作的话,我会感到某种懊悔,不是么?然后,我想我应该试着动手写一篇文章或一首诗。可是我想:我已经写了几百篇文章和几百首诗。如果我不能写作的话,我马上就会知道我不中用了,对我来说一切都结束了。于是我想,我应该尝试着写一些我没有写过的东西:如果写不了,那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我干嘛要写短篇小说呢?——它会为我准备好压倒性的最后一击:知道我已经山穷水尽。于是我写了一个短篇,题目叫做……让我想想……我想应该是《玫瑰角的汉子》,大家都很喜欢。那对我是个很大的安慰。如果不是脑袋上挨了特别的一击,我多半不会写短篇小说。
记者:您的作品多半也不会被翻译吧?
博尔赫斯:没有一个人想到翻译我的作品。因此,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那些小说不知怎的就流传开了。它们被译成法语,我获得了福明托文学奖,后来又被翻译成很多语言。第一个译者是伊瓦拉。他是我一个私交甚密的朋友,他把这些小说译成了法语。我想他对作品改进很多,不是么?
记者:怎么是伊瓦拉,最早的译者不是凯卢瓦么?
博尔赫斯:他和罗歇·凯卢瓦都是。晚年的时候,我开始发现,全世界有很多人对我的作品感兴趣。这似乎很奇怪:我的很多作品被译成英语、瑞典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葡萄牙语、几种斯拉夫语、丹麦语。这总是让我大吃一惊,因为我还记得,我曾出版过一本书——我想应该是1932年——那年年底,我发现那本书至少卖掉了37本。
记者:是《恶棍列传》么?
博尔赫斯:不是,是《永恒史》。起初我想找出每个购书者,为这本书向他们道歉,同时感谢他们的所做所为。这里面有个解释。假如你想到37个人——全都是真人,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张脸,一个家庭,住在自己特定的街道上。为什么说,如果你卖掉(比方说)2000本,跟你一本也没卖掉是一回事,因为2000这个数字太大——我的意思是,对于为了理解这个问题而想象来说,这个数字太大。而37个人——或许37还是太多,17个、甚至7个没准更好——但37终归在想象的范围之内。
记者:说到数字,我注意到某些数字在您的短篇小说中反复出现。
博尔赫斯:噢,是的。我很迷信。我对此感到羞愧。我告诉自己,毕竟,我认为迷信是一种轻微形式的疯狂,不是么?
记者:或者说是一种宗教?
博尔赫斯:没错,宗教,但……我想,一个人要是活到了150岁,他肯定会相当疯狂,不是吗?因为所有那些小症状都会发展。直到我看到自己的母亲,她90岁了,她的迷信比我少得多。现在,当我第10遍读(我想是吧)詹姆斯·博斯韦尔的《约翰逊传》的时候,我发现他满是迷信,同时他很害怕疯狂。在祷告中,他祈求上帝的一件事就是他不该是个疯子,所以他肯定很担心这件事。
记者:您是不是说,正是同样的理由——迷信——导致您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同样的颜色——红,黄,绿?
博尔赫斯:我使用过绿色么?
记者:只是不像另外两种颜色那么频繁。不过您瞧,我做了一件有点琐碎的小事,我数颜色用……
博尔赫斯:不,不是。那被称作文体性的,在这里研究过。不,我想你会找到黄色。
记者:但红色也经常变化,淡化成玫瑰色。
博尔赫斯:真的吗?我从来都不知道。
记者:就仿佛今日世界是昨日大火的余烬——那是您使用的一个隐喻。例如,你说到了“红亚当”。
博尔赫斯:没错,我想,在希伯来语中,亚当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红土”。此外,它听上去挺不错,不是吗?“红亚当”。
记者:的确如此。但那并不是你打算展示的东西:通过隐喻性地使用颜色使世界变得更糟糕?
博尔赫斯:我不打算展示任何东西。(笑)我没有意图。
记者:仅仅为了描写?
博尔赫斯:我描写。我写作。至于黄颜色,自有它的物理学解释。当我开始失明时,我看到的最后的颜色,或者说最后的醒目颜色——因为眼下我当然知道你外套的颜色和这张桌子或你身后木制品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是黄色,因为它是最鲜艳的颜色。这就是你们美国为什么有黄色出租车公司的原因。起初,他们想到把车漆成深红色。后来有人发现,在晚上或有雾的天气黄色比深红色更鲜艳。于是,你们有了黄色出租车,因为人人都可以把它们分辨出来。现在,当我开始失明,当世界开始从我的眼前逐渐暗淡下去,我的朋友们就有机会(他们很好地利用了这样的机会)……取笑我了,因为我总是系黄色领带。于是他们认为我真的喜欢黄色,尽管实际上黄色太耀眼了。我说:“对你们来说是这样,但对我不是。因为实际上,它是我能看见的惟一颜色!”我生活在一个灰色的世界,就像银幕上的世界。但黄色引人注目。这可能就是原因吧。我还记得奥斯卡·王尔德的一个笑话:他的一个朋友有一条领带,上面有黄色、红色等等。王尔德说:“我亲爱的伙计,只有聋子才能系那样的领带!”
记者:他可能说的是我现在系的这根黄色领带。
博尔赫斯:噢,没错。我记得曾跟一位女士讲过那个故事,可她完全不解风情。她说:“当然,那想必是因为聋子听不到人们对他的领带说三道四。”这肯定会把奥斯卡·王尔德给逗乐了,不是吗?
记者:我倒是很想听听他的回答。
博尔赫斯:那当然。我从来没有听到像这样被完全误解的事。愚蠢至极。当然,王尔德的话是机智风趣地转译了一种观念,在西班牙语和英语中,都有“响亮的颜色”(loud color)的说法。“响亮的颜色”是一个常见短语,但在文学中和“鲜艳的颜色”的意思是一样的。重要的是说的方式。比方说寻找隐喻:我年轻时总是搜寻新的隐喻。后来我发现,真正好的隐喻始终是一样的。我指的是,你把时间比做道路,把死亡比做睡眠,把生活比做梦。在文学中,这些都是很好的隐喻,因为它们符合某种本质性的东西。如果你创造了某些隐喻,它们往往在转瞬之间令人惊艳,但不论怎样都打动不了更深的情感。如果你把生活想象成一场梦,那是个想法,真实的想法,或者说至少是大多数人都会有的想法,不是吗?“想法人皆有,欲说已忘言。”(译者注:此语出自英国诗人蒲伯)我认为这比让人震惊的想法好,比在之前没有联系的事物之间找出联系要好,因为并不存在真正的联系,所以整件事就是某种欺骗。
记者:仅仅是言辞上的欺骗吗?
博尔赫斯:仅仅是言辞。我甚至不会把它们称为真正的隐喻,因为在真正的隐喻中,两个术语确实联系在一起。我发现一个例外——古斯堪的那维亚诗歌中一个古怪、新颖而漂亮的隐喻。在古英语诗歌中,一场战斗被说成是“舞刀弄剑”或“长矛相碰”。但在古斯堪的那维亚语中,我想在凯尔特诗歌中也是如此,一场战斗被称作一张“人网。”这很古怪,不是么?因为在一张网里,你有一幅图案,一个由人编织起来的图案。我想,在中世纪的战斗中,你有某种网,因为对立双方都有了剑和矛以及诸如此类。于是,我想你有了一个新的隐喻;当然,关于这个隐喻,有一种噩梦般的触觉,不是么?一张网的概念,由活人织成,由活物织成,但依然是一张网,一幅图案。它是一个古怪的观念,不是么?
记者:在一般的意义上,它相当于乔治·艾略特在《米德尔马契》中所使用的一个隐喻:社会是一张网,你不可能从中解出一股线而不触动所有别的线。
博尔赫斯:(很有兴趣地)这话谁说的?
记者:乔治·艾略特,在《米德尔马契》中。
博尔赫斯:哦,《米德尔马契》!当然!你指的是整个宇宙都连在一起,一切事物都是相连的。这就是斯多葛派哲学家相信预兆的原因之一。有一篇文章,是德·昆西论述现代迷信的一篇文章,像他所有的文章一样,也非常有趣,文中他介绍了斯多葛派的理论。其观念是:由于整个宇宙是一个活物,因此那些看上去似乎相距遥远的事物之间有着密切关系。比方说13个人一起用餐,其中一个人今年一定会死。不仅仅是因为耶稣基督和《最后的晚餐》,还因为一切事物都是绑在一起的。德·昆西说——我倒是很想知道他那个判决是如何执行的——世界上的每一事物都是宇宙的一面神秘的镜子。
版权所有:The Paris Review
采访者:Ronald Chri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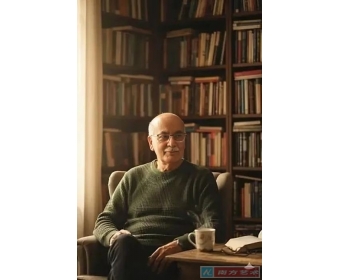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