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过多年的写作实践,我意识到我努力要创造的,其实是一种更接近英雄的诗歌。如果说迄今未能完全实现,那一定是笔力和才情所限,但私下,我一直希望在它们的血肉和魂魄里,应当尽可能多地保留了那些属于英雄的元素。这种血统的诗歌,无意于成为宠物的皮毛,仅仅只为了有闲人的观赏和抚摸而存在;也不屑于以名利为指向,精心虚构出一个幻美的彼岸,去诱引善良的读者上当,——它们应当因自由而坦诚的言说,成为人生前方最先点亮的灯光和人生中途亟待取得的能量;对于一个剧烈变革中的时代而言,作为一种进步和推动的力量,它们有时候是毁灭和再造的武器,有时候是支持回忆和反省的良心。
在我看来,诗歌的言说无论多么精致和纤弱,无非是一种英雄的言说,大体可以看作是一种英雄主义梦想的代用品,带有明显的精神补偿性质。那些在日常生活里终将湮灭的事物,都可以在诗歌中挽留;在黯淡的物质生活里不可能亲历的梦幻,都可以借助诗歌经历。伟人通过推动社会改造的狂风暴雨来宣示或强调英雄的意志,是对人类历史的现场书写,来得比较剧烈、直露,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暴力、血泪和呻吟;诗人通过诗歌写作,重温或者复活经验中那些可以统称之为英雄主义的部分,是在灵魂内部对生存事实的反刍和追问,来得比较舒缓、仁慈,意味着精神于黑暗中永无止境的历险和在烈火中的复活和再生。一个诗人在面对物质世界的时候可能显得软弱和力不从心,但诗歌给他高度,给他以超凡脱俗、直取事物本质的力量和气度,使他变得强大和英勇无畏。——最终是诗歌而不是别的东西,暴露了一个诗人企图通过语言的便利在这个世界上成就一番英雄事业的野心。
理想的地图像冬天的积雪一样慢慢破碎、淡去。揭开盛世的外壳,暴露出来的很可能是一个更为真实的人间。在现实面前,政治家振振有辞的许喏和勉为其难的努力,在旁观者看来不只无力,甚至显得虚伪。这大抵并不是时代的过错,也不能就此责难历史上的某些具体的个人。人类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理想状态,正如大爆炸以来的宇宙物质,永远在崩溃的边缘,在崩溃的中途;人类社会如果是水,当是高原之水,永远有一种倾覆的倾向,永远在向每一个方向的深渊倾斜,是一种崩溃的趋势:无数的人正如无以计数的水滴,永远没有一致的方向,将社会整体拉向自己一面的深渊。
凡是人曾经面对的,诗人也将面对;凡是人曾经遭遇的,诗人也将遭遇。就诗人而言,除了人类的痛苦,再没有别的痛苦;除了人类的命运,再没有别的命运。诗人在本质上不是一种凌架于读者之上的角色。一个人选择了诗歌写作,并不意味着从此变得比读者高明,相反,他可能更谦卑更坦诚,在更高层次上与读者成为同道,成为患难与共的兄弟和最富人情味,也最忠实可靠、永不油滑、永不背叛的朋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个诗人有可能超越国界、语种和时间的限制,在一个更大的范围里建立尊严,赢得尊敬和热爱。那指引人生的车轮碾过流水的、作为人生终极目标的事物到底是什么?在生存的无边黑暗之中,人如果不是孤单的,那么作为支持的友军它在哪里?人们需要知道,除了物质的一面,凡庸的日常生活能否给予更多?人们需要从诗人不倦的言说中,看到对自己主体力量的肯定,从中得到有力的支持和新的启示。诗人的言说也许只是为了安妥自己漂泊的灵魂,但细心的读者,却总能从其中有所发现有所收获,正如一棵树不为什么存在,却给看见的人以力量;一盏灯可能仅仅为了自己点亮,却给黑暗中的眺望者以美的享受和无穷的遐想。苦难的存在亦即诗歌根的存在,它将成功地阻止诗歌总是向比较轻飘的方向蒸发和逃逸的倾向,使诗歌在获得美的灿烂外观的同时,也拥有金属的质地和重量。
二
诗人的生命不在于肉体生命的长短和贵贱,不在于苦心的包装和明里暗里抱成团进行着的阴险和卑鄙的炒作,也不在于对诗歌话语的龚断和对某种方便条件的恶意透支。只有诗歌的门外汉才将不断的发表误以为得到了诗神的首肯,将写进了名人辞典或入选了什么选集,误以为从此获得了诗歌的不朽生命。一个有出息的诗人不应当满足于在已经过多的书海里再增添几本新书,他必须时刻警惕和限制自己内心的虚荣,将手伸入变化的急流深处,紧紧抓住那些诸如石头、河床一类恒定不变的部分,防止为急剧变化的喧嚣声浪所惑而误入歧途。一个有出息的诗人必须具备足够的毅力和勇敢,准备将曾经卸下的粗重重新拿起,比如大地的苦难,否则诗歌高贵的存在必将向另一个方向滑落,成雕虫小技而壮夫不为。最终,谁怯于英雄的代价,从英雄的位置退却,谁就堕入平庸;谁将在炼狱中煎熬着的读者抛弃,也必将被读者抛弃。为艺术的艺术即或存在,多半不是一种现成的权力,只是一个时代诗人和诗歌理论家集体堕落的证据。
真正的写作无异于雕刻,诗人都是他那个时代勤勉的雕塑家,由于他札实的劳动,诗的浮雕将湿淋淋地浮出苦海的水面。真正的诗人都是他那个时代诗歌艺术的集大成者,作为幸福的收割者,他头戴草帽手拿镰刀,从诗创造的田野上将成熟的谷物席卷而去。
有两种诗人,一种为理论写作,他们的意图仅仅在于让人惊奇,一种为内心的要求写作,它们的意图首先在于使自己心灵安妥。第一种诗人诉诸于读者的好奇心,为这个世界留下一些新鲜的句型,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丰富了诗歌的语汇,第二种诗人诉诸于人的灵魂,为这个世界留下更多值得记忆的作品;对于第一种诗人而言,理论可能足以点燃血液,是他们诗歌生命的支点;对第二种诗人而言,理论往往显得短视和孱弱,他们诗歌满载的车辆将从经验出发,碾着理论自相残杀堆积如山的尸体,最终抵达艺术的远方。
三
我之成为一个现在这样的诗人,与其说是源于对诗歌价值的某种坚信,毋宁说是命运的规定。底层生活的漫长经历,使我有幸看到了比常人所见更多的无耻,更多的人性的恶和人性的善以及人性的全部高尚和卑俗。在开始意识到成长的时候,我已经由最初的不情愿看到自己踩死一只蚂蚁、亲自宰杀一只活鸡,变得可以平静地直面一个活人被枪毙时鲜血淋漓的场面。从底层没有声音也没有痕迹的黯淡生活中,我开始明白什么是生的挣扎和绝望,什么是生存的黑暗和灵魂内部的黑暗,我听见了善与恶——灵魂内部的两张嘴两种声音。就像在另一些写作的人那里发生的情形一样,我写诗,不是因为预料到诗歌可能给我带来非凡的荣耀或难以言表的好处,而是基于必须有效地缓解与现实紧张关系的一种类似饥渴的需要。每当这种紧张关系达到不可调合的尖锐程度,很可能意味着一个写作的小高潮也将随之来临。这个时候的河流、道路、人物、原野乃至一切平常的事物都不再只是自身,而是被全新的情绪场赋予了全然不同的含义;另一面,每当一首诗或一批诗歌作品相继完成,现实便重又返回:山重又回到山,水重又回到水,曾经剧烈冲突和令人不安的世界重又恢复了宁静和安详,变得可以忍受,甚至不无美丽和温柔。就我而言,诗歌不仅是试图打开自己的一次没有终点的旅行,也是面向世界时的一种严密防守;不只是对抗的一种形式,也是对话的一种尝试,包含着我对于这个世界意识到的和暂时还没有意识到的全部生活内容;不只是由方块字固定起来的某种经验,而且是与现实一次次摊牌的真实记载和一次次自我拯救的成功事实。在漫长的年代里,是诗歌为我提供了突破围困的秘密通道和眺望风景的高地,是诗歌高贵的手臂引领我从存在的低地上升,获得了穿越人类生活沧桑变化的非凡勇气。诗歌是如此简洁有力地深入了事物的本质,连接起现在与无比悠远的过去,它不再是一种独立于生命的东西,已经与生命本体在最高程度上达成一致,不仅成为参与生活的手段,同时也成为我作为一个诗人的鲜活呼吸。除了诗歌写作,再找不到别的更好的办法,使我与曾经深陷其中的现实达成和解,并与之长时间地和平共处。
四
这是一个失去了标准和判断的时代,从总体上看,这似乎不大可能是一个文学的时代。歧见迭出且针锋相对的争论和求新求异求变的不懈努力,不是映现着文学的繁荣,更多地反映了艺术创造加倍的艰辛,从某种程度上也映现出这个时代的文学家在与强大的本土文化传统和西方文化传统同时遭遇时内心的焦躁和绝望。就当代汉诗创作而言,想象空间的缩小,感觉力的萎顿,追逐现世名利地位的匆忙,以及众多文人墨客私下与雄心纠缠在一起不便明言的垄断的企图和称霸的欲望,使人们更多地忙于“包装”和“炒作”,乃至结帮“对骂”,无力、也无暇去构建起一个时代诗歌应有的价值尺度和美学理想。看来我们的文坛未必像一个文学青年想象中的那样住满了圣徒。这个很大程度上是虚拟的然而曾经是星光灿烂的文坛,也许是拥有极为深厚久远的文化背景的,但它似乎正在日益远离这个背景;它的存在有点像是一次没有预定期限的难产的过程,只有阵痛,却没有期待中的圣婴降生。自由而平静写作、人人都以极欣喜的心情守候着文学新苗绽露头角、并对此报以热烈欢呼的时代,几乎是刚刚到来便匆匆消逝,像别林斯基、鲁迅那样勇于在一个漫长年代里培育和领袖整整一个民族文学潮流的伟大胸襟和气度,已经成为遥远年代的绝响。大师固然很多,但大师无一不是很忙。一切都已经成为资源,被过早地分配完毕;信息社会所能提供的种种便利,不但没有带来诗歌生产力的解放和诗歌内在品质的提高,诗歌写作的职业化和诗歌生产对于作为商业行为的出版业的绝对依赖,反而将当代汉诗写作拖入了一片没有希望的死水。拙劣的演出已经逼近高潮:在这里,在我们这样一个急于工业化的、人人争相发出声音的后农业社会里,更多的是沉沦和埋没,而不是发现和复活;一个初出茅庐的生手最终在文学上能有多大的成就,不是看他在多大的程度上对这个所谓文坛保持了虔敬,从而得到它的奖掖和青睐,而是看他敢于在多大程度上无视这个所谓文坛,并在多大程度上摆脱和战胜了它的威逼利诱和无情压制。
五
感谢曾最先对我的作品进行过一些介绍的《诗刊》和《诗神》的编者,感谢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给我以长期支持的《农村青年》主编 李军 先生,感谢《陕西日报》资深编辑 张延荣 女士、尤其是陕西人民出版社资深编辑、对诗歌鉴赏独具眼光的 何大凡 女士、 李向晨 先生,由于他们的热情扶持和鼎力帮助,本书的出版终于成为现实。这当然未必就是荣耀,倒是意味着我此前二十年地下的写作,将不得不同时进入读者和时间严厉目光的双重审视。对此能说些什么呢?如果一定要说点什么,我只能说这是一本地上的诗人写给地上的人们的诗。作者没有打算为神写作。作为万能的大于诗的角色,神拥有包括诗歌在内的超现实的一切权力,因而不需要诗歌,正如没有肉身,神也不需要进食、打扮、占有和性。诗人充其量只是他那个时代诚实劳动的众多劳动者中的一种。老是想在天堂里占有一席之地,理所当然地享用现成的牛奶和面包,与写作上的见月伤心、见花流泪一样,反映出的是那些二流诗人的矫情。如果还要吹嘘自己,试图把自己打扮成真理的惟一发现者,将与中国古代皇帝总是试图将自己说成上天的儿子一样愚蠢和阴险。作者关注那些和他一样的普通人,并愿意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投身其中,无论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都准备与他们一起走到最后。不敢指望写出的是他们认可的诗歌,但希望能够看出上述明显的努力。
本卷书名借用了一位姓 黄的 先生对它的概括。那时候我是北方内陆小城的一个怀才不遇的求职者,他是南方一家用人单位的大头目,据称颇喜舞文弄墨,我将这批诗作的一部分给他,无非是为了得到赏识。但是没有;他那里不需要诗人,他不是圣者,也没有义务对一位困难中的诗人给以支持和帮助。他只是好奇地问我:究竟是在什么心境下写作了这些愤怒的诗篇?我意识到他可能无意间说出了这批诗歌作品的关键字,这关键字甚至连我本人也曾一无所知。不过本书的出版与此无关,愤怒的宇宙更大,包含的内容更为深广;它既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美的实在,包含美的种类繁多的事物。愤怒未必与丑结缘;比起河面上的浊流和浮沫,愤怒的位置更低,低于河床底下的石头和地层深处的矿物,当天上的闪电在云层里倏然消逝时,它萌孕闪电并支持生命。愤怒比较孤独和内省,只准备在那些不约而至的夜里为等待中的灵魂言说,当它宁静地焕发,人们会想起恒星的某些性质:一颗被愤怒压迫而高度紧张的诗心,会像恒星内部一样更逼近透明,其美感,有可能像星风脱离引力向所有的远方吹送,使偶然经过的慧星将灿烂的慧尾朝向相反的方向。
因此,假定有一日你偶然碰上了本书,请不要像那个自以为是的南方人一样对愤怒本身感到惊讶和不安。愤怒虽然是普遍的存在,但对一个时代而言,只有那些来自真来自爱、同时不可调合、不可替代、并放射光辉的部分,才具有价值。
2000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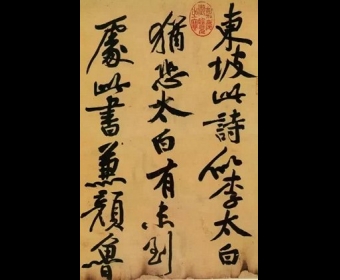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