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岛,原名赵振开,祖籍浙江湖州,1949年生于北京,1969年当建筑工人,1989年移居国外。中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诗人,近十余年来一直被视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现为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宋岗 摄影)
唐(唐晓渡):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无论就个人生活还是写作而言,你都一直处于——让我们使用一个比较谨慎的约定说法——“漂泊”的境遇中。由最初的非常态到后来的常态,这种境遇对你的写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如果变化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这种变化是否首先与你对母语的新的感受有关?布罗斯基曾经有过一个比喻,说在这种境遇中母语会“同时成为一个人的剑、盾和宇宙舱”,对此你怎么看?
北岛:我在海外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你在外面漂泊久了,是否和母语疏远了?其实恰恰相反,我和母语的关系更近了,或更准确地说,是我和母语的关系改变了。对于一个在他乡用汉语写作的人来说,母语是惟一的现实。我曾在诗中写道:“我在语言中漂流/死亡的乐器充满了冰”。我想在布罗斯基的三个比喻外,再加上“伤口”。这种“漂泊”中有一种宿命。我相信宿命,而不太相信必然性;宿命象诗歌本身,是一种天与人的互动与契合,必然性会让人想到所谓客观的历史。
唐:但宿命不也意味着一种必然性吗?当然这是说一种被个人领悟到并认可的必然性,而不是来自外部的、被强加的必然性,更不是指令性的必然性。所谓“认命如宿”。这样来谈“宿命”,似乎和通常所谓的“信念”有点关系;而在众多论者的笔下,你确实被描述为一个“有信念”的诗人。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扩大一点说,你怎么看待诗和诗人的“信念”?它是必须的吗?在我看来你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内心充满困惑、疑虑,并坚持在诗中对世界和自我,包括诗本身进行种种质询的诗人,你是否认为这是一个有信念者的基本表征?信念会给一个人带来方向,至少它要求一个方向;如果是这样,你怎么理解你作为一个诗人的方向?我注意到你有一首题为《借来方向》的诗,在这首诗中,所谓“方向”不仅被讽喻式地表述成是“借来”的,其本身也被从不同的角度反复消解。是否可以据此认为你持一种反意识形态化的“方向观”?而这种眼光和态度也同样适用于你对“信念”的看法?
北岛:自青少年时代起,我就生活在迷失中:信仰的迷失,个人感情的迷失,语言的迷失,等等。我是通过写作寻找方向,这可能正是我写作的动力之一。可我不相信一次性的解决。在这个意义上,“方向”只能是借来的,它是临时的和假定的,随时可能调整或放弃;而意识形态则是一种明确不变的方向,让我反感。你这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信念,对不信的信念。
唐:你说到了“伤口”,这让我想到了你在你刚刚征引过的那首诗中的一个设问。你问道:“谁在日子的裂缝上/歌唱……”这里“日子的裂缝”是否与你所说的“伤口”对应?这首诗开头的一句是“夜正趋于完美”;后面你又说:“必有一种形式/才能作梦”;能否将所有这些——包括你征引的那两句诗,包括末节“早晨的寒冷中/一只觉醒的鸟”的总结性意象,也包括标题《二月》——视为你所说的“宿命”,或者说觉悟到这种宿命的一个完整隐喻?换言之,诗对你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作梦”的形式,飞翔的形式;而你的诗之所以总给人以二月早晨寒冷(我更想说冷峻——当然不止是冷峻)的感觉,是因为它们来自“伤口”,来自“日子的裂缝”,来自——与其说是世界的,不如说是人性和语言内部的——“正趋于完美的”夜?
北岛:现代汉语既古老又年轻,是一种充满变数和潜能的发展中的语言。但近半个世纪来由于种种原因,它满是伤口。说到宿命,其实诗人和语言之间就有一种宿命关系:疼和伤口的关系,守夜人与夜的关系。如果说什么是这种宿命的整体隐喻的话,那不是觉悟,而是下沉,或沉沦。写作的形式,显然与这种沉沦相对应。《二月》这首短诗说的是,在一个“正在趋于完美的夜”里沉沦的可能。再说到宿命与必然性,在我的看来,其实有两种不同的色调,宿命是暗淡而扑朔迷离的,必然性是明亮而立场坚定的。
唐:每个诗人都有自己写作的“发生史”,并在一定阶段上形成自己的“个体诗学”和“个人诗歌谱系”。但你在这方面对绝大多数读者来说似乎还是个谜。能否请你简要地谈一谈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写诗的?迄今大致经历了哪些阶段?有哪些相应的诗学主张?与你有过较为密切的精神血缘关系的诗人都有谁?曾有论者认为你最初受到前苏联诗人叶甫图申科的影响,是这样吗?
北岛:对我来说同样是个谜,就象河流无法讲述自己一样。我试着讲述自己写作的开端,但发现每次都不一样,于是我放弃了回溯源头的努力。我想,写作是生命的潜流,它浮出地表或枯竭,都是难以预料的。外在的环境没有那么重要。我年轻时读到一本黄皮书《娘子谷及其他》,曾一度喜欢过叶甫图申科。他八十年代初来北京朗诵,我只听了三首诗就退席了。他让我恶心。那是由于当年阅读的局限造成的偏差。这个世界诗人众多,由于精神上的联系而组成了不同的家族,与语言国籍无关。我喜欢的多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诗人,包括狄兰•托马斯、洛尔加、特拉克、策兰、曼杰斯塔姆、帕斯捷尔纳克、艾基、特郎斯特罗姆。后两位还健在,幸运的是我还认识他们。二十世纪上半叶是世界诗歌的黄金时代,让我如此眷恋,以至于我想专门为此写本书。
唐:欧阳江河在一篇文章中曾表达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在他看来,“北岛这个名字一方面与一个人的确切无疑的写作有关,另一方面,又与历史的真相想要阐明自身因而寻找一个象征物的要求有关”,由此他怀疑“北岛本人也是‘北岛’这个名字的旁观者。”你认为他的观点有道理吗?你乐于充当“北岛”这个名字的旁观者吗?如果乐于,请谈谈你对他的看法。
北岛:历史与个人的关系的复杂性,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我想起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诗句:“我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在我看来,“伟大的记忆”比“历史的真相”可靠得多。我对“北岛”倒是有时候有旁观者的感觉。
唐:为存在和美作证被视为现代诗的伟大职责之一。它提示着更多被遮蔽、被抹去和被遗忘的可能性。你的诗一方面忠实地履行着这一职责,但另一方面,却又一再对此表示怀疑。在《蓝墙》一诗中,“作证”被表现为一种荒谬的要求(“道路追问天空/一只轮子/寻找另一只轮子作证”);而《无题》则干脆取消了类似的要求(“煤会遇见必然的矿灯/火不能为火作证”)。这究竟是表达了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看法,还是一种必要的语言策略?它是诗的一种自我怀疑方式吗?
北岛:“一只轮子/寻找另一只轮子作证”反应了我在本体论意义上的怀疑。这个世界难道还不够荒谬吗?美国大学的那些大多数学术论文,就是互相寻找作证的轮子。进一步而言,这世界得以运转的整个逻辑体系在我看来都有问题。《蓝墙》是反着说的,《无题》中的“火不能为火作证”是正着说的。
唐:你去国后的作品在保持了此前作品尖锐、机警、精致的超现实主义风格的同时,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除了欧阳江河已经指出的音调和意象更为内敛、更具对话性质等“‘中年风格’的东西”外,最明显的是反讽和自嘲的成份大大增加了。这种变化的心理学依据容易理解,我更感兴趣的是美学上的考虑,能不能请你谈一谈?
北岛:说到美学,应该是你们评论家的事。我一直在写作中寻找方向,包括形式上的方向,寻找西班牙诗人马查多所说的“忧郁的载体”。那是不断调音和定音的过程。诗歌与年龄本来就相关,特别是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岁月年华一直是重要主题。
唐:你一直非常注重炼字炼句。你早期作品中的若干警句至今长驻人心不仅是你个人的一个胜利,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诗学的一个胜利。你近期的作品则似乎更注重炼“境”,并往往通过末句提行来增强其穿透力。同时你的诗还具有阶段性地集中、反复、高度个人化地处理某几个意象的特征。这些意象及其用法对解读你的诗具有“关键词”的性质,诸如早期的“石头”、“天空”,此后的“孩子”、“花朵”等等。斯蒂芬. 欧文认为你的诗“也许……概括了汉诗的传统”。作为《唐诗的魅力》一书的作者,他这么说堪称是对你的极高褒奖;然而在国内,你的名字却是和“反传统”联系在一起的。显然,在这种悖谬中包含了对“传统”的复杂认知。请从个人的角度谈谈你的创作与中国传统诗学的内在关联。
北岛:这些年在海外对传统的确有了新的领悟。传统就象血缘的召唤一样,是你在人生某一刻才会突然领悟到的。传统博大精深与个人的势单力薄,就象大风与孤帆一样,只有懂得风向的帆才能远行。而问题在于传统就象风的形成那样复杂,往往是可望不可及,可感不可知的。中国古典诗歌对意象与境界的重视,最终成为我们的财富(有时是通过曲折的方式,比如通过美国意象主义运动)。我在海外朗诵时,有时会觉得李白杜甫李煜就站在我后面。当我在听杰尔那蒂•艾基(Gennady Aygi)朗诵时,我似乎看到他背后站着帕斯捷尔那克和曼杰施塔姆,还有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尽管在风格上差异很大。这就是传统。我们要是有能耐,就应加入并丰富这一传统,否则我们就是败家子。
唐:在诗学上你无疑是一个倾向于“极简主义”的诗人。极简主义的至境是“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但也容易沦为趣味化,把诗写得太像诗,或故弄玄虚。请问你是怎样把握其中的界限和张力的?为了防止趣味化,或拓展更多的可能性,一些当代诗人不在乎写出来的是不是诗,甚至故意把诗写得不像诗,你也会有这样的冲动吗?
北岛:我意识到这个问题,这也是你提到我的诗中自嘲与反讽的来源。趣味化往往是大脑的游戏,是诗歌的迷途或死胡同。我自己就有这类失败的教训。防止趣味化,就应该把诗写得更朴实些,而不是把诗写的不象诗。当然反诗的试验是有好处的,那就是告诉我们诗歌的疆界。
唐:我注意到《白日梦》是你惟一的一个组诗,这在当代诗人中是罕见的。绝大多数有成就或试图有所成就的诗人都对组诗或长诗投以了相当的关注,希望以此建立自己的“纪念碑”。你是不是对独立的短诗情有独钟?假如的确如此,其根据是什么?在你未来的写作计划中,会有长诗的一席之地吗?
北岛:《白日梦》对我来说是个失败的尝试。这先搁置不提。说到长诗,几乎没有一首是我真正喜欢的。自《荷马史诗》以来,诗歌的叙述功能逐渐剥离,当代诗人很难在长诗中保持足够的张力。我确实只喜欢短诗,因为在我看来这才是现代抒情诗的“载体”,即在最小的空间展现诗歌的丰富性。现代抒情诗根本没有过时,它的潜力有待人们发现。当今“抒情”几乎已经成了贬抑词,那完全是误解。
唐:近些年来国际汉学界不断探讨诸如“中国性”、“中文性”、“汉语性”这样的问题,似乎这已经成了“全球化”背景下的一道文化风景;海内外不少诗人、作家都就此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但至少是我本人,迄今还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你认为这对你的写作而言是一个问题吗?抑或只是个假问题?
北岛:我在十几年前写过一篇文章,谈到“翻译文体”问题。我的主要观点是,1949年以后一批重要的诗人与作家被迫停笔,改行搞翻译,从而创造了一种游离于官方话语以外的独特文体,即“翻译文体”,六十年代末地下文学的诞生正是以这种文体为基础的。我们早期的作品有其深刻的痕迹,这又是我们后来竭力摆脱的。在这一点上,我想这是个真问题,至少对我个人而言。抽象地谈“汉语性”很难,那是评论家的事。
唐:八十年代初,你曾经最早警告说当代诗歌正面临着“形式的危机”,那是“不够用”的危机。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有人认为情况被反了过来:危机依然存在,但已经变成了“形式过剩的危机”。在你的视野中是这样吗?你现在怎么看所谓“新诗”的形式问题?
北岛:现在我依然认为我们面临着“形式的危机”,背后当然潜藏着各种危机。我之所以这么说,因为形式是我们唯一能看到的东西。诗歌神秘莫测,只有从形式入手,才骗不了人。这些年正因为我们忙于空谈,而缺少诸如细读这类的形式主义的批评,才造成鱼目混珠的现象。
唐:既是一个诗人、作家,又是一个事实上的公众人物,这种“双重身份”是否经常令你为难?你是怎么协调二者之间从根本上说是彼此冲突的关系的?
北岛:说来每个窗户都有双重身份:内与外,打开或关上。冲突也可以是一种平衡。
唐:你曾在《背景》一诗中写道:“必须修改背景/你才能够重返故乡”。我理解这里的“背景”、“重返“和“故乡”都有着多重涵义。现在“故乡”的“背景”确实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修改”了,“重返”的可能性也相应增加了,问题是,这种重返很可能不会是你原本所预期的“重返”。它完全可能成为一种错位。假如是这样,你会感到失望吗?
北岛:其实这是个悖论。所谓“修改背景”,指的是对已改变的背景的复原,这是不可能的,因而重返故乡也是不可能的。这首诗正是基于这种悖论,即你想回家,但回家之路是没有的。这甚至说不上是失望,而是在人生荒谬前的困惑与迷失。
唐:相对说来,你了解这些年国内诗歌的发展情况可能要方便些。能谈谈你的有关看法吗?
北岛:这些年来我未置身其中,故有隔的感觉,距离也给了我作为局外人的特权。令人欣慰的是,某些重要诗人包括年轻一代的诗人仍在坚守岗位,他们的作品构成中国当代诗歌的支点。九十年代的诗歌,给我印象是相当复杂的。我常在想,发端于五四运动的中国新诗,在漫长的停滞后,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在地下酝酿,到八十年代初爆发而成气候,然后进入商业化的九十年代。作为一个传统,它的动力和缺憾在哪儿?其实说来,九十年代的问题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是从我们那儿开始的。我们从来没有足够的自省意识,没有对传统更深刻的认知。这是中国当代诗歌根儿上的问题。不刨根问底,我们就不可能有长进。记得八十年代中期,当“朦胧诗”在争论中获得公认后,我的写作出现空白,这一状态持续了好几年,如果没有后来的漂泊及孤悬状态,我个人的写作只会倒退或停止。八十年代的“胜利大逃亡”,埋下危险的种子,给后继者造成错觉与幻象。再加上标准的混乱,诗歌评论的缺席,小圈子的固步自封以及对话语权的争夺,进一步加深这一危机。我有时翻开诗歌刊物或到文学网站上浏览,真为那些一挥而就的诗作汗颜。我以为我们,对此有共识的诗人和评论家,有必要从诗歌的ABC开始,做些扎实的工作,为中国诗歌的复兴尽点儿力。
唐:让我们抓住你所说的(新诗)传统的“动力和缺憾”问题。在我看来它极为重要。你能不能扼要地从正面谈一谈你的个人看法?
北岛:马查多认为,诗歌是忧郁的载体。也许这就是我所说的“动力与缺憾”的问题所在,即在中国新诗的传统中,要么缺少真正的忧郁,要么缺少其载体。这样说似乎有点儿耸人听闻,但细想想是有道理的。你看看,如果一个诗人不是被悲哀打倒的人,他能写些什么呢?而那些被悲哀打倒的人,往往又找不到形式的载体。回顾近一百年的中国新诗历史,是值得我们好好反省的。我想这和我们民族总体上缺乏信仰注重功利及时行乐的倾向有关。
唐:这肯定是一个大题目,但这次恐怕来不及深入了。好在还有的是机会。非常感谢你接受我的访谈。就我个人而言,你与其说回答了,不如说提出了若干问题,而这些问题启示着我们展开进一步的讨论。我想这也会是许多读者的看法。再次深致谢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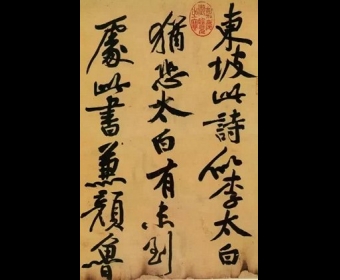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