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与边境
周瑟瑟最新诗集《世界尽头》讨论会在诗人故乡召开

2019年3月23日,“周瑟瑟最新诗集《世界尽头》讨论会”在湖南湘阴周瑟瑟的故乡召开,系第四届“栗山诗会”活动之一。活动由湖南省诗歌学会、湖南理工学院文学院、湘阴县文联、《卡丘》诗刊主办,湘阴县诗歌散文学会承办。
160多位来自湖南、武汉、河北、广东、新西兰等地的诗人、作家、批评家、翻译家参加。周瑟瑟向湘阴县诗歌散文学会、湖南法华古寺白梅诗社、张家界天门寺、圣安寺、南泉寺赠送诗集《世界尽头》,湘阴县诗歌散文学会会长姚娜,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湖南省佛教协会副会长释怀梵法师,岳阳市佛教协会副会长、湘阴法华古寺主持、白梅诗社社长早国法师,接受了赠书。
《世界尽头》是周瑟瑟最新诗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百年诗库·实力诗人”之一,全部为新作,并且还收入了诗人参加拉丁美洲国际诗歌节的摄影作品与诗人的书法作品,古朴典雅的裸背装,外加牛皮纸护封,厚达500多页,智利聂鲁达黑岛故居的鱼形旗与古老的风铃摄影为封面,独特的国际化装帧设计风格让人爱不释手。这是周瑟瑟继《暴雨将至》之后,对“元诗歌简语写作”与“走向户外的写作”的进一步实践,超语义的文本更加典型,在无意义中建立新的意义,是近年来当代诗歌现代性探索的成果之一。
诗人、批评家黄明祥主持了《世界尽头》讨论会。王跃文、梁尔源、罗鹿鸣、路云、张战、李建春、雷武铃、草树、荣光启、李不嫁、莫笑愚、典裘沽酒、杨厚均、张勇、吴投文、刘羊、周艺文、陈惠芳、陈群洲、宾歌、李冈、陈新文、周伟文、高宏标、刘起伦、云经立、肖歌、(新西兰)萧萧、刘炳琪、叶菊如、茉棉、莫莫、魏斌、熊棕等先后发言,从《世界尽头》谈到了“写作与边境”、“走向户外的写作”,以及“好奇诗人”、“目击而发”等有价值的话题。
下面摘录部分诗人的相关观点: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作家、诗人邱华栋:《世界尽头》是周瑟瑟一年时间的作品的结集,继《暴雨将至》之后,他再一次强化了他的“元诗歌简语写作”。他在创造接近事物本质的极简的写作,他采取的是冷客观的语言策略,以索绪尔语言学的“能指-所指”来解释他的写作较为恰当,他在建立诗歌语言的无意义中的意义,从“第三代诗歌”、上世纪90年代诗歌叙事到口语或口语化写作,诗歌语言的探索经历了波浪式的发展,现在似乎处于停止状态。周瑟瑟在他大量的写作实践中,开始创造属于他的诗歌的“语义”或“超语义”。祝贺“栗山诗会”在他的故乡举办,我不能来诗人的故乡参加“《世界尽头》讨论会”,问好新老朋友们!
《十月》编辑、诗人谷禾: 近几年来,诗人周瑟瑟和他以身践行的“走向户外的诗歌写作”越来越引起了诗坛内外的重视和关注。在我看来,这一诗学观念所导向和强调的不仅是“诗写”与现实的对应,更是诗人在场的目击,以及其通过现场诗写所拓展的诗意空间,它犹如费孝通之于《乡村中国》,曹锦清之于《黄河边的中国》,布尔迪厄之于《世界的苦难》,以及奥登之于《战地行记》,更遥远的杜甫之于《三吏》《三别》和《秦州杂诗》。需要强调的,周瑟瑟不是在寻找着典型化的诗歌,而是在行走中不断相遇着最日常的诗歌。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在以一己之力不断拓展着自我写作的边界和我们对诗的认知。《世界尽头》就是这种不懈探索结出的丰硕成果。
湖南省诗歌学会会长、诗人梁尔源:周瑟瑟是一个勤奋多产的诗人。也是湖南诗人中颇具国际影响的诗人。周瑟瑟的诗歌在语言表达上讲究“极简主义”,白话和短句是其标准性的表征。但这种“简约”是不“简单”,而是力图返回语言的本体,予生活与世界以重新命名,并对生活与世界充满了敬畏。在“言不尽”的总体审美意蕴中清晰地指向“世界尽头”——有关于生存世界“真理”或“本真”的猜度。尤可称道的是,诗人在返回语言的本体和指向“世界尽头”的同时,也从一而终地指向了“自我”,有反思,有追怀,有悲悯,有叩问……是“有我”的诗学。“我”、“语言”、“世界”三者在互动和并进中呈现出真正的艺术张力。
湖南省诗歌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诗人罗鹿鸣:这几年,周瑟瑟以每年出版一到二本诗集的暴雨向我倾泻,直将我逼入《世界尽头》。在这里,我遇到了无数的动物——或可爱或可憎或可怜。
在这本新书里,及物的诗写,涉及动物的最多。我粗略地按目录中的标题做了一下统计,就达四十多首。既有当下的动物,也有史前的动物;既有现实的动物,也有幻境的动物;既有出世的动物,也有入世的动物。天上飞的动物有鸟、杜鹃、大雁、鹰、鸽子、萤火虫;地上跑的动物有虫、牛、马、狗、猪、猫、白犀、豹、狮子、海狮、老虎、熊、盘羊、羊羔、恐龙、骆驼、鸡、狐狸、刺猬、老鼠、松鼠、蛇、蜘蛛;水中游的动物有鱼、青鲫、江豚、海豚、企鹅、象龟,等等。
我在想,作者为何写了这么多动物之诗?我看不仅仅是作者的观察力强、记忆精准,而是这一群动物群像隐喻着什么重大的使命,以动物之所指扩引为能指,唤起人之于物的共鸣。动物身上有很多别的事物所没有的诗意,它能够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动物的态度、立场与生存的境遇,从而由物及人,将人的焦虑、压力、窘境间接表达出来,达到寄物抒怀、言近旨远的效果。在写作客体上,作者已转入对日常生活的深挖精耕;在写作手法上,摈弃技巧,完全浸入一种口语白描,以一种轻淡的笔法化入平常事物。而这群动物便是作者找到的一个通向物性深处的幽秘洞口。
我在他众多的动物诗中,拈出几首写猪的诗仔细研读过。发现猪也分门别类,写到了江猪、花猪、横猪、野猪。这些“猪诗”,轻描淡写、生动活泼、诙谐机智,像一幅幅画面的切换,富戏剧性,读后又大快朵颐,或酸涩苦辛,唤醒我们沉睡的悲悯情愫。
《江猪》其实写的不是猪,而是写的江豚想救屈原而不得、自己也还需救赎的故事。《花猪》是我亲眼见他在手机上按出来的。2017年8月25日,我与他同车去常德参加湖南年度诗歌奖颁奖典礼,所坐的大巴车在宁乡段高速公路上跑的时候,他就灵感骤至,立马成诗。一头花猪从山上奔下来咬住裤腿,到回味中午在长沙吃过美味花猪肉,从一首乌黑的躲进灌木丛的诗到骑着花猪向益阳跑去,频繁的意象转换,跳跃的思维,都给人一种目不暇接的审美趣味。
《野猪》这首诗,给我的冲击是最大的,其情境设计在过新年的前一天,在这个喜庆的、亲人团聚的日子,一头野猪闯入人间,被人与狗致死。几乎是将一篇短篇小说的题材浓缩在23行诗中:那头在河边出现的野猪,被大狗小狗追赶,躲进草丛中,村民用锄头挖它,它奋起反抗,先是咬住“凶手”的手腕,后又咬住了一条“帮凶”狗,虽经浴血奋战,最后还是寡不敌众,被打死在河边。尽管死前它嗷嗷大叫,那只有苍天能听懂的呼号,人类还没有学会谛听。它改变不了最终被打死的命运。尤其最后那一句:“走出山林的野猪/死得没有一点尊严”,令人震撼,意味深长。人与动物一样,也是环境的产物,离开供养与保护自己的环境,危险就随时可能发生,那种安全感也荡然无存。鱼离开了水的结果人尽皆知,虎落平阳遭犬欺的道理大家都懂。但作者在给野猪的挽联里用了“尊严”一词,这个在人类社会里稀缺的东西,是不是也是动物们渴求而不得的“痴人说梦”呢?
《横猪》里的猪也是一头具有初心、葆有野性的猪。作者臆想自己服用三次公猪脚炖的草药,来恢复那种天生的野性,摆脱各种束缚。是不是说我们的人性被某种强大的东西压抑已久,本真与本性丢失在慌不择路的逃逸之途。如果作者的表哥给他开的处方管用,我也想煎服这剂良方,恢复自己的活力与本性。不过,我再怎么也不会像横猪那般横冲直撞,不仅因为我敬天畏地,具有底线与红线思维,也因为世上各种火车、汽车在窜,我明哲保身的理由是:肉身是碰不过铁家伙的。
诗人、艺术家黄明祥:虽然主持《世界尽头》讨论会,我有些话并没有说,也不止下面这些。
假设一个哑巴突然开口说话,也许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他的口头表达能力在短时间内突飞猛进。近二十年,自媒体打开了人们的话匣子,也打破了语言文字的专业藩篱。现在,无名者的语言文字水准盖过作家是常有的事。诗人应该有紧迫感,更多的“对手”并不在诗人圈子。
我的印象中,大致从2017年开始,周瑟瑟启动了一种“暴写”模式。我理解,他在将倦怠的感官重新激活,恢复少年的新鲜知觉。一个平日里悠悠漫步的人,不知哪天突然暴走起来,运动量的剧增极大地刺激着他的关节、肌肉。瑟瑟的父母前几年先后离世,生命之痛的暴雨应是在他的天空下过,他2018年出版的诗集名字却叫《暴雨将至》,他心中还有另一场暴雨。此次,又将献给智利、哥伦比亚的《世界的尽头》带回故乡。他曾经反复跟我提过一个概念——启蒙,并说诗人要自己给自己启蒙,不要争论。因此,我进一步将他这种对自己施暴的方式理解为他对自己的重新启蒙。他不仅在国内“暴写”,也在国外“暴写”,对自己施暴不分国界。他提出走向户外写作,将自己拉将出去感知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
瑟瑟说的“走向户外”,似乎是一个宅男痛改前非。艺术家阮国新先生在赠我的一幅画上的题词:“云里雾里路里,不知要去哪里,天地空空荡荡,随便走走可以”。瑟瑟说的户外,并非野外。户外,比野外更广阔,比如街道。这个说法,将世界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室内,一部分是户外。户外之大,正好反映室内之小。走向户外,除了包含走出房子,也包含个人走向人群,敢于进入人群,在人群中展现个人,正是近二十年来最大的变化。瑟瑟是这样一个人,一个这样的诗人。他又是一个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诗人,通观《暴雨将至》《世界尽头》的诗歌,都是瑟瑟目击而发写就的。评论家陈亚平说到的“简语”,是当今语言运用最多的形式,不仅诗歌,瑟瑟干脆利落明快很多,他在诗里问“有没有大刀阔斧的理发师”。
诗人、批评家路云:瑟瑟的写作在经历卡丘主义阶段之后,也就是说他走到了这一阶段的尽头,具体点说就是他在认同“解构”这个词的玩法之后又以其道反施彼身,最终完成了对“写作解构之类的诗”本身的解构,这意味着得淘汰原来的关于写作的观念系统,重装一个系统。《世界尽头》证明这个新系统运行速度快,几乎每天一首,稳定性好,差不多坚持快两年了,而且像苹果系统一样能抵抗各种病毒,这个阶段瑟瑟不再被任何主义所动,以即兴的方式深入现场,毫无挂碍地在表达。对于瑟瑟来说,“世界尽头”就是现场,写作的奥秘或者说进入的路径就是即兴。
希尼有一首诗,《来自写作的边境》,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写作,一个是边境,正好可以帮助我加深理解瑟瑟这个写法,即一个诗人如何在语言世界再次突围,当然前提是这个诗人是一个热衷于创造的人,而不是一个守成的诗人,这两者思维方式不同,都有相对应的典范人物,没有高下之分,瑟瑟是一个典型的创造性的诗人,因此他很容易就能触及写作的边境,对于写作者而言,差不多就到了语言世界的尽头。摆在这里的,仍然是两个老问题:一味追求创新很容易滑向肤浅与搞怪,而沉迷经典则难勉滑向俗套和无效。如何解决这两大难题,瑟瑟选择用作品说话,具体的我就不说了,说一个总的感受,我认为是有效果的,是因为他挑战了我的观念,在最初阶段带给我不适感,显然,对于创造性作品,如果没有带来不适感,则说明这个创造是可疑的。
对应于瑟瑟的写作,我想到张枣的一个感叹,为什么诗人写到最后还是要勇敢?
现在我多了一些理解,勇敢源于对创造性不懈的追求。感谢瑟瑟的勇敢与创造,带给我阅读的快乐,并反观自身的写作,眺望还在遥远之中的隐约可见的尽头。
诗人、批评家、《明天》诗刊主编谭克修:早前的周瑟瑟,属于一个沉醉于大题材写作的诗人。不少诗人认为,大主题类型的写作,容易成就大诗人。据我的观察,别说那不是通向大诗人的必经路径,对多数诗人来说,反而是陷阱或歧途。大主题类型的写作,同时对思想深度,文本结构能力,语言能力提出了超级考验,作为诚实的诗人,或者说成熟的诗人,就算他偶尔也耽于某种自认为的超级题材带来的大诗幻觉,也会敏感到其中的危险因子。大约三年前,周瑟瑟突然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过去的大主题类写作,转向了即兴式写作。他随时随地在写诗,就用手机写,不再预设什么主题,不再在意于每一首诗多么成功,语言上不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而在于写作本身带来的快感。他的诗歌写作就是生活本身的重要部分,他时刻在让具体而微的生活,和他的肉体,语言发生肉搏战。他的身体到哪里,诗就在哪里出现。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这种看起来无限碎片化的写作,却是一种真正在场的写作,身体写作。他不在乎是否写出的是一首大诗,而在乎自己是否在写作的路上。周瑟瑟近年的写作,让我想到一个词——行吟诗人,一千年前从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开始出现的行吟诗人。当然,周瑟瑟属于新派的行吟诗人。他把自己的整个生活状态,沉浸在诗里。他也不再迷醉于某种之前那种元写作之类的先锋口号,或卡丘概念,把自己还原为一个行走在大地上的诗人。他把诗集命名为《世界尽头》,已经明确说出了这些信息。走到哪写到哪,一直到世界尽头,一种让自己的身体和诗歌同时抵达远方的写作。这种写作本身,显然比具体分析其中某首诗的得失更有价值。
湖南省诗歌学会副秘书长、诗人刘羊:周瑟瑟在中国诗坛是一个越来越庞大的存在。他在知天命之年仿佛诗神附体而知诗命,在诗学理论、创作实践和诗歌行为多个维度迸发出持久而惊人的创造力。
周瑟瑟是在诗学修养上知行合一、持续精进的诗人,他的诗歌是“有范”的诗歌。这种“范”,是家国范和国际范的统一,是极简主义和精确气质的碰撞,是“灵范”和“范式”的对话。
在他的最新诗集《世界尽头》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有两点:一是诗意发现的“边缘情境”,二是诗歌语言的“膝跳反应”。
“边缘情境”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提出来的,指的是当一个人面临绝境——例如死亡、失败、生离死别时的一种突然觉醒,这个时候,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对话关系出现了全面断裂,赖以生存的世界瞬间瓦解,于是,人们不得不睁开眼睛重新认识这个熟识的世界。用“边缘情境”去读周瑟瑟所作的一系列缅怀父亲母亲、回望故乡的诗歌,就可以理解化身泥土的父亲为什么会看着我说:“在异乡/如果水土不服/你可以吃了我”,就可以理解《世界尽头》的很多特别体验。
“膝跳反应”是生理学概念,移植到这里是想说明周瑟瑟诗歌语言的那种特有的感官性或者说身体性。以《死海》为例,诗中体现身体感官的词语(如自杀、躺、闭紧嘴巴、享受、涂抹、美容等)有十余处,这种写法能引发读者强烈的代入感,产生直接的身体反应和精神共鸣。这样的作品在诗中很多,如《地球》《戈壁大漠》《方言》《我原来生活过的地方》等等,这是否是周瑟瑟提倡的“简语写作”的一种美学向度?尚不得而知。总的感觉是,他的诗歌除了需要用经验来链接,还需要用身体来阅读。而这,正他诗歌语言的不凡之处。
潇湘晨报新闻研究室主任、诗人李不嫁:世界或许有尽头,但诗歌的追求是没有尽头的。从周瑟瑟这本新著,我看到一个雄心勃勃的追求者,朝一个既定的方向高歌猛进。许多诗评家已经对他的简语风格和“走向户外的写作”予以肯定。此话题的提出,对死板、呆滞的诗歌写作有纠偏的意义,瑟瑟在这条路上的奔跑才显得活跃。正如本书的扉页所题写的献给智利、哥伦比亚,那是聂鲁达的智利,是马尔克斯的哥伦比亚,那是两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名字。
诗人、批评家李建春:我曾在为瑟瑟的前一本诗集《暴雨将至》写的跋中,赞叹他的明朗敏捷诗艺和近于空性的、长袖善舞的写作状态。《世界尽头》这本书把《暴雨将至》中出现的独创性都延续下来了。不同的是,过去的作品已发完,不再收入,因而在审美品质上更为纯净明确。都是去年、前年不到二年的作品。唯一的差别是词触及的对象。周瑟瑟是一个已到了“目击成诗”境界的诗人。整本书给人的感受,像波斯地毯一样,在一个平面上展开,无尽的事物,无尽的惊奇和喜悦,若有所思,点到即止。我觉得他实际是一个“远方诗人”,一个“好奇诗人”,他所写的东西,已不再是过去爱提的日常生活了,日常性美学在他的诗中已经过时。这是我的一个感受。在周瑟瑟的笔下,一种新的美学已经出现。它的意义还有待于深入探讨。
诗人、批评家草树:这些年周瑟瑟一直在行走,边走边写,结集《世界尽头》。从南岳到安第斯山,从北京到哥伦比亚、智利,所到之处,诗篇如野草生长,遍布于野。周瑟瑟倡导走向户外的写作,其核心是走出书斋,面向现场,因而他的诗也就自然而然脱尽书卷气,有强烈的在场感。《世界尽头》的诗有着一个共同的基本特征,干净,鲜活,口语生成的是具有吉光片羽般能指意蕴的语言形式,难能可贵的是,它从口语诗政治正确和反驳姿态中摆脱出来了,是一种独立的、不反对什么、立足于倾听声音的写作,既没有寻师访道式山水诗的仙气,也没有悲天悯人的伦理性感叹,而是带着烟火气和生命气息,有一个活生生的写作主体在场,有一种语言感觉的沉浸。它对当代口语诗写作做出了一个低调的示范,冲淡平和的背后,有着“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大境界。
湖南理工学院文学院教授、诗人、批评家杨厚均:几年前父母的相继离世,拉近了周瑟瑟与他自命名为“栗山”的故乡的距离。“返乡”在瑟瑟这里,成为一种常态,既是生活的,也是生命的。在他的诗里,父母得以复活,他自己得以重生。他无限接近生命的终极处。
2018年2月的某一天,寓居北京的瑟瑟在梅兰芳大剧院听家乡花鼓戏剧团刘光明先生吟唱屈原的《山鬼》,我以为这于瑟瑟的诗歌写作是一个重要的事件。他写了一首诗《在梅兰芳大剧院听<山鬼>》,父亲、黑夜、赶路、哀音、神灵,这些意象聚合在一起,构成先辈的世界,故乡的世界,也是他自己要抵达的世界,这或许就是他说的“世界尽头”?
与此同时,他周游世界,到拉美,像当年的父亲,不断赶路。空间拉大了,视野开阔了,但焦点却更集中了,他诗歌的原乡“栗山”更清晰了:亲切而神秘,琐碎而伟大,超然又哀伤。
“世界尽头”,就是此在的故乡。
由此,他的诗歌在形式上便如此放心地谋求一种被称作“简语”的境界:随便从某个语境出发,顺其自然,且行且走,不经意间便抵达另一个世界。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湖南科技大学教授、诗人、批评家吴投文:周瑟瑟的诗歌创作日益精进,不断带给读者新的惊喜。他近期的诗歌更多地融入了叙事的因素,带有强烈的现场感,显得新奇而且充满情绪上的生动和饱满,使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恢复了诗性的诱惑。他的写作看起来随心所欲,实际上却有老到的布局,一切似乎都是自然地拥到他的笔下,却有秩序上的妥帖感,不显得拥挤,也不显得松弛。他对抒情的理解大概有自己独到的用心,叙事带着情绪上的变化,使抒情在写实中有一种绵延的厚实。说到底,他近期的诗还是延续着原来对幻觉的陌生化处理,对生活的介入表现为瞬间的领悟,使生活的一瞬间停留在记忆的印记上。周瑟瑟近期的诗在修辞上也不刻意,追求水到渠成的本真表达,眼见为实,却有下笔成趣的情调,这使他的诗里晃动着生活纷纭变幻的光影。作为一位成熟的诗人,他在追求写作的变化中有一种自在地面对生活的底气,所以,他写作的横断面很宽,同时也有内在的深度。
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诗人、翻译家雷武铃:我读周瑟瑟的诗,感觉他的诗句一直在运动,从不停留,最后一句结束后仍在向前。人们会因为他的诗不聚焦,抓不住他诗中的焦点,难以进入沉浸、留连式的阅读而感觉困惑。在知道他是个深有佛缘的人之后,我才醒悟到,他的诗所追求的,也许正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至高境界。
衡阳市作协主席、诗人陈群洲:在当代中国诗坛,周瑟瑟的特别之处在于他独有的写作路径、黄金写作态势和带给繁荣发展中诗歌的影响。写什么,怎么写,始终困惑着包括许多成熟诗人在内的诗写者。事实上,他从来没有为题材和技巧苦恼过。作为这个春风激荡的时代的发现者、思考者、记录者和探索着,他保有与众不同的写作方式、昂扬激情和旺盛的创造力。他有目共睹的常态化高产无疑是诗歌的一个异象。跟读他的创作,我认为,跟同时代诗人比较,他的诗歌至少有两个个性化特点:完全放开的写作,始终在场与及物。这也是他走向户外的写作理念结出的果实。他的诗歌创作永远处于一种极度轻松自如的状态,永远有着极其丰富的表现力。在他的视界里,几乎没有什么不是诗。而在场与及物,又诗化了他的生活,拓展了他的创作源泉。就创作风格而言,周瑟瑟跟写出了《尤利西斯》的意识流小说代表性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异曲同工,擅长于通过日常生活和精神变化的细致刻画,揭示人类社会的悲喜、英雄与懦夫的共存以及宏伟与沉闷的同现。
衡阳市诗歌学会会长、诗人宾歌:周瑟瑟怀着淡泊的心志,像一个出家人一样“紧紧搂抱住,野水自由的身子”(《水渠》)。他更多地宣扬对于诗歌的信仰,而不追求从诗歌里捏造出来的所谓意义,“像看不见的灵魂,吹到一摊泥水里”。(《土路》)他随心所欲地写作,所见所闻皆有在场的真实感。比如与土著男孩的寻常相遇,他就能捕捉到稍纵即逝的灵光,“有一颗宝石,在我们中间闪烁”。(《土著男孩》)他展现的就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玉石。他大部分时间手捧的是一把泥土,但只有眼光犀利的农夫,才能看到这些泥土中孕育着闪光的种子。
湖南日报科教卫新闻部主任、诗人陈惠芳:“瑟瑟体”简约而不简单,随性而不随便,是“走向户外”主张的实践,“低调中的震撼”。
诗人郑德宏:今日读周瑟瑟的诗,有这样的感觉:虽踏雪无痕,却也钝刀断铁。诗功夫已化无形。似未构华丽一词,然读一身惊艳。诗大开大合到宇宙世界,小幽小闭至一城一人。瑟瑟老师的诗歌写作似乎已自成一体系流派,而这是99%的诗人做不到的,有的诗人的诗写的确实好,也有一定的识辨度,但创造并形成自己的独立的写作体系却还远远不够。
诗人张明宇:收到瑟瑟兄又一厚重的诗集《世界尽头》,昨晚一口气读了一半,瑟瑟兄的诗娓娓道来,如入百花园:或在世界各地游走,或在往事回味中伫立,或在情感深处徘徊。瑟瑟兄的语言是简练的口语的迷人的,而他的世界是丰富的智慧的深邃的!
瑟瑟兄的诗有很多写动植物以及万物的,他用平和的平等的目光注视着万物,与万物对话,甚至进入万物,替万物思考,替万物发声。这便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殊为难得。当然,面对万物里的人,他的目光会更柔和更生动更深情。无论生者逝者,无论贫民富豪,在他眼里都是平等的存在,这种平等刻在他的骨头上的。他,就是在自己的肩胛骨刻诗!
诗人北琪:读周瑟瑟的诗,从《缪斯的情人》《披着语言飞翔》,到《松树下》,再到《世界尽头》,是一次奇特而美好、辛苦而感动的旅程。30多年的诗歌修炼,使得他能够自如调动一切语言于无形。他要把诗歌这门古老手艺的抒情特性发挥到极致。他选用的语言和词汇,经过了独家秘方的萃取,看似平淡,实则耐品,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恰到好处放在不可替换的位置,以其精准性提升了表达和呈现的无限可能性;他要表达的情感,经过了生活和生命的双重磨砺,看似朴素,实则绚美,每一丝、每一缕都牵动着你的心灵触角,以其真诚与温暖点亮了当下和尘世间微弱的炉火;他不仅仅属于栗山和洞庭湖,而是一再走向更远,哥伦比亚、墨西哥和智利都留下他的足迹;他是一位诗歌的太极妙手,化“诗硬骨”为“绕指柔”,一招一式松沉柔缓,人间烟火为阳,人生悲喜为阴,万物因阴阳变幻和循环而获得永恒。这是诗歌的力量,亦是诗人的功德。
诗人、学者赵思运:周瑟瑟的诗写已臻于就地取材俯拾即是的境界,他时时刻刻活在诗感的世界里,生活与诗处于同构之中。所以,每隔一两年,他就会自然而然地从生活历程中截取出一本厚厚的诗集!
他的诗有一种朴素温暖的品质——先锋而不偏狭,口语而不失锐利。他的口语诗经过诗艺的淘洗,即使俗语入诗,亦是干净洗练,意味醇厚。他的口语貌似轻描淡写,实则深蕴着诗学积淀。如《树雾》一诗的开头:
树冠升起
白色的雾
从鸟的喉咙里
慢慢吐出来
鸟鸣隐藏其中
我听不见
森林内部
它们的吵闹
在这里,不经意之间,就流溢出一种古典神韵,我仿佛感受到唐诗的“鸟鸣群山啭,花吐一树烟”的意境。
再如《天池》意象的营造所呈现的大境,亦令人惊叹:
六月
长白山天池
进入开冰期
我听见
冰块撞击
冰块的喀嚓声
天池的子宫
正暗暗扩张
伟大的产道
挤出了
一半冰块
一半蓝色湖水
这种石破天惊的艺术想象,撼人魂魄的造境功力,大大提升了口语的艺术表现力,而其深层原因,盖在于诗人精神主体的胸襟之深广。
作家网总编室主任、诗人安琪:人到中年,写作经常卡壳,看到那些创作力不曾衰竭的同行自是无限羡慕,周瑟瑟便是让我羡慕的非常重要的一人。他不仅不曾衰竭,还吃了猛药一般愈发生猛。2018年,诗歌界都知道有一个周瑟瑟,无论到哪个地方采风,都能现场直播,图片和诗,均热气腾腾。一场活动结束,人得回到家中对着电脑苦写,这家伙早已收工并且直接发布微信,20首是常事,30首乃至70、80首也有过,如果那个活动长达十天半月,他可以给你100首,譬如他飞越太平洋长途跋涉到达的智利、墨西哥、哥伦比亚,这些地方在他的诗中称之为“世界尽头”。在世界尽头,船长驾驶的是“一整只鲸鱼鱼骨”,水手端来的是“聂鲁达汤”,此时,罗伯特先生正款待瑟瑟一行,一顿饭后,瑟瑟即报之以“太平洋餐厅”一诗。这就是瑟瑟速度。
高产、优质,使周瑟瑟成为2018年度最受欢迎的诗人,被邀请到祖国各地,送诗、送诗歌写作模式。瑟瑟的诗,和一般采风诗还不同,极少直接把地名冠到诗题,也不是你想象中的歌功颂德,他只负责捡拾彼时彼地发生的事并随手放进诗里,我们通常说的“生活处处皆诗”,瑟瑟用行动实践了。他回家乡,吃到家乡甘甜的橘子,想到一个问题“橘子为何如此甜蜜”,于是他请出姚村长,姚村长把秘密告诉了“我”:把白糖埋在树根上。姚村长真的会这么说吗?存疑。其实瑟瑟经常在诗中进行合理的延伸,譬如这首《橘子为何如此甜蜜》,有可能姚村长真的这么回答,那证明这个姚村长很有幽默细胞,我的猜测,这是瑟瑟自己送给姚村长的答案,他经常这么干,在诗中融进自己的阅读感受、生存智慧和语言策略。回到这首诗,里面有一个人物“陶渊明”,瑟瑟写到,“一个老人走出来迎接我/我以为他是陶渊明”,这个老人就是姚村长。诗的最后,“我恍然大悟地望着/家乡的陶渊明”,瑟瑟总是有这种奇妙的联想能力,他到哪里,哪里的古人就被他请进诗中,跟当代人享有同等待遇,读者也由此知道了这个古人原来与这里有关系。这就是瑟瑟采风诗个性之所在。
瑟瑟反对“采风诗”的说法,因为采风诗已变成了单纯的讴歌风景,瑟瑟认为,无论到什么地方,他写的永远还是自己的诗而不是对方要求的诗,他的情感、他的思考、他对生命的态度一以贯之,它们不会因为地点的改变而改变。瑟瑟更喜欢用“走出户外的写作”来取代“采风诗”概念。我有多次和瑟瑟一起外出开会的机会,我真切观察到了瑟瑟不被采风之处限制的能力,也亲见他边坐车边写诗,车到站,一首诗就出来了。因为现场写作,瑟瑟会很认真地听导游讲解、询问相关典故、阅读展厅资料,它们,就在瑟瑟的脑海里经过化学反应,以诗的形式走到他的微信上。跟瑟瑟出门,大家白天看风景,晚上就读瑟瑟的诗,边读边叫,我怎么不知道这些事,你不知道是因为你没注意接收这些信息,你不知道是因为瑟瑟并不只为此地而写作,他写此地,把陈年旧事都唤了过来,参与了他此诗的创作。
瑟瑟的现场诗完全为他所有,旁人只有惊叹的份,想学也学不到,想抄也不敢抄。有一阵子我也想学瑟瑟现场写诗,同一个场景,我写起来就单薄,因为我只能就事论事,欠缺瑟瑟庞杂的知识面、奇异的想象力和儒释道兼修的看待世界的方式。现场写诗除了脑力的付出,还有体力,人家安心睡觉,你夜不成寐地写诗,第二天又得参与系列活动,没有好身体吃不消。据我所知,瑟瑟天天五点起床跑步,练就了一身仙风道骨,从未见他疲惫过。
中国当代诗界,身体好又能现场写的,不止瑟瑟一个,但现场写又写得好的,瑟瑟绝对是一个!不信,读读他的《暴雨将至》和《世界尽头》。
诗人、译者莫笑愚:周瑟瑟的诗歌,在中国诗歌现场来说是个异数。他的诗在语言上独树一帜,因为他并不追求词汇的华丽、惊悚或陡峭的人为做作的效果,而是以贴近生活的平实、朴素、精炼和准确的语言,揭示平凡之人之物之象中的不平凡的诗意。从这点来说,周瑟瑟可以称得上是语言的巫师。
谈论周瑟瑟的诗歌,不可避免地要谈到他作为首倡者之一的卡丘主义。百度百科上对卡丘主义是这样介绍的:“卡丘是‘文化’一词的英文译音,在这里当然并无文化之意了,强调一种对现实生活的‘生理反应’,发现新的生活可能性。卡丘主义是对‘人类社会的生理现象’的真实的写作。……卡丘主义者在严肃中嬉戏,在嬉戏中警世,它既不是神秘主义,也不是现实主义”。卡丘主义主张只有通过“有趣”与“认知”消解“无聊”与“无知”对人内心的伤害。事实上,我认为“卡丘”加上“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或文化现象,因而与文化有割不断的关系,甚至其自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既然用英文的“文化”一词的英译直接命名一种其倡导者所主张的文化,它本身就是包容的。卡丘的这种包容性在周瑟瑟的诗歌里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比如他的诗歌写乡村,写农耕文明在当代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的衰落、迷茫与迷失,体现了诗人对文明之根的苦苦追寻和执守;写当代人日常生活中的悖谬、无聊中的意义,平淡中的谐虐,往往不着一字而尽得风流。传统与现代是一种包容。最近几年,周瑟瑟频繁受邀出席国际诗歌节,在拉丁美洲朗读诗歌、做诗歌讲座,他在哥伦比亚、墨西哥等国访问期间的人、物、风景、历史、宗教等等都进入他的诗写现场,这是另一种文化和文明的包容。
事实上,周瑟瑟诗歌的丰富言说,需要读者悉心体会,反复咀嚼。他的诗歌看起来极容易进入,但是当你以为自己似乎理解了他的诗歌,却会恍然惊觉,那表象之下似乎潜藏着另外的东西,那是某种更深刻的东西,不靠意象或隐喻带来,就藏在他朴实无华的诗句下面。那里是一座金矿,需要付出努力,才能真正得到一颗金子的诗心。因此,作为一个喜欢探幽的读者,你需要走进周瑟瑟的诗歌,体验他的诗歌的妙处。
诗人幽林石子:《世界尽头》见证了“简约”之风里个性的空间与走向,读者能清晰看到精神的境遇。幽默风趣,耐人寻味。丰富的思想铸就绵长的创作,在汉语中修行的他,参禅悟道,简约的笔尖点向世界尽头。
诗人云经立:作为一个探索性极强的诗人,周瑟瑟有一颗敏感而又热情的心,他有着超乎寻常的艺术感受力,使得他走到哪,诗就在哪儿诞生!他对这世界,对亲人,对朋友,对古今圣贤,对山川草木,对蓝天白云,有着倾吐不尽的热爱与依恋。在父母面前,他永远是一个渴望荫庇的孩子。在他的笔端,无论在家乡栗山——只是他一个人的栗山,还是在异域,父母的音容笑貌,田野的劳作,日常起居,甚至父亲的咳嗽,母亲悄悄的眼泪,都会时不时地涌到眼前。思亲之痛,何其痛!走到哪,他就与哪儿的先贤对话:屈原,李白,杜甫,诸葛亮,王夫之,左宗棠,马尔克斯,聂鲁达……这些穿越时空的对话,又显现他内心的丰富,机智,活泼,多情!而他的诗又充满了浓厚的地域色彩,他走到哪,那儿的花鸟虫鱼,大地万物,历史风俗,都有恰当的呈现。这又构成周瑟瑟诗歌多彩的一面。同时,作为一个小说家,周瑟瑟有时会启用一下他小说家的功力,这又使得他的诗歌如虎添翼!
诗人金黄的老虎:湘人的气概里,最可贵的就是较高自我确认和社会担当,所以才有无湘不军的说法。周瑟瑟的诗歌创作意识形态也秉承着这个传统,不单体现于其诗论中,在其诗作之中亦是熠熠生辉。
周瑟瑟诗歌还有一个源头,就是湘楚之间的巫气。湘楚最擅鬼神交往,湘楚有对自然膜拜的深幽传统,湘楚也是骚人的渊薮。对自然不一样的敬畏和高度敏感往往是其诗歌的奇光异彩。这也是我阅读范围内诗人里最自觉最成功承接上这个源头的诗人。透过他的诗行,很容易看到那份湘楚人心灵深处对万物有灵的心理依赖和自得。
周瑟瑟的诗歌可贵的地方还有一个:那就是始终自觉保持着汉语诗歌的特质,呈现出接受过西方诗歌影响之后维护汉诗传统的觉悟和信心。
附诗集短评:
周瑟瑟一直是有成熟观念和娴熟技艺的诗人。近些年他的诗愈发返璞归真,凸显抒情之本,尤其在表达亲情的深挚与丧失之痛方面,更益深切而感人。触物生情,言近意远,形象简洁而富有蕴藉,节奏鲜明而又跳脱自如。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诗人、批评家 张清华
作为周瑟瑟语言实验的最新力作,《世界尽头》那种自然的节奏、鲜活的语感和现代性强劲的空间,共同构筑起了诗集的独到发力点,其平静的叙述背后常隐含着更高形式的语言策略,容易被人误读的口语表达,实则属于诗人不可复制的个性所在。延续《松树下》《栗山》《暴雨将至》三部诗集的艺术路线,《世界尽头》的语言与情绪愈发轻松、开放、自由与互动,从栗山、全国到拉美,周瑟瑟的诗歌空间视阈广阔,无所不包,却又皆归于微小的心灵内宇宙,“世界尽头”乃诗人的艺术状态,更是他理想中的高远精神境地。
——南开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诗人、批评家 罗振亚
周瑟瑟是挥洒自如的那一类诗人,擅长从万事万物的临界拱动诗芽。《世界尽头》看上去是在走“事实诗意”的路线,同时克服陈述背后的寡淡;他其实是在结构完善的铺展中做平实穿行,且把稀释性语像当作照明。《世界尽头》有着语感清明、修辞剔净的亮点,总体根源上归属于 “本事写作”,作为“在场”阵营突前的骠骑,他有自己醒目的排扣与披风。
——厦门城市大学教授、批评家 陈仲义
周瑟瑟近两年的诗以“栗山”为空间场域,以亲人的孤独、死亡和故乡的空无为中心展开个人之痛、家族隐忧与时代之思。在那些逝去之物那里展开的是此时代的虚无和无着,诗人的情感得以最大化的强化。
——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诗人、批评家 霍俊明
从个人的记忆出发,处理个体生命和现实的大主题,个人的回忆和闪烁的意象结合,提供了独到而鲜明的表达,彰显了周瑟瑟对于诗歌独到的把握和理解。
——北京大学教授、文化学者 张颐武
周瑟瑟的诗里,形式的痕迹被诗人甩到后面,但形式是存在的,肃穆的日常和真实的力量在诗人迈出的每一个脚印中,是有准备的战士的出征,经历过多次战事检验的老兵再次选择的命定苦旅。见识到克制之美从现实的艰难困苦中贯穿通过,怎样一个一个烙印落到实处而不被实际生活所困扰和牺牲。诗的意义和质量被诗人映照出来。
——中国作协社联部副主任、作家 冯秋子
周瑟瑟以举重若轻的结构能力,在细节与场景中完成了精神对位与思想观照,从而在对个体之痛的抚摩中完成了对时代创伤的揭示。
——文艺评论家 徐忠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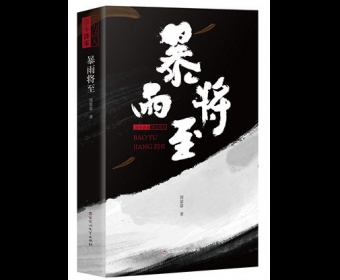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