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中国翻译》2019年第4期
转自: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
翻译家的选择与坚守——杜特莱译介中国当代文学之路
刘云虹
摘要:中国文学外译是中国文化走岀去的必然途径。在中国文学外译中,翻译家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工作对译本品质以及文学译介与传播的效果具有决定性作用。在当下的中国文学外译研究中,国内译学界对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探讨较多,而对其在英语世界之外的其他地域的译介却明显关注不够。法国著名翻译家、汉学家杜特莱是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法译者之一,对中国当代文学在法语世界乃至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做出了突岀贡献。本文拟从翻译家的选择出发,结合"翻译什么"和"如何翻译"这两个中国文学译介领域的根本性问题,探析杜特莱30多年来致力于译介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现、选择与坚守之路。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译介;杜特莱;选择;伦理
“翻译什么”和“如何翻译”是关于“中译外”的探讨中两个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而要回答这一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双重之问,除了首先必须深刻把握文学翻译的本质、目标与价值之外,另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就在于探析翻译主体在整个译介过程中的主观选择与能动作用。译本的品质如何、文学译介与传播的效果如何,甚至中国文学与文化“走出去”的目标能否得以实现,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并依赖于翻译家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工作。在当下的中国文学外译研究中,国内译学界对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探讨较多,而对中国文学在法语世界的译介及重要译者的关注却相对较少。实际上,法国不仅具有深厚的文学传统,旦对异域文化的幵放和接纳程度较高,一直以来都是世界范围内译介中国文学的重镇之一。
杜特莱(No lDutrait)是法国著名翻译家、汉学家,多年来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是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法译者之一。他先后翻译出版了阿城、韩少功、苏童、莫言等作家的20余部作品,其中包括莫言的主要作品《酒国》、《丰乳肥臀》、《四十一炮》等,他的翻译被认为对推动莫言获得诺奖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拟从翻译家的选择出发,结合“翻译什么”和“如何翻译”这两个涉及中国文学译介的根本性问题,探析杜特莱30多年来致力于译介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现、选择与坚守之路。
一、相遇、发现与选择
翻译首先是两种语言的相遇。杜特莱自1969年开始学习中文,当时的目标“并不是能用中文阅读文学经典作品,而是通过阅读小说来从‘内部’了解中国社会”(刘云虹、杜特莱,2016:37)。在后来研读中国文学作品和准备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杜特莱关注的重点一直是中国的报告文学,还专门撰写了学术论文《一种中国独特的文学形式:报告文学》,发表于法国中国研究会会刊1982年第3期。此后,杜特莱慢慢将关注的目光转向中国当代文学,并在中国朋友的推荐下幵始阅读阿城的作品,出于喜爱,他很快便翻译了《棋王》、《树王》和《孩子王》三部小说并于1988年结集出版。在不同场合谈及翻译过程中如何选择原著的问题时,杜特莱多次表示自己“对翻译的选择经常是出于偶然”,对阿城小说的翻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我选择翻译阿城的小说时,是因为不少中国朋友向我推荐了他的小说集《棋王》。我想,有那么多中国人都在谈论这本书,一定值得翻译,于是就决定将它译成法语。”(刘云虹、杜特莱,2016:38)如果说选择翻译阿城的小说,这或多或少源于偶然的相遇,那么,杜特莱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选择却无疑渗透着明确的理性意识。我们知道,在法国的汉学传统中,一直颇受关注的是中国的古典或经典文学,当时的汉学家中并没有多少人对中国当代的“新文学”感兴趣,杜特莱之所以对中国当代文学情有独钟,是因为在他看来,通过阅读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可以直接地了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以及他们的生活处境”(同上)。而他在30多年的翻译生涯中始终坚持译介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最根本的原因也正在于希望可以让法国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社会现实、了解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状况。应该说,这是杜特莱对翻译工作的理解与追求,他曾明确表示:“我的工作就是翻译更多好的文学作品,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的,我都会翻译,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故事”(中华网文化频道,2014)。
在确定了译介中国当代文学这个大方向后,杜特莱所要面对的便是如何选择具体翻译文本。实际上,这不仅仅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由中文译出的文学作品在法国逐步增加,以汉学家何碧玉和安必诺的统计为例,1994-1997这四年间,法国翻译出版的中文文学作品至少有66部(Dutrait,2011:77-78)。杜特莱对此有自己的判断:“我觉得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中国当代文学有了令人惊异的进步,她自己的一片蓝天正在涌现,正如同俄国文学、日本文学、拉丁美洲文学所拥有的那样。”(杜特莱,2005:5)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国翻译界和出版界同样必须面对“翻译什么”的问题。在杜特莱看来,面对这一发展,译者和出版者必须解决一系列问题:“如何在中国期刊和出版社推荐的众多作品中进行选择?应该选择中国读者喜爱的作品还是优先考虑法国大众可能喜欢的作品?……应该认为任何一种文学创作都是自足的,因为它具有普世价值并因此可为所有读者接受;抑或认为读者需要前言、后记、用语汇编、注释等可以帮助理解的补充信息?”(Dutrait,2011:78)不难看岀,他对翻译文本选择之于中国当代文学译介的重要性有着明确认识,同时,他敏锐地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法国文学界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认知与接受立场上的变化。法国哲学家、汉学家弗朗索瓦 于连对这一“新目光”曾有如此论述:“人们通常把中国当代文学视为纯粹的文献。文学服务于历史(和历史学家):她阐明外国观察者无法直接理解的(中国有意无意向我们’隐藏的’)东西;她用以测量这个大国的意识形态温度;她被当作证词、标记、指数或症候来阅读。而从今以后,我们也许应该幵始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待今天的中国文学:作为文学的角度。”(同上:83)
把中国当代文学视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而不再是证词、文献或某种揭露,即充分重视作品的文学性及其内在价值,这也正是杜特莱在选择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时始终秉持的原则。文学之镜固然可以透视社会现实与个体境遇,但作为一种审美再现与文化建构,文学的内在价值必然首先体现在其文学性上。如果说,翻译不仅是历史的奇遇,更是一种有温度的相遇,那么,对作品发自心底的喜爱无疑是对这温度最好的注解。杜特莱不止一次坦言:“我非常喜欢中国小说的文学性”(中华网文化频道,2014),并明确表示,“对于选择来翻译的作家,我所欣赏的是其笔下的艺术灵性及叙述方式”(杜特莱,2005:6)。自翻译岀版阿城的三部小说起,杜特莱真正幵启了译介中国当代文学的漫长历程,先后翻译了阿城的《迷路》;韩少功的《爸爸爸》;苏童的《米》及莫言的《酒国》、《丰乳肥臀》、《师傅越来越幽默》、《四十一炮》和《战友重逢》等20多部中国当代文学著作。无论就这些作品的成就或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而言,作为翻译家,杜特莱无疑具有慧眼识文的独到眼光。
早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杜特莱就开始关注并翻译他的作品。2000年至今,他共翻译出版了莫言的5部小说:《酒国》(2000)、《丰乳肥臀》(2004)、《师傅越来越幽默》(2005)、《四十一炮》(2008)和《战友重逢》(2017)。论及杜特莱对莫言及其作品的选择,文学性依然是他考量的首要因素。在他看来,莫言作品几乎涉及了关于中国社会的所有主题,更重要的是莫言“从来没有忽视文学本身的品质”,“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一位作家、一个关注周围世界的观察者。他能探测人类的灵魂,并展现美与丑、人性与非人性在什么程度上是接近的。”(刘云虹、杜特莱,2016:40)此外,杜特莱十分欣赏莫言在作品形式上的探索与创新,以被法国媒体誉为“小说中的小说”的《酒国》为例,无论是其中潜心营造的“套中套”多重结构,还是字里行间渗透出的幽默风格、侦探小说的味道,无不深深吸引着他,令他欣然接受出版社的邀约,翻译这部莫言的重要作品。丰富的主题与创新的风格,尤其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深刻揭示,都是杜特莱眼中最为可贵的文学品质与价值,也是促使他选择译介莫言并大力推动其作品在法国的接受与传播的根本原因。
与绝大多数翻译家一样,杜特莱并非职业译者,他的主要工作是在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从事中国语言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据不完全统计,自1982年至今,杜特莱发表了30余篇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文章并出版了颇具影响的《中国当代文学爱好者阅读指南》一书,除了对莫言、阿城等重点译介的作家有深入研究之外,对张抗抗、池莉、刘震云、余华、阎连科和姜戎等其他代表性作家也有所关注,同时力求深刻了解并全面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的总体特征与发展进程。就翻译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杜特莱曾明确表示,“对我来说,翻译是一种帮助我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及其翻译与在法语国家的接受进行研究的工具。”(Dutrait,2013:109)
在文学翻译范畴内,翻译实践与文学研究之间应形成一种紧密结合、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事实正是如此,一方面翻译促进了杜特莱对中国当代文学及其译介的研究,另一方面,他在相遇并译介中国当代文学过程中的可贵发现和理性选择,可以说都与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深刻理解和整体把握分不幵,而后者则完全源自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长期关注与研究。
二、翻译伦理的坚守
近年,翻译的重要性进一步突显并受到学界和媒体的普遍关注。不难发现,一方面,翻译在文学译介与文化传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得到充分肯定,原本在中国文学译介领域默默耕耘并大多默默无闻的翻译家们一改往日的“隐形人”身份,纷纷从幕后被推至台前,不仅迅速成为媒体的新宠,学界对其也毫不吝惜褒奖之辞。另一方面,翻译原则与方法、译者的选择与责任以及翻译观念、标准、价值取向等涉及中国文学外译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却不断引发争议和质疑,亟待翻译研究界进一步展幵深入探讨。正如笔者所指出的,“在受到学界和文化界普遍关注与空前重视的同时,翻译在种种现实问题下无疑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刘云虹,2014:90)。翻译方法的运用直接影响译作的风格与品质,进而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文学在海外接受与传播的效果,因此,翻译所面临的首要挑战便是在中国文学外译中如何选择恰当的翻译方法。翻译是否要忠实于原文?所谓葛浩文式“连译带改”的翻译方法是否应在中国文学外译中加以推崇?如果说翻译方法不应被孤立看待,那么其背后涉及的深层次要素有哪些?围绕翻译方法产生的种种疑问与某些有待澄清的认识,使其成为当下中译外研究中的一个焦点问题。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法译者之一,作为长期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在法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并做出杰出贡献的翻译家、汉学家,杜特莱在其翻译过程中究竟遵循何种翻译理念与原则、采取何种翻译策略与方法,这同样是我们在考察中国文学外译中不容忽视的重要论题。在文学翻译范畴内,倘若我们借法国翻译家、翻译理论家贝尔曼的目光来探究翻译过程与目标,“方法”是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字眼,因为正如贝尔曼所深知的,把翻译视为交流、归于方法的观念在翻译界几乎根深蒂固。如果把翻译仅仅视为一个交流的过程,一个从出发语到目的语的“信息”传递过程,那么它就只与方法有关。然而,在贝尔曼看来,"尽管同样包含着信息,但文学作品并不传递任何形式的信息,而是向一个世界的经验幵放”(Berman,1999:70)。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明确指出,“翻译是有意为不懂原文的读者而作的吗?(……)那么一部文学作品‘说’什么呢?它传达什么呢?它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告诉'理解它的人。它的本质属性不是交流或传达什么信息。”(本雅明,2005:3)这就意味着,翻译不应被理解为单纯的交流与传达,翻译自身的最终目标在于“在书写层面与他者展开某种联系,通过异域的媒介来丰富自我”(Berman,1984:16)。因此,贝尔曼一再强调,翻译不仅仅是方法的,而首先是伦理的、诗学的和哲学的,是“与真理的某种关联"(Berman,1999:74)。
翻译因“异”而起,语言无处不在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最直接地构成了翻译的必要性,同时,正如法国哲学家利科所指出的,翻译“对所有交流而言都构成一种范式,不仅是从语言到语言,也是从文化到文化"(Ricoeur,2004)。许钧同样强调,“异语间的交流,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他认为,"在这种交流中,各自的独特性虽然为对方通过他者之镜认识自己、丰富自己提供了可能,但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严峻的考验。’异’的考验不仅体现在语言的差异给翻译造成的障碍上,更表现在对’异’的认识上,体现在对待异域文化的态度上。”(刘云虹、许钧,2016:72)在这个意义上,译者如何对待渗透于原文中的语言文化差异性,进而如何内化翻译行为与生俱来的既克服差异又表现差异这一悖论式双重目标,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原则与方法等层面的种种选择,这实际上构成了翻译伦理的重要维度之一。
考察杜特莱译介中国当代文学之路,我们发现,其间不仅有美好的相遇、敏锐的发现和理性的选择,更有一种弥足珍贵的对翻译伦理的坚守。具体而言,或可从以下两个主要方面进行探讨:
(一)以忠实为翻译的根本原则
翻译是一个渗透着译者主观选择的能动过程,而任何选择都不应是盲目的,翻译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译者必须自觉地遵循一定的原则、合理地运用一定的方法。杜特莱始终以忠实为其根本性的翻译原则,他明确表示,“我始终努力做一个尽可能忠实的译者,即使作家本人有时候鼓励我进行改写或删去一些对法国读者来说难以理解的段落”(同上:39)。从翻译史的角度来看,尽管“忠实”可以说是翻译活动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对于翻译忠实性原则的争议和质疑似乎从未停止过,翻译的“忠实”概念究竟该如何理解?是忠实于原文的文字、意义、风格,还是忠实于原文的审美效果,抑或忠实于读者的审美需求与体验?在对葛浩文翻译的探讨中,忠实性问题就是一个难以简单定论的问题,在不少学者看来,葛浩文所惯常采用的删节和改译等翻译方法无疑是对翻译忠实的违背,而葛浩文则明确表示,“我的责任在于忠实地再现作者的意思,而不一定是他写出来的词句”,在他看来,两者之间具有“重要的区别”(葛浩文,2013)。实际上,葛浩文对文学翻译的立场十分鲜明,并就此有过多次表述,例如在一次演讲中他直言,“我们的工作目的是尽量取悦于一位不了解目标语国家语言的作家,尽力去忠实于他的原作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作者写作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他的译者,而是为了他的读者。而我们也是在为读者翻译。”(同上)如果说“为读者服务”在某种程度上可谓是葛浩文对于翻译忠实的理解,那么,杜特莱则明确表示,“在我看来,必须尽可能尊重出发语”(Karaki&Carbuccia,2013:7)。的确,作品总是为读者而创作,翻译也始终面向读者,翻译策略与方法的选择不仅取决于译者的翻译观念与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也与读者的接受息息相关。围绕文学翻译的可接受性及其与翻译的忠实性原则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翻译学界在中国文学外译研究的语境中有过颇多探讨和争论。有学者认为,只有得到读者的广泛接受,文学译介才算是成功的;另有学者却持不同意见,提出不能仅仅以读者接受情况来衡量文学译介的意义,尤其强调,若以可接受性为目标而对异域作品进行改写,并导致对原作中语言文化异质性的抹杀,这从根本来看是对翻译伦理的背离。究竟如何在原作和读者两者之间进行选择?对于这一点,杜特莱的态度十分明确:“首先为作者服务,其次为读者服务”(刘云虹、杜特莱,2016:39)。他不仅认为“不应该对我们翻译的作品进行改写”,也“从未打算用法语来改写任何一部中文小说”(Karaki&Carbuccia,2013:7)。他直言,“某些译者从头至尾地对作品进行改写,读者读到的根本不是张三或李四的书,而是杜邦先生或迪朗先生的书。我总是害怕读我的翻译的法国读者会觉得阿城、韩少功、莫言或苏童都用同样的方式写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对我来说就是彻底的失败。这也就意味着我没有能力翻译出这些作者迥然不同的风格。”(刘云虹、杜特莱,2016:39)
翻译接受并非简单的语言问题,而是受到目标语国家的文化语境、读者接受心态以及两种文化之间关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删改等权宜之计既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可能是中国文学外译进程中的一种阶段性需要。但同样必须明确的是,就翻译活动而言,“忠实”不仅由其本质所决定,而且从伦理的角度来看甚至是翻译自身存在的内在需要。正如上文中所提及的,在贝尔曼的视域中,翻译在他者与自我之间构建一种对话关系,并以对自我的革新与丰富为最终目标。尽管具体的翻译结果永远是有待完善的一种历史性存在,但翻译忠实应成为译者自始至终的追求,其关键在于对翻译最终目标的忠实。对此,杜特莱有明确的认识,他相信,“无论如何,如果一部作品在翻译中被删改了,那么它很可能会在以后的重译得到完整的呈现。一部出版的文学作品既不属于它的作者,也不属于它的译者,它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因此,迟早有一天,一定有译者会完成一个比现有译本更加忠实的重译本。”(同上)可以说,杜特莱不仅始终秉持翻译的忠实性原则,并且,他对于翻译忠实性的理解具有明确的历史意识。
(二)依据原文灵活选择适合的翻译策略与方法
在杜特莱眼中,对出发语和原文的尊重并非一种孤立或僵化的信条,他主张“根据不同情况来处理翻译问题,既要始终考虑最好地尊重原文,让读者感受到原文的特质,又应保持译文的可理解性与可接受性,避免陷入异国情调、神秘或可笑之中”(Dutrait,2013:110)。
从根本上看,尊重原作就意味着尊重原作的语言文化异质性。“尊重”是翻译伦理的核心概念之一,贝尔曼主张尊重差异性的翻译伦理,提出翻译的本质是“幵放、对话、交杂和非中心化”(Berman,1984:16),韦努蒂提倡差异性伦理,将翻译活动定位为“不再是一种同化行为,而是一种对跨语言和跨文化差异性的承认”(Godard,2001:56),明确提出翻译的伦理就是对语言和文化的差异给予更多的尊重。在对翻译的价值判断上,他们都认为,保存并展现异域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性的翻译是“好”的翻译,反之,压抑甚至抹杀异域文本中的语言与文化差异的翻译就是“坏”的翻译。同样,杜特莱强调,在翻译过程中应注重对原文语言文化异质性的保留与传达,因为“如果删除所有的异域特征,或在译文中抹去一切可能使读者感到困惑的东西,那么就会存在令小说失去其趣味和’现实性’的巨大危险”(Dutrait,2010:92)。当译者可以在完全尊重原文的情况下毫无困难地、完美地译出一句话时,一切都没有问题。然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时常要面临难以传译的情况或对目标语读者来说难以理解的表达,绝对的忠实往往无法实现。正如本雅明所言,“如果翻译的终极本质是努力达到与原作的相似性,那么,任何翻译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其来世生命中——如果不是对活的东西的某种改造和更新的话就不能如此称呼之——原文经历了一次变化。”(本雅明,2005:5-6)也就是说,翻译不可能是简单的转换或复制行为,翻译必然是对原文的某种改造和更新,以成就其来世的生命。杜特莱对此有深刻认识,在他看来,“译者总是像走在钢丝绳上一样,左右摇摆。他必须努力保持平衡,既不掉在这边,也不掉在那边,换句话说,就是既不完全是’异化翻译’,也不完全是'归化翻译',而是根据他所翻译的文本进行合理的选择。”(刘云虹、杜特莱,2016:39)
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杜特莱认为每一种语言都有其停顿规则和标点符号体系,在翻译过程中他非常重视对标点符号的处理,主张应像翻译文本一样翻译标点符号。从实际翻译经验出发,他看到,“绝对忠实于原文的标点符号只能改变作者的风格(有时会将中文里完全'古典的’风格变为法语中的'现代主义风格’)”,因此提出对于标点符号的翻译而言,重要的是必须“在法语中找到恰当的对等,就像在句子中为词和分句找到对应的位置一样”(Dutrait&Dutrait,2007:128)。相反,他也意识到,如果过于干涉原文的标点符号,则可能妨碍原文风格的再现。在翻译苏童的《米》时,杜特莱就遇到如此情况。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将对话和内心独白混杂在一起,完全不以引号或破折号加以区分。在杜特莱看来,这一形式恰恰体现出《米》区别于其他文学作品的文学风格上的异质性,应在译文中予以保留,以力求最大程度地再现原文和原作者的风格。
正是通过在忠实性原则基础上灵活而合理地选择翻译策略与方法,在尽可能接近原文、再现原文的语言文化异质性与译文的可接受性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杜特莱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在法国获得了巨大成功。
三、结语
尽管随着莫言摘得诺贝尔文学奖、阎连科获卡夫卡文学奖以及《狼图腾》、《解密》和《三体》等一批中国文学作品在海外热销,中国文学在国际舞台上的认知度和影响力有所提高,但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总体“出海不畅”依然是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背景下,翻译家,特别是海外著名汉学家,对中国文学外译的积极推动作用日益凸显。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在法语世界最重要的翻译与推介者之一,杜特莱数十年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为中国当代文学在法语世界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推广做出了突出贡献。探寻杜特莱译介中国当代文学之路,可以看到,那是一条饱含热情的探索与发现之路,更是一条充满理性的选择与坚守之路,不仅值得我们深深的敬意,也为中国文学外译及其研究带来了宝贵的启迪。

【作者简介】
刘云虹,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参考文献及注释省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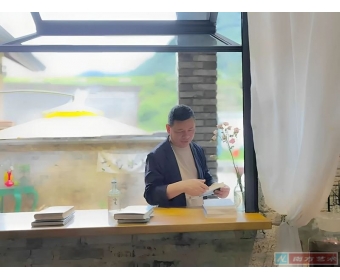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