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仿佛昨天我们还在“做一个怒吼的人 / 让回声痛击我的无礼,让我否定我自已 / 吼累了,再吼一遍:‘世界是个鸟,’”(何房子《山中即景》)但转眼间,我们这些出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的人似乎已经老了。尽管我们的头发还未脱尽,离全秃的境界尚有一段距离;尽管我们的老脸尚未长斑,还有“近黄昏”的“夕阳”一般的光泽,仅仅是人到中年,剩下的不多的激情内部甚至还“足以再住下一两个小妾”(宋炜《赠宋强》),但是毫无疑问,我们的心真的已经苍老了,不再认为自己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不再认为这个世界属于自己,对多余的、来路不明与晦涩不清的小妾,也不再怀有年轻时的兴趣和渴望。在似乎怎么也挥霍不尽的少年时代,我们自信有能力走遍千山万水,有足够多的时间依次爱上每一个心仪的姑娘……那时,我们以为自己将永远处在青春期,所有的理想都不在话下。面对这等猝不及防的难堪局面,我的同龄人,诗人何房子,在轻微的咏诵中至少给出了难堪局面之所以到来的部分原因:
近二十年……我乐于置身人流,亦在人流之外
我看见自己,这些年碾转两省四地
其间的小起伏
不足以大论,不足以语重,不足以心长
独木桥上请客送礼,人来人往
我潜水,过河
头埋得比生活还低
偶尔换气,水面冒出几个字句的泡泡
(何房子《解诗》)
人到中年,我们对青春年少时“不知老之将至”、不知老为何物的懵懂状态依然怀有深深的留恋,但对此等无知而幸福的境地我们今天却唯有羡慕。是破碎、难缠和消磨激情的生活最终毁了我们。有不老的、打败天下无敌手的时间推波助澜、助纣为虐,我们的失败指日可待,我们能收获的也必将是失败。事实上,我们逐渐苍老的骨头中有时间沉闷的回声,有激情死去后留下的灰色化石——它导致了我们的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前列腺的老化、子宫脱落或更年期结束后的干涸;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处于通往彻底失败的羊肠小道。相比于无法无天、没心没肺却幸福无比的少年时代,人到中年,我们看待万事万物的眼光和面对万物的姿势自然就要低一些。房子对此心知肚明,他因此写道:“景色被照亮,它就不是真实的。绿的、红的 / 来来回回地跑动,而昨天它们是灰的 / 对面的山包高出了些许,我又渺小了些许/ 在沙坪公园的一张滕椅上,我索性躺着 / ……这样的角度很好。”(何房子《在沙坪公园闲坐的一个下午》)低一点的姿势是被时光打败的我们被迫习得的动作,更低一些的目光,则是必败的我们对无敌的时间被迫做出的最好唱和,只因为“上次,一块石头是软的,顺从我的意愿滚到山脚 / 这次,那块石头换成了野花一片,对着我大喊大叫”(何房子《山中即景》)。时光总是倾向于帮助我们在通往失败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因此,在“顺从我的意愿”和“对着我大喊大叫”之间的相互挤压中,最终获胜的定然是“大喊大叫”,因此,“这样的角度很好”。但这是真的么?
人的最大宿命或许在于:面对不败的时间,唯有自动服输才是智慧的唯一来源,因为生而为人——这个“终将一死的可怜虫”(爱因斯坦语)——必将认领他最终的失败,不管他愿意还是不愿意。所谓人定胜天,除了在虚妄中给人鼓劲外,唯一能证明的,只是人的狂妄和智慧的丧失,因为一切东西最终都注定不是我们的:“而另一片天空,其实是空的 / 它在我头颅之上,是多余的。”(何房子《向下生长的芦苇》)事实上,“我们只要活着,只要经验到自己与他人的活着,我们就会觉悟到:我们仅仅是还活着的死人,以及,死去的活人。对于任何独一性的个体都是如此:作为‘活着的死者’—与—‘死去的活物’,这个同时性的双重结构,这个永远不在场的生命余存样式,是生命的基本结构。”(夏可君《无余的生命》)因此,谁领会到自动服输的真义,谁就走在了通往智慧的道路上;因此,唯有在时光中被打败的人类,才是一切艺术最伟大的主题。失败的人类才是人最终和最深层的命运。记录我们的失败、记录我们对失败的感受,从各不相同的失败样态中窥见命运的蛛丝马迹,是一个有智慧或走在智慧之路上的诗人必修的功课,诗歌也有望因为对失败的体贴入微而获取成功——这也许是我们能在尘世间获得的唯一成功。房子的近作听从了来自生命底部的轻声召唤。很显然,并不是每一个诗人都有这样的幸运——太多的诗人还在用分行文字撒娇、骂人、抱怨、为自己的怀才不遇愤愤不平。他们挥霍诗行宛若他们曾经挥霍青春。房子因此能够高迈而低调地“厌倦修辞”,试图“以一次还乡 / 重温现实主义的颠簸与病痛”(何房子《长途汽车站》)。我们从他新近写成的一批高质量的诗作中,看到了对失败人生和各种失败样态的倾心记录,最让我觉得惊心动魄的是《墙上的木刻:鱼》——
在白天,它是暧昧的。鱼刺卡住木头的喉咙
木头一直在用力
咽下桐油、钉子以及一小块墙壁
鱼倒挂。与客厅的一面墙相比,它是忧郁的
挤干了水份的鱼鳞趋向木纹
它的不规则正如空气的不规则
到了鱼尾,缺氧的船队一字排开
蚊子紧随其后,这袖珍的吸血鬼
在盘旋,在立秋之日扑向墙上的木刻
可惜,用力过猛
蚊子头破血流,它的江山已经皮之不存
鱼的江山呢?木头的江山呢?
它们结合得如此深刻,我一眼看出了破绽
没有江,鱼头就只有向下低垂
没有山,木头就只有方方正正
现在看来,蚊子、鱼、木头聚到一起
不是出于偶然,而是那四颗钉子
这一天,堵住了东西南北,堵住了它们的来和去
高超的诗歌技艺、洋溢在诗行间的平缓呼吸、错落有致、呈阶梯状的心绪,都暂且按下不表,因为人到中年,事情已经紧急到了无法关心技艺的地步。我唯一感兴趣的是这首诗中隐含的失败主题:曾经活着现在死去从而作为艺术品的鱼和木头,被人的艺术品欺骗准备向鱼实施偷袭行动以养活自身而肉体的“江山已经皮之不存”的蚊子,它们中究竟谁失败了?抑或其中的每一个都失败了?从表面上看,作为艺术品的墙上木刻——鱼——表征着人的胜利,因为它勉强可以被称作“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但“四颗钉子”的坚实存在,让蚊子、鱼、木头必然性地聚到一起,却刚好组成了关于失败的人类的精致隐喻——四颗钉子不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必将遭遇和认领的必然界限么?在这首诗所谋划出的轻柔语境中,蚊子可以代表人类,木刻(即鱼和木头)可以代表我们讨生活的场域,由于钉子(而且是四颗!)的存在,它们三者之和不是更能成为我们失败的象征么?事实上,我们就是那只蚊子,小眼睛中辉煌的木刻被我们错误地当作了光明的前途,以为它完全值得追求,却没有想到等待我们的终将是无可挽回的失败——我们的全部激情和失落来源于此,我们的全部希望和智慧来源于对这种境遇的体察。“我承认,我老了,我对生活的误解与日俱增。”(何房子《深深感谢这浑浑噩噩的一天》)但对于写作诗歌的房子来说,这样的陈述刚好称得上一个轻微的自谦:只有洞悉智慧之秘密的人,才有资格谈论对生活的误解;充满欲望、两眼发绿地深陷于生活之中、肉体的江山尚未皮之不存的蚊子却不配谈论对生活的误解——它们顶多是在敲诈生活而已。
但我们命中注定的失败并不必然意味着这个世界是可恨的,尽管它在有些时候确实是非常可恨的。在诗歌中,我们的失败和各种不同的失败样态不仅可以被陈述,也可以有暂时性的解救方式。虽然四颗钉子依然热情地为我们搭建了坚实的牢房,依然让我们无路可逃,但冒犯界限的冲动在自动服输后必须要得到平息。在诗歌中,在想象力组建起来的框架之内,房子给出的解救方式首先是后退、在四颗钉子组成的界限之内后退:“这事物的身世,这些现实之阔中的小衰哥 / 通过后退,后退,再后退 / 才有一丝缝隙 / 看见自己没被现实改变的模样 / 我不唱不和,只需跟着,走进无人之境”(何房子《沿着现实主义道路后退》);紧接着是返乡,从讨生活的场域(即木刻)、从对光明前途的不懈追求中返回故乡:“沿着河堤慢行,今夜,我摸黑回家”(何房子《小镇春秋》);再接着是退回婴儿和婴儿懵懵懂懂的休憩:“我也在后退 / 退到婴儿的睡眠里 / 我是一个婴儿,还是一个无所事事的父亲 / 退到一匹瓦中,我抱住更多的瓦 / 对着一根饥饿的烟囱,诉说我周游大江南北的疼痛”(何房子《长途汽车站》)。但面对自动服输和智慧的召唤,更重要的、终极的诗篇房子至今还没有写出来:撤退到婴儿的睡眠和童年时期的瓦片还不够,必须退回到永恒,为等待再生做好准备,因为这个狗日的世界依然值得我们用再生为方式去继续爱它,因为我们不怕失败,因为我们乐于失败,并在乐于失败的过程中获得再生和永生。
2010年3月31日,北京魏公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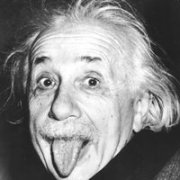 爱因斯坦的绵祆 评论 敬文东 | 撤向源头:何房: 近二十年……我乐于置身人流,亦在人流之外 我看见自己,这些年碾转两省四地 其间的小起伏 不足以大论,不足以语重,不足以心长 独木桥上请客送礼,人来人往 我潜水,过河 头埋得比生活还低 偶尔换气,水面冒出几个字句的泡泡 (何房子《解诗》)
爱因斯坦的绵祆 评论 敬文东 | 撤向源头:何房: 近二十年……我乐于置身人流,亦在人流之外 我看见自己,这些年碾转两省四地 其间的小起伏 不足以大论,不足以语重,不足以心长 独木桥上请客送礼,人来人往 我潜水,过河 头埋得比生活还低 偶尔换气,水面冒出几个字句的泡泡 (何房子《解诗》)  南方的南 评论 敬文东 | 撤向源头:何房:在诗歌中,我们的失败和各种不同的失败样态不仅可以被陈述,也可以有暂时性的解救方式。
南方的南 评论 敬文东 | 撤向源头:何房:在诗歌中,我们的失败和各种不同的失败样态不仅可以被陈述,也可以有暂时性的解救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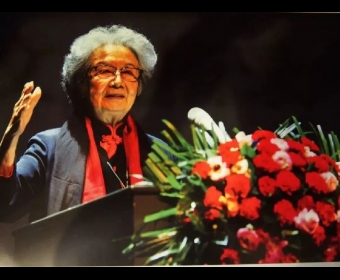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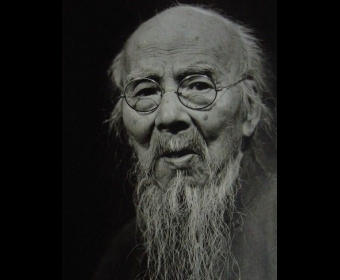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