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性的沼泽中获得救赎之梯
——泉子诗论
江雪
泉子,无疑是中国当代青年诗人的杰出代表之一。他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江南一带,其品质独特的诗歌作品,诗中殖入的幽暗而独立的人文精神,深深影响了国内一批同道诗人;同时,其丰富的人生阅历与诗歌建树历程,也促使他的写作愈加走向成熟大器,并且在他的带动下,形成了一个以泉子、江离、胡人、飞廉等为代表的极具才华与个性的江南青年诗群。诗人王家新从泉子的诗歌中,发现诗人在诗歌中修行,追寻来自江南山水的“伟大的教诲”;诗人宋琳在评价泉子时,则称他是一个在语言实践上有着冒险精神的诗人;诗人飞廉则认为泉子是一个“中西混血儿”,从他的身上可以同时窥见博尔赫斯和王维的“身影”。但是,飞廉在论述泉子诗歌时,转述了英国诗人艾略特的一段话:“诗人,任何艺术的艺术家,谁也不能单独具有他完全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他的鉴赏,就是鉴赏他和已往诗人以及艺术家的关系。你不能把他单独评价;你得把他放在前人之间来对照,来比较”。在我理解看来,飞廉强调的是诗人与读者之间如何建立阅读与诠释的关系,如何寻求在古典性与现代性的碰撞中的诗意重逢,如何真正深入到诗人灵魂中无数个隐秘的光源或黑洞,就像一个星象观测员一样,去观测它的光度与深度,从而发现诗人的诗学理想中葆存的参照物。
要想全面理解诗人泉子的诗,作为读者,不能不了解泉子生活和成长的故乡——淳安。据统计,淳安历代进士有300多名,光中进士的人数就是整个杭州城的五分之一,是全国县市平均数的17倍,仅一个云村就有产生了21位进士,淳安无愧为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淳安代代出名人,比较著名的有东汉时期的方储、三国时期名将贺齐、中唐诗人皇甫湜、中唐词人皇甫松、晚唐诗人方干、南宋理学家詹仪之、南宋学者黄蜕、南宋诗人方一夔、南宋布衣钱时(象山书院主讲席)、浙江儒学提举鲁渊、明朝三元宰相商辂、明代戏曲家徐田臣、明代清官海瑞、“浙中三毛”之毛际可、清代古文学家方楘如、光复会同盟会成员邵瑞彭等,真是不胜枚举;让人惊叹的是淳安还曾产生了两位农民起义领袖,唐高宗时期的陈硕贞和北宋时期的方腊,尤其是陈硕贞被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称帝的农民起义女领袖”(诗人泉子的外祖母就生活在陈硕贞诞生的村子里)。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曾经在淳安郭村的瀛山书院讲学,写下杰作《咏方塘》;诗人李白来到淳安后,亦留下名句:“清溪清我心,水色异诸水。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向晚猩猩啼,空悲远游子。”
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故乡——淳安,孕育了诗人泉子,赐给诗人一个不平凡的“童年”。诗人在一次访谈中这样写道:
童年就像是一个核或者是一枚种子。它储藏着我们一生的秘密。我感激于命运与我的父母带给我的一个近乎完美的童年。那是置身于中国乡村背景中的,作为辽阔与自由的代名词。我想我今天的写作正是我重回人生这最初阶段的努力。我还要感谢我的亡兄,这个以他的疾病与死亡换得我的生命的人,他与我一同见证与描绘了另一个童年。他并没有死去,他依然在我的身体中,或者说,我们在同一个身体中延续着那共同的生命。这另一个童年依然是命运的馈赠,正是在对疾病与死亡的逼视中,它为我揭开了那通往生命本质的道路。
泉子的童年是在20世纪末中国转型时期,强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与贫瘠饥饿的时代语境中度过的,我们不难想象诗人的童年不仅仅是一种肉身的记忆,还是一种“命运的馈赠”,是诗人创作的生命源泉。泉子出生于淳安县梓桐镇并峰村,原名胡伟泉,而“泉子”是他哥哥的小名。在我看来,诗人用“泉子”作为自己一生的笔名,自然有着意味深长的纪念意义,既是怀念自己英年早逝的哥哥,同时也是在永恒追忆他们兄弟相依为命的“童年”。然而,我认为诗人泉子,还在这个笔名,赋予了他一生的追求与想象力,或者说,这个名字暗藏着一种理想与抱负。
“子”字作为文人名字后缀的时候,与其说“子”寓意“有道德、有学问的人”,不如说是寓意“有思想、有抱负、胸怀天下而谦卑之人”。大约从春秋时代起,在士大夫和文人中间开始盛行表字,用“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来表字,一些心性谦卑而旷达的文人更加乐意于采用崇下的第四等爵位“子”来表字,甚至我们可以从伟大的哲人与诗人的名字中,寻觅到一种来自人类“童年”的古老情结与文明基因:孔子、庄子、老子、孟子、荀子、墨子、鬼谷子、韩非子……柳亚子、海子……。另外,用“子”字表字的文人是特别多的,几乎成为一种既崇低又形而上的精神传统,比如司马迁字子长,杜甫字子美,苏轼字子瞻,唐寅字子畏,曹寅字子清……事实上,这些古代圣人的思想智慧,就是人类童年的经验展现。人类童年经验的重要性,亦如一个人的童年经验在其一生中的重要性。泉子的诗歌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不少的诗篇中,抒写和称颂了人类童年之子,正如诗人在诗中所言:“屈原是我心中的英雄……荷马是我心中的英雄,穆罕默德是我心中的英雄,耶酥是我心中的英雄,释迦牟尼是我心中的英雄,孔丘是我心中的英雄,庄周是我心中的英雄……”(《莫名的惊悚》)诗人在这些圣人面前,是谦卑的,甘愿做一个眺望者,甚至对他们的景仰怀有“莫名的惊悚”之感:
那在未知中,永远无法完成的你,会成为另一个英雄吗?
哦,你依然无法说出这颤栗,这莫名的惊悚!
——《莫名的惊悚》
批评家尼尔・波兹曼说,人类后现代工业社会后的童年正在消逝。童年之所以对整个人类而言具有极大的永恒魅力,很大程度上与生理年龄无关,最主要的在于其天真烂漫的天性,在于它无限的想象力。人类的童年,蕴藏着一种了解、征服世界的原始力量与无畏的冲动。历史告诉我们,希腊哲人和东方圣人,几乎同时发现和预示了“童年”这个概念,罗马人又借用希腊人的思想,发展并超越了希腊思想的“童年意识”。而到了十八世纪,随着工业社会的来临,人类的“童年意识”开始削弱,随之而来的欧洲工业文明催生出人类的“成人意识”。19世纪英国与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与艺术中突然兴起一股“自然主题”与“童年主题”,从某种程度上说,即是诗人、小说家和艺术家对人类文明中的“成人意识”进行反思与批判的结果。他们意识到“童年意识”作为一种经验,在人类历史中的深刻意义,他们认为在大机器文明主宰下的现代性社会里,人性不可避免地趋向于物化、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丧失了人类原本在文明的自然状态下充分呈现与拥有的自由和善良的意志、崇高的想象力、纯真的好奇心和真实的情感世界,使人类变得自私、邪恶,变得封闭、迟钝,缺乏创造力和想象力,而这一切,终将导致人类文明基因的匮乏与衰退。诗人泉子的诗集《杂事诗》(2012)、《湖山集》(2014)中书写了大量体现“童年经验”的诗作:
在更年轻的时候,我曾以为爱情会永恒
就像我曾以为我能永远年轻
在更年轻的时候,我曾把清晨树丛深处一声雀鸟的啼鸣
与一群乌鸦的翅膀在天空中划出的低低而倾斜的弧线
作为一种永恒的形式
随后的那些否定与新生,那些由孤独与欢愉编织而成的时光是漫长的
直到有一天,我们试着,并终于理解了
爱并非作为一种情欲,甚至并非作为你与单个事物的连接与束缚
而是对至真至美的永恒的激情与热爱
直到有一天,我们终于理解了每一次生命
都是我们向那圆满之地的再一次出发
直到有一天,我们终于理解了
清晨树丛中一声雀鸟的啼鸣与一对对黑色的翅膀在天空中留下的那些光滑而破碎的圆弧
都是真理从空无中发出的召唤
——《直到有一天》
同样,诗人在《反对》一诗中这样写道:“……他的眼睛中充满了他在幼年时,一个人被他的同伴引向,并站在悬崖边时的恐惧与茫然 / 但他很快就适应了,并不再因这样的画面而困扰 / 并把它作为这个时代最强势的文明的一部分……”;“衰败啊!我记得那些曾经的美 / 并渐渐理解了那寓于持续了整个夜晚的狂风的 / 残暴的善意 ”(《衰败》);“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你三岁零七个月又二十天 / 我在与你相仿的年龄对时间的第一次思索同样是突然的…… 也许等你长大后,/ 你可以用魔法让爸爸妈妈永远不老,永远不死 / 可以让我们永远在一起!……”(《启示》);“二十年前,我十岁,祖母死于那年夏天一次普通的睡眠 / 祖母说,她累了 / 她先去睡了 /一次普通的睡眠囚禁了一次绵长的有始无终的睡眠 / 并从众多的睡眠中抬高”(《记忆》)。这样有着“童年经验”叙事抒写,在诗人的诗集中随处可见,尤其是在诗集《杂事诗》中。显然,在写作中长期存在“童年经验”与“童年意识”的诗人,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早慧的,有着先知先觉的禀赋。诗人在诗歌中,把自己喻为“从童话中走失的那个人”:
我就是从童话中走失的那个人
我永远也不要成为那个中年的死胖子
相对于对浑浊的目光与浓重的口臭的忍受
我更愿意死于一次少年的决斗
一场青年的瘟疫
或者在耄耋之年,一次马背上的眩晕
——《我就是从童话中走失的那个人》
“童年经验”仅仅是泉子诗歌中写作的重要征象之一,而我十分重视这个写作征象。童年经验在很多杰出诗人、艺术家与思想家的作品中可以找到蓝本。在中国当下文化视野中观察,顾城就是一个拥有“童年经验”的代表性诗人,何多苓也是拥有“童年经验”的杰出艺术家,尹朝阳也是拥有“童年经验”的70后重要艺术家,这样的例子太多,不一一列举。而当我们放眼西方文化,我们同样可以找到“童年经验”的杰出文本:本雅明的《驼背小人:1900年前后的柏林童年》(此书亦有翻译家简译为《柏林童年》,现存有“最后稿”和“基森版”)。本雅明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进行片断式书写,全书由30段彼此独立的文本组成,而整个文本又不具备回忆录在时间、地点、事件、人物等方面的连续性,但是他的敏锐洞察与细腻笔触,深刻呈现了柏林都市生活影像与时代语境:胜利纪念碑、动物花园、电话机、西洋景、捉迷藏、小人书、幽灵等,一切在本雅明的眼里,无不耐人寻味。本雅明多次表示,不愿将该书简单地视为自传性的童年回忆,他在该书1938年的“最后稿”的序言里写道:“我有意唤起我心中那些在流亡岁月里最能激起我思乡之痛的画面——来自童年的画面”,“在此,思念的情感不该主宰我的精神。我努力节制这种情感,旨在从特有的社会发展必然性中,而不是从带偶然性的个人传记角度,去追忆往日的时光”。无疑,本雅明在回忆柏林童年的过程中,他已经自觉地将童年的记忆上升为童年经验。对本雅明而言,对柏林的现代都市生活的体验,并非是个体生命的体验,而更多的是对21世纪初开始成型的现代主义的体验。日耳曼文学德裔教授、本雅明研究学者乌维・斯戴纳尔(uwe Steiner)指出:“《柏林童年》与《巴黎拱廊街研究》共同指向19世纪下半叶,并不单纯是对这一历史时间的关注,也是对现代主义之源起的关注”。
在我看来,人文意识状态下的“童年经验”具有强烈的时代隐喻与社会表征。并非每个诗人、艺术家都能够成功地运用和创造“童年经验”,持有深刻的“童年经验”的诗人、艺术家们的童年几乎都处在一个复杂而动荡的时代,正是这个时代赋予了他们宝贵的童年记忆与时代记忆的叙事能力,从而深刻影响他们的思考与创作。泉子的童年经验所对应的时代正是我们这一代共同经历的文革“尾声部”。他的“童年经验”既不同于本雅明的“童年经验”,也不同于顾城、何多苓的“童年经验”;他的童年经验与尹朝阳的童年经验,则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他的童年经验,是隐秘的,忧郁的,也是诗意的,深刻的,既有理性的时代思考,同时又是对个体人生命运的追问与怀想,这种追忆与怀想,同样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以及当下后工业文明交集呈现的多元现代性,产生悖离与抵触,而当下很多诗人、艺术家们之所以不能深刻地表达与抒写“自我”与“他者”的命运,不能进行时代的诗意终极追问,创作中呈现出一种真实的苦难诗意匮乏与衰竭,同时又没有返照和回归传统文化的童年意识,这样的创作自然缺乏生命力与诗意源头,其结果形成一个关键性问题——那就是他们在创作主观上丧失了创造与挖掘“童年经验”的能力,或轻视了“童年经验”在文化艺术中呈现的永恒价值与人类诗意生活的复归与再生。当我们翻阅泉子新近出版的两部诗集,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泉子个体的“童年经验”弥漫其间,增持了诗歌文本“清澈的质地”(诗人江离语),无形中加剧了他诗歌写作的深度体察与诗思远见:
我们去钓雪,我们去钓山,我们去钓水,
我们去钓漫天的粉末,
我们去钓离去的鸟群为我们快递来的纷纷扬扬的鹅毛,
我们去钓奔跑的兔子,
我们去钓漫山遍野而无人放牧的羊群,
我们去钓一夜之间全部逃脱的树木,
我们去钓阴郁而灰蒙蒙的天空,
我们去钓雾蒙蒙而明晃晃的大地,
我们去钓昼与夜之间仿佛而又如此细微的不同,
我们去钓那一直追随我们,
又消融在我们此刻回望中的蜿蜒小路,
我们去钓白茫茫的寂静与孤独。
——《我们去》
如果说,泉子的“童年经验”是“星光”,是“必须在剧痛中才得以完整保存的皎洁(《在西泠桥》)”,以诗人与生俱来的先天性禀赋而存在与激活,而且并非每个诗人能轻松持有;那么,如何有效继承东西方和谐共生的诗思传统与独立思辩的精神向度,则是泉子诗歌写作中另一个显在的重要征象,它是具象的,又是抽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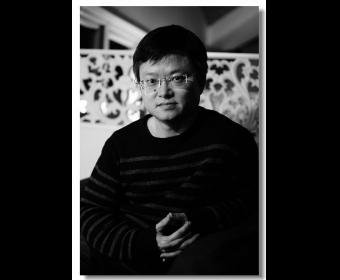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