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1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算起来已经从事哲学训练整整28年了。在这28年里,我曾经遭遇过不少尴尬的时刻,比如在火车上,来自天南海北的陌生人开始试探着闲聊,每当问到我的职业和身份时,原本热闹的场景往往会瞬间变得尴尬,空气也随之凝固:‘哦,学哲学的。’”
整整10年,周濂都以这样的方式,开讲西方哲学史——那是面对刚入学新生而设立的一门通识课。
因《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等书,周濂被视为公共领域写作的代表作家,却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位出色的教师,他主讲的西方哲学史是中国人民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之一。
把哲学讲成“热门课”,绝非易事。
马克思曾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可面对生活压力,理论思维往往苍白。更何况,哲学又是那么虚无缥缈,每一代哲学家的最大工作似乎就是在推翻前人的工作。几千年过去了,哲学的基本问题依然没有答案。
没有哲学,文明的发展就会失去方向,无数代人会被同一道门槛绊倒。历史本无宿命,可一旦智慧受限,我们就注定无法挣脱历史的周期律。
如今周濂已不再教西方哲学史,曾经的“热门课”凝聚成《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从课堂走上读者们的案头。
“作为职业,哲学并不是性价比最高的职业,但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我相信哲学是值得我们用一辈子去实践的。”在序言中,周濂这样写道。
哲学是一条“贼船”
北青艺评:哲学是个很冷门的专业,您当年为何要学哲学?
周濂:我高中时喜欢辩论,常说些绕弯、难懂的话,老师、同学听不懂,自己却觉得很有道理。在我成长的那个县城,当时文化资源很少,只有一家新华书店,上高中时买了两本书,一本是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一本是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其实都没看完,但它们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
我从小喜欢写作,作文常被老师当成范文,那时最大的梦想是将来当编剧,或者当导演。上高二时,读《作文通讯》杂志,上面有一篇复旦大学哲学系学生写的文章,自称是“曲线救国”,他想今后去写作,所以学了哲学,因为哲学更有深度,对写作有帮助。
这篇文章给我很大影响,我也想今后去写作,为什么不同样来个“曲线救国”呢?所以高考时,我也报了哲学系,没承想,上了“贼船”就下不来了。
高考报志愿时,我父亲想让我学国际关系,说将来能当外交官,为此我们大吵一架,好在他没强迫我改。拿到录取通知书时,我狂欢了一晚上。
北青艺评:为何上了“贼船”就下不来了?
周濂:刚上大学时,我对文学还挺感兴趣,写了一些小说和诗,在院刊上也发表过。那时雄心勃勃,准备写一本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最终只写了1—2万字,就放弃了。
那时迷恋先锋小说,特别喜欢余华、苏童、格非等。每次假期回家,需转道上海,路上要走一两天,只有绿皮火车可乘。在车上,我随身带着小说,一个凌晨,我读完了《麦田的守望者》,当时想:这样的小说,我也能写出来。可惜后来再没这种感觉了。
至于说为何上了“贼船”就下不来了,因为高中时我对哲学了解太少,只读过弗洛伊德、马尔库塞的东西,可他们二人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进哲学系后,开始接受专业训练,口味改变了。再看小说,便觉得思想密度不够。小说中也有一些引人深思的话,但这样的话太少,看小说可以很快,常常是一目十行,因为找不到太多有营养的东西。相比之下,哲学书的思想密度就比较大了。上大学时,我在北大第二教学楼的一间教室里,读了尼采的《悲剧的诞生》,那时非常感动,便将书中几句话抄在课桌上,希望别的同学也能看到,也能产生共鸣。
北青艺评:您当年是出于爱好去学哲学的,这个热情始终没消退吗?
周濂:从事任何专业,初期都是靠热情,但后来热情会渐渐消退,走向专业化。不论做什么学问,乐趣可能只占10%,专业的东西要占90%。成为专业工作者,就意味着为了10%的乐趣,去忍受90%的折磨。所以说,学科化、专业化对人的热情是一个巨大的消耗。
哲学家在思考什么
北青艺评:哲学是挺有趣,可读到康德,普通人恐怕都会放弃吧?
周濂:确实如此。我给学生上课时,一讲到康德,大家反应最强烈,因为听不懂。邓晓芒先生曾说,西方哲学到了康德,便进入了专业领域。
此前哲学使用的概念多来自日常生活,读者有亲切感,比如笛卡尔,他的哲学书写得像小说一样好看。可到了康德那里,哲学有了门槛,康德使用的概念非常专业,再到黑格尔,哲学离现实越来越远,大众对哲学的评价也越来越低。
对于术语,要两面看。一方面,有些术语是没必要的,成了“哲学黑话”;另一方面,有些术语是必需的,这样才能表述严谨,但只有哲学家能懂。哲学家能辨析概念间的细微差别,这对于更深入的讨论很重要。这就像音乐家,他们能听出不同曲调的细微差别,普通人却听不出来,只能说,他们的耳朵和普通人的耳朵不在同一频道上。
哲学家的价值,在于将普通人忽略的问题锚定出来。比如六岁的小孩也会问:“这是什么?”他思考的是,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而哲学家巴门尼德却在思考:这个“是”本身,究竟是什么。
北青艺评:如此说来,普通读者此生只能与哲学无缘了?
周濂:任何学问都分专业和普及两个层面,普通读者了解了普及性的知识后,再深入一步会比较难,必须有老师教。自己生啃文献,肯定行不通。如今网上有视频、慕课等,会提供一些方便,关键看你能否保持对知识的好奇心。
北青艺评:您给学生上了10年通识课,今天大学生的思辨能力如何?
周濂:在教学中,很多学生张口就是术语,而且都是中学课本上的那些术语,这给他们学习哲学带来很大困难。他们头脑中有一套固定的认识框架,是为应付高考而被灌输进去的,可真正的哲学需要更开放的视野,不再有唯一的、标准的答案,而且要打破对标准答案的迷思,这样才能呈现出世界本来的高度复杂性和内在矛盾性。
情感教育也应从娃娃抓起
北青艺评:教育真能提升理性能力吗?从网络言论看,许多网友缺乏逻辑,动辄骂人,可他们也受过教育啊?
周濂:英国哲学家休谟曾说:理性是激情的仆人。很多人养成了固定的情感反应模式,一看到某个词、某句话,便立刻产生强烈的情感反应,在这时,他的理性能力会大大下降。所以休谟有个骑象人的比喻,即:人的情绪犹如大象,理性犹如骑象人,与丰富的情感相比,理性相对弱小,想调转情感的方向,犹如操控大象一样,慢慢来才行。这说明:说理之外,还需情感教育。
情感教育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靠不断读书、反思来实现。人人都会有许多刻板印象,要靠理性一点点消除,但在很多时候,我们明知是错的,可在情感上依然很依恋,情感与理性未能同步。比如我们父辈中的一些人,在经历了苦难后,明知错了,却坚持“青春无悔”。对此,只有予以理解之同情,通过有效沟通,慢慢改变。
我觉得,情感教育也应从娃娃抓起,不过,随着时代发展,人的情感也在转变。比如今天许多城市人谈起性倒错,不再像30年前那样,会出现生理上的厌恶感觉,能更客观地去看,这就是理性对情感的纠偏。
北青艺评:竞争越来越激烈,年轻人驾驭情感的大象似乎更难,该怎么办?
周濂:个体的力量太微弱了,无法对抗环境的压力。今天孩子们的学业压力更大,而这样塑造出来的人难免带有残缺性、不完整性。但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同的,没有共同的解决方案。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希望他们在压力之下,尽可能找到平衡。
如今也有不少中学老师意识到问题,也尽其所能在弥补,包括鼓励学生多读课外书。来听我课的新生中,有一些人在高中时就读过我的书。我觉得,所有努力都不会白费。反过来说,压力可能也是馈赠,经过之后,也可能让人变得更深刻,更好地理解社会。
北青艺评:在教学中,面对学生们的种种问题,会不会有时感到失望?
周濂:那倒没有。毕竟通过高考筛选,能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还是相对优秀的。改变犹如涟漪,初期只有中心有震动,慢慢就会扩散到边缘。我很早就已放弃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了,谁也不知道影响会在何时、何地发生,那么只要在做,总会有结果。
警惕虚幻的思想果实
北青艺评:会不会有学生问,哲学已有几千年,基本问题至今未能解决,为什么还要学它?
周濂:哲学没有进步性,它不断回到最初的问题上。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有景观性,后人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不断进步。所以,哲学不是科学,没有经验可证实的假说。所以几千年来,人类的观念系统并未与时俱进,传统哲学的体系已失败了,但其中的思考和表达仍在闪光。
比如黑格尔,他提出的“为承认而斗争”“主奴道德”等,今天还在说,包括“历史终结论”,也来自黑格尔哲学。哲学的宏大体系犹如一座神庙,今天已没人进去烧香了,但它还保留在风景线中,人们依然会去瞻仰一下。学习哲学,可以加强我们对人类整体历史的理解,那其中有历史上最伟大的心灵、最智慧的头脑留下的成果,对我们仍有启迪意义。
北青艺评:能否举例说明这个启迪意义呢?
周濂:比如维特根斯坦,他是一位特殊的哲学家,被称为“哲学家中的哲学家”。他的书都是写给哲学家看的,专门帮他们诊断“哲学病”。普通读者看后,会觉得不知所云,因为普通人没患上“哲学病”,只有先把你的“哲学病”诱发出来,才能给予治疗。
二战时,维特根斯坦一次曾跟他的学生马尔库姆聊天,讨论英国会不会暗杀希特勒。马尔库姆认为,英国的民族性格决定了,他们不会这么干。维特根斯坦听后大怒,斥责道:你跟我学了这么多年,居然还用民族性格这么大而无当的概念来讨论问题,你怎么可能理解世界?维特根斯坦的意思是,人要看到事物间的精微差异,千万别停留在宏大叙事层面,可很多人也会不自觉地犯这个错误。
北青艺评:这个话题至今热门,少有人意识到它是个伪问题。思想家太多,哲学家太少,这是为什么?
周濂:因为当思想家比较容易,只要对世界有一些独到的、宏大的判断,就可以了。思想家就像闪电,他们划破暗夜。普通人更欣赏思想家,因为思想家能简单地解释这个世界,甚至将其概括成一句话,使普通人能不费力地获得深刻性。
当然,对于真正的思想家,社会还是需要的,我们有漫长的顿悟传统,只说能说清的,对于说不清的,便选择沉默。所以我们没有自己的逻辑哲学导论,只见登楼,不见扶梯,不能通过一步步严谨的论证导出结果,而没有这一过程,给人带来的,往往是虚幻的思想果实。
北青艺评:顿悟是方便法门,岂不是很有效率?
周濂:快不等于好,这种效率都有代价,只是现在还没付,所以很多人便以为没有代价,这是错误的想法。
我们看西方近代史,没有宗教战争,就不会有宽容精神;没有宗教革命,就不会有启蒙思想;没有怀疑精神,就不会有科学精神……忽略了前者,后者也难成功,很多人以为可以跨越,直接拿成果,少走“弯路”,可结果呢?以请赛先生为例,如今全社会崇拜科学,可依然缺乏科学精神。精神结构的改变是漫长的,真正习得宽容、尊重等,没有捷径可走。
读书人要接受被边缘化的现实
北青艺评:在今天,公众眼中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似乎是兜售鸡汤的大富翁们。
周濂:出现这一现象不奇怪,我们有“君师合一”的传统,既是封建帝王,也是导师。封建时代已过去了,类似的思维方式仍在,所以不同单位涌现出大大小小的人生导师。我去山东一家私企,老板办公室里挂满了画像和标语,他不仅抓生产、抓管理,还要抓员工的生活和思想。
至于大学生,大一、大二的新生还没有生存意义上的焦虑,他们比较关注哲学。而大三、大四的学生面对毕业问题,焦虑主要来自择业、户口、房子、工资等,这些年竞争又比较激烈,他们中可能也有人看哲学书,但程度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在课堂上,我会建议学生们,在大学四年中,应每天读一小时经典著作,真踏入职场,就没时间读书了,到那时,只剩看娱乐节目的脑力了。上过我课的学生,有的会写信与我讨论哲学问题,他们中不少人的思考非常深入。
不过,与上世纪80年代比,思想界的影响力确实在下降。我在班上做过调查,来听我课的100多名学生中,他们对思想还是有兴趣的,可听说过秦晖的从没超过10人。在商业化时代,英雄不再是思想家,而是商业精英和娱乐明星,如果问马云、迪丽热巴,恐怕没人不知道。虽然有心理准备,我还是吃了一惊。我想,今天读书人应接受被边缘化的现实。
北青艺评:这本书是您过去10年教学的总结,您希望读者能有怎样的收获?
周濂:概括来说是两点,即:批判思维和人文素养。我认为,批判思维应是大学本科生的必修课,因为他们从小缺乏相应的训练。在中文语境中,常有人误解批判思维,批判思维不是否定,也不是斗争思维,它是通过一定的标准评价思维,进而改善思维,是合理的、反思性的思维。掌握批判思维,是进入公共空间的基本功。至于人文素养,我也一直在给本科生讲古希腊悲剧,希望他们能看到,许多时代问题其实来自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古老。
本文原载于5月31日《北青艺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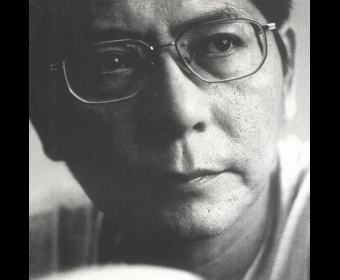
![作家专访丨熊焱: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视频]](/uploads/allimg/250606/0T124O47-0-lp.png)
![Liu Zongxuan 柳宗宣 | OUR BODIES AS RUINS 身体的遗址[视频]](/uploads/allimg/200606/1-200606111H3436-lp.jpg)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