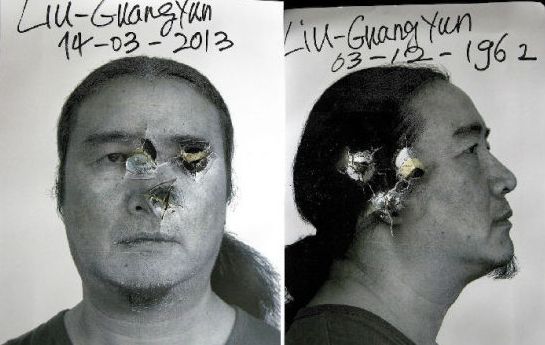
沈其斌对话刘广云
访谈时间:2013年8月16日
访谈地点:德国莱茵河美丽堡
沈其斌:这次来德国非常舒服,有一种真正放松的感觉。
刘广云:和你平时生活的反差还是蛮大的。
沈其斌:平时比较累,这一次有一种比较放松的感觉。还是切入正题吧。你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的,什么原因会导致你去考这个学校?或者你是由于什么原因开始画画的?
刘广云:画画真的从小就喜欢,没有任何原因,我家里没有艺术的背景,那个时候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有一个考学的目标 。 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文革才结束,谁知道高考会恢复呢?没有人能预料像今天这样的未来,所以画画完全是出于一种爱好,不是把它当作一个未来职业来规划的。
沈其斌:后来怎么开始考学的?
刘广云:上了高中以后,学校里来了一位美术老师,借给我一本书,就是苏联的契斯恰科夫的《素描教学》,我才接触到了正统的学院派训练,那时大概是1978年,高考开始恢复,自己也意识到这是一个用自己的爱好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于是开始走考学的路。
沈其斌:学了几年考上的。
刘广云:考学蛮坎坷的,考了三年,十分艰辛,当时的执着和面临的实际问题是现在的学生根本无法理解的,像我小学的时候被送到少年宫搞儿童创作很多文化课都没上过,就是在学校里的时间也不太上课,老被组织起来闹革命,根本就没好好学习,美院恢复高考后开始文化课只是象征性的,等我们该考了,规定除了艺术还要加试外语,政治,地理,历史,这等于把人先折腾死然后让你再活一遍,我幸运,活过来了,很多童年的画友就因为文化课被淘汰了,他们其中很多都是很有艺术天分的人,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多谋生的可能性,他们以后的日子一蹶不振,现在我回老家都不敢见他们。
沈其斌:这个经历我们都有过。 你是哪一年进中央工艺美院的?
刘广云:83年。 那是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代,我在校期间正赶上85思潮那个时期,在学校里学了些什么都不重要了,印象深刻的是那种自由的精神状态,我是83-87年在北京上学的,那个时候思想界,文化圈子里非常活跃。
沈其斌:当时考上学校以后有什么特殊的记忆和经历,感觉有什么变化?
刘广云: 那时候大学生出门有种很牛逼的感觉,你到哪里别人都对你高看,比如我骑自行车旅游山东,喜欢戴一个校徽,别人一看你是大学生,上面写着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觉得你是中央来的,吃喝都不要钱的,住宿也有不要钱的,还记得当时骑车行走了两千多公里,用了21天,一共花了70多元, 就靠这枚校徽可省了不少钱,现在还有学生出门带校徽的吗?这不是明摆着告诉人家自己是这个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吗,现在这个社会把学生整成一副整天为未来前途忧心忡忡的苦逼相真是不正常
沈其斌:从83年进大学这四年,让你感觉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刘广云:就是一种视野的开阔,思想的转变,实际上是一种精神的洗礼。从除了画画什么都不懂到突然感到自己要建立一种理想,想承担一种文化的责任,而不是像今天的学生一样考虑很多功力性的东西。后来可以很明显地区分有过这个阶段的人和没经历过这个阶段的人很不一样,不是哪个好哪个坏,是不一样。
沈其斌:有没有难忘、记忆特别深刻的事情?
刘广云:太多了,不知道从哪儿说起。先说入学的第一天吧,这个我倒是真永生难忘,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去报到,负责登记的一位女老师看了我一眼说,头发太长了,先理发去。无奈我去理了,完了再回去登记,那老师又看了我一眼说,不行,鬓角还是太长。当时全国在开展反对精神污染的运动,对发型衣着要求特别严格,我们学院周围的理发店都被新生占满了,一些同学都是在理发店里第一次碰面的,打个招呼一问,原来是一个班的。我理了两次才通过也没什么脾气,我觉得很牛逼的是装潢系的男生,齐刷刷地都理成了光头,以表示对这种规定的抗议,新生敢这样,你想想,那个时候的年轻人血液里就有一种很强的反叛的力量,一种今天再也看不到的精神。在校期间求知欲特别强,喜欢读些有新思想的书,当时北大出了一个《走向未来》丛书,系列发行,是一种白皮黑字的封面设计,估计那个时候在北京读书的学生都会记得,买了一本等下一本,那个系列我几乎都买了,印象很深的是一本金观涛的《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你听这名字就知道,那个时候已经在这样的角度看文化了,那是80年代初啊,那边文革的惯性还持续着哪,这边西方自由精神的洪水猛兽就扑面而来了,多好玩的年代!还有就是满北京地跑着听讲座,哪个学院有好讲座,大家都会传消息,劳申伯格,伊夫圣罗朗等很多大师级的艺术家都来北京做展览和讲座,我都在现场,为了在北大听张岱年主讲的一次哲学讲座我还和史论系的朋友画过入场卷。我在学校的四年正好经历了中国一段思想巨变的时期,到了快毕业就很开放了,八十年代后期文化环境非常宽松,比今天宽松,大家对新思想的追求有一种报复性的爆发力,被欺骗太久了,被压抑太久了,记得拿到毕业证的那天晚上,大家爬到宿舍的楼顶,喝酒唱歌,对面的女生宿舍也遥相呼应,大家狂吼,唱崔健的《一无所有》,将旧物丢得满天飞,闹了个通宵,第二天大家挥泪而别,不知道功利社会的今天的学生还有这份情谊吗,我有点怀疑。那时的交通和咨询没有像今天这么发达,联络主要还是靠写信,很多同学真的就是一别便音信全无了。
沈其斌:那个时候尤其像中央工艺美院毕业的是抢手货。
刘广云:是抢手货,那个时候恢复高考不久,招生也少。可以预见毕业肯定是前途一片光明, 我去了山东工艺美院研究所,在那里待了三年, 别说搞研究、搞艺术,更多的是搞项目,那个时候自由经济的浪潮已经冲击过来了。
沈其斌:那个时候没有进入所谓的创作?
刘广云:大学毕业以后研究所很支持我,我做了一个巨大的软雕塑,我用的材料是麻,我坐火车去泰安,到农民那里收麻,用卡车运回来,我自己支个巨大的锅染颜色,还好研究所比较支持我,给我资金,然后我用我买的地毯机在研究所的车间里扎起架子来干了三个月,自始至终一个人干,最后做成一个巨大的高4米,宽4米,重200公斤的一个软雕塑。展览了一次,获了一个奖,接下来扔在那里就成了垃圾了,现在都不清楚那个时候哪来那么大的劲。同时期还做了一些实用性的水墨,叫《艾滋病系列》,在济南做了一个地下的展览,当时栗宪庭主持的美术报也做了介绍。
沈其斌:照片还都有吗?
刘广云:能找到一点资料。 那个时候做作品 没有任何的附加的想法,那么差的条件,10平米的房间,兼画室和住宿,还有一些当地的文艺青年,老外留学生常聚在我那里,那地方早就被公安局盯上了,现在是请去“喝茶”,客气多了,那个时候没茶喝,让你坐在一个冷板凳上,盘问一番,在我后来出国办护照的时候他们给了我不少麻烦,托了很大关系才洗清自己。就那样的条件,做作品却是很投入,所以说谁要说他今天工作室太小,条件不够好,画不出东西来,我根本不信的,那就是没有感觉了。
沈其斌:后来什么机缘离开了济南?
刘广云:我在山东工作的时候就一直觉着那是临时的,你想想从北京热血沸腾了四年,再回到地区很难安心的。
沈其斌:觉得容不下。





![作家专访丨熊焱: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视频]](/uploads/allimg/250606/0T124O47-0-lp.png)
![Liu Zongxuan 柳宗宣 | OUR BODIES AS RUINS 身体的遗址[视频]](/uploads/allimg/200606/1-200606111H3436-lp.jpg)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