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时代的写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少功以其多方面的文学成就在文学界以至于整个思想文化界均都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其中,又以其长篇小说和思想性的散文随笔的创作,以及卓有影响的《天涯》杂志的主办更加受到人们的重视,而对他的中短篇小说,人们的关注往往较少,除了《鞋癖》和《梦案》等少数篇什之外,韩少功自己对此也似乎很少谈论。但在实际上,作为其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韩少功的中短篇小说与其长篇小说和散文创作一样,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它们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全部的文学写作所具有的精神特征,而且还有着自己的独有特点。
在韩少功的文学观念中,文学的精神特征一直有着相当突出的强调。他认为在人类众多的实践活动中,“选择文学实际上就是选择一种精神方向,选择一种生存的方式和态度”,1文学的意义与力量就在于其所具有的精神价值。对于社会现实与大众生存,作为一种精神实践方式的文学,不仅是审美,还“是怎样把握判断现实的精神尺度,是如何对自己和大众的生存现实保持一种创造性的价值追问的问题”。2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殊的历史语境之中,中国作家的“选择文学”,就有了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此一时期的中国以至于整个世界的精神现实与文学状况,韩少功有着这样的基本“判断”:“九十年代冷战结束,全球正在实现经济一体化和‘经济挂帅’,东、西方的理想主义都受到形式不同的重大挫折,精神危机正在威胁着人类生活,人类文明的命运正在面临着新的现实难题”、3“现在的生活中‘精神’的含量越来越稀少了,文学创作打不起精神”。4“精神危机”的情状广泛而深重,但正是文学实现其精神价值的历史性契机。所以韩少功进而又认为:“精神危机的时代倒是为文化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创造空间”,越是精神出了问题,才越是需要并且越有可能出现优秀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在此意义上,精神危机的现实又“刚好可能成为人类又一个精神高峰的前提”。5也正因此,对于韩少功这样一位具有深刻的思想力量、批判精神与现实关怀的重要作家自身而言,作为一种精神实践方式的文学实践正是其所找到的宿命般的精神“皈依”,是其将以自己的生命“一次次奔赴的精神地平线”。6正是以其丰富多样的文学实践,韩少功建立了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因为具有自己的本质特征而相对自足却又与阔大的历史与现实息息相关的独特的精神世界。
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少功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思想性的散文随笔与小说创作两个方面,是与张承志、史铁生、李锐和张炜等人一样为数不多的以散文随笔的写作产生重要影响的小说作家之一。在他那里,散文与小说是两种不同的精神活动。它们在韩少功精神世界的营构之中承担着各自不同的功能。对此,韩少功曾经这样说过:“想得清楚的写散文,想不清楚的写小说。这是个通俗的说法,其意思很明显:小说与散文之间存在着一种对抗、紧张的关系,tention的关系。有时候,它们甚至互相怀疑和互相消解。大体上说,散文是我的思考,是理性的认识活动;而小说是我的感受,是感性的审美活动。它们承担着不同的功能,也有不同的价值观。在散文看来是很重要的东西,比如对现实问题的敏感,比如思想的深度,常常在小说那里变得不怎么重要。”7在另外一个场合,韩少功又曾这样说过:“我是个笨人,没法用小说来实施抵抗,只好逃到散文里去”。8毫无疑问,韩少功对9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实较为清晰的理性思考,更多地是以散文的方式进行表达,而由于在90年代以来中国的历史语境之中,这些表达有着相当突出的批判力量,所以在实际上,散文所承担的基本功能就是进行直接的精神“抵抗”。但在另一方面,韩少功的那些并不一定“清楚”的复杂“感受”的表达,却是选择了小说。某种意义上,小说在韩少功这里明显有着不同于散文的别样的精神价值。在他看来,“我们身处一个没有上帝的时代,一个不相信灵魂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之中,“周围的情感正在沙化”,“到处可见浮躁不宁面容紧张的精神流氓”,“灵魂纷纷熄灭的‘痞子运动’正在成为我们的一部分现实”。而“意味着一种精神自由”的小说,正可以“为现代人提供和保护着精神的各种可能性空间”。但在实际上,9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的现实却在总体上难以承担其应有的任务,丧失灵魂的技术操练充斥文坛,“关于乏味的偷情的百科全书”倒似乎成了“历经了极左专制又历经了商品经济大潮的国民们,在精神的大劫难大溶冶之后”的“最高水准的精神收获”。正因如此,韩少功才认为9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的主要问题便是“真情实感的问题,是小说能否重新获得灵魂的问题”,所以,他才竭力推崇张承志和史铁生所展开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反抗精神叛卖”的“精神圣战”,并且高度肯定他们的小说创作所形成的“完全自足”和“独特的精神空间”。9如果根据其文学理念甚至更为具体的小说理念来进行考察,我们就会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少功的中短篇小说所形成的,正是一个相当独特的、不仅不同于他人而且也有别于其自身的散文及长篇小说创作的精神空间。
历 史 记 忆
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少功的中短篇小说最为首要的特征便是对历史记忆的深入开掘。对于记忆问题,韩少功曾经有过这样的阐述:“人的记忆是很不可靠的。我们的往事总是在遗忘中沉埋和流散,总是被时间慢性谋杀,于是身后常常只留下一片空白。贵贱沉浮,冷暖忧乐,在这一片空白中当然已经都无从区别,对于我们来说也就毫无意义。如果事情就是这样,那么一种向身后无限倾泻着空白的人生,与猪狗的状态,与疯傻者的状态,其实并无二致。这种丧失记忆的状态如果不产生精神迷失乃至神经错乱,倒会是生理学上的咄咄怪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写作是对遗忘的抗争,是对往事的救赎,甚至是一种取消时间的胆大妄为——让难忘的一切转化为稿纸上的现时性事件,甚至在未来的书架上与我们一次次重逢。只有在这一过程中,人性才能够获得记忆的烛照,才能够获得文明史的守护和引导”。10在他看来,人的记忆正有着人之为人并且使人不致于产生精神迷失的重要价值。文学写作对于记忆的“珍藏、清理以及复活”,不仅是“对遗忘的抗争”和对人性的烛照,还是对“自己的精神世界”的精心“编织”。11也正是通过这种相当独特的精神实践,文学写作者才得以在一个物欲横流的世俗现实中不断地寻求和确证着人生的意义。也许,正是本着这样的认识,90年代以来韩少功的大部分中短篇小说,才都集中于对记忆的书写。
在韩少功那里,往昔的记忆是那样顽强,它甚至会不期而然地强行“闯入”我们的生活,从而“复活”于我们的精神深处。在《北门口预言》中,就在以周老二作为象征的屠戮历史正在被人们渐渐淡忘的时候,偶然出土的西汉石俑,却在陡然之间复活了人们的历史记忆。《余烬》中的福生因为公务而重新回到当年插队的山区,但是故地的一切似乎都使他“感到陌生”和“不适应”:“他发现他已经不能找回自己的过去,连橘子也完全吃不出当年的味道”,往昔的一切,似乎都已经杳不可追。但是,二十年前作为“知青”的自己上山伐竹时所曾写下的一张字条,却将他的记忆猛然唤醒。他开始重新忆起并且依稀地寻得了当年的一切。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总有一些神秘的东西将过去与现在牢牢联结。《余烬》之中,这样一些神秘的东西,正是那位鬼魅般的妇人和字条。正是她的再一次闯入,使得福生清晰地记起了“知青”时代那个狼狈不堪的夜晚。而在《暗香》之中,代表着记忆而强行地闯入老魏的生活的,却是一个叫做竹青的人物。正是竹青的两次深情厚谊的突然造访,促使他“一步步开掘自己白茫茫的记忆”,进而重新书写自己的历史。蒋竹青原是老魏在“文革”时期所写的一部小说手稿中的人物,在这部小说手稿中,“这个竹青是个混迹于花工队伍中的右派分子,竟然向少年儿童灌输反动思想,破坏教育革命,又造成一次校园火灾,最终被革命师生愤怒地扭送公安局”。而当老魏翻阅手稿发现了此点后,“他越看越觉得恼恨。他怎么写出了这样糟糕的东西呢?竹青被打成右派,肯定是冤案。把他写进公安局,更是冤上加冤,居心何忍。他恼恨自己当初缺乏足够的勇气,还竹青一身清白——他至少应该写出,竹青者仁义之士也,不但不会犯罪,而且正是他真正关心着孩子们的健康成长”。这样一件似乎是极为微末的历史失误,竟然使老魏“后悔不迭”,难以心安,并且“决心改写旧稿,重写过去的日子,弥补自己的歉疚”。正是通过这种对于“过去的日子”的特殊方式的“重写”,小说中的老魏不仅在精神上重获安宁,甚至还变得重生般地振奋与昂扬——他“跨上木椅,志得意满,无限风光。他站在上面从容四顾,看到整个世界在他面前突然怯怯地矮了一截”。强行闯入的记忆竟然导致了已近暮年的老魏在他的精神深处完成了一次灵魂的洗礼,也使他的生命散发出特有的芳香。宿命一般无法摆脱的历史记忆,就是这样借助于一切可能的机缘与物事刺破着我们遗忘的假象,让那些我们曾经遗忘的历史,那些或者是杀气腾腾、狰狞可怖(《北门口预言》)、或者是别含隐曲、有待追悔(《暗香》)的社会或个体生命的历史重新进入我们的生活,重塑着我们的精神与灵魂。
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少功的中短篇小说较多地书写了其个体自身的生命记忆,比如《那年的高墙》、《走亲戚》、《鞋癖》和《兄弟》之中的童年记忆和家族记忆,以及《很久以前》、《山上的声音》、《余烬》和《兄弟》之中作为“知青”一代的“我”的青春记忆,但在这些作品中,对于个体自身的生命记忆的书写显然又是与中国社会在1949年以后严峻而又壮阔的历史进程紧密关联(而他的《领袖之死》和《北门口预言》则更是直接书写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记忆)。这样,也就决定了韩少功所书写的历史记忆大多都处于个体生命的记忆范围,无疑属于有着更加特别的意义的“近期历史记忆”。
近期历史的记忆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忘记近期的历史和忘记遥远的过去是不一样的。……忘记(近期历史事件)意味着扭曲用以察看现今的视镜。这是一种有意无意的逃避或排拒。它把发生过的事想象为未发生过,把未发生过的事想象为发生过。这种遗忘其实是拒不记忆”。12对于近期历史的“拒不记忆”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国家有意识的遗忘,另一种是社会无意识的遗忘。国家有意识的遗忘是出于政治目的,禁止在官方说明之外公开讨论某些事件。斯大林式的极权国家统治可以动用宣传和行政机器来实现这种强制性遗忘。软性的极权统治则可以不单以惩戒为手段,而兼以诱导来使得社会集体逐渐对某些近期世纪失去兴趣。这样发生的社会性遗忘便具有很大的无意识成分。对近期历史事件的遗忘往往通过国家遗忘和社会遗忘的结合来实现”。13
韩少功出生于1953年。从“文革”爆发的1966年迄止于结束的1976年,韩少功刚好度过了其13至23岁黄金一般的青春时代。他所书写的近期历史记忆,自然主要是改变了其一生以至于其家庭命运的“文化大革命”。在一篇题为《记忆的价值》的文字中,韩少功曾经这样说过“文化大革命”对于包括其自身在内的“知青”一代的重要意义:“发生在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间的一场政治和经济危机是如此盛产着记忆。数以百万计的青年学生被抛到了穷乡僻壤,移民运动的规模几乎空前绝后。这些青年衣衫褴褛,身无分文,辗转于城乡之间。饿其体肤,劳其筋骨,苦其心志。他们常常以日当年地守着油灯企盼。他们多年后带着心灵的创伤从那里逃离的时候,也许谁也没有想到,回首之间,竟带走了几乎要伴其终身的梦境”。14韩少功的不少小说,正是当年的“知青”运动所“盛产”着的历史记忆。实际上,除此之外的其他方面的“文革”记忆,在其小说中亦有着相当深刻的书写。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罪衍与荒诞,对于他所特别看重的“知青”生活,韩少功的《鞋癖》、《走亲戚》、《那年的高墙》、《领袖之死》、《兄弟》和《很久以前》等小说中都有相当充分的书写。但在这里,韩少功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复杂性的深刻揭示,却是我们值得关注的重点。
“文革”后中国的一种普遍的政治情绪,便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全盘否定”。在这种普遍性的政治情绪的支配之下,人们对“文革”往往只是简单化地进行政治的或道德上的批判,而对其历史复杂性却有着相当严重的忽视。但在韩少功看来,“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一个可以用“全盘否定”的态度简单对待的重大事件,人们也不应该以这样的态度放弃自己的深入思考。作为一个离开我们并不久远的历史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内在真相仍然有待重新揭示。他以小说的方式一方面揭示了简单的“全盘否定”所造成的历史遮蔽,另一方面,还很深刻地揭示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广泛的迫害运动中的一种复杂情状。
对于简单化的“全盘否定”所易导致的历史遮蔽问题,韩少功曾经在历述“文化大革命”中千差万别的不同情状后指出:“如果这些千差万别统统被抹杀,那么历史就不可理解了,也就不可能被诊断了,就只能用‘全民发疯’来解释——事实上,现在的新一代青少年对‘文革’就是以‘发疯’一言以蔽之。这正是多年来‘文革’缺乏如实分析和深入研究的结果,是再一次‘文革’式愚民的结果,将使人们难以获得对‘文革’的真正免疫力。我们不要在人事上算旧帐,历史恩怨要淡化处理,这是对的。但不能没有严肃认真的学术探讨,更不能随意地掩盖历史和歪曲历史”。15在其自身的经验与思考的基础上,在他的中短篇小说中,韩少功所着力揭示的一种遭受“掩盖”或“歪曲”的“文革”真相就是其中的“革命”。他认为,在现代中国的革命历史中,“革命与极权呈现为一种交杂的结构和演变的过程,在‘社教’、‘反右倾’、‘反右’乃至延安‘抢救运动’中,‘文革’一脉其实已经初露端倪而且逐渐发展”,“文革”不过“是革命社会演化为极权社会的一个标志”。“而在另一方面,即使在极权最为严重的‘文革’期间,革命的某些内容仍在延续”。16“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革命”与极权相互交杂的复杂的社会形态,因此,他不赞成将“文革”中的“革命”完全等同于极权或疯狂来“全盘否定”,“不赞成在批判极权的同时完全否定革命,不赞成对一个革命与极权相交杂的社会形态贴上简单的道德标签。那只能增加批判极权政治的难度,甚至最后需要借助谎言”。17在《很久以前》和《兄弟》这两部中篇小说中,韩少功都很突出地书写了“文革”之中青少年们的“革命活动”。《很久以前》在以一种充满追怀的笔调书写了红卫兵们对于革命的诗意向往的同时,还很具体地书写了“我”与孟海的“革命活动”,以及孟海的身上所延续着的“革命精神”与“文革”后社会的时生龃龉。韩少功对这些方面的书写虽然突出了其中 “革命的罗曼蒂克”的一面,尤其是孟海与“我”的“革命活动”对于俄式革命的刻意模仿,显示出十足的幼稚可笑,笔调之中不无揶揄。但在另一方面,亲切与自赏亦在其中。而其《兄弟》关于“文革”的“革命记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其与《很久以前》一样记述了当时的青少年们对于革命的诗意向往,特别是汉军与汉民兄弟的尚武精神和对军事生活的模仿;另一方面,却以痛惜与崇敬的笔调书写了民间思想者罗汉民的“革命活动”。汉民因为主要参加了当时的一个叫做“马克思主义劳动社”的“反动组织”,并且在不同的城市散发和张贴“反动传单”,“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毛主席和党中央。还提出要为彭德怀和刘少奇翻案……”,因此被作为主犯而被杀害。但这个组织无疑是相信马克思主义和相信革命的。小说曾以自我独白的方式拟写了临刑前的汉民:
我们全家和亲戚那一天没有一个人去刑场,倒是在劳模父亲的带领下,关起门来
学习了一天的毛主席语录。他们在高声诵读的时候,我挂着“反革命组织主犯”的牌
子,在五花大绑之下度过了最后的时光,正在从看守所通往刑场的路上东张西望,一
直在围观的人群中寻找熟悉的面孔,对亲人抱有最后一丝微不足道的希望。……我
只是想看一眼,让我的目光触摸一下母亲和亲人的面容,让目光在这一片人海里还有
最后的接纳和停靠,让自己离开得不至于过于孤单。
我眼中的世界模糊了,可耻的眼泪流了下来,于是我用高喊口号的办法来镇定自
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万岁!”“打倒……”不过第二句口号没有喊出来,早已套在
我脖子上的一条毛巾已经突然勒紧,勒得我两眼发黑,发不出任何声音。……
“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极权曾经将无数个自认为是追求革命的民间组织和民间思想者指认为“反革命”进行严酷的政治迫害。“勒紧”或“割断”他们的喉管,使他们“发不出任何声音”,是他们的普遍命运。但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一些特殊的禁忌,却使他们在新的时代之中仍然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使他们对革命的追求湮没于历史的烟尘。正如克里玛在谈到作为“幸存者”的作家应该书写战争或集中营中的死亡者的命运时所要求的——应该“去变成他们的声音”,为他们而呐喊。韩少功对“文化大革命”中另一种“革命”的极力张显,正是在使自己变成那些牺牲者的声音。在一篇题为《文学和记忆》的文字中,克里玛曾经这样说过:“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的问世是作为其创造者的一种喊叫,是对于笼罩于他本人、同样也笼罩于他的前辈和同代人、他的时代、他所说的语言身上的遗忘的抗议”。18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韩少功的写作成了揭破遮蔽、反抗遗忘的抗议和呐喊。
韩少功的中短篇小说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内在真相的揭示,还在于其深刻揭示了“文革”期间广泛的迫害运动中的一种复杂情状,即“ 当时的受害者也往往表现出施害者同样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种结构性的社会病相,这种冲突双方的互相复制和互相强化,是‘文革’重要的奥秘之一,在简单的道德批判中却一直成为盲点”。19《兄弟》里的秦老师对“我”的态度突然恶劣并且“宣布免掉我班长职务,声称这与我的个人表现无关,而是在学生中开始贯彻阶级路线的必要举措”,其原因,不过是“她的丈夫是一个右派而且正在蹲牢房,阶级也不好,她不得不在脸上表现出更多的革命觉悟”;而在《那年的高墙》中,曾为地主的爷爷和“我”的父亲同样对作为“剥削阶级”的邻居“屙吃困”一家充满了歧视。很显然,作为“受害者”的秦老师们所遵循的思维逻辑都不过是当时走向极端的“阶级路线”这样的政治思维。在此方面,韩少功的《领袖之死》表现得要更加深刻。在这篇作品中,因为“读过洋学校”等历史污点而“被灰溜溜地开除回乡”的长科最大焦虑,就是要因领袖的去世而努力表现出悲痛。长科在起初的刻意悲痛不过是对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氛围和政治情感的“悲痛”的复制,但是,他在追悼会上终于因家庭的原因而第一个悲痛而哭后,却被非常荒诞地误作为政治忠诚的表率而在官方那里备受推崇。“自从那次国葬以后,他不知为什么比本善家的媳妇还容易抛眼泪,一提起领袖,或者一听到国歌什么的,他就情不自禁地鼻子酸,完全没法管住自己的鼻子,没法平息胸中奔涌澎湃的悲壮。他总是望着天,浑浊的泪水在眼窝里旋动和蓄聚”。从此,“长科成了大忙人”,“经常外出”去参加县里的很多会议。“他悲痛得越来越出色”……很显然,官方的推崇又不断地“强化”着长科的表现为“悲痛”的政治作秀,将原属强加的政治情感积淀为被迫害者的政治本能。除此之外,《领袖之死》的深刻之处还在于,长科在起初担心自己在追悼会上难以哭出的惶恐以及后来的以上种种,都是在以小说中的“黑洞洞的枪口”作为象征的“专政”之下得以发生的。实际上,这也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韩少功所曾指出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结构性的社会病相”的基本原因。
精 神 创 伤
韩少功在接受台湾作家施叔青的采访时曾经谈到以精神病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独特意义,他说:“精神病是个很好的窗口,可透视人的内心深处,常人掩盖的部分被打开了,可看到很多东西”。20作为一个对精神问题特别关注的作家,韩少功曾在一些小说中通过人物的精神病象逼视其精神世界,进而揭示由于社会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问题。而在他的中短篇小说中,这些问题则更多地体现为形形色色的精神创伤。他对这些精神创伤的揭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更加注重在发掘历史记忆的同时揭示人们的精神创伤,而在其较有影响的几篇中短篇小说中,其所揭示的,却更侧重于人们的精神病象中所隐藏着的创伤记忆;另一方面,在不多的一些现实题材的中短篇小说中,精神创伤则体现为某种形式的精神焦虑。
《北门口预言》、《鞋癖》、《领袖之死》、《走亲戚》、《很久以前》和《兄弟》等作品,均以不同的方式揭示了现代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灾难所造成的精神创伤。《北门口预言》是一篇以刑罚为题材的作品。从鲁迅开始,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屡屡对砍头之类的刑罚表现出独有的热情,很多作家乐此不疲地以此为题材。21在此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仍未稍减,其中,尤以余华的中篇小说《1986年》、莫言的长篇小说《檀香刑》和周实的系列小说《刀俎之间》最为突出。而韩少功《北门口预言》的一个虽极细微但却十分独特的方面在于,它很明显地注意到了刽子手周老二长年的“砍头”生涯所形成的一个职业性“习惯”——即对人的脖颈的注意。比如在写到周老二的晚年时,小说中有这样的文字:“据说周老二还活着,老得牙齿都掉光了,还偶尔去酒店喝盅包谷酒。据说他看人还是职业性地往颈根上看,说人还是职业性地往颈根上说。比方说某人当上了林木站站长,他就说此人是个干大事的,颈根粗壮,颈后边的肉足有寸多厚,同邮电局彭家老三的颈根差不多。邮电局确有彭家也确有老三,与他不曾交道,却不知自己的颈根如何被他仔细观察并牢记在心,甚至可以随口拿来作比方”、“他自斟自饮,依然呆坐,三两只苍蝇叮在他的鼻尖和眼角,他似乎也没力气去摇摇头或扬扬手,把苍蝇赶开。他衰弱的目光颤颤抖抖地浮游出去,停留在人们一棵棵可爱的颈根上,照例把它们温柔地触抚”。而他的《领袖之死》,则揭示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暴力给小说中的长科这一人物塑造养成的哭泣的“习惯”,这就是他一听到国歌或一提起领袖什么的,就会条件反射一般情不自禁地流泪。中篇小说《鞋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小说中的“妈妈”对于鞋子的近乎病态的癖好,以及作家对此癖好的探究。小说中,“妈妈”的鞋癖发生于遭受政治迫害的父亲失踪之后。“父亲离家后,妈妈特别热心做鞋,扎的鞋底也特别硬,一双一双我们根本穿不过来”。而当她年事已高,“人已经扎不动鞋底”,“而且儿女都有了称心的工作,无须母亲做鞋”以后,她的“鞋癖”则体现为不断地催促“我”为其买鞋,并且对它们时加摩挲,妥善保管。作家在小说曾对“妈妈”的“鞋癖”进行多方面的探究,不断地追问“妈妈的鞋癖到底是怎么来的?”他也曾从清朝乾嘉年间故乡的一次民变及其所导致的“嗜鞋习俗”的角度进行考察,认为当时的朝廷在平息这次民变的时候,曾经断足六百,由于“乡民断足太多,鞋稀而贵,便对鞋子产生了一种特殊心理”,故而“嗜鞋成癖”。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妈妈”的“鞋癖”则很自然地是乾嘉年间的历史暴力所造成的深藏于民间习俗中的精神创伤,或者说,是一种严重的历史创伤具体地体现于“妈妈”身上的精神遗存。但在小说中,“妈妈”的“鞋癖”却很直接地来自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迫害。这是因为,“父亲”失踪之前,“妈妈”并无这样的“鞋癖”,只是由于“父亲”的失踪才使其有了这样的“怪癖”。而且,她在后来找见“父亲”的遗体时所发现的“父亲”的鞋子,以及其自身的“鞋子糊满黄尘,成了个泥壳,右边的一只鞋已前头开花,露出了大趾头”这样的形象,和她带领着全家投奔“二姐”却遭拒而归的伤痛经历,均都不断地强化着她对鞋子的特殊感情,这正如小说中的“我”所终于醒悟到的:“妈妈是何等的睿智,她偷偷摸摸做了那么多鞋,是因为她早就明察秋毫地预知了今后的一切。她知道父亲的消失,将使我们走很多很多的路,惟鞋子可以救助我们,可以启示我们”。
保罗·康纳顿在论及人的“身体记忆”时曾经指出:“许多习惯技能的记忆形式说明,对于过去的记忆来说,虽然从不用追溯其历史来源,但却以我们现在的举止重演着过去。在习惯记忆里,过去似乎积淀在身体中”。22在《北门口预言》、《领袖之死》和《鞋癖》之中,无论是《北门口预言》中周老二对别人脖颈的习惯性注意和《领袖之死》中长科的哭泣习惯,还是《鞋癖》中“妈妈”的“鞋癖”,都是一种特殊的身体习惯,正是在这些特殊的身体习惯中,潜隐着深刻的历史记忆与精神创伤,或者说,这些不无病态的身体习惯,已经不仅仅是“身体的”,而且还是精神创伤的“身体操演”。这些“身体操演”已经成了一种仪式,不断地展示着人物的精神创伤。
当然,除了通过对人物的身体习惯来揭示“文化大革命”所施予的精神创伤(“病象”)之外,韩少功对精神创伤的揭示,还有着其他的角度。比如在《很久以前》中,他曾这样写到小说中“我”的“月光恐惧症”:“我特别不喜欢月光,害怕月光,特别是在秋天,一见到月光我就哆嗦,冷汗大冒,甚至呕吐”。对此,韩少功在作品中虽然只是偶而提及,亦未对其过于细究,但在小说的结尾,他在介绍一未犹太作家的作品时,却对此作了一定程度的暗示。韩少功是这样写的:“我最近校了一本书稿,是一未犹太作家写的。他写到他一位朋友也有月光恐惧症。是因为那位朋友曾经在月夜里逃走,从尸体堆里血淋淋地爬起来,爬过了他妻子的尸体,爬过了他女儿的尸体,爬过了他父亲的尸体,爬过了一条条没有主的腿或胳膊。他从此以后一见到月光就呕吐,就情不自禁地要往地上爬。这与我的症状有些相似”。在这样一篇“文革”(“知青”)题材的文学作品中,通过这样的暗示,我们无疑可以推想出“我”的“月光恐惧症”源于何处?再比如在《兄弟》之中,叙事人“我”的精神创伤却有着这样的病象:“我不想说出我所知道的一切,甚至好些年里不再愿意提到罗汉民这个名字,以免再一次使自己全身发冷和心痛欲吐”。这样一种精神病象,无疑来自于“我”在得知好友罗汉民遭到枪决时所产生的“被害”幻觉:“我感到不是那个少年而是我在这个茅房里被一枪击毙了。拉动枪栓的声音传来,钢铁的枪口对准我的后脑勺,钢铁的子弹带着嗖嗖的冷风飞驰,清脆地击破了头盖骨,然后旋起碎骨和脑浆四向飞溅,在前面那一个草坡上播开一片雨状的腥物,把我推入突如其来的无边黑暗。……我在这一天知道了死的滋味”。
除了通过精神病象之外,韩少功的中短篇小说还经常通过“情感创伤”来揭示人们的精神创伤,这在《鞋癖》、《走亲戚》、《很久以前》和《兄弟》等作品中都有体现。在《走亲戚》中,情感创伤表现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政治所造成的我们与三姑妈一家“亲情”上的怨隙;而在《很久以前》中,则是当时的回城政策充当着伤害了小说中的“我”的爱情的重要因素;《兄弟》里的罗大伯,则是因为其政治觉悟而大义灭亲,导致其子罗汉民的被判死刑,尤具讽刺意味的是,小说中的罗汉军等人,还对当时的当局充满了天真的幻想,而这一切,都给罗家的亲情造成了难以弥合的严重创伤。一般来说,韩少功是一个偏重于理性的作家。他的创作,一般少见个人感情的流露。但在《鞋癖》之中,这种感情却有着相当动人的表现。正如我们在前面所阐述的,《鞋癖》中的精神创伤非常突出地表现于妈妈的“鞋癖”这一精神病象。但在另一方面,作品中的精神创伤还很突出地表现于当时的极“左”政治对于亲情的伤害,这些伤害,有政治迫害所造成的“爸爸”自杀,还有因为政治的原因二姐与母亲及我们全家的决裂。作品中的“我”所时常表现的对于父亲深厚情感与怀念,实际上正是对“文革”暴力造成普通民众的精神创伤的愤怒控诉。
韩少功对现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北门口预言》)、特别是近期历史“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精神创伤的深刻揭示无疑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实际上,我们毋宁将这些形形色色的精神看作为我们这个民族特殊的“精神遗产”。对于它的冷峻逼视,正可以对我们的民族精神进行较为切实的清理,从而对整个民族的精神健康起到应有的作用,或者说,也正是我们建设健康的民族精神的必要基础。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作为一个民族和一个社会的“自我意识”(或者是“良心”)的知识分子,正应将对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创伤的揭示作为自己的历史性责任,而韩少功的文学写作,无疑是这一责任的自觉承担。但在这一方面,韩少功的意义远不止此。这是因为,他对历史记忆的深入发掘和对精神创伤的冷峻揭示,都使他在承担这一责任的同时,显示出自己的独特与深刻。
现 实 焦 虑
正如我们前所引述的,韩少功认为,文学是“把握判断现实的精神尺度”,应该“对自己和大众的生存现实保持一种创造性的价值追问”23,所以他在发掘历史记忆的同时,还很热切地关注着其所处身的社会现实,但是,他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仍然集中于人们的精神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现实作为正在运行着的“历史”,仍然在对人们造成严重的精神创伤。不过在韩少功的小说中,这些创伤更多地表现为人们的精神焦虑,不安、疑惧或惊恐,便是这种焦虑的典型症状。
中篇小说《梦案》所书写的,是“我”在睡梦中所遭遇的一场未遂谋杀。整个小说的叙事进程,就是“我”以动荡不安的复杂心理千方百计地追索凶手。他先曾怀疑过一位姓秦的文学青年和一位叫C的“现代派”作家,但在后来,却将目标锁定为公司的一位“我”曾有恩于他的文秘干事周中十。小说在最后虽然并没有确定到底谁是凶手,甚至是究竟有没有这样一位凶手?但是整个叙事所呈现出来的“我”的精神焦虑,却很突出地展示了改革以后的中国社会特别是科层制的公司之中人际关系的高度紧张。正如佛洛伊德所说的:“梦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毫无意义的、荒谬的,也不是一部分意识昏睡而只有另一小部分意识乍睡稍醒的产物。它完全是有意义的精神现象。实际上,是一种愿望的满足”。所以说,小说中的梦案不过是“我”在现实生活中所曾感受到的精神焦虑在无意识深处的集中体现。
而短篇小说《真要出事》中的“副科长”却以完全病态的惊恐与不安时刻担忧着形形色色的凶险,这些凶险是那样的神秘莫测、随处可见,潜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他挖空心思地研究坐在中巴车的哪一个位置更加安全、乘坐出租车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司机、出差乘火车应该乘坐哪一个车厢?他甚至设想,各种各样难以料及的因素都会导致致命的灾难:“火车当然比汽车安全得多,但也不能盲目乐观,尤其是一座座铁路桥很值得提防。可能有扳道工酗酒,车轮就要出轨。可能有桥架年久失修,桥身就会突然断裂。而且苏联解体海湾打仗,什么事情都发生了,恐怖分子就不能在桥上安放一个炸弹针对与你同车的某位高级要人?每逢咣当咣当的车轮声突然厚重膨大,钢铁桥架的黑影张牙舞爪劈进窗来,副科长就缩腹提肛,进入了准烈士的心理状态。他暗暗遥感地面与自己脚心之间愈来愈拉开了的距离,明确体会出列车积蓄着愈来愈大的落差势能,身不由己地一步步向绝望前进”;似乎是无处不在的各种凶险使他整天疑神疑鬼:“他看见公园的黑暗角落就想到这里可以埋伏流氓团伙,看见雨伞雪亮的杆尖就想到这东西可以戳瞎眼睛,看见起重机吊起集装箱就想到钢索随时可能拉断——因为他这种想象力,他上班下班走过即将封顶的十八层海通大厦时总是频频抬头,警视那上面的安全网和脚手架,任何微小的动静也不会轻易放过”。虽然如此胆战心惊,但他最终仍然未能保住其小小的“副科长”的职位,并且反而非常荒谬地成了一场事故的肇事者而被扭送警察。
中篇小说《红苹果例外》中的精神焦虑其又表现为另一种特点。在这篇小说中,“我”的精神焦虑主要是他对“真实”的怀疑。小说中的“我”应朋友阿中的邀请去一个叫做“鹿湖”的地方,但在途中,却在并不知情的情况下非常荒诞地参加了一部所谓“原型主义”的电影拍摄,并在其中令人心惊肉跳地扮演了一位饱受折磨的人物。作为一种追求仿真的现代文化工业,电影生产、特别是这样一部所谓“原型主义”的电影生产拆除了真实与虚幻之间的界限,在他惊魄未定地终于知道事情的真相后,他发现自己所经历的一切都不过是完全的虚假:在杂乱的拍摄现场,“地上还有一些梨子、柿子、枣子,还有滚来滚去的鸡蛋,甚至还有一支便携电话机,却没有人要。我后来才知道,除了有几筐苹果是真的,其他那些都是假的,是塑料制品或蜡制品,可以多次使用的道具。瓷瓶是马粪纸做的,怎么也摔不烂。我踢着了一个瓷瓶,果然有空落落的响声”,那个剧组中的“大胡子”,也不过是一个骗子。这样一番相当怪异的冒险经历,使其从此产生了对于现实的怀疑。他对生活中的一切都不相信:“我常常一觉睡醒之后,不知道这幸福是不是真的。我爬起来,在房里走来走去,担心突然听到一声长哨,又碰到一个拿点喇叭的家伙,宣布这一切都是戏。我忍不住检查冰柜里的食品,检查衣柜书柜以及阁楼上那一切可疑的黑暗。我忍不住看看床下,又猛地掀开窗帘看看窗外,看这些地方是否隐藏着可恶的摄影机。我检查铁子(其妻——引者注)的衣物以及她的包,甚至检查孩子胯下那些隐秘之处,看是否有‘ⅹⅹ摄制组NOⅹⅹ’之类的公物标记。我还检查过她带回来的每一张钞票,把它们一张张对着灯光照,看它们是不是道具……我把蓝天、白云、太阳也都要一一检查”。他在最后,甚至对妻子的姓名与身份也都产生了怀疑。似乎他惟一所信的,就是他在历险中的惟一真实——即苹果:“很久以来,我在果品中只愿意吃苹果,上街也只买苹果。货架上那些五彩纷呈的橘子梨子什么的,我总觉得它们是蜡做的或塑料做的,越看越生出疑心”。韩少功曾经揭示过符号对现实与人生的剥夺和扭曲,短暂的一番“被符号化”的生活经历,就给小说中的“我”带来了如此严重的精神灾难,在此意义上,《红苹果例外》不正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甚嚣尘上愈演愈烈的“符号化”现实的批判性寓言?
在论及人的精神焦虑时,弗洛伊德曾经指出:“真实的焦虑或恐怖对于我们似乎是一种最自然而合理的事,我们可称之为对于外界危险或意料中伤害的知觉的反应”。(《精神分析引论》)他认为,人的精神焦虑可以分为现实焦虑、神经性焦虑和道德焦虑三种类型,质之于他的理论,韩少功笔下的精神焦虑,显然是一种典型的“现实焦虑”,是“由于认识到外界存在着危险而产生的一种痛苦经历”。而在《梦案》、《真要出事》和《红苹果例外》等三篇作品所揭示的“现实”之中,这些外界的危险,刚好存在于“公司”、“机关”和“文化工业”。也许在有意无意之间,韩少功恰好揭示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实之中有可能存在的几种主要的精神压迫力量,从而使他的写作又一次抓住了“历史”,抓住了9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实这一正在行进中的“历史”。
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少功的中短篇小说对于历史记忆的开掘、精神创伤的逼视和对现实焦虑的表达,显示了他特有的精神关切与精神力量,亦有着相当特别的意义。正如马尔库塞所说的:“真正的理想都是以记忆为基础的。……对于在现实压迫戒律下生活的人来说,忘却过去的苦难和快乐都能平抚现实压迫的痛苦。相反,记忆激发人们去征服苦难和追求快乐。历史的天际仍然是开敞的。如果对过去的回忆可以在改变世界的斗争中成为一种动员力量,那么这一斗争就能成为一场被先前历史所压制的新的变革”。24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现实,韩少功显然有所不满。他的《梦案》、《真要出事》和《红苹果例外》等小说所表达的现实焦虑,其中的那些“在现实压迫戒律下生活”的人物充满了不安、疑惧与惊恐,他们形形色色的精神危机充分说明了90年代的中国现实并不能够成为我们真正的精神家园,精神的理想仍然在未来。但是,精神理想的真正实现,不仅应该像《梦案》等作品那样立足于对精神现实的批判与揭示,还应该像《领袖之死》、《鞋癖》和《兄弟》那样“以记忆为基础”。韩少功对历史记忆的开掘和对精神创伤的逼视,正是通过反抗“忘却过去”所可能带来的“平抚痛苦”的精神虚妄,来建立我们精神理想的可靠“基础”。韩少功不仅从现实,而且还从历史的深处冷峻地逼问我们的精神,以“激发人们去征服苦难和追求快乐”,追求我们的理想。正是通过对历史记忆的执着书写、通过他从现实与历史深处的精神逼问,韩少功以其特有的精神姿态,挑战着种种“压制”性力量,有力地“介入”了历史。
1 韩少功:《我为什么还要写作》,《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版。
2 韩少功:《九十年代的压力与选择:与荷兰学者雷马克谈话要点》,《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版。
3 韩少功:《精神的白天与夜晚》,《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版。
4 韩少功、鲁枢元:《关于“精神”的对话》,《东方艺术》1995年第3期。
5 韩少功:《精神的白天与夜晚》,《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版。
6 韩少功:《我为什么还要写作》,《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版。
7 韩少功:《精神的白天与夜晚》,《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版。
8 《韩少功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237页。
9 韩少功:《灵魂的声音》,《文学的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版。
10 韩少功:《与遗忘抗争》,《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版。
11 韩少功:《与遗忘抗争》,《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版。
12 I·甘卜斯(I·Gambles)语。转引自徐贲:《文化批评的记忆和遗忘》,《文化研究》第1辑,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
13 徐贲:《文化批评的记忆和遗忘》,《文化研究》第1辑,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
14 韩少功:《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版。
15 《韩少功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1~12页。
16 《韩少功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5~16页。
17 《韩少功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1~12页。
18 克里玛:《布拉格精神》,作家出版社1998年7月版。
19 《韩少功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3页。
20 韩少功、施叔青:《鸟的传人》,《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版。
21 王德威:《从“头”谈起:鲁迅、沈从文与“砍头”》,《想像中国的方法》,三联书店1998年9月版。
22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23 韩少功:《九十年代的压力与选择:与荷兰学者雷马克谈话要点》,《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版。
24 转引自徐贲:《文化批评的记忆和遗忘》,《文化研究》第1辑,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
(本栏所有文章为中国南方艺术独家所有,不得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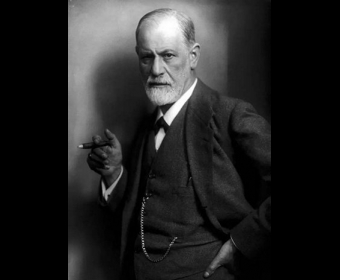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