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现代国家中的法律共同体
上述关于交往共同体和语言共同体的阐释并没有完结哈贝马斯关于共同体的设想。因为交往共同体和语言共同体若要真正得以形成和发挥功能,还必须依赖法律共同体的整合作用。正如哈贝马斯所说:“文化和语言所确立起来的文化躯体,还需要一件合适的政治外衣。语言共同体必须在民族国家当中与法律共同体重叠起来。”(哈贝马斯,2002年,第12页)对于哈贝马斯来说,法律(Recht)在社会整合中具有关键意义。他把法律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实定法,它要求系统地论证和有约束力地诠释、执行。而法律共同体则是由平等而自由的法律同伴所结成的联合体。从社会整合的角度来看,法律必须同时确保共同体行为在事实层面的合法律性(Legalitt,即确保共同体成员对规范的遵守)和在规范层面的合法性(Legitimitt,即规范得到共同体成员的承认)。
法律共同体的成员是来自于特定生活世界、具有交往理性资质、遵守法律规范的公民。在哈贝马斯看来,法律共同体不是一个自我陶醉的封闭系统,它需要得到公民的民主伦理生活的滋养和自由政治文化的推动。因此,法律共同体必须植根于生活世界,同时构成生活世界的“社会”的一部分,并从中吸取意义养料,因此,法律共同体有时被他称为社会共同体。换句话说,法律共同体的成员是来自特定文化传统中遵循特定社会规范且具有特定个性的公民。这些公民需要具备基本的交往理性能力,能够与他人在特定的语言媒介中展开以言施为的话语交往,而这些交往不是随意的,需要遵守特定的法律规范,其交往具有明确的任务,最重要的是立法和司法。
法律共同体的首要任务就是确立规则,即立法,立法机构是社会整合的首要场所。立法的参与者需要采取法律共同体的视角,在立法行动中起关键作用的应该是以对共同体其他成员的理解为目的的交往行动,而不是以对其他成员的成功掌控为取向的策略行动,应该是以形成共同体规范为目的的政治行动,而不是以价值获取或评价为导向的伦理行动。这种政治行动遵循的是普遍道德原则和民主原则,而不是伦理原则。哈贝马斯说:“法律共同体成员们可以假定,在自由的政治性意见形成和意志形成过程中,他们作为承受者必须服从的那些规则,恰恰是他们自己赋予权威的。”(哈贝马斯,2011年,第46页)也就是说,联结法律共同体各成员的是出自其自主意志的普遍规范。
立法只是为法律共同体准备了有法可依的前提条件,共同体的运行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司法当中。从宪法的判决实践到依法决策的实施,法律共同体都面临着合法化危机的挑战,即法律是否得到公众的认可和服从。哈贝马斯辩证地分析了司法的合法化问题。在他看来,如果法律是共同体成员运用政治自主能力和交往理性能力来形成的,那么他们就有义务来遵守法律,自觉维护法律共同体的团结。反之,如果法律未经相关参与者的同意,那么其成员可以不遵守或者有理由违抗。也就是说,哈贝马斯信奉的是自下而上的法律合法化路径。以此为据,他批判了当今西方法律的合法化危机。他说:“当代法律批判的核心,是在一个越来越承担量多、质新的任务的国家中,议会制订的法律的约束力降低、权力分立的原则受到威胁。”(哈贝马斯,2011年,第530-531页)那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哈贝马斯认为,应从源头上将法律共同体视为理性公民通过政治自主和理性交往而形成的自我组织,从而确保法律是公民自我意志的体现,进而使得遵守法律不过是遵守自己的意志。在这里可以看到哈贝马斯尽力弥合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法理学的努力,即既想凸显出个体在立法司法中的主体地位,又想彰显共同体的总体意志和价值;既想承认既成法律规范的事实性约束力量,又想提升共同体价值的引导性力量。理想的法律共同体既体现个人意志的总体意志,又体现共同体价值的普遍规范,成为兼具事实性与有效性的行动系统。
这样的法律共同体要发挥其作用,必须贯彻法治国理念,即必须在现代法治国理念的指导下才可能形成和运转。所谓法治国理念,哈贝马斯将它解释为这样的要求:“把由权力代码来导控的行政系统同具有立法作用的交往权力相联系,并使之摆脱社会权力的影响、也就是摆脱特权利益的事实性实施能力。”(同上,第184-185页)这种能力往往表现为以公共权力为核心的政治共同体。在他看来,法律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必须拥有一个被授权来代表整体而行动的制裁权威、组织权威和执行权威,这个权威就是国家。正是在国家之中,交往权力、行政权力、立法和司法权力才得以平衡。只有在特定法治国家的共同体中,通过法律的授权,个人的尊严、生命等平等权利才能得到根本保障。(cf.Habermas,2010,p.464)
其实,在哈贝马斯的语境中,法律共同体与法治国是相辅相成的一体两面。借助法治国的理念,社会整合的三种媒介——经济货币、政治权力和交往团结可以被统摄起来加以平衡。这样,作为一种整合机制的法治国使得法律共同体介于系统性整合与社会性整合之间。如果说,经济系统通过货币,政治系统通过权力各自在一定程度上都实现了系统性整合的功能,生活世界通过团结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社会性整合的功能,那么法律则尝试将这三种媒介和两种整合资源结合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社会分裂的危机。哈贝马斯说:“以这种方式,现代法律同社会整合的三种资源都有了连接。通过那要求公民共同运用其交往自由的自决实践,法律归根结底从社会团结的源泉中获得其社会整合力量。”(哈贝马斯,2011年,第48页)相比于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的目的理性运作机制,以交往共同体为基础和以语言共同体为路径的法律共同体则更依赖于团结这一社会性整合资源。对于现代法律共同体而言,被称为“宪法爱国主义”的团结纽带尤为重要。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是一种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一直蕴藏在现代法治国家中不可缺少的社会资源。相对于民族爱国主义来说,宪法爱国主义指的是一种依据根本规范宪法而形成的一种对国家的普遍认同。这种认同不是来自天然联系的民族情感或利益,而是来自基于话语民主政治的理性共识。他还试图用这种宪法爱国主义来促进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团结,甚至继承康德的永久和平观,“通过国际公民权利的法律化来驯化国与国之间的争斗”(吴功青,第5页)。正是基于对这种现代法的理解,哈贝马斯才对现代社会的整合抱持希望。
四、对哈贝马斯共同体理论的反思
综上所述,在哈贝马斯看来,生活世界中的交往共同体为公共领域中的语言共同体和现代国家中的法律共同体提供意义源泉和主题背景;公共领域中的语言共同体则将交往共同体的问题主题化,并通过言语论证为法律共同体提供合法性;现代国家中的法律共同体则将交往共同体的意义和语言共同体的共识诉诸法律规范。这样,交往共同体、语言共同体和法律共同体就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三个基本层面,它们并非各自独立的领域,而是同一现代社会中相互联系和制约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化共同体、历史共同体、宗教共同体、科学共同体、民主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国际共同体等则穿插其中,辅以各个侧面,并各司其职,从而形成整合现代社会的基本架构。只有在这种架构中,现代社会的分裂危机才能得以克服,复杂社会才能够被有机地整合起来。
哈贝马斯这一共同体理论从社会整合的角度展示了其批判理论的逻辑思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导致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裂危机,交往共同体不断扩展的交往需要及其意蕴关联为克服这种危机提供了强大动力,语言共同体所蕴含的交往理性潜能为克服这种危机提供了基本纽带和路径,而法律共同体所提供的规范要求则为克服这种危机提供了有力保障。这样,从个体到族群,从民族到国家,从国家到人类,就可能逐渐形成多元互通而命运与共的共同体,资本主义社会这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就可能重新变得稳固起来。若只就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而言,这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了较为完备的社会整合方案,为现代社会克服分裂危机提供了一条思路。
然而,我们不难看出,哈贝马斯为其共同体设定了太多的条件和赋予了太多期待,以至于这样的理论不管是被置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其他社会,终将水土不服而无法实施。
首先,哈贝马斯共同体理论的出发点是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社会现实,然而这一理论的基础是基于合理化生活世界中的无限制交往共同体。如果说前者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那么后者却又放弃了这种唯物主义。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一定程度上哈贝马斯所揭示的生活世界殖民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既然如此,那么生活世界中的无限制交往共同体如何可能呢?这个殖民化事实得到改善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不仅没有被纠正,而且愈演愈烈。这对于其共同体理论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没有合理的生活世界,就没有理想的交往共同体,更没有公共领域中的语言共同体,那法律共同体就只剩下系统性整合功能了。所以,哈贝马斯的共同体理论存在着一条从出发点到立论基石的鸿沟。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应该是根据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社会危机去探寻现实的社会病理,到人们的实际交往实践中去奠定交往共同体形成的社会基础,而不是半先验地设定理想条件。
其次,哈贝马斯的共同体是被屏蔽了阶级矛盾、没有根本利益冲突、没有革命向度的共同体,这种理想化设定使得其语言共同体和法律共同体都是片面的。在哈贝马斯看来,推动现代历史进程的根本力量不是社会生产,更不是基于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阶级斗争,而是人与人之间基于语言的互动,即交往行为。正是这一历史观促使他过多地看到共同体的统一性方面而忽视了其斗争性方面。他明确指出:“只有在一种从阶级限制的驱壳中生长出来、摆脱了千百年社会分层和剥削之桎梏的社会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一个没有拘束的文化多元性的潜力。”(哈贝马斯,2011年,第381页)在这种社会共同体中成员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即双方或多方以承认其他成员的根本权利为前提。哈贝马斯的这种观点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以德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状况的变化,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通过福利国家制度等措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参见王凤才,第25-36页)然而,马克思在200多年前的判断“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1页),在当今依然具有说服力。纵观人类发展史,阶级矛盾是贯穿整个阶级社会历史的基本矛盾之一,往往表现为不可调和的阶级对抗,而国家只不过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法律不过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并非全部消失了,其主要部分随着全球化浪潮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变成了全球资产阶级与全球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哈贝马斯则忽视了这种对抗,其公共领域的实质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其中的语言共同体是资产阶级牢牢掌握话语霸权的共同体。因此,他所诉诸的法律共同体所提倡的成员之间的平等与自由只不过是就资产阶级而言的。这样的共同体只能是统治阶级共同体,而被统治阶级共同体的意志则被忽视了,由此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对抗与调和机制更被忽视了。至于在全球社会生产体系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如何建立交往共同体、语言共同体和法律共同体的问题,哈贝马斯直接抛弃了这种阶级分析方法。他虽然雄心勃勃论及国际共同体,却仍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如核心欧洲的层面论及的。
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仍然存在着阶级或阶层斗争、民族压迫与抗争、身份蔑视与反抗等激烈冲突,而这些冲突所造成的分裂无一能够通过交往行为来整合,相反,往往需要阶级革命、民族革命和身份革命来克服。因此,哈贝马斯的共同体即使被置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只是一种思想实验,而非真正的现实共同体。而欧洲共同体就是这一思想实验品。在他看来,在现行生产体系下,建立统一的欧洲共同体是抵制资本主义最有效的路径。然而,欧洲共同体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体系内由资产阶级所主导形成和运行的,其中的阶级、民族、信仰、身份等激烈冲突使它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分裂危机。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恐怖主义、新帝国主义、民族主义、难民问题以及由互联网所引起的社会变革,都不断冲击着欧洲共同体的基石,令哈贝马斯感到“愤怒”甚至“绝望”。愤怒是因为他还寄予厚望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利益而达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绝望是因为在这种社会内部来实现其基于各种共同体的社会整合已回天乏术。究其根本原因,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仅靠个体的交往理性是不足以抵抗资本的操纵的,仅靠共同体的话语共识是不足以消除帝国主义宰制世界的尖端武器的,仅靠宪法或国际法的一纸规约是不足以协调共同体之间为了生存发展而展开的利益冲突的。这种情形之下,哈贝马斯仍然不愿意寄希望于革命,仍然在资产阶级共同体内向这些令他愤怒的主体妥协。
对于在话语中居于弱势地位的广大无产阶级和弱势族群来说,要实现哈贝马斯所说的共同体,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在交往共同体中创生出充足的、与资产阶级对等的意义来源,在公共领域中获得实质上同等的话语交往的条件,在法律上获得同等的立法和司法保障,而这就需要通过革命改变资本主义这种宰制的社会生产体系。换句话说,只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的逻辑,改变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从而改变资本主义的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才可能真正实现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交往共同体、语言共同体和法律共同体才得以形成和发展。
最后,哈贝马斯的共同体是剪断了情感联系的理性共同体,无法牢固维系主体间、代际间的团结。对于作为理性主义者的哈贝马斯来说,通过交往行为形成的关系都是合理的互动关系,通过论证语言表达的都是可理解的观点,通过程序确定的法律都是无情的规范。他对话语的三个有效性要求的理解有意地消除了交往主体之间互通共感的情感联系。虽然对主观世界的真诚性包含了情感的因素,然而,哈贝马斯强调的是对说话者自身内心的真诚性,而关于听话者以及共同体的情感世界则没有被涉及。即使是在最有可能安置情感的生活世界中,也很难找到情感的因素。总而言之,共同体的情感冲动被压抑了,情感纽带被刻意剪断了。而这一缺失的情感维度则被霍耐特弥补了。在《为承认而斗争》一书中,霍耐特就将那表示人与人之间情感互动本源关系的爱理解为人与人之间“互相承认的第一个阶段”(霍耐特,2005年,第103页)。在《物化:承认理论探析》中,他从相反方向证明,既然承认就是联系自我与世界的原初形式,就是与他人维系共感参与关心挂念的情感联系,那么对这种基于情感共鸣的承认的遗忘就是物化。(参见霍耐特,2018年,第50页)对于霍耐特来说,情感共鸣是共同体得以形成的前提,是共同体成员之间确立相互依赖相互需要的承认关系的第一步,并贯穿始终。对情感联系的破坏,就会造成个体同一性的破坏和共同体社会的分裂。此外,这种情感联系在共同体中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维系代际之间生活形式的连续性。哈贝马斯的共同体侧重于同一时空下的同代人之间的话语交往,对于代际之间的话语交往则鲜少涉及。因此他无法回答奥菲提出的问题:“如果连当代的薄弱纽带都明显不足以激励行动上的团结,那么跨时代共同体又能依靠什么呢?”(Offe,p.82)因为代际之间因信息的不对称、生活形式的差异、时代要求的不同很难展开有效的话语交往,然而每代人始终都是历史的话语主体。维系社会历史承前启后的纽带一方面是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另一方面就是代际间的情感互动。正是情感的互通共鸣将不同时空中的人们联结起来,形成内在稳固的代际共同体。
注释:
①关于“社会整合”概念的译法,本文采用童世骏先生的观点,参见《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第48页注释:把Gesellschaftliche Integration译成“社会整合”,把soziale Integration译成“社会性整合”,把systemisch Integration译成“系统性整合”。“社会整合”中的“社会”指的是广义的包括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在内的整全社会,而“社会性整合”中的“社会”则是指与系统相对的社会。
原文参考文献:
[1]冯周卓、王益珑,2015年:《哈贝马斯对社会共同体的二维架构分析》,载《河北学刊》第5期.
[2]哈贝马斯,1994年:《交往行动理论》,洪佩郁、蔺青译,重庆出版社.
[3]哈贝马斯,2001年:《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
[4]哈贝马斯,2002年:《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5]哈贝马斯,2004年:《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
[6]哈贝马斯,2011年:《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7]哈贝马斯,2013年:《在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郁喆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8]哈贝马斯,2019年:《分裂的西方》,郁喆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9]霍耐特,2005年:《为承认而斗争》,胡继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0]霍耐特,2018年:《物化:承认理论探析》,罗名珍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
[12]王凤才,2016年:《新世纪以来德国阶级问题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13]王晓升,2018年:《现代性视角下的社会整合问题——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启示》,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14]吴功青,2019年:《道德、政治与历史: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及其内在困难》,载《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15]严宏,2019年:《从交往共同体到法律共同体——哈贝马斯对现代西方国家的演进式重构》,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16]Habermas,J.,1991,“A Reply”,in Honneth,A.,and Joas,H.(eds.),Communicative Action:Essays on Jurgen Habermas'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trans.by Gaines,J.and Jones,D.L.,Cambridge:The MIT Press.
[17]Habermas,J.,2010,“The Concept of Human Dignity and the Realistic Utopia of Human Rights”,in Metaphilosophy 4.
[18]Offe,C.,1992,“Bindings,Shackles,Brakes:On Self-Limitation Strategies”,in Honneth,A.,McCarthy,T.,Offe,C.and Wellmer,A.(eds.),Cultural-Political Interventions in the Unfinished Project of Enlightenment,trans.by Fultner,B.,Cambridge:The MIT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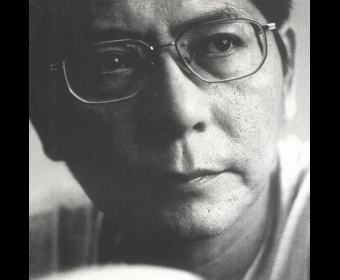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