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夜中穿越黎明的祈祷
——浅议熊焱诗歌中“诚”的表达
蓝 紫
“在长夜中穿越黎明的祈祷”是熊焱诗歌《写诗的过程》中的最后一句。在这首诗中,他把诗歌写作的过程融入一系列生动的比喻,让枯燥的脑力劳动在形象的描绘中得到了升华;在抚慰生活带来的创伤的同时,也使灵魂与精神有了向上攀升的通道。正如他在另一首诗中所写:“……从修辞的炼金术中/找到脉搏的跳动,生命生生不息的欢乐与痛苦。”(《一首诗的沉默》)。诚如他诗中所言,他的诗歌多描写人生的境遇,对生命与命运的困惑、彷徨、焦虑、怜悯以及在这种种境遇中的领悟与超脱,还有对生命的希望与喜悦。他的诗歌诚恳、本真而又质朴、悲悯,是来自灵魂震颤的蛩音。读这样的诗歌,很难不被诗中真挚的情感所打动。这种动人心弦的品质,皆来自作者的真诚与善良——尤其是诚,不仅是真诚,还有围绕诚的其他品质。
对于写作,古人早有告诫:修辞立其诚。对熊焱来说,其“修辞的炼金术”主要也是诚。关于“诚”的词组有真诚、诚恳、诚挚、忠诚、诚实……这些词语大都指向同一个意思。而要想到达“诚”,必然要“走心”,所以,与这一品质密切相关的,是“心”。“诚”与“心”所带来的,则是善,是悲悯。读熊焱的诗集,可以看到,充盈于其诗歌内核的,正是这几个关键词。这些最为平常也最难能可贵的品质,成为熊焱诗歌创作的背景与底色。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周敦颐在《通书·诚上》中如是说:“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关于诚,古人已有深刻的体会与研究,甚至到了“诚者圣人之本”,表明“连圣人也不过是唯诚而已矣;甚至连圣人之教也依然不过是唯诚而已矣”。由此可见,“诚”对于人生、对于写作的重要意义。熊焱的诗歌之所以打动人心,其本质原因也在于此。本文试从这个方面,来探究熊焱诗歌中关于“诚”的表达。
一、忠于内心的真诚表述
在熊焱诗集《我的心是下坠的尘埃》中,大多篇幅是生命历程的感悟与记录。诗歌就是他的传记,也是他内心的独白。他抒写生命中的病痛、孤独,抒发对生命、命运的感叹,都是基于内心真实的情感,诗歌作为他的心灵外在于文字的表现方式,是他心性的真实体现。这种忠于心灵的诚实表述,说明了“诚”与“心”的关系。“孟子认为‘诚’下贯上达,贯通天人的整个过程都是以‘心’为中介展开的……荀子则从道德修养的角度把‘诚’与‘心’直接联系起来,如‘君子养心莫善于诚’”。熊焱用诗歌,同样也印证了如下逻辑:诗歌的语言离心更近,因而更无限接近于诚。
他在诗歌中多次提到病痛:“十六岁的夏天/我接受了一个生死未卜的大手术”(《我的出生》);“我坐在候诊的人群中,压着隐隐作痛的胃/那里是潮汐涨落,沉积着生活的酸辣苦甜”(《在医院》);“年少时我体弱多病,屡次与死亡擦肩/母亲心急如焚,躲在暗夜里啜泣/咸涩的泪水泡软了岁月的荆棘”(《岁月颂,3》);“整个少年时期/我历经病痛的折磨,多次命悬一线”(《轨迹》)……这些对自身经历的朴素而真诚的讲述,在传达给我们心灵震颤的同时,也正如华兹华斯所说,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溢。
病痛是每一个人都不愿面对、只能无奈接受的体验,是原初的、灵敏的,是生命发出的警告,让人知道身体哪些地方出了毛病,提醒人们珍爱生命。肉体的疼痛作为人类固有的体验,同时也会让人对生命的体验更为深刻,从而更多地去倾听自我、体悟生命,对生命、命运自然也有了比常人更多的慨叹。诗人在诗歌中关于病痛的抒写,则是一种疼痛的诗学。
当然,这种疼痛,不仅来自身体,还来自精神的负重,如“中年的焦虑、生活的艰辛、奋斗与挣扎”等。诗人的写作与思维,不同于作家或评论家。比如美国作家、评论家苏珊·桑塔格在患病后痛苦的治疗中写出了《疾病的隐喻》,并依靠文学赋予的顽强意志战胜了病魔。桑塔格对待疾病的看法是: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熊焱的诗歌便是如此,他在诗歌中直面病痛,直抒因病痛带来的慨叹:
……肉身听任机器的摆布
灵魂却在怜悯活着的艰辛
人世虽有尽头,但生命的深度却远得不可探测
我醒来时,头仍在眩晕
身体仍在下沉。我走出门去
就像是从梦境中疲倦地回归
长途坎坷,人间风霜弥漫
满走廊都是同病的可怜人啊
一张张焦虑的面孔,隐忍着身体的劫难
而身后的门缓缓关上了,就像死神正躲在门后
认真地盘点着生死的清单——《在医院》
关于熊焱诗歌中的病痛,已有诗论做出过恰当的阐释:“身体作为人永远敞开的感知场,无时无刻不在承受时间与生命当中发生在人身上的苦难、挫折、病痛、离乡、漂泊、孤独、惊诧等复杂的体验。对一个诗人来说,他的诗歌的思考与表达往往来源于这些对身体冲击力大、让身体形成神经反射的‘伤害性’体验。”在医院中被冰冷的仪器扫描、检测,是几乎所有人都有过的经历,唯有这样的慨叹来自诗人,它在被写下的同时,也有着如医药般的救赎作用,类似于桑塔格依靠文学的力量战胜病魔。诗歌的魅力也正在于此。
诗人对自身境遇的真诚表述,揭开了现代社会下人的真实精神状况。在被现代性消解的现代生活中,在嘈杂、喧嚷的社会环境中,在商业化、快节奏的裹挟下,浮躁成了常有的心理状态。浮躁在一定程度上,使“诚”的品质成为稀有之物,与之而来的,则是每个现代人都体验至深的孤独。
若说病痛是肉体的经历,孤独,则来自内心的境遇。作为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单子式个人,孤独,是现代性赋予每个人的必然心境。对这一现象,哲学家赵汀阳有过深入研究:“现代人的孤独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孤独不是因为双方有着根本差异而无法理解,而是因为各自的自我都没有什么值得理解的,这才形成了彻底的形而上的孤独。”喧闹的现代生活,反而使人对孤独的体验更深。正如熊焱在诗歌中所写的,“我为人世汹涌的喧嚣而倍感孤独”(《自省书》)。在熊焱这里,孤独不仅是生命的底色,“生存是一种漫长的匍匐/长天下的人和牲畜,都在艰难的生存中/有着相似的孤独”(《水灌进田里》),同时还是抒写的主题与意象:“我幻想独立荒野,与全世界的孤独保持一致”(《我幻想的人生》)。正如他在诗集前面直言:“我写诗歌,是为了抵达孤独。”
新诗因语言的变革、社会的发展与变迁而来,走进人类孤独的精神世界的同时,它的情绪底色,也同样是孤独:“新诗的情绪底色必将是孤独;每一首具体的新诗作品,无论其主题为何,原则上都得到过孤独情绪的预先浸泡。”孤独在本质上是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之一,但在诗人这里,则“是在热闹的人群中独享灵魂的静谧和心灵的富足”(《我写诗,是为了抵达孤独》)。正因孤独,诗人才有了对时间、岁月、命运的怜悯与感叹,而在这怜悯与感叹中,诗人更感孤独。在《我的心是下落的尘埃》这本诗集中,可以看到,诗人使用频率比较高的词语有:孤独、寂静、怜悯、命运、中年、时间、岁月、生命……这是一组关于心境、情绪的词语,同时也可以勾勒出一个大致形象:这是一个懂得享受孤独、安于寂寞、心怀悲悯的诗人。因此,他对自己的诗歌写作有着清醒的认识:“我确信诗人的声名不是来自认同与赞美/而是从这世界获得的孤独,比岁月还深”(《轨迹》)。
二、“诚”由“静”生,静致所至
“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也,神也。”周敦颐认为,“诚是一种‘寂然不动’的本然状态,诚‘无为’‘无欲’。所以,在道德修养中必须‘惩忿窒欲’,必须主静。何为‘主静’?周敦颐认为‘无欲故静’,否则就达不到‘诚’的圣人之境”。由此可见,“诚”与“静”相辅相成。在普遍浮躁的时代,在喧嚣的环境中,保持心灵的安静与安宁,是一种难以习得的能力,也是难能可贵的品质之一。读熊焱的诗集,可以明显地感知到他心境的安静与安宁。
作为人到中年的诗人,因为工作与生活的烦琐、忙乱,已难得有自己的独处时间,熊焱在诗集序言中这样描述他写诗的环境:“常常在飞机的轰鸣下,在高铁穿过千山万水的呼啸中,在公交车摇摇晃晃的颠簸里,在地铁向着幽暗的奔跑中,我用手机断断续续地写下诗篇。四周都是人群杂乱的喧嚣,我独享那文字赐予我幸福的美好时刻。”这样的诗写状态,只能建立在心灵的宁静之上。
与心灵的宁静互为呼应的,是“寂静”——作为心灵能感知到的一种静谧状态。“寂静”时而是心灵的映照,时而是吟咏的对象。从词义上,喧嚣是寂静的反义词,在喧闹的世界中保持心灵的宁静,是诗人独有的能力。正如诗中所写:“在一个发光的窗口里/我将从世界的喧嚣中找到寂静”(《夜归》)。而孤独是寂静的同义词,它们在熊焱的诗歌中常偕同出现,如:“唯有大地以宽容回应我的平庸/群山以沉默回应我的孤独与寂静”(《四十岁,初秋登峨眉山》);“西天一轮银月高挂,向人间派送着白银/我却只领到了三两孤独、半斤静谧”(《夜里从海边醒来》);“我只要世界给我添加血液中的两勺盐/一勺是孤独,一勺是寂静”(《生命在庸碌中衰老》)。
正如华兹华斯所说,诗“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感情。诗人沉思这种情感直到一种反应使平静逐渐消逝,就有一种与诗人所沉思的情感相似的情感逐渐发生”,这是诗写过程的精准表述。“与诗人所沉思的情感相似的情感逐渐发生”这句话,指的就是情感的自然流溢。这在其他某些诗歌写作者那里,若不加以节制,很容易成为泛溢的抒情。但因为有过“持续地花费时间去认真阅读、思考和打磨技艺”,在熊焱这里,体现的则是卡内堤说布洛赫的那种“不知不觉的技巧”。在写作中的具体表现为:当诗人写下自身真实的境遇之后,即会有情感上的升华与跟随。如“我的母亲怀着我的时候,差点去了医院引产/我幸运地来到人间,就像一滴水珠汇入大河/从此跟随浪花奔腾”(《轨迹》),前两句看似平淡的讲述,道出生命之偶然。其实,每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皆是偶然。承认生命的偶然,也就是承认生命的无奈与无意义。在无意义的生命中,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在赋予生命以意义,比如阅读、写作、旅游、劳动等等。但诗人的经历不同,因为在这偶然中,同时还有幸运。这些真实的历程,此时如果继续花费笔墨,则很容易流于散文化。所以,成熟的写作者都会在此刻及时打住,在后两句进行情绪上的渲染。这也是诗歌写作常用的一种技艺:由实到虚,虚实结合,从而形成情感上的张力,也很容易获得读者的共情。
熊焱的诗歌从写作环境(需要心灵的宁静),到内容(人生与世界的孤独与寂静),到过程(平静中的回忆),是“静”之全方位的展现。他在宁静的状态中,用诗歌来自我反省和领悟,从而达至“诚立、明通”。这种“静”经由诚挚的心灵,进行诚实的抒写,抒发对人生、岁月、命运、时间的沉思,自带沧桑与悲悯的属性。
三、“诚”从细节处来
法国大文豪福楼拜说:“仁慈的上帝寓于细节之中。”真诚的讲述,从来不是那些大而化之、浮于表面的笼统叙述,而是源于细微处的精当描摹,不经意间触动读者的心灵,从而感受到作者的诚挚。而一篇作品的价值,很多时候也取决于细节的考究。正如巴尔扎克说的:“当一切的结局都已准备就绪,一切情节都已经过加工,这时,再前进一步,唯有细节组成作品的价值。”细节写作已是各种文学体裁中老生常谈的话题,诚然,细节写得好并不代表“诚”,只能说明作者的写作技巧好、水平高。但真诚的写作,一定会有细节的加持。细节描写,是写作者进入场景或事物,与所要描写的对象最大限度地近距离接触,用心去感知场景或事物中那些微小、细腻的一面,找到属于作者独特的发现或感悟。这个过程因为心灵的贴近与深入,因而更显诚恳与真挚,也更容易打动读者的心灵。
作为成熟的写作者,细节是熊焱比较重视的一个方面。比如前文所提到的那些使用频率高的词语,在熊焱这里,并不是一种“冷漠而快速处置的单词现象”,他在表现这些词语(或说境遇)时,也不是“通过外部的‘语言暴力’”,而是“巴尔特说的‘协同行为’”来实现的。此种协同行为,便是熊焱在诗歌写作中极为注重的细节。比如他写孤独:
酒已饮尽。下山的路上夜虫齐鸣
仿佛酒盅里珍珠滚动,桌子上的空杯
正等待着承接住清泠泠的回声
有时,我们需要的孤独
是在山巅上寻得一阵微醺。人到中年
岁月洞悉我灵魂深处的那份酩酊
在一个山坳处,我们下车观看悬崖上的飞瀑
一匹白练的孤绝之路,就像命运走到绝境
却义无反顾地跃下深渊,完成人生壮烈的美学
有人突然掩面哭泣。头顶明月高悬
碧蓝的夜空仿佛青花的瓷器——《我所理解的孤独》
身兼编辑与写作者的双重身份,熊焱在诗歌写作上还多了一重审视的眼光。他在序言中谈道:“我们在谈论诗歌的技艺时,很多诗人已将诗歌写作中最基本的、规范化的元素置之不理,而对奇崛的形式、聱牙的语言、荒诞的审美情有独钟,并视之为技艺。而对那些朴素中显智慧、平常中见崎岖的作品,视为无技艺……”“朴素中显智慧、平常中见崎岖”在此可以认作诗人的诗观,也是他遵循的写作准则。比如在这首诗中,诗行在朴素的叙述中铺陈情境,把读者带入其中,跟随他的情感波动。这情境,便来自一系列的场景细节,比如他抓住了空杯在桌子上带给他的细微的感受(等待泠泠的回声),这让这个平常的场景生动了起来。而这等待的过程,便是孤独。再如他观看飞瀑时,从飞瀑直流而下的细节处,感悟命运之孤绝。这些细微的动作、细小的景观、细腻的心理描写,在饱满的情感中,还带有克制、隐忍的语言感觉。
再如另一首诗《夜里听闻一则喜讯》,由“我起身到窗边”这个细节动作带来的,是窗外的夜景:“夜空正捧着月亮的银勺/向世界倾倒着寂静。山坡下的大海波光粼粼/它们与人世隔着一个梦的距离”。这衬托了诗人的心境:“夜晚虽美,我却怅然若失。”喜讯本应让人心生欣喜,而诗人却说“喜悦更让我感到悲切”,这样的心境,通过前面对窗外景色的细致描述,有了情绪上的感染力,从而让读者明白作者的心情。
关于诗歌中的细节,熊焱有自己的心得,并以诗歌做出回应:“太幽微了:显微镜下的秘密/心灵深处曲径通幽的迷宫/有多少孤独、爱与惶恐,多少悲悯、幸福与宽容/像萤虫的微光,对应着浩瀚的星空/正如滴水有穿石之力,羽翼有天空的高度/一首诗要在细节中,看见人类的欢愉与悲苦”(《在细处》)。从这首诗中可知,细节并不全是对事物的细致描述,更高的境界是能从一滴水中,看到它的穿石之力,能从一片羽翼中,看到天空的高度。而人类的普遍情绪诸如孤独、爱、惶恐,则像萤火虫的微光,从而由小见大,一叶落而知秋。
在熊焱的诗歌中,生活中的某一个动作、记忆中的某一个瞬间,这些细节都有一个指向:人类的欢愉与悲苦。这种朴素而真诚的表述,同时以“虚实结合”的方式,就像是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这种写作方法所造成的“不知不觉的技巧”,已经内化成诗人的呼吸,并且让读者很容易体会到写作者心灵的真诚,使诗歌写作真正成为他在序言中所说的“人类心灵世界的真实认识、记录和洞悉”。
总的来说,熊焱的诗歌之所以动人心弦、有着憾动心灵的力量,主要来自一个对诗歌、对生活的“至诚之人”及“诚”所带来的一切品质。他的诗歌写作,是生活在尘世中的肉身不断向心回溯的过程,也是通过文字靠向生命本质的过程。其所带来的共鸣与震撼,不仅来自文字的力量,更在于命运本身被文字揭示了出来,犹如揭示了读者自己的命运。他的写作也因此回到汉语最为本真的初心:“只要用汉语写诗(无论新旧),心与诚事实上一直是在场的;用汉语写诗(但不仅限于写诗)意味着一场迈向诚的艰苦却欢快之旅,意味着修行……它指向心为中心组建起来的道、智慧和悲悯。”如果我们现在的诗歌写作能重新回到汉语的本质与伦理,抛却那些玄浮的辞藻、浮夸的技艺,回到诚,回到心,有善与悲悯,诗歌中人性的光辉才会升腾。
原载《诗收获》2023年冬之卷·季度诗人





 蓝色恋歌 评论 熊焱:我的平静来自人到中:学习了
蓝色恋歌 评论 熊焱:我的平静来自人到中:学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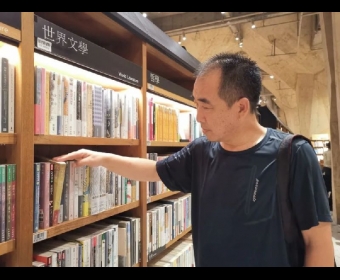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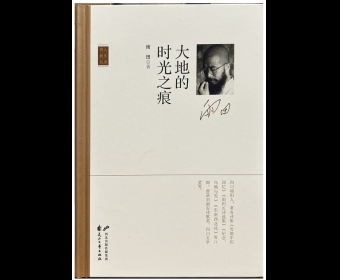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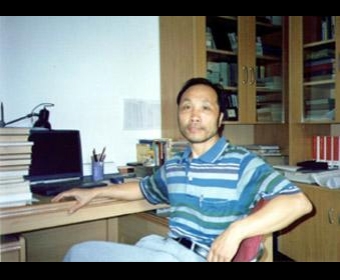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