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一萍,70后作家。四川南江人。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90年入伍,2000年成为新疆军区文艺创作室专业作家,2012年调成都军区文艺创作室,任副主任。2016年退役。已出版长篇小说《白山》《激情王国》《我的绝代佳人》,小说集《帕米尔情歌》《天堂湾》《父亲的荒原》《银绳般的雪》,长篇纪实文学《八千湘女上天山》《天堑》等二十余部,作品曾获第九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第三届中国报告文学大奖、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第三届“天山文艺奖”、第九届四川文学奖,第九届上海文学奖等。长篇小说《白山》先后入选“名人堂—2017年度十大好书”“2017《收获》文学排行榜”“南方周末2017文化创意榜年度图书”,被评为“亚洲周刊2017年十大小说”。
虚构是到达真实的惟一途径
卢一萍vs郭发财
问:我发现,从2007年开始,你的写作发生了变化。
卢一萍:我又重新开始写小说了。这对我个人的写作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我喜欢的表达样式。通过虚构来把握世界的真实性。
问:之前有好长一段时间,你写了许多纪实类的作品,那不也是写作么?
卢一萍:那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写作,报告文学也好,纪实文学也罢,我一直把他归为新闻报道。它本来就是对一个事件、一个人物、一段经历的报道。其实这类作品也不是很多,总共只写了3部,其中2部是与人合著的。写这类文字其实很简单,其创作体现在开始的采访中,这一步多少能体现一点作家的观点、才能、对事件的看法,这决定了你所呈现的事件的面貌。采访到了,其后整理好就是所谓的报告文学了。它需要体力,而不需要才华。要采访就得到现场去,就得找到被采访的人,所以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差不多有十年吧,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做这件事。
问:我觉得,这些经历对你的创作还是很重要的。
卢一萍:是的。它为我积累了创作的素材,也改变了我看待生活的方式。为了写第一部长篇报告文学《神山圣域》,我沿着西北边境跑了半年,去了每个边防连队,那是一次壮游。《八千湘女上天山》让我得以了解新疆“兵团人”的生存状况;《卡德尔和一个村庄的传奇》则增加了我对维吾尔人的了解。我利用这种机会,来为自己的虚构做准备,以使自己的虚构更加真实。我如果只想着去写那些报道,我这十年就虚度了。
问:这三部作品都获了奖。
卢一萍:《神山圣域》得过解放军文艺奖,《八千湘女上天山》得过中国报告文学大奖、《卡德尔与一个村庄的传奇》获过“五个一”工程奖。但我内心对这种文体是不喜欢的。它在无形中消磨你的想象力和对语言的敏感,所以我觉得自己干的是辱没文字的勾当。我的目的仅仅是把单位交给我的一项工作做好。我觉得惟一有点价值的,也就《八千湘女上天山》,这本书是我主动要去写的。它的价值在于触及到了一代人的真实经历,给一个本来已被历史湮没的群体留下了可以寻找的蛛丝马迹。
问:这部书现在还在产生持续的影响。
卢一萍:也谈不上有什么影响,也很难持续。在这个时代,一本书能有多大影响呢?如果说它还没有被人遗忘,主要因为我是带着感情来做这件事的,湘女和我母亲是一辈人,我把她们视为母亲。我也想尽可能全面地了解她们这辈人的经历和想法。这是了解一段历史、一个时代的最有效的方式。通过对近百名湘女的寻找、采访、整理成文字,我觉得自己都快成她们那一代人了。我增加了对她们的理解,也通过理解她们而理解了命运。命是自己的,运则只和你所处的时代有关。你对理想的追求,你的生存方式,你对生活的选择都是由它来决定的。
还有一点就是,这部作品之所以还有影响,就是因为报告文学这种文学样式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已经被败坏了,我这部作品的问世,恢复了这种文体的一些尊严,它至少恢复了它的真实性品质。
问:你怎么理解真实?
卢一萍:对一篇作品来说,真实就是能让读者从作家的文字中感受到人性和良知的光照。而虚构是到达真实的惟一途径。
我们都知道,虚构是小说的灵魂。但很多小说家正在丧失虚构的能力。他们的小说读起来更像“纪实”和“报告”。
问:请你谈谈你的写作状态。
卢一萍:我很多时候是在书房对着书或稿纸自语。我把这叫做自语症。小说家都是自语症患者。小说写作是一个很孤独的职业。我打交道的都是虚构的一些人物。我爱他,我恨他,但看不见他们的影子,他们活在我的心里,这还不够,他们要能够活在读者的心里、能够活在时间里才行,只有这样,你这个虚构的人物才算立住了。我们只能通过文字对话。在写作小说的那一段时间,我们魂牵梦绕、朝夕相处,一旦写完,他们就离开了。这就像一场激烈的爱情,爱过之后,恩断情绝。我再试着去虚构新的人物。很多人都有个印象,小说家大多不会说话。这是因为一个长期在斗室以虚构为生的人,他的言说功能有可能退化。
小说是所有文学体裁里的重体力活。一部短篇构思好后,连写带改,也得十天半月;一部中篇至少需要一个月时间;一部长篇就是长期的苦役了,有时可以折磨你三五年。甚至十余年,还有人为了一本书,即使付出一生,也未必能够完成,比如曹雪芹写《红楼梦》只写到了八十回;德国作家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捷克作家哈谢克的《好兵帅克》均属未竟之作。
问:你早期的作品是很有探索性的,比如《激情王国》,你现在对那个时期的作品怎么看?
卢一萍:那是受了八十年代先锋思潮的影响写作的一部先锋小说;加之在学校接受了一些西方的文学观念,很想以特立独行的方式步入文坛。写那篇小说是在1994年,开始的名字叫《黑白》,《激情王国》是1998年出版单行本时编辑给改的。那个时候年少轻狂,没有多少生活,更谈不上对生活的理解,但有观念,有想法,也有胆量,也自认为有些才华,所以才敢那样写。好多先锋小说的手法在这部小说里都使用过,打破了时空的限制,把历史与现实置于同一个平面,等等,“炫技”的痕迹非常重。从提笔写作到完稿,其实只用了三个月。写完之后,我不能确定我写的是什么。先在同学中传看,他们为我写出了这样的东西感到惊讶。这部作品虽然不少地方显得幼稚,但我喜欢它。因为它带着发端于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的绝唱意味,显得有点悲壮。当时《芙蓉》杂志的副主编颜家文老师到北京来约稿,我把小说交给了他。他在1995年第二期以“长篇未定稿”的形式在《芙蓉》发表后,引起了一些反响。能以先锋的姿态步入自己的写作,我觉得不错。后来我又写过中篇小说《寻找回家的路》、短篇小说《鱼惑》、长篇小说《我的绝代佳人》。这种探索一直持续到了2000年。
我觉得这是我写作上的青春期。但是我小说写作一个重要的阶段。就像我们在青春期探索人生一样,它也为我更好地理解小说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途径。
问:是什么引发你写了这部小说呢?
卢一萍:是爱情,我当时爱上了一个女孩子,非常爱她,但我一无所有,我想写一部小说献给她。
问:但你在这部小说中探讨的是理想的脆弱性。
卢一萍:爱情也是理想的一种,追求爱情和追求理想有一种相似性。两者都是脆弱的。
问:你后来的小说有了很大的变化,是对以前观念的屈服吗?
卢一萍:不是屈服,恰恰是对以前观念的尊重。我的文学理想受八十年代先锋写作的影响。我就读的学校当时采用的是讲座式授课,请的都是国内很优秀的学者和教授,西方的各种文学艺术流派和每个与众不同的作家都会集中介绍给你。的确很新鲜,很震撼,好多时候给震懵了。可说是内心壮怀激烈,脑子里风云激荡。整天做的都是大师梦。
大学毕业回到新疆后,心里平静了,脑子也清醒一些了,发现这些观念只有内化为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后才有用。这需要把它打碎,回到中国的现实生活。从对天空的仰望回到对土地上的芸芸众生的关照中。这些观念只有从这里出发才有用,才能被称之为自己的创作。这是一个重新孕育、蜕变的过程,是很痛苦的。我差不多用了八年时间才勉强做到。
问: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呢?
卢一萍:我从学院天马行空式的狂想回到现实之后,觉得这样写小说不行。因为它不是你的东西,而是某个观念影响下的产物。因为我发现,要玩形式其实是很简单的,并不像理论所阐释的那么高深。既然如此,玩它还有什么意思呢?那些理论确实给了我们一些启示,可以利用它,但绝不能被它束缚。就是说一种文学观念有完善它的无限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必须立足于自己所生活的现实才有意义。说白了,就是你无论接受的是哪里的观念,但写出来的必须是具有中国品质的作品。这一点非常关键。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中国现实的某个部分有较为深刻的把握,从生活本身来逐步认识它。这需要时间。
其次,这也与我的阅读有关,我之前的阅读多以西方先锋小说为主。回到新疆后,我在帕米尔高原工作了三年,那里海拔高,脑子缺氧,东西写得很少,但可以阅读,所以较为系统地读了一些“非探索性”的作品。我对先锋和探索作了新的思考。我发现这个概念本身比较狭隘。我认为,任何具有开创性的写作都是先锋的,都具有探索性的。比如《战争与和平》,比如《卡拉马佐夫兄弟》,比如《静静的顿河》,比如《魔山》,比如《红楼梦》。这种具有辽阔感的作品令我着迷。它们像一列列山脉,横亘天地之间,有森林草原,雪山冰川,养育奔腾的河流,在很远的地方,即可进入人类视野,永远探究不尽。而那些先锋小说,的确精致,就像精致的工艺品,但大多只能玩弄于庭室之间。
从那以后,我希望自己的心相变大,可以包容万千事物。我的雄心是写一部有趣的辽阔之书。
问:开始了吗?
卢一萍:我会在四十五岁后做这件事。
问:为什么要等到那个时候?
卢一萍:这是我人生的计划。我的下半生会以小说写作为主。我给自己定的计划是,每年写三五篇短篇小说,二三部中篇小说,每五年写一部长篇小说。
问:你近几年的创作主要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发表了不少作品,口碑也不错。
卢一萍:我从2007年再次开始小说写作,其实也没有写多少。结集起来,也就一部中短篇小说集,一部短篇小说集。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就更少了。
现在杂志上发表的小说同质化问题非常严重。也就是说,如果把一本杂志所发作品的作者名字隐去,你会以为那是某一个人写的。写的都是那些事,人物都是那个样子,故事的结构、叙述的语调都有定式,对现实的表达不痛不痒,四平八稳,故事的结局都会有些“暖意”。一期刊物上发表的小说基本上就是对另一期刊物上所发小说的重复,这是十足的“八股体”写作。这与杂志编辑的引导和作家过于功利有关。因为我们“70后”作家基本都是靠在杂志上发表作品起家的,很多人都是根据杂志的口味、迎合编辑的想法来写作,所以,这一点在我们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所以,我重新开始写作后,就想着要从语言、故事发生的地域、塑造的人物形象、小说内在的精神品质上把自己的写作与他们区别开来。在这些要素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最为重要。而这一点在这些年的小说写作中,很多作家只满足于故事的讲述,所以很多故事读起来很精彩,但读完之后什么感觉都没有留下。
问:怎么会出现“八股体”写作,你能说得具体一些吗?
卢一萍:这跟我们“文学体制”的转化有关。自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大量文学刊物消失,存下来的也多要死不活,没有什么生气。八十年代那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万元户”成了社会的关注点,伴随而来的,是锐意进取的作家写作意志的消沉。作为文学后补的“70后”在老一辈作家留下的残汤剩羹中觅食生存。他们的起步必须依靠杂志,而很多文学杂志已没有什么影响。所以大家都希望挤进那几家还残存着一点影响的刊物,以期获得文坛这个坛的认可。为此,各路神仙各显神通,结交编辑,亲近主编。有些人为此要么长驻京阙,要么定期朝贡。这样很多人的写作就会去迎合刊物的调子或编辑的胃口。后来就像西藏有句民谚说的,“我赖于此并扎根于此”了。到2000年后,这些编辑已利用政府提供的刊物平台,打造起了一个个文学小王国,成为文学诸霸,树立权威,四处代言。而随着各类“研讨会”和文学奖的增多,评论家也乘势而上,成为作家巴结的对象。这就是后来名作家不多,评论家和名编纵横江湖的原因。这也就形成了文坛一大怪现象。
问:作家是懦弱的吗?
卢一萍:作家可能是懦弱的,是生活的弱者,但在面对写作时,良知会占上风,他会变成一个不惧一切的战士,为此,他可以承受外力加给他的一切。因为作家的职责是给人类建立一个良知的标高。
问:现在在鼓吹“非虚构写作”,你怎么看待小说的虚构?
卢一萍:这不是什么新鲜的提法。它就是纪实文学的另一种称谓。我更愿向虚构致敬。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史虽然没有“虚构”这一说法。但文学理论家常常论及想象,晋代陆机在《文赋》中说,写作时“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观古今於须臾,抚四海於一瞬”;南北朝的刘勰则说:“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这其实是对“虚构”状态的最精确的描述。
那么,什么叫虚构呢?按我的理解,所谓虚构,就是小说家为了使小说反映出来的生活比实际生活更强烈、更集中、更典型、更理想、更真实,依托合理的想象所采用的一种艺术手段。
问:一部小说虚构的成分究竟有多大?
卢一萍:这是很难量化的。
但从我自身的阅读经验来讲,我们会常常忽略这个问题,把它当做我身边的另一个世界,另一种生活,另一种人生。就像孩子们相信童话中的世界一样,我们在读一本小说前,也很少要先确定它是不是虚构的。我们只会享受阅读的过程,我们会沉浸其中,前往那个世界,为其中人物的命运欢喜或悲伤。
所有小说都是童话。只不过成人的童话有时显得过于深奥、过于残酷一些。还有一点,读者需要一个虚拟的现实来和面临的现实对抗,他们需要逃避。所以,他们和作家一起维护着这个虚拟的现实。
问:请你谈谈真实和虚构的关系。
卢一萍:美国作家安妮·普鲁有一本短篇小说集《近距离:怀俄明故事集》[①],从这本书的感谢致辞中,我感觉到了作家为寻找到虚构的真实所做的努力。她说,“我热爱地方历史,多年来收集了北美多地的当地生活、事件的回忆录与叙述。”她还说,“非现实、奇思异想与未必成真的元素,为这些故事添上色彩,正如真实人生因这些元素而多彩多姿的道理一样。[②]”电影《断背山》成功后,她在谈《断背山》的创作过程时,有一段话,可能我们一般人听起来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对写作的人却很重要,她说:“我和一位羊倌谈话,以便确定我所描写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可以有一对白人牧童看护牧群,这一点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安妮·普鲁为什么这么较真,为什么耗时耗力地寻求历史的那一点真实?小说不是虚构吗?有什么是不能虚构的?这告诉我们,事实的真实是很重要的,小说是创造一种假设的生活,这种假设的生活是在真实的条件下发生,派生出故事和细节,真实是虚构的源泉。正是有了这个源泉,她才能“用锐利的笔法破开(美国西部)牛仔粗野狂放的生活方式背后的生命激情与渴望,用诗一般的语言从残酷和粗砺中淬出美和希望。”
所以,虚构是建立在对生活了解的基础上。
每个作家都在寻找能真实反映现实的虚构之路。我离开北京之后,下了个很大的决心,要做一个小说家。但很长时间,我写不出令自己满意的作品。我到帕米尔高原,原想写一本有关它的小说集,但生活了近四年,还是写不出来,我走完了整个西北边防,走完了辽阔的新疆的每个地方,我还没有找到能文学地反映这块土地的文字。积累生活,其实是积累生活中的细节,我这么做,也是在寻找便于为虚构服务的细节。
也就是说,并不是有了细节就能把它们转化为小说,就像有了材料不一定能修好房子一样。
问:那么,你重新进行小说创作是怎么开始的呢?
卢一萍:那是2006年8月,我独自返回南疆,再次前往帕米尔高原,在塔合曼小住数日后,一位塔吉克族老乡给我讲起慕士塔格峰雪崩的事儿,我的心中豁然一震,感觉万千世界在那个时刻一下汇聚到了我的内心,小说中的人物、我该使用的语言,包括语调和语速,都一下显得明晰起来。我知道我该怎样写自己的小说了。我一气写了《帕米尔情歌》《夏巴孜归来》《北京吉普》《七年前那场赛马》《克克吐鲁克》等小说,我再次建立了小说创作的自信。
问:生活中的细节很多,那些可以转化为小说细节呢?
卢一萍:小说的真实是建立在细节上的。而一部小说由成千上万个细节组成。所以,每一个严肃对待写作的作家都非常重视细节的独特和可靠。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再次小议文学与现实》这篇短文中说,“我的作家生涯最艰难的经历是《家长的没落》的准备工作。在几乎十年当中,我阅读了我可能弄到的一切关于拉丁美洲,特别是加勒比地区独裁者的材料,旨在使我要写的书尽可能少的与事实相像。”
问:小说的虚构品质怎么建立?
卢一萍:主要来自于他对世界、对生活、对人生的看法。有不少中国作家曾模仿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写了大量的小说,但为什么很少有人取得成功呢?这就是他们没有把握魔幻现实视为现实的真实反映。他们没有把握中国的现实,其作品只能模仿,也只有他们自己制造的“魔幻”,所以他们反映的现实也就成了虚假的现实,“魔幻现实主义”也就成了“虚假的魔幻现实主义”。
所以说,虚构是“小说最真实的成分”。
正是这虚构的真实,让我们在阅读时感觉到时光的停滞,感觉到已经逝去的时光在文字间完整地保留着。它构成了我们所处时代一个最迷人的部分。我们不能沉溺于现实,但可以沉溺于那个虚构的部分。
一些作家常在小说开篇提上一句“本小说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有这种说法的小说常是些不入流的作品。为什么呢?他要么是在故弄玄虚,要么是与现实靠得太近,担心有人从其作品中看到自己。故弄玄虚会使小说的真实性流失;与现实靠得太近的作家,其虚构能力则让人怀疑。虚构故事的高手常常会强调自己作品的真实。博尔赫斯在谈到自己的短篇小说《俘虏》时,就肯定地说,“这篇小说当然是真实的”。马尔克斯在谈论他的创作时,也总是在强调他笔下的魔幻来自现实,在拉丁美洲可以找到其出处。
即使很多按真实事件写成的小说——比如巴别尔的《骑兵军》,马尔克斯的《一个遇难者的故事》,作家的目的也不是把这件事实再叙述一遍,如果这样,他就不会有任何意义。事件是为小说服务的。事实对于一篇小说来说,是呈现在表面的东西,是大海中冰山露出海面的八分之一。为了达到这一点,常常需要做出艰苦的努力。
问:虚构与真实之间的确存在一种微妙的关系。
卢一萍:这一点我也深有体会。比如说,我在帕米尔高原的经历已足够写一部书,还有我曾在边疆的漫游,包括我对湖南女兵的采访。但帕米尔高原的小说,我时隔六年才写出来,湘女的故事时隔八年才进行了虚构的尝试。我最大的疑惑时,比如一位湘女的经历足够震撼人,它也是湘女亲口告诉我的,我用纪实的手法来表现它时,感觉很自然。我相信它传达出来的一切,读者也会相信。但当我要用虚构的方式来表现,我就觉得这个故事可能会让读者感觉我是编造的。我要把一个真实的故事用虚构的方法还原出来。这其实就是虚构与纪实的差别。纪实作品的标签不会让读者对你的文字产生警惕,他们乐于接受。但当它成为小说,他们看完之后,就会说,这家伙真能瞎编。如果读者这样评价一部小说,这无疑是对作者彻底的否定。所以,我要寻找到现实之下八分之七的部分。我要寻找到这部小说发生的时代的气息,主要人物说话的方式,他的象征性,这个人物的价值。也就是一部小说作为小说的意义。所以,小说家这个行当很不好干。他集帝王、圣人、魔鬼、暴徒等众多角色于一身,正如弗·莫里亚克所说,“像生活那样复杂地描写生活就是我们的行当”。
问:那么,小说的叙述格调是从哪个部分开始确定的?
卢一萍:从小说的开始就确定了。比如《百年孤独》去看冰的那个著名开头,这个开头就决定了这部小说的叙述方式。再看《好兵帅克历险记》的开头“‘他们就这样把我们的斐迪南(奥匈帝国皇帝,即引发一战的萨拉热窝事件)给杀了,’女佣人对帅克说。几年前,当帅克被军医审查委员会最终宣布为白痴时,他退了伍,从此以贩狗营生,替七丑八怪的杂种狗伪造纯正血统证书。”这个开头就确定这是一部“含怒骂于嬉笑之中”的小说。
细节的虚构很多时候来自自身的经历,但更重要的是你的经历能否升华为文学的力量,能否成为人类对某个方面感受和认知的象征。
问:问最后一个问题,小说是否永远涉及意义?
卢一萍:是的。一种可能性摆在这里,如果说小说还有情节,就必然有意义的问题。在意义问题的角度上,现在的小说家身处大海。一人游到大海上,只要看到还有灯在闪,就是安全的;如果没有,则觉得世界根本无从把握。
中国知识分子倾向于给世界一个说法,而忘了这个说法从来是在任何意义上都站不住脚的。知青作家永远告诉我们要有理想啊——这绝对正确,但解决不了小说的问题,因为它与心灵生活经验无关,它是从知识分子的逻辑推理出来的。对小说家来说,要通过虚构超越社会的定见,直接超越生活。
所以,作家总是为了更好地表达而痛苦地挣扎。陀思妥耶夫斯基五十九岁了还在祈祷,“我经常痛苦地发现,我连二十分之一想表达,甚至也许能够表达的东西,都没有表达出来。拯救我的,是锲而不舍的希望,但愿上帝总有一天赐予我力量和灵感,让我更完整的表达,总之,让我全部表述我的心迹和想象。”
他的执著,其实也就是他的绝望。正是有绝望,所以希望才会无限地存在那里。
问:请你用一句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问答吧。
卢一萍:那就用我在我的中短篇小说选《帕米尔情歌》后记中的话来结束我今天的胡言乱语,“诗人和作家是梦的巫师。怀疑和惶惑是诗人和作家的本能。它推动作家不断探索和超越。……他那邪恶的童真之眼总想从这个陈旧的世界中发现新鲜的玩意,他天生苍老的躯体总想借助巫师的力量创造不一样的人生。他的内心是联通虚无与真实世界的灵媒。他寻找真理,所以满嘴谎言;他寻找真实,所以只能虚构;他忏悔,却不思悔改;他想创造不平凡的作品,所以整日与平凡事物为伍;他想成为圣徒,却以罪恶之身下到地狱。”
[①]宋瑛堂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
[②]《近距离:怀俄明故事集》第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1月版
来源:收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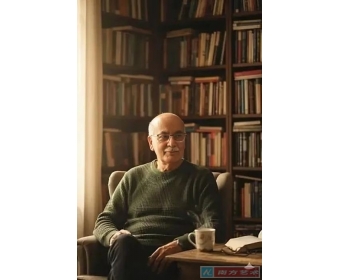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