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
三年半之后,1983年春天,罗娜和我蜗居在伦敦一个两居室里,它在一栋非常窄的楼里面,这栋楼位于这座城市的最高点之一。附近有有一个电视天线,当我们想听唱片时,播音员幽灵般的声音会不时干扰我们的扬声器。我们的客厅没有沙发或者扶手椅,有一些靠枕放在床垫上,两个床垫就那样直接摆在地板上。有一个大桌子,白天我用它写作,晚上我们用它做餐桌进食。那里并不奢华,但是我们喜欢住在那儿。一年前,我的第一部小说发表了,而且我还为一部即将在英国电视台播出的短片写了剧本。
有一段时间,我非常满意自己的第一部小说。但是那个春天,有一种吹毛求疵似的不满意感悄然而至。问题在于,我的第一部小说和第一个电影剧本太相似了。不是故事情节相似,而是风格和方法都太相似了。我越看它,越觉得方向和对话都像电影剧本。
在某种程度上,这没什么问题,但是此刻我希望写出的是只恰如其分在纸上呈现的小说。为什么去写这样的小说,假如它能提供的,或多或少只是某些人打开电视就能获得的相同体验呢?如果小说不能提供一些独特的、其他艺术形式无法替代的东西,它怎么有希望在对抗电影和电视的冲击时幸存下来?
在那个时候我染上了病毒,在床上躺了好些天。当我从最糟糕的状态中回转过来,我不想一直睡下去。我发现,那种在我床垫之间使我烦乱的沉重的东西,事实上,是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的第一部。
可能是我在发烧,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仍然困在序曲部分。除了这些段落的纯粹之美外,我对普鲁斯特用一个插曲导致下一段的方式感到很激动。事件和场景并没有跟随普通的线性叙事结构。偏离主题的意识流,或者记忆的变幻莫测似乎将写作从一个插曲转移到另一个插曲。
有时候我发现自己在想,为什么这两件完全不相连的事情同时出现在叙述者的脑海里。我突然看到了一个令人惊喜的,更自由的方式去编排我的第二部小说,这种可以在纸面上产生丰富性但是在屏幕上无法捕捉的内心活动。
如果我可以根据叙事者的联想或者漂流的记忆来逐章推进我的写作,我就能像抽象画画家那样选择颜色和图案在画布上。我可以把两天前的事情放在二十年前的事情旁,让读者去思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开始觉得,用这种方式我可能会揭示出很多人自我欺骗和自我否定的多重标签,这些标签掩盖了任何一个人对于真实自我以及过去的看法。
肆
1988年3月,我33岁。我们家里这时已经有了沙发,我正躺在上面听汤姆·维茨(Tom Waits)的专辑。前一年,罗娜和我在看起来并不时髦却令人愉快地伦敦南部买了房子。在这所房子里,我人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书房。书房很小,没有门,但是我兴奋异常,把自己的文件塞满每一个角落,同时不必在每一天结束时把他们清理干净。
在这间书房——或者说我认为在这里——我完成了第三部小说的写作。这是我第一次没有使用日本作为写作背景——通过我前两部小说的写作,“我的”日本已经不再那么脆弱了。事实上,我这部叫作《长日将尽》(TheRemains of the Day)的新小说,看起来极其英式化,尽管并没有,或者说我希望并没有按照许多老一辈英语作家的写作方式进行写作。
我试着尽量不去假设——因为我感觉他们许多人确实这么假设——我的读者是清一色的英国人,对英国文化的细微差别和偏见有种与生俱来的熟悉。到那时,像萨尔曼·鲁西迪(Salman Rushdie)、V.S.奈保尔(V.S. Naipaul )这样的作家已经铺就了一条更为国际化、外向型的英国文学之路,一种并不主张英国中心论、英国重要论的文学样式。从广义而言,他们是后殖民主义的写作。我希望像他们一样,去写更为国际化的小说,甚至在我将小说背景设置在一个明显的英语世界当中时,它仍然可以轻易地跨越文化和语言的边界(boundaries)。
我笔下的英格兰,将会是一种神话般的存在,它的轮廓,我相信,早已在世界各地人们的想象之中,包括那些从未到过这个国家的人。
我完成的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位做管家的英国人,他意识到——这时已经太晚了,自己这一生所奉行的是错误的价值观;他把自己一生最好的时光用在服务一位纳粹同情者上;而且,由于未能肩负道德和政治的责任,从深远的意义而言,虚度了一生。更糟糕的是,在他努力想成为一名完美的仆人时,他禁止自己去爱那位与他两情相悦的女人。
我曾经多次通读自己的手稿,觉得自己有理由感到满意。然而,我还是有种吹毛求疵式的感觉,有什么东西在作品中缺失了。
于是,正如我说的,一天晚上我在家里,躺在沙发上听汤姆·维茨。唱片中,汤姆·维茨开始唱《鲁比的手臂》(Ruby'sArms)这首歌。或许,你们当中有人听过。(我甚至考虑过在这个时候唱给你们听,但最终我还是改变主意了。)这是一首关于一个男人——很有可能是名士兵的民谣,他离开了在床上熟睡的爱人。
时间在清晨,他走在路上,上了一辆火车。这看起来平淡无奇。然而,这首歌却是以一位完全不懂得怎样展现自己内心深处情感的、粗鲁的美国流浪汉的声音传达的。在这首歌中间,有这么一会儿,歌手告诉我们此刻他觉得心碎。这样的时刻让人难掩心中的感动,这是由于这首歌的情感本身与克服强大的阻力去展示这一情感之间存在着的张力。汤姆·维茨把这首歌演绎得无比顺畅、精彩纷呈,你能感受到一个硬汉一辈子郁结的巨大悲伤在脸上摇摇欲坠。
当我听汤姆·维茨时,我意识到自己还有什么事情要做。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决定,在小说中很久之前就设计好的地方,我笔下的英国管家应继续保持自己的情感防线,这道防线他要设法向自己以及他的读者隐藏,直到最后。
如今,我明白了,我不得不改变当初那个决定。在故事的结尾,在我精心挑选的时刻,我必须让他心灵的盔甲开裂。我必须让人一窥他心底那种无比巨大、无比伤痛的渴望。
在此,我应该说——正如许多其他场合一样,我从歌手的声音中汲取了重要的养分。我所指的,较少是被传唱的歌词,更多的是“真实的歌唱”。众所周知,在歌曲中,一个人的声音能够表达深不可测的幽微、复杂的情绪。
多年以来,我创作的许多方面都受到尤其是鲍勃·迪伦、妮娜·西蒙、爱美萝·哈里斯、雷·查尔斯、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纪里安·威尔奇以及我的朋友和拍档史黛西·肯特他们的影响。受他们声音中某些东西的感染,我会自言自语:“啊,对了!就是这样。这正是我那个场景要捕获的东西。与我想要的非常接近了。”通常,这是一种我无法行诸文字的情绪,但是,它就在那里,在歌手的声音里,现在我知道自己该朝什么方向努力了。
伍
1999年十月,我受德国诗人克里斯多夫·休伯纳(Christoph Heubner)邀请,以国际奥斯维辛委员会的名义去参观之前的一个集中营。我住在奥斯维辛青年中心,离第一个奥斯维辛营地和比克瑙死亡营两英里远。他们带我转了这些地方,并非正式地会见了三名幸存者。
我感到至少在地理位置上,接近了我这一代人成长阴影下黑暗势力的中心。在比克瑙,一个潮湿的下午,我站在如今被人们无端忽视、无人照看的瓦斯残骸的废墟前,就像德国人把它们炸掉并逃离红军后留下的那样。他们现在只是潮湿,破碎的石板,暴露在波兰严酷的气候下,逐年恶化。
主办方告诉我他们的两难状况,这些尸体是否应该受到保护?是否应该建造有机玻璃圆顶来覆盖它们以保护它们为后代所见?还是应该让他们慢慢自然地腐烂?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更大的难题的一个比喻。这些记忆该如何保存?玻璃圆顶会把这些邪恶和痛苦的遗物变成驯服的博物馆展品吗?我们应该选择记住什么?什么时候忘记和继续下去更好?
我那时44岁了,我开始考虑二战,属于我父母那一代人的,它的恐怖和胜利。但是现在我突然想到,目击过这种大事件的人很多都死去了。记住历史的压力是不是到了我们这一代人肩膀上?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但是我们被父母抚养长大,战争不可磨灭地摧毁过他们的生活。我,作为一个公众面前讲故事的人,有没有我还没意识到的责任?有没有一种责任去把我们父母这一代的记忆和教训传递下去?
之后,我在东京的观众面前演讲,前排有一位听众问我接下来准备怎么做。更具体地说,这位提问者指出,我的书经常关注那些经历过重大社会和政治动荡时期的人,然后他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并想方设法向自己更黑暗、更可耻的记忆妥协。她问我未来的书是否会持续相同的领域。
我发现自己给出了一个没有准备好的答案。我说是的,我总是写那些在遗忘和回忆之间挣扎的个体。但是未来我想写一本关于一个国家或者社区是如何面临这个相同问题的书。
一个国家记得和忘记事物的轨迹和个人一样吗?他们在哪儿保存记忆?记忆是如何被形成和控制的?有时候忘记是制止暴力循环,阻止社会瓦解成混乱或战争的唯一途径吗?另一方面,稳定的自由国家是否真的可以建立在任性随意的失忆和令人沮丧的正义的基础之上呢?我听到自己回答她这些问题,但是那一刻,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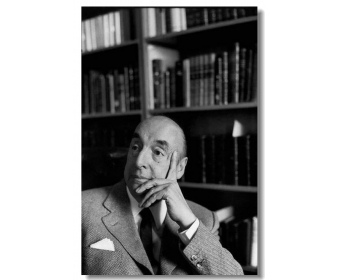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