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何孤身前往(访谈)
采访人:木朵
受访人:柳宗宣
①木朵:《分界线》(2005)以一种后见之明的方式回顾了六年前(“1999年2月9日8点”)的一次由南至北之行。这首诗以两种天气的变化(“雨水”、“阳光”)为喻,概述了早年一次抉择所富含的象征意味,简言之,去北方被称为寻找光明之旅。但这首诗并不是即景诗,也不是抵达目的地后当晚写就的纪游诗,而是时隔多年之后一次回眸,就好像那个发明了两个自我形象的关键日子仍是决定性的。从此,诗屡屡带来关于“北方”的通讯。可以说,一旦要归纳那些年写作的特征,就绕不开这条界线:整个人牢牢地钳制于那个太过深刻的作为旅客或奋争者的自我形象之中。到什么时候这种关于界限的记忆在诗中不再显得重要?
柳宗宣:蛮高兴你一下子找到我们交谈的切入点。你谈及的确切,此诗不是什么即景诗或纪游的文字,它是事隔多年后从潜意识里冒出来的,它是“后感知”到的。这个分界线似乎不能仅用所谓的象征和单一的隐喻来描述,应该说是直观到这个分界线:颇有丰富意味的场景。事隔多年,你能重新回到那个刺激你的分界线,进行对那个场景和那个时刻自我的双重直观,这样的双重直观昭显出了有意味的形式。
在直观前者的时候也没有强加所谓的象征或隐喻,是听从那个场景原本所给予的来加以描述:阴晴,潮湿与干燥,南方与北方,这瞬间相遇的分界线让你发现有多重的意味与神妙,而且你一时说不清,在遭遇的瞬间被它们打动了。人所面对的也不会总是可以把握的对象,陌生的处境、突至的事件打破惯性,也搁置了记忆;当下向着一个空白敞开。因此这空白虚无可以生发新的意义、新的可能性,而且对它的直观并不是一次性的,是反复到来反复被体会领悟的。我的写作受现象学的影响是有的,注重诗生发的最初的情感震动,这样身体自然出场,在具体写法上,自然放弃了所谓象征主义诗歌给语言带来的负重,象征诗在表现自我时太过用力了,它破坏了你与事物邂逅互动的客观性。写作时讲究主客观的双重呈现,我力求写出的是能够被“看见”的诗歌。
从诗作品中能体验到有质感的意象、场景与事件,同时能触摸到你的身体的感动与情感的波动和感应。如近作《复调》中体验着的直观着的主体活动在诗行间,这里也有元叙述的成分,使诗的生成、推动与变化构成了多种声调齐声共鸣的效果;身体性在诗歌写作过程中或作品显现上见出其原动力与重要性,也就是说诗的写作不仅仅是智性的纯思辨的产物。这样强调新感性的写作也是考察诗作是否具有真实性的试探器;那不关己身不涉及人对自身命运的领悟与体验,写作没有身体参与所呈现出某种惊奇感,那首诗几乎是不可信的也是失败之作。也可以这样表述,没有“我”身体的游走也不可能有这首《分界线》,从诗的生成到作品的出现都不能缺失一个运动着的身体。
说到这个“分界线”,就我个人的写作它也显出它的一种特殊的意义。以前我在南方的写作是没有北方的。我是到了北方生活才发现了南方。一度喜欢美国诗人毕肖普,着迷于她诗里的南方与北方,她的出生与经历确实给出了一个她的南方与北方,她曾多次在加拿大、美国和拉丁美洲南来北往。她的漫游流浪使她的诗歌呈现出“特殊的地理”,多重的空间与维度。
自从我的生活与写作有了那个天然的“分界线”,诗歌经验的维度与幅度发生了变异或拓展,我想再编一本个人的诗集就将这首短短的《分界线》放在开篇。是的,可爱的分界线显明地出现在了作品中,像《母亲之歌》场景与细节都是南北的,我是到了现在才理解为什么要把参加母亲葬礼者的名字罗列于诗中,这固然受美国纽约派诗的影响,当我在写出南方亲人朋友学生的名字时加入了隐在的感情,那些年在北方想念南方啊,你知道这是在四十岁找到北方的,诗歌里才能出现那苍茫的景观,或者说我到了北方才真正认识生活多年的南方,我的故乡。那在北方张望中呈现的南方的人与事。《还乡》就把这种意念与感情推向了一个高潮。还有《今晚》《棉花的香气》等诗也参与营造一个小气候。我有一个偏执的做法,总是过分在意一首诗的切入角度,《棉花的香气》一诗的生成的角度让我把一些似乎不存在的事象给呈现出来了。一首诗如果找到了一个相对有意味的角度,这首诗就差不多可以成形了,如果没有找到,它可能就出不来,也就别谈什么诗的空间、结构、张力与意味什么的了。
从北方回到了南方的写作,应该说是近年的写作,诗中的南北分界线才淡了些或者说它内在于诗作的生成与组织。我想着它们南北浑然含融于一体,看不见这个分界线,即便你曾经一度迷恋这个分界线。
②木朵:《母亲之歌》给我最深的印象不只是“人的名字罗列于诗中”,还有“我看见……”这个主谓词组的结构起到的支配性作用。这应是一种最合理的悼念方式。按你的说法,这也是一首“能够被‘看见’的诗歌”:这是对“看见”的看见。或在汽车后视镜中看,或“在国道上饥渴观看”,或“从落地玻璃窗望过去”,或在错乱集市的小餐馆“旁观”,或从一把藤椅中看到父爱……那么在多次观看中会受到怎样的启蒙呢?如何做到观看上的前后有别?大量外界因素加入,诗因此看上去更富有现实主义色彩吗?而附带的噪音,怎么祛除?
柳宗宣:“看”确是我诗歌里的一个关健词。胡塞尔的现象学其实是教我们如何观看的学问。看是一门艺术。你如何从不同角度瞄向或直观到你身体周围的生活世界,获得现实客体和意向性主体生成的映象,获得存在的真相,这是一个得持续做下去的功课。情感在我看来它是身体感知的具有空间性的客观的实体。诗的情感也是可以被“看见”的,诗的情感传达依存于视像与视像之间波动,我在写《母亲之歌》这首诗时,克制了多余的抒情,因为它本来就在移动画面的拼贴与组合的空间和语调里,浪漫主义的微尘不得不也在诗行中被拭去。我曾写过关于“母亲之死”的几首诗,只有这首觉得找到最佳的表达方式,完成了从传统写法的离身撤退。
我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诗歌写作的,诗歌的实验与观念的更新吸纳了当代艺术多种语言,而且最初的起点很低,停留在对诗老派的认知和写法,其实诗歌写作不断地更新诗的生成与表达方式,它似乎影响了相邻艺术门类的表现,当然也从绘画与电影、音乐等门类获得灵感,印象最深的是留意刘小东等人的绘画,其创作拉近了艺术与生活的距离;对虚张的大观念的回避,愿意回到现实生活中,重新审视自己确切的不夸张的位置;喜欢描述日常生活,从非常具体的人和事件中投射出情绪性、观念性的精神因素。当时,电影也开始出现第六代了,他们的摄影机不会撒谎,技艺考验着艺术家们的诚实。革新也就不断地出现了:纪录片与剧情片断开始交汇,即兴创作的出现;电影的叙事割裂剧情的连续性,甚至肢解音效和构图,绘画与电影的新的元素与诗歌实验互动。新的艺术形式要求着作者为人们的观看提供诧异,为艺术发现提供新的可能,那年月,像这里。现在。此在。现场。成了当时热门之词,私人写作将我们所在的地名,人名,生活场景写了进来,对自己的生活进行近距离的细微打量。
九十年代中期我的《她穿过黑夜的楼顶回家》强化了诗的叙事。描述成了一个重要的元素;《上邮局》一诗叙事出现了怪诞的超现实的画面与场景,还有双重互动的结构生成。其实《母亲之歌》一诗不能说没有电影纪录片不动声色的画面感,那看似客观的拼贴与组合。你提到的《旁观》一诗的最后一句,我看到了一个存在在高处打量我和身边虚空人事。这是在观看中的难得的“出神”。
由于诗歌中发生的完全不同八十年代的实验,我的诗歌几乎成了“街头现实主义”。如你如说,大量客观映像在诗里的呈现,是有那么一点如加洛蒂所说提倡的“无边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可以在自己所允许的范围内“无边“扩大。当下现实提供了诗的细节、场景和原始素材,可是兰波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了,如何摆脱现实生活与诗歌文本间的矛盾,诗不仅是描绘世界,他更是要创造一个世界。史蒂文斯的诗试图用想象力观照并改变现实,用诗的想象力赋予世界与经验以秩序和形态;弗洛斯特的诗里呈现的多重现实,最后指向的是玄妙抽象之境;秘鲁诗人巴列霍谈到新诗歌时就强调现代生活提供的物质,必须被精神所汲收,再转化为一种新的感性。这个转化之功确实十分必要。洛加蒂在提出无边的现实主义理念后,他也补充了“抽象现实主义”的概念。是的,艺术最终要创造出全新的词语的现实,这是被摧毁了的现实,它感性但非现实。要经过此转换是很难的,你所说如何祛除诗中外部现实的噪音,我想即弱化诗的性线描述,词语不可过分粘滞于现实的泥浆,从现实场景的束缚中的解脱出来,对现象描述中非诗意的部分剔除,呈现出对自身生活纯粹的领悟,让词语运转腾挪,进入词的互动生成,并精心于诗自身结构的营造,等等这方面的努力会使诗语言的现实从文本层面真正展现出来。
③木朵:现实会教我们还可以怎么理解“现实主义”,比如在《牙科诊所》(2008)这首触及疼痛的肉体之现实的诗中,“鸦雀”扮演着推动情节发展的精灵,像这种非现实因素——也可理解为抒情符号——给一首涉及当下处境的诗带来不少便利,它让诗看上去更富有生机和逻辑,也增加了人与他者周旋的戏剧性。如今,对一只鸟、一棵树或一枚残月的描写,容易被认为是老套的、不解迫在眉睫的现实之风情的做法(另一方面,当代诗人要把这些事物吟咏到位也很难),然而,不经意间,鸟儿还是溜进了诗中,即便是一个配角,也让人受益匪浅,比如《山中交谈》(2012)就靠“奇怪的鸟声”来收尾。现在,你可能会怎样来写一首纯粹的咏物诗?
柳宗宣:牙科诊所中的那只鸦雀确不同于传统咏物诗的兴叹的客体,它是一个现代诗歌场景里的一个与我们对应的细节。它也不同于波特莱尔诗的中的“信天翁”,一个比附或象征体,即诗人形象的隐喻。这只鸦雀只是这首诗中一个小的声部,参与了此诗的合奏与生成,确如你所云,它的再现给全诗带来了某种戏剧性,它的出现比衬着我们的痛苦世界,它隐隐作用了我们在诊所的世界痛苦感知强度,它既是写实(新写实)但又有散逸开去的意味,难以挑明,影影绰绰,如果没有它的到场,诗的写作也没有冲动与乐趣,似乎是一个想象的世界,同时是一个自然世界,虽然这个世界在退避我们日益膨胀的欲望,渐渐从我们的生活世界和语言世界里消失,这个世界还有什么“物’可咏的呢。
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在我们的语言世界里出没现身必然是飘忽断续偶然的,你无法赋予它一个相交融的客体并去咏叹它。我的写作存在主义意趣颇重,注重个体生命的在世感,目光总是盯着自我,状写着自己的境遇时偶尔看看外部。所以这只鸦雀的出现也是只加深了我和我们生存的痛感,我是在人的世界里转悠太久,突破不出去,什么时候能向外部世界投向它的短暂一瞬——能以物观物,而不是以我观物。这“鸦雀”又似乎是对专注于自我的一种唤醒,一种自我的镜像,它隐隐地昭示一种古老恒常的生活形态把我们抛弃了或我们失落了它,是我们对可能生活的一种张望形式,这样说来,鸦雀参与了我们对存在诗意的反思与审察,这鸦雀以它轻盈反衬出诗所思主题的凝重,而且它触发了对痛苦的多种现实的发现。
对鸦雀的看,或诗歌里的看,看也是感知,看也就是在思想。对它可见性的描述以及对可见性中的不可见性的想象与着迷,使此诗涌现出模糊的多种层次,甚至让人生出福科的“目光考古学”的联想,鸦雀暗含着对不可见性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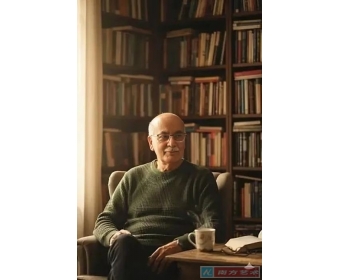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