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们的散文写作处在某种盲目的自信、不自觉的自虐和败坏之中——在写作中,我们更多的关注了散文写作的形式、语言、题材和物象,而忽略了一些根本的问题。下面将要谈到的问题应当是致命的,而其又在散文中长期、大量、霸道地存在着、反复着和高扬着的。令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么多年来,没有一个人发现和提出。就我本人而言,也是在偶尔之间,在向往甚至崇敬的阅读当中,突然发现,我才猛然惊醒:我们的散文中竟然存在着这么多的非散文因素。
如若仅仅是非散文因素倒也无可厚非——我们永远都不可能从文章当中剔除那些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词句。而散文的非散文因素,它们显然已经成为了“问题”。它们在文字当中,明显或者隐藏,自觉或者无知,都在一定程度上消弱着,也毒害着我们的散文写作。我所要说的第一个问题:应当是散文中的官僚主义了。这种传统的根深蒂固的东西一直在我们的散文中出现,据我的阅读,它们大都彰现在一些老散文家和官僚文人的文字之间。譬如,2003年在《十月》杂志开辟专栏的河南散文作家郑彦英,其散文《熊耳考水》中说:卢氏县有关领导得知他要去该县,便派人带车来接。这是一个明显的官僚主义特征。我从下面的文字当中没有读到相应的羞愧之感,并且获得了一种理所当然,甚至沾沾自喜,自认为应当和高贵的词语颜色。这一点,我蓦然感到了悲哀——我们的文人是什么呢?谁可以剔除他们的骨子里面的阴暗的有毒的部分呢?这种官僚的,传统士者的思想意识,在文字当中复活,成为一种身价的标榜和身份的象征,这是不是一种悲哀呢?起码也是散文和散文家的一种肿瘤和恶疾。第二个例子是周涛和他的大部分散文作品,我在翻阅其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的散文集《天似穹庐》时,看到了令许多人拍手叫好的《半坡村》。这个文章的开头,也是这样一副姿态和语调,说某人的巡洋舰(好像是一款轿车的名字),载着他出了太原城,心情和风景如何如何。不仅此篇,在周涛先生几乎所有涉及出行和军人的文字当中,理所当然的,自以为高贵的迎来送往,亲自陪同、推杯换盏的场景比比皆是。我在想:一个作家,他究竟有什么资格和理由来享受额外的高于己身的优厚待遇,他的这些待遇由何而来……对此,我们当然可以往深的地方说……但我只能缄口,虽然我心有不甘。但也只能引用一下马丁·路德·金话,他说:“对此我并不满足,除非正义和公正有如江海之波涛,汹涌澎湃,连绵而来”。(《我有一个梦想》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1月第一版)
第二个问题是暴力主义。这里面,首要的一个因素是散文中的意识和人为的暴力。这种暴力虽然不怎么明显,但它们就在散文所涉及物象和事实之间。这方面的例子应当很多,不仅仅存在于老散文家和官僚文人和他们的文章当中,年轻一代也多有此种倾向和迹象。张承志的散文作品一直是我所景仰的,但其中也有明显的暴力主义充斥。在《心灵史》这部巨著当中,在宗教的关照、生命的抚摸背后,我们仍旧可以嗅到血腥的味道。刘亮程的散文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在我们这个时代开创了一种自在的贴近大地的写作路数(虽然他伪饰或者消隐的真实的乡村)。但他仍旧没有消弭内在的暴力倾向,我记得他在一篇文字当中写到一头驴,更远处有几个衣着鲜艳的妇女,刘用极其隐晦的笔调说出了“鞭长莫及”——这种意识中的暴力主义,显然一直在驾驭着作家意识形态和写作本能。刘文当中的暴力主义不仅仅这些,只不过他做的比较隐秘和诗意一些罢了。第二个是词语的暴力,这种暴力是明显的,一目了然的,在语词上进行一种陌生感、断裂感和幽深感,这是散文写作的一条道路,这种路子黑陶的作品最为成熟。关于他的作品,我只是感觉到了强烈的断裂感、陌生感和对词语的一种极端暴力。当然,这种暴力对阅读者造成了视觉的乃至内心的某种割裂感。他并没有使坚硬的词语成为一种温暖的照耀和抚摸,而是一种破坏、阻断和远离。
第三个问题是诗意主义。这个问题是很多人存在着的,很多人学习并且顽强地在进行着。诗意仅仅是一种阅读的美感,深入内心相当大的部分是空朦。过多的诗意是对真实的一种反动和反叛,是诗意的倒闭和诗意的廉价出售。刘亮程散文所呈现的诗意是一种自然的虚假表现,一种顺理成章的诗意自渎。虽然我们在其中看到乡村真实、生动、沧桑、恬静、幽静的一面,但诗意是不是乡村的唯一表现方式呢?还有沈阳的鲍尔吉����原野,通篇都是诗意,相对刘亮程散文,他的诗意是狭窄的,微小的,甚至是相当虚假的。他总是在一草一木、琐碎小事中反复和制造着这种无聊的诗意。不仅这些散文作家,目前在坛子里面仍还活跃的散文家们,不管年轻的、中年的、老年的,很大部分人都在诗意当中深陷,头顶玫瑰花冠,青枝绿叶遮眼,在他们看来,散文写作除缺诗意不成文,除缺诗意都干瘪。这种以诗意作掩护的散文写作,其实是一种自我出卖和自我蒙骗。
第四个是脱皮主义。这个问题有点抽象,它具体在我们写作者的文字表现当中。一个作家,去了一趟农村,回来之后便是泱泱万言,走马观花的俯瞰本质上是对农民(他们总要提及一些新近结识的农民)的一种人格侮辱,也是对现实的残暴篡改。我们的散文家总是以为,自己始终站在意识形态的前沿,能够透彻地说出当下社会每一个人的真实命运和真实生存。这种想当然的写作,犹如脱皮的知了和蛇,原本是这样的,到他们那里,便就成为了另外一副模样。这个问题其实是最大的悲哀,是我们散文作家的一种耻辱,也是知识分子的耻辱。
以上,是我在阅读中蓦然想到的,它们显然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但我来不及细想,作为一个较为清醒的发现和参与者,我想我说出来也就足够了。无庸讳言的是,当前中国散文界的真实情况是:我们的散文写作基本上已成为了“消闲”、“做作”、“假饰”的复制品和代名词,我们的写作显然已经坠入到了一种自我消费和自我欺骗的境地。散文的清澈、激越、直接、简约和丰沛品质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我们一些所谓的写作者转换成为了单纯的技巧、情感、语词的雷同和寡廉鲜耻的“扮演”与“装饰”。我所理解的散文应当回到她的本质上来,回到我们所需要的平等、人性、怜悯、同情、高贵、温暖的特质上来,回到文学的核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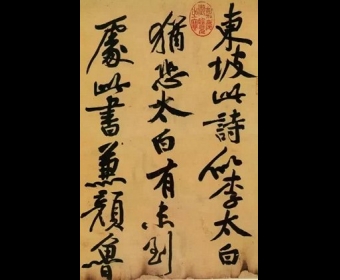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