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在中国的战乱中出生,抗战中长大,国家、中国这两个名词对我一向是极为神圣,但是经过我这一段分分合合理出来的线索之后,终于在50岁之年把这个褊狭的国族观念放在一边。这个过程并不容易,也不舒服,要常常跟自己在脑子里面打架。现在我认为任何国族观念都是褊狭的,就跟从前的社区观念、宗族观念一样,都是褊狭的。国族确实是想象、造作出来的社会单位。
虽然我在思想上可以跳出来,但是那些洒热血、抛头,手上绑了手榴弹,爬到日本坦克车上,连手带手榴弹一起塞进炮筒去炸的烈士,飞机上的飞行员,连人带飞机冲向日本军舰,或者连人带飞机、带汽油开下去冲日本的军人,这些人不就跟我一样有国族观念?他们的牺牲也是一条生命,今天固是壮烈无比,一百年、两百年后又怎么说?就像我们读古代史,读《刺客列传》,荆轲也罢,田横也罢.当年壮烈无比,今天看起来不是开玩笑吗?当时吴王跟越王打得昏天黑地,越王卧薪尝胆,还吃粪,也是为了国族,但是今天江苏跟浙江分得开吗?
我对自己的感情挑战,结果我只认为两个东西是真的,一个是以全人类为前提,一个是每个个人,只有全体人类,还有个别的个人,这两个才是真实不虚,其他都是假的。我受到美国宁静革命的影响,参加他们的民权运动,老是和他们一起辩论。这段经验也让我超越国族观念,正面地认识人类本身的价值。我不是说世界主义,而是对人本身的尊敬与爱护,这两个观点是我现在做人最基本的条件。
我读书、研究以及我自己的世界观念、人性观念,都是不可分割的,这两条路我一辈子没办法切开。如果只是专业,我一定拿自己守住一个专业伦理的小圈圈,跟外面分隔,但我不能这么做;我也不能是纯粹的知识分子,畅言高论,完全不受任何拘束,因为我还要顾全我自己专业里面的伦理和教条、规则、训练。我不能像30年代张季鸾他们一样,撒开手来写,也不能像梁任公那样,撒开手来写。梁任公在学术方面是不谨严的,感情重于理智。所以我在这两方面是两无着落,但是我不懊悔,我自己找我的路。
七〇年代我刚到美国时,正好发生钓鱼台事件,我的同班同学、前后班朋友、宿舍的朋友,纷纷投入这项运动,直接和当时已经涌现的“台独”运动冲突,后来钓鱼台这个议题被转移为国家认同的争执了。有人主张回归大陆,有人主张“台湾独立”;我夹在统独中间,两边没着落,我对中国故国的支持不能丢,台湾是我成长的地方,我属于那里,所以这两群朋友冲突的时候,我心里极为难过。那时候我唯一能说服自己的理由是台湾可以民主化,因此我也投入报章杂志的工作,我认为民主化高于国族的感情。但是我觉得很伤心,有回我替《历史月刊》写东西,我谈到“民主”、“自由”这两个字的滥用(abuse),它们被糟蹋掉了。
六
八〇年代那一段对我而言是重新整顿自己,那时候我最高兴的就是理清楚仰韶文化、庙底沟那一系统,能够从关中一直拉到郑州,不断地发展,最后终于成为中原最根本的文化基础。在山东同时代的龙山文化,以及龙山前面那个系统,虽然和它一样强大,但是没办法和它对抗,至于河北那一系统,老早就被山东一系打败了,而东北系统和东南系统都无法发展下去。
长江系统是从大溪到石家河,也有它的发展方向。黄河边上的庙底沟和江汉接壤的石家河、屈家岭这一系之间,显然有互动。这个认知使得我后来能够解释战国文化的大变化,战国文化之所以能够异锋突起,变得那么磅礴,终于替中国找上统一的局面,乃是江汉和黄河两套东西互相融合的结果。这个融合是儒和道的融合。前几年在湖北荆门市郭店出土的战国文书,证实那时候的“道”,跟我们后来了解的“道”,不是一个事情。
我搞西周搞到今天,写了《西周史》,大陆上考古界以及历史界的朋友,每次发现新东西,就告诉我;“你的话又对了!”我看见新的东西又证实我的想法,更是高兴。这就是掌握一个大线索,掌握对了,别的就容易掌握了。所以我奉劝大家,一辈子做学问,要掌握大线索,没有大线索,理路就搞不清。而且绝对要跳出自己专业范围,跳出自己的文化圈子,才能掌握大线索。
周代提出天命观念,就是普遍性(universalism)的呈现,这也跟雅斯培有关系,我的硕士论文就是写天命,那时候认为“天”和“帝”是对冲的,现在晓得天是可以容纳帝的。天是一个天命观念,周人以为天命有其道德裁决,而普遍性这个观念很重要,因为天命的普遍性替孔子的普遍性打了基础。没有周代的天命观念就没有孔子,也就等于没有犹太教的大先知在巴比伦以后的反省,就没有耶稣基督,没有耶稣基督就不可能有圣保罗拿希腊文明和犹太文明合并,并出基督教文明一样。
天命观念的重要性是替孔子铺路,孔子采人文主义,单单靠商代那个狭窄的祀奉祖先的观念,是没办法形成普遍性的。因为祖先是血脉的,天是广阔的,覆育万物。我写硕士论文时,天和帝是对立的观念,等到我写《西周史》的时候,天就笼罩着帝了,在对抗性之外注意到两个观念的互补了。
后来我研究汉代农业时更清楚了,汉代做那么多努力,要拿“帝”和“德”解释成“力量”、“特质”,不拿它人格化,结果它拿宗族祖先的“帝”转化成一个无所不在的力量和要素,变成五德、五行之一。这是汉代学者花了好大努力去做的,拿孔子的伦理思想扩大成一个宇宙论。
汉代早期一百多年的发展,很了不起,从思想影响到人做事,以及组织社会的方法,这是汉代一百多年下来了不起之处。欧洲中古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是Thomas Aquinas,合哲学与神学为一炉,以理性神学取代启示神学。但他毕竟是在一个宗教系统里面翻滚,没有牵涉异教徒(pagans)在内,面临的挑战要比汉代的学者小多了。
从汉初到董仲舒,从董仲舒到王莽,这一段是大建构的时代,从宗教思想到礼仪、技术、医学,无所不包,无所不用,中国文化在那一段时间奠下基础,真是奠得扎实,以至于两千年来我们都没办法撼动它,直到西潮打过来,才把它打翻掉。虽然被打翻掉,但现在可能又站起来了,我讲“站起来”不是中国国力站起来的问题。
七
2005年南京大学办了一个高级研究院,由南京大学副校长张异宾领军,周宪做院长,我当不拿薪水的顾问,本来他们要请我当院长,我说:“我不做你们的官,我不做官!只尽心意,也不拿任何报酬。”他们尊敬我的想法,于是每年我有一段时间在那儿,每天和一两个年轻学者谈话,一个人谈两个小时,也跟五个人、八个人、十来个人、各种不同队伍的团体,谈两三个小时。
为什么我说中国可能站起来呢?因为大陆上很多年轻学者没留过学,他们受到西方的影响相当小。我印象很深的是他们对知识的饥渴,对追寻思想出路的饥渴,台湾的年轻学者很少有这种饥渴感。我们在做专业的工作,他们在做安顿性命的工作,安顿性命比专业重要啊!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南港自己要想一想。
他们找来新马克思主义,找来青年马克思,不要看这条路好像是炒冷饭,他们的努力是有目标的,不是学术性的目标,是安顿心灵的目标,替中国找方向的目标。因为语文能力不够强,所以他们对整个西方的东西往往从中国的角度翻过来想,拿中国传统的一切理念和青年马克思思想合在一起。这一点不能轻视它,因为美国的自由主义是英国长期传下来的欧洲自由主义,它们都面临了知识上与心灵上的穷困,美国在科技上的进展,让西方自由主义学者生活得太舒服了,而专业化的地步,又让西方自由主义学者不去想外面的事情,知识上的穷困使得自由主义没有根,很难有活力。在美国,基督教的衰微也使得信仰上、热情上没有根,所以许多六〇年代参与美国宁静知识革命的人,寻找心灵的安慰和灵感的泉源,最后寻找到印度,或者虚无主义去了。
欧洲也在找同样的东西,欧洲新教在衰微,天主教还勉强能维持,美洲与欧洲大陆自己原来源头的线索都切断掉了,而一些中国年轻学者,正不自觉地下意识地以中国的东西来解读青年马克思。资本主义面临大难关的时候,中国如果拿中国和青年马克思合在一起,搞得巧,仍有可能取代今天的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平庸的政治、不负责任的自由。
不负责任的自由是社群解体之后的结果,而且欲望又很强,我们的物质生活发展到了一个地步,每个人都可以过,而每个人也都付出代价,不再想到社区、社群。大的团体没有了,又不像我想那个全体人类的社会(human society),只晓得想一个人,最后就变成我讲的四个东西:平庸的民主制度、不负责任的自由、衰微到快要解体的资本主义,以及一个本身无处着落的自由主义。今天这四个东西确实是雅斯培所说的,旧的文化死掉,礼坏乐崩,确实要新的文化出来,就是科技文明挂帅的新东西。但是科技知识的本质乃为工具,科技下面的目的在哪里?这个目的弄巧了,真是青年马克思人文主义,加上中国儒家的人道主义,搁在一起,真的可能找出一条路来。张异宾就走这条路,他这个人不错,不要看他是当官的。他跟我说,他在这方面努力是有个道理的,他说:“我不怕!”
其实这方面欧洲一直在做,在欧洲几个政党之中,所谓基督教社会主义就是走这个路线,还有从意大利开始的欧马(欧洲马克思主义),基本上都在做这件事,付诸实现的是北欧几个国家。虽然我们旁人看来北欧国家的社会福利好得很,但老百姓一点也不高兴,觉得日子无聊得要死。我的老朋友Moner是研究拉丁美洲史的专家,他在匹兹堡担任讲座教授,我说:“你好好在瑞典过日子,过得那么舒服,跑到美国来干什么啊?”他说:“什么好?”我问他有什么不好?他说.“我眼睛一闭就晓得我将来睡什么样的棺材。”他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所以他又说:“假如我有孩子,我眼睛一闭就知道我给他睡什么样的床,他哪天到哪里打什么针,上什么学,一清二楚,这是很枯燥乏味的生活。”他还说.“在这里你的英文不如美国人,我的英文也不如美国人,但我们两个人用英文对话,三种思考方式摆在一起,瑞典方式、中国方式、美国方式,我们两个要拿事情交流、搞清楚,十分令人兴奋。”他对瑞典、挪威那套东西不满意。
瑞典、挪威不怎么去想这些问题,他们就是把制度摆好,然后执行,出不了什么大思想家。有一个人真正有思想,就是电影导演伯格曼(Ingmar Bergman),这个人了不起,他真会想,可是很多人将他的电影当娱乐看,没想到他却是个不可思议的思想家。
我自己主要是活下来做个人,因为做人的要求,看材料时才能看出另外一个意义,大多数人做了专业家之后就不去追求其他意义了。孔子讲过,我们要做个人。世界上所有文化没有一处做到这一点。我怎么跟神保持好的关系,怎么过日子,虽然有种种的苦难,我还要过下去,孔子说:“你要做个人,还要做个有意义的人。”雅斯培也要人家做个有意义的人,雅斯培是个积极的存在主义学者,和消极的完全两样,他的思想和孔子暗合。我觉得不但他跟孔子暗合,德日进也跟孔子暗合,德日进是从专业之中整顿出自己的思想,安顿自己的性命,因为单单靠天主教,他安顿不了自己的性命,所以他将信仰重新做了很大的解释,而那些重新解释的源头就是他的专业,从古生物学上得来的一些想法。
我相信我的基础是儒家,在儒家上面摆了一些其他的东西。我从小就对朱(熹)王(阳明)有兴趣,但我喜欢王,不喜欢朱。我觉得朱太勉强了,王是自由的,这很可能跟我没有读过制式教育系统的小学、中学有关系,所以我可以自由自在,不受制约。
战时的生活经验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让我体验到一个活蹦乱跳的生命,嘭!一个炸弹就完了!一个好好的、年纪轻轻的生命,忽然之间就消失了,不该死的死掉了,就是“冤”,看过冤之后,我更珍惜每一个人的价值。
一个文化体系会找到若干基本的运作模式,文化是活的,因为每个活人摆了自己的观念进去,这几个模式发展到了一个地步时,它成了型,一旦成型,活力少了就僵化了,所以不能结晶化(crystallize)。水晶是高度纯化的硅,漂亮、好看,金刚钻是高度纯化的碳,但不能变,也是一种僵化,僵化以后,它的活力就没有了。文化体系僵化后,可能会有两个活力来源,一个是里面的异议分子蹦出来,另外是外面进来的异议分子跳进来。
从里面蹦出来的异议分子就是,假如这个僵化的秩序中,有强势跟弱势,掌握资源少的是弱势,例如穷人、苦力、低阶层的人,或者天生脑子里想别的念头的人,是少数派,不甘愿在多数派里面委曲求全,这些少数派跟弱势就会蹦出来。但是如果少数派跟弱势,不在那个僵化的体系中造成强大压力,造反也成不了功。而外面进来东西,观念也罢,事物也罢,东西也罢,它的影响可以从上到下全面的。碰到个外来的玩意儿,迎头撞上,第一遭一定撞到头昏眼花,也许两个都昏;到了第二遭就认为,这玩意儿也挺不错的嘛!肯面对外来刺激,由拒绝而转向欣赏,再转为吸收,然后慢慢就相互融合起来了。
融合有接纳、有修改,层次完全不一样,在物质方面是接纳,在思想方面是修改,修改的成分极大,进来的东西我修改它,进来的人我也修改他。另一方面,凡是由文化体系外面进来的,不管是观念还是人,都会造成很迅速、很强烈的影响,比从底下翻上来要快。从底下翻上来要蓄积一大堆能量,才会闹个大地震,有时候震完了,还是跟原来一样,中国古代每次大地震、大革命,革完了命之后,农民做皇帝,原来秩序又恢复了。但外来的力量碰上了,力量就强得多,而且会产生相当基本的改变,两条支流合成一条大河,这条大河又碰到另外一条大河,所以我的新书叫《万古江河》。江河碰在一起要修改,每一次这种修改,它的幅度之强大,深度之深刻,远比里头翻上来搞革命的力量要强大。
假如没有外来的东西,它会再循环,成长、成形、僵化、搞革命,搞革命之后可能是两败俱伤,不搞革命就衰微,这是封闭系统的演变。中国基本上是个相当长期的封闭系统,其间不是没有外来的刺激,第一,中国国土很大,每一次区域性的整合就是个冲击,汉朝以后还常常有小区域性的冲击,西南的扩充、东北的扩充、北方的扩充,都是这个冲击,中国真正受到外来影响最大的是佛教,而物质生活碰到外来的大影响是北方的生活,生活资源上碰到外来大影响是南方资源的进人。今天全国上下都吃米,已经不是北边面南边米了,今天的中国是全国吃米,也全国吃面,但是我年轻时,北面南米,还是有显著的分别。
近一百五十年来,几种冲突让我们碰得头昏眼花,但是现在我看中国田野考古时,每次都会在最荒僻的地方发现中国古老的东西,杀都杀不掉,砍都砍不光。现在中国大陆这些40来岁的中年人,活力比我们强,我们40来岁时没有那么强大的活力啊!60岁以上的吃过苦头,他们认为能活到今天已经不容易了,要过点好日子,所以没有动机,不问了,但40岁左右的很认真在问。因为他们饥渴,压制太久所以反弹很强,而我们一直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一点点一点点地压,压到大家心服囗服,没有反弹的意愿。
这些大陆的年轻学者找安身立命之道,而我们找安家、过日子之道,过个舒舒服服的日子所以每个人都想升等,没有人敢冒险不升等。我看到他们,感觉很像我年轻的时候,我年轻时从来不想工作的事情,然而工作也没缺过,也从来没要求升等,我还常常要求迟一点升等。
假如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能找到一条路,这四分之一就可以影响到全世界。而这四分之一是我可以管得着的,因为我的语言通,我的思想通,可以影响,在美国我没有这样拿我自己想的东西来用,因为那里专业的架构太严格了。
本文摘选自《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倬云先生一生回顾》,许倬云/口述,陈永发等访问、记录,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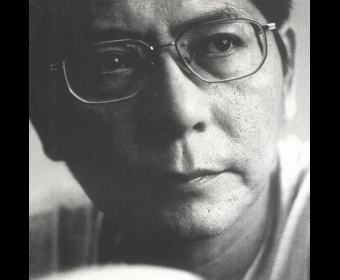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