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是否会生病?
文/弗洛姆

一个社会整个地在精神上不够健全的说法暗含着一个有争议的假设,这个假设与当今大多数社会学家所持的社会相对主义(sociological relativism)立场对立。这些社会学家认为,任何一个社会,只要它能运转,它就是正常的,而所谓病态则只能从个人不能适应他所在的社会的生活方式的角度来加以界定。
“健全社会”这一说法包含着一个与社会相对主义不同的前提。只有假设有不太健全的社会,这种说法才有意义。这种说法暗示,世上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衡量精神健康的标准,我们可以依据这些标准来判断每个社会的健康状况。这种标准人本主义(normative humanism)的立场基于几个基本前提。
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解剖学和生理学的术语来给“人”这个种属下定义。人类社会的成员有着共同的基本精神素质,共同的支配他们的精神和感情运行的规律,都以圆满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为追求的目标。诚然,我们对人的了解还很不够,迄今为止,我们还无法从心理学的角度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人”的定义。“人学”(science of man)的最终任务便是对那些可以称为“人性”的东西给出正确的描述。人们通常所说的“人性”实际上只是人性所具有的众多表现形式之一,而且常常是指那种病态的表现形式。人们根据这种错误的定义辩护说,一个特定类型的社会是人的精神结构的必然结果。
与人性概念的这一极端保守的用法相反,自由主义者从十八世纪以来一直强调人性的可塑性和环境因素的决定性影响。这种强调既真实又重要。很多社会学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一种假设:人的精神构成犹如一张白纸,其本身并没有什么天生具有的品质,社会和文化在这张白纸上盖上它们的印记。这种观点和与它对立的观点一样,既不能自圆其说,对社会进步也起着破坏作用。真正的问题是从人性的无数表现形式——包括正常的和病态的形式——中推断出整个人类共有的根本的东西;这些形式我们可以在不同的个人身上和不同的文化之中观察到。这项任务就是要进一步认识人性的内在规律以及人性发展的固有目标。
这种人性概念不同于“人性”一词的惯常用法。人在改造他周围世界的同时,也在历史的进程中改造了他自己。事实上,人创造了他自己。但是,正像他只能按照自然物质的性质来改造和改变自然界一样,他也只能按人的本性来改造和改变他自己。人在历史进程中所做的便是开发这种潜力,并按照人性的可能发展方向来改造这种潜力。如果说“生物学的”观点及社会学的”观点是把人性的两个方面相互割裂开来的话,那么,这里所提出的观点既不是“生物学的”,也不是“社会学的”,而是超越了这种二分法的。
这种观点认为,人内在的主要感情和动力是人的全部存在的产物,这些情感和动力是明确的,可知的,一部分有益于健康和幸福,另一部分则易于造成疾病和不幸。任何一种社会秩序都不会创造这些基本的感情和动力,但却决定着哪几种潜在的感情会比较普遍或者占据优势地位。当人出现在任何一种既定的文化中时,他总是人性的一种表现,不过,这种表现的具体情形却是由他所处的社会情况决定的。婴儿一生下来就具有人的一切潜力,这些潜力能够在有利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得到发展,同样地,整个人类也会在历史的进程中演变成它潜在地可能成为的样子。
标准人本主义的观点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就像其他问题一样,人的存在问题的解决办法也有正确的和错误的,令人满意的和令人不满意的。如果依照人性的特征和规律发展至成熟,他的精神就会是健康的。精神疾病的发生即由于没能实现这种发展。从这个前提出发,精神健康的标准并不在于个人能否适应某个特定的社会秩序,它应该是适用于全人类的普遍准则,能够就人的存在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关于社会成员的精神状态,人们在观念上的“共同确认”(consensual validation)非常具有欺骗性。由于大多数人共同具有某些思想或感情,这些思想和感情就必定是正当的——这种想法十分幼稚。再没有比这更错误的了。这种“共同确认”与理性和精神健康都毫不相干,我们可以说“两个人发了疯”,也可以说“上百万人发了疯”。数百万人都有同样的恶习,这并不能把恶习变成美德;数百万人都犯了同样的错误,这并不能把错误变成真理;数百万人都患有同样的精神疾病,这并不能使这些人变成健全的人。
不过,个人的精神疾病与社会的精神疾病之间有着重大的区别,这意味着我们应区分两个概念:缺陷和神经症。如果一个人无法获得自由,没有自发性,无法真正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我们又认为自由和自发性是人人都应达到的客观目标,那么,他就可能被视为有严重缺陷。如果这样一个目标没有被一个既定社会的多数成员达到,那么,我们谈论的就是社会造成的缺陷现象。
一个人和其他许多人共有某种缺陷,但事实上,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缺陷,没有感到自己与人不同或被人抛弃,因此并未感到自身安全受到了威胁。
他知道,他的生活可能不会那么丰富,他也会失去真正的幸福感,但他与全人类协调一致,由此而来的安全感会使他的所有损失得到补偿。事实上,他的这种缺陷也许会被他所处的文化奉为美德,并因而增加他的成就感。
加尔文教义在人们心中所激发的罪恶和焦虑感就是一个实例。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一个人深感自己软弱无力,毫无价值,不断地怀疑自己是得到了拯救还是被判处接受永恒的惩罚;如果他几乎无法拥有真正的欢乐——那么,这个人就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但是,这一缺陷是文化造成的,在这种文化中,它被看做是特别有价值的,这个人因此免于患上神经症。可是,如果换成另一种文化,同样的缺陷就会给他带来孤独,使他深感精神不健全,他会因此患上神经症。
斯宾诺莎非常明白地说明了这种社会造成的缺陷。他说:“很多人一直受到同一种东西的影响。当一个东西强烈地影响着他的感官之时,即使这东西根本就不存在,他也相信它在那儿。要是这种情况发生在他清醒之时,人们就会说他疯了。……但是,如果贪婪的人只想到钱财,有野心的人只想到名位,人们并不会认为他疯了,只是觉得讨厌,看不起他。但是事实上,贪婪、野心等等都是疯狂的表现形式,虽然人们并不把这些看做 ‘病症’。”
这段话是几百年前写下的,至今仍然适用。但是,由于文化的作用,现在许多人已不再讨厌和蔑视这些缺陷。如今我们遇到的是这样的人:行动和感觉如同机器人一般,从未有过真正属于自己的经验,完全把自己当成他认为自己应该是的那个人。他用做作的微笑代替了真正的笑声,用无聊的饶舌代替了坦诚无隐的交谈,用迟钝的失望取代了真正的悲坳。
对于这种人,我们可以用两句话来作评论。第一,他在自发性与个性方面存在着缺陷,这也许是无可救药的了。同时,我们可以说,他与处于同等地位的数百万其他人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文化为大多数人提供了行为模式,使他们能够既带着缺陷生活又不会患病。似乎每一种文化都提供了应对神经症症状突然发作的方法,而这些病症正来自于文化造成的缺陷。
假设在我们西方文化中,电影、广播、电视、体育赛事及报纸。停止活动四个星期,在这几条主要的逃避通道关闭之后,人们不得不重新依靠自身的力量,这时情况会怎么样呢?
我坚信,即使在这样短的时间之内,也会有数以千计精神崩溃的事件发生,更多的人将陷入强烈的焦虑状态,这跟那种被临床诊断为“神经症”的情形没有两样。(我曾经以大学各年级的学生为对象做过这样的实验:我让他们想象,在三天之内完全与外界隔绝,独自待在房间里,没有收音机也没有能帮他逃避现实的小说,只有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正常的食物以及其他生活设施,然后,我要他们设想他们对这种体验会作出什么反应。
大约百分之九十的学生说,他们会感到极度痛苦,或者觉得特别恼火,只有靠做一些杂事或者睡大觉来消磨时间,期待这三天赶快过去。只有极少数人表示,他们会感到十分自在,很享受这段独处的时光。)如果停止注射缓和社会所造成的缺陷的麻醉剂,病症就会明显地表现出来。
对于小部分人来说,这种文化提供的逃避模式并没有什么作用。这部分人的个人缺陷比一般人要严重些,因此,文化提供的补救之策不足以防止明显病症的发作(我们可以举一个恰当的例子,比如说,有这么一个人,他活着的目的便是谋取权势和名誉。虽说这个目的本身就是病态的,但是,一个人运用自己的力量去实际达到他的目的与一个人沉浸在自己幼稚的幻想中坐等奇迹发生是不同的;后者的病态更加严重,他越来越感到自己无能,最终陷入了徒劳和痛苦的感觉中)。
还有另一类人,他们的性格构成以及由此而来的内心冲突不同于大多数人,因此,对他的多数同胞有效的良药,对他也不起什么作用。在这类人中我们有时会遇到这样的人,与大多数人相比,他们具有更完满的人格,对事情更加敏感,因此,他们无法接受文化麻醉剂,但同时,他们也无力“对抗潮流”,从而健康地生活下去。
以上那些关于神经症和社会型缺陷的区别的讨论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无论社会造成的缺陷有多大,只要社会能提供防止神经症明显症状发作的药物,一切都会好起来,社会也会继续正常地运行。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情况并不是这样。
的确,与动物相比,人显示出一种几乎可以说是无限的可塑性:人几乎可以吃任何东西,可以生活在任何气候条件下,并调整自己以适应这种气候。同样,人也几乎可以忍受任何精神条件,并在这种条件下继续生活下去。他可以自由地生活,也可以在奴役下苟延残喘。他可以过豪华奢侈的生活,也可以生活在半饥饿的状态中。
他可以当一名战士,也可以与人和平相处,可以做剥削者、强盗,也可以与人合作,相互关爱。世上几乎没有什么精神状态是人在其中不能生存的,没有什么事是人所不能放弃的,没有什么事是人不可以为之出卖自己的。所有这些考虑似乎可以证实这样的假说:根本没有人的通性这回事,这也就意味着,事实上,除生理学和解剖学上的意义外,根本就不存在“人”这个种属。
人性的要求和社会的要求会相互冲突,因而整个社会是会生病的。这一假设在弗洛伊德那里是很清楚的,在他的著作《文明及其不满》中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应用。
弗洛伊德的看法有这样一些前提:整个人类有着共同的人性,它贯穿一切文化和各个历史阶段,内在地具有某些明确的需要和追求。他认为,文化与文明的发展会愈来愈和人的需要对立,由此他给出了“社会神经症”(social neurosis)的概念。
他写道:如果文明的进化与个人的发展如此类似,如果我们把同样的方法运用到两者之中,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诊断说,许多文明体系或者文明的各个时期——甚至整个人类——都在文明趋势的压力下患上了‘神经症’?我们可以就剖析这类神经症提出一些治疗建议,这可能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我并不觉得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来诊断文明社会是异想天开的事,或者注定毫无结果。不过我们应当非常小心,不要忘记,我们毕竟只是在类推。
不论是针对人还是针对观念,把他们(它们)从他们(它们)发生、长成的地方硬拔出来都是危险之举。此外,对集体神经症(collective neuroses)的诊断还会遇到特殊的困难。诊断一个人是否患了神经症,我们可以将病人同他周围的环境(假定这环境是‘正常的’)作一对照,以此作为我们的诊断的出发点。
对于患了同样病症的社会,我们却没有可以参照的背景,我们不得不通过另外的途径来获得这种背景。不过,就把我们的知识应用于治疗而言,即使对社会神经症作出了最透彻的分析,那又有什么用呢?因为没有人有能力迫使社会接受治疗。尽管有这些困难,我们仍可以预料,总有一天,有人会敢于从事研究文明社会病理的工作.。”
这本书意在冒险进行这项研究工作。它的基础是这样一种观点:一个健全的社会是一个符合人的需要的社会——这里所说的需要并不一定就是人认为他所需要的,因为即使是最病态的目的,也可能被人在主观上认为是最需要的,这里所说的是人类客观的需要,我们可以通过对人的研究明确这些需要。我们的第一项任务是确定什么是人性,什么是根源于人性的需要,进而我们必须考察社会在人类进化中的作用,研究社会对人类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人性与社会之间不时发生的冲突和这些冲突给社会,尤其是现代社会,带来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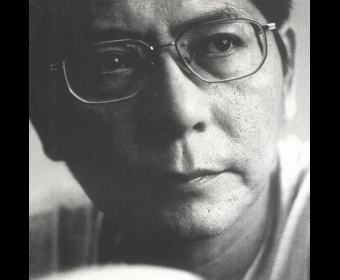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