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地》/白鹤林

白鹤林,本名唐瑞兵,1973年生于四川蓬溪,现居四川绵阳。著有诗集《车行途中》、评论集《天下好诗:新诗一百首赏析》等多部。曾获四川十大青年诗人、全国鲁藜诗歌奖诗集类一等奖、骆宾王青年文艺奖等多种奖项。
《飞地》:你平时是一个具有幽默感的人吗?(如果有的话)是否会经常将这种幽默感带入写作中?也请谈谈如何处理诗中的幽默性成分?
白鹤林: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具有幽默感的人。在写作中,我更多是把幽默感理解为一种调侃。就像生活中没有调侃就会索然无味,幽默(或者说戏剧性)往往是文学作品最迷人的部分,甚至是它的精神气质。在不少的诗歌中,我都在调侃,调侃我们的命运、世界的荒诞和人的无可奈何。但这必须视情况而定,须恰当处理。比如要视主题而定,视一首诗的具体语境而定。
《飞地》:请举例说说你认为的“好玩”的诗,并谈谈诗的游戏性。
白鹤林:“好玩”的诗很多。在我的阅读中,柏桦、萧开愚、祁国、哑石、蒋浩、张尔、刘川等很多诗人都有“好玩”的诗。我曾经在我新浪博客的“天下好诗”(诗歌赏析)中,分享过柏桦的短诗《为人》,其中有这样的诗句:“人,我在想(很迷惘):/怎样保持喜悦的分寸/——这是一个问题”。我认为这里的“喜悦”,就是指诗的游戏性。在人类的童年,“游戏”是我们的天性,但天性却是一个越成长越泯灭的东西,因为生活中大人们的“吊儿郎当”是被认为不正经的。但文学不是这样,诗歌不是这样。游戏性很多时候是诗歌的解药,可以让诗意真正被激活而妙不可言。
《飞地》:你如何看待“戏谑”或“反讽”之于诗的意义?
白鹤林: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写得太一本正经了,写诗变成了一件苦差事,诗意的丰富性不够。同时因为很多诗都太像诗了,作为读者的我们的阅读激情也在大幅度丧失。我想,“戏谑”或“反讽”之于诗的意义,就在于可以同时拯救了作者和读者,可以同时增强创作和阅读的趣味与热情。
《飞地》:在诗中,戏谑体现为“轻”质的时候,似乎偏向于揶揄和取悦;戏谑体验为“重”质的时候,则更常偏向于讽刺与批评。在这两者中的哪一种情况下你会更倾向于使用戏谑的方式来书写?
白鹤林:更倾向于后者,即“重”质:讽刺与批评。这是性格或者经历决定了的吧。
《飞地》:为了达致某种表达的愉悦,你倾向于在诗中进行精心的安排,还是自由放纵的书写?在你看来,这两种方式是否有什么不同?
白鹤林:我倾向于在诗中进行精心的安排。因为我认为诗歌的形式(技巧)跟内容(主题)一样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精心的安排,其实就是对情感和思想进行巧妙而有效的组织,有时候这就是一种节制。自由放纵的书写也能写出好诗,但几乎凭借的是运气,要想成为诗歌大家(或者至少是越写越好的诗人)是很难的。换个角度说,自由放纵应该是在我们动笔之前——即发挥我们的想象力的时候,而真正到了“表达”即书写环节时,诗人必须要擅于管理自己的情感和思想,才能完成一首好诗。
《飞地》:将诗视为对语言和情感加以节制的艺术,并着重智性而非抒情性因素,几乎是现代以来诗人和批评家的普遍观念。在这种经典论述的笼罩下,强调语言的狂欢和叙述的腾挪,几乎构成了一种新的偏离。请结合自己的创作,谈谈这个话题。
白鹤林:在我看来这里面并不矛盾,关键是怎么处理。也就是说,诗人自己的原创力很重要。比如在我自己的诗歌中,既有很理性的作品,也有很放松的作品,要解决两者之间的问题,核心的问题还是我们的文学观念必须解放。也就是说,我们至少要在理论上意识到:没有一个什么必须怎么写或不能怎么写的原则。
《飞地》:作为一种自身即带有自由基因的文体,现代诗似乎同时为作者和读者提供了穿梭于不同时空之间而不必考虑“设定”的可能性。如果你有多文体的写作经验,请谈谈这种在诗中的穿梭和腾挪跟在其他文体中有何不同;如果没有其他文体的写作经验,那么就聊聊你在诗中处理时空的方式吧。
白鹤林:我想,这里的“其他文体”应该指的是小说、戏剧和散文吧,这些我几乎不涉及,除了偶尔写随笔。在诗歌中,处理时空应该说是很多见的。尤其是现代诗,新奇、断裂和自由联想等是重要特征,处理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的经验不是新鲜事。比如我在《梦(或吃桔子的人)》《电影和一条狗的生平》《市郊之歌》《献给赛·西的十四行》等作品中,都有处理时间与空间、梦幻与现实、个人经验与历史经验的案例。而处理方式就像是回忆梦境,类似于电影的蒙太奇。
《飞地》:在日常生活和阅读经验中,你是否发现或开拓出一些可能激发腾挪意识的途径?并有效转化于写作之中?
白鹤林:没有专门思考和梳理过。在这方面,我可能还处于一种不自觉的写作状态吧。
《飞地》:经由密集修辞术或对日常场景的戏剧化书写所组织起来的诗,和在日常性中窥见具有戏谑效果的瞬间并以白描或口语的方式书写的诗,(这里面似乎也暗含着当代诗的两条不同的路径),于读于写,你倾向于哪种?
白鹤林:在写作上,我认为自己倾向于前者吧。但在阅读上,两者都关注。
《飞地》:新诗百年,通过数代作者的劳作和赋魅,已逐渐构建起独属于自身的“神话”,并俨然塑造出了某种具有公共性、严肃性和翻译腔的诗的“正统形象”。这种情况似乎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有所改变,而改变的方式则多种多样。请结合你的写作历程和阅读经验,谈谈三十年来当代汉语诗人在这方面所作出的改变。
白鹤林:我的写作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的,至今二十余年,所以谈近二十年来的当代汉语诗歌,可能更有值得信赖的感受和体会。而关于这二十年,可以直接引用我在《迷惘与启蒙——我的九十年代诗歌“年表”》(刊载于发星主编《边缘的自由精神群像——诗歌回忆录(1949-1999)》(天鹰图书出版社/2015年5月第一版))一文中的一段文字,来表达我的看法:“九十年代实则是一个重新出发的年代,是我们更年轻一代的思想启蒙年代。而九十年代也是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个重要时期,是诗歌潮流产生巨大变化的时期,是叙事性、日常主义与个人化写作等成为重要诗学特征的时期。至少,它在一定程度上让汉语诗歌告别了八十年代及更早以前整体上的“群体抒情”和“宏大叙事”,而走向了更为开阔的、多元化的境地。当然,也因此涌现了一些重要的、值得研究的诗人与作品。”简而言之,因为产生的诗歌流派或群体众多,贡献的优异诗人和文本众多,这个时期可能是汉语诗歌真正意义上的、迟到的“白银时代”。
(此文刊载于《飞地》2015第四辑·总第十三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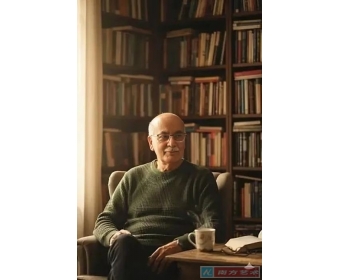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