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萧耳(作家,媒体人,高级记者) 黄孝阳(写作者,出版工作者)

萧耳:《人间值得》出版后颇多好评,获得19年度深圳读书节十大文学好书,入围多种榜单。我很好奇,为什么你想为“恶人”写一部“自传”?你给“好人”写过自传吗?一个叫张三的人渣的野蛮生长史,是你这么多年来对社会、对人性观察的浓缩吗?
黄孝阳:一个老评论家看到这本书后有点儿激动,从上海到南京专门与我谈了下,说他看重这本书,根本是:它塑造出一个当代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恶棍形象。
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后记里有部分相对哲学层面的思考。书出版后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为我的兄长们立传》,给予世俗解释:
“他们不是乡村秩序下的蛋,也不是都市文明的孩子,他们体内的基因片断是在一个被现代性浪潮重组的过程中,与中国改开四十年紧密勾连,有诸多崩毁残存,亦有突变进化。他们人至中年,现已多半在事实上成为县域政治经济文化各生态系统内的话事人,是权力的毛细血管,亦是各种潜规则与隐秘秩序的制订者,谙熟不同的话语体系,自如切换,能在一个时辰内分别扮演畜类与人类。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尚未成为当代中国人精神的主体部分,在实际日常层面开始影响大多数百姓的生活。中国有二千多个县城,这是一个如同风暴的广袤现实,是‘真实的真实’。而他们中的一小撮人,比如张三,试图从历史与现实情境等维度,以及生命意志的高度,反思“人”这种奇妙存在,讲述唯独属于他们的故事,或者说传奇,故而《人间值得》。”
一个写作者的首要品质是诚实。因为这个诚实,我们才可能理解这颗正在变得越来越小的蓝色星球,理解存在之诗,人在虚无与万物间等等命题。保持诚实是一件困难的事,尤其是在今天。路两边有太多的深渊诱惑与奇花异草。我只能说是努力保持我对自身的诚实,日省吾身,尽量忠诚于那团让自己成为写作者的风暴,忠于所见所思,不太考虑外部发表与出版的事。《人间值得》的男主张三的野蛮生长史,是我曾经历过的,目睹过的,他是对这数十年时代变迁的某种概括,亦是我灵魂深处某个人格在深夜里的咆哮。
至于有无给“好人”写过自传,那必须是写过,否则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文学青年了。比如十几年前的《遗失在光阴之外》等,但多半还是一个文学青年的脆弱敏感与自我抒情,还缺乏对时代的一个俯瞰性的思考,属于“内心肿胀”不得不写,不得不如此写。
其实,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这是极复杂的。这个世上存在着太多二律背反的悖论,比如著名的电车悖论。2013年的洛杉矶,这个悖论成为现实。一个女士面对失控的电车做出了决定。她救了五个人,但另外一个无辜的人因这个决定死去。她扮演了“上帝”,因此被告上法庭。对于死者来说,她是凶手;对于另外五个人来说,她是恩人。凶手与救人者这两个矛盾,奇妙地交织为一体。当然,我们讨论的好坏基本还是一个世俗的主流价值观体系,尽管这种狭义的好与坏在这个体系里仍然并不互相兼容,比如一个好父亲同时又是一个罪犯。哪怕是从这个体系来说,张三的坏也是有底线的,一个他不惜用生命去捍卫的底线。而这个底线要高于我们经常熟视无睹的日常生活中的“平庸之恶。只是我们习惯了这种恶,对此无动于衷。
萧耳:你说要写一个“作恶,并且有能力对恶进行思辨”的人,你觉得现实生活中,符合这两个条件的人多吗?你印象中的文学作品中,有哪些人物是符合你这两个条件的?
黄孝阳:现实生活中作恶的人多,有能力思辨的,寥落晨星。至于文学作品中,比如出没于歌德《浮士德》中的魔鬼靡菲斯特,比如卡夫卡《在流放地》的那个军官——那个执刑过程中自愿替换掉囚徒,被机器杀死的人。“我知道我的罪行了,你看,我的生命戛然而止。”等等。常人普世的价值观恒足珍贵,但它之所以得以形成,是奠基于那些斑斑血泪,以及对血泪的思辨深度(这需要叙事)。否则我们还在一个原始童稚的社会结构里。
广义来说,文学作品中的坏蛋都是作恶者。如果这个坏蛋弃暗投明了,或有片刻反省,良心发现,那他多少还是“思”了一下,真正有能力思辩的,并且付诸于实践的,不多。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会有“它塑造出一个当代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恶棍形象”这句评价。

黄孝阳《人间值得》
2019年深圳读书节年度十大文学好书
腾讯探照灯书评人图书奖2019年度好书榜(年度长篇小说10种)
华文好书2019年11月好书榜
百道网2019年11月好书榜
中国出版传媒报2019年10月好书榜
萧耳:作为70后作家,你以小说出道很多年,一直被称为“实力派作家”,印象中你小说的路子很宽,好像什么类型都想尝试一下,甚至科幻类的也写过,至今为止,你觉得自己最能驾驭什么类型的小说?
黄孝阳:我不在乎外界对我的称呼。前几天看到王春林老师写的一篇二万字的评论,就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文学术语“批判现实主义”,专门发明了一个新词语,“批判现代主义”来谈论这本《人间值得》。
我尊重评论家的阐释。但就我个人而言,我的写作只有一个核心:写人,写我所理解的人,写其所以然,其之所以然。同时提供时代细节,以及支撑起这个时代的结构体。
我无所谓类型。对于出版商来说,那是销售技术。对于读者来说,那是超市货架的分区。对于评论家来说,那是文学谱系及位置。
这些都很重要。对我的写作来说不重要。
写作是我一个人的事,是某种极端性的输出,是无穷尽的时空中那只敲打出莎士比亚巨著的猴子附体,是通过对“人的叙事”,把不可逆的时间与那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变为一个大地之上的奇异建筑,建造有时,塌垮有时。我们肉身所经历的那些可感可知的时刻,因为这种叙事过程,获得了他真正的主体性,并化身千万,不再匮乏;我们也可能真正拥有眼前这杯咖啡、这杯茶、这次有关于爱的神秘邂逅。
重要的是人,是中国人,是今天的中国人。
文学报的傅小平问过我一个问题。
当我们谈到马尔克斯,包括其他的拉美作家,自然会想到拉丁美洲大陆。中国作家某种意义上,会不会因为欠缺亚洲意识或人类意识,乃至相对狭窄的中国意识,以致难以以一个整体的形象融入世界,从而影响了“文学中国”的建构?
我回答过这个问题,展开来会是一个长篇大论。这里说下结论,一言以蔽之:
我想有这种人类意识。
有了这个意识后,再做这个中国叙事。这个意识的核当由一个全球性的当下视野,对人之存在本身的反复提问所构。
人是奇迹,是造物主对自身的复制与迷恋,所以说“人类大脑结构和宇宙结构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又或者说:人类就是宇宙的大脑。在这个恢宏框架下,我们开始讨论数千年来的哲学家对人分析与定义,人的内核与边界,人的历史何以延续,何以如此叙述,人是否配享信仰,值得被给予关于天堂的允诺,又是否应该拥有科技之力,对此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讨论人还可能拥有什么样的未来图景,而构建未来的关键节点与变量蕴藏何处,又如何找到激发节点引擎的能量。等等。
我们来到了一个新现实,我把它称之为知识社会。中国与美国是新现实里最重要的两极。要阐释人,阐释这个新现实里由传统与现代性共同塑造的人,对中国人的叙事是最好的维度之一。我很高兴自己是中国人,有幸生于这个汹涌澎湃的时代。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大概还在田间锄草吧。我对这个时代抱有深情。我想以我的方式来求解眼前这个世界,这个极其复杂,且日益复杂的世界。
今天的中国人是迥异于四十年前的,更别说四百年前的,这是两个物种。这里有传承,也有“突变”。我想把构建出这个新现实的深层原因,用“人”这个最富有主体性与创造性的词语,叙事出来。我想做这个。
类型这件事,是学者与读者考虑的事。我不大关心。当然,我也很清楚讨论类型也是在一个“文学之用”的大框架内。关于文学之用,我也讲过太多。包括许多作者在内,目前基本是谈个人感受,比如在这个由科技与资本建构的世界,发现美与激情,重新审视爱与恨,构建一个人的乌托邦,对抗滞重与虚无,感受痛苦的各层次,自我拯救等。少有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比如,文学不仅是一种专门的知识体系,它还是各种知识体系的叙事策略。知识体系与知识体系之间有融合,更多的时候是相互为敌,尤其是在思想层面。哪种知识体系真正掌握了文学的力量,就可能对世界的未来起一个主导性的支配作用。解释趋势的人,必定影响趋势。我们讲的中国梦,美国梦,这两个词及其衍生文本就是文学叙事。
我尊重类型。只是自身不大考虑这种自我命名与传播策略。
萧耳:有没有为了读者考虑而妥协自己的表达方式的写作?你写作时考虑读者的阅读能力吗?
黄孝阳:刚开始写作的那几年有,但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不是说你愿意下海就能当名妓的。后来,就不考虑了。
这基于两个逻辑。一是,当代人的特征之一,即既是读者,也是作者。我无意扮演那个云层之上的启蒙角色,我不是蜿蜒闪电;也不愿意跪舔金主,那是对我体内那条龙的蔑视。大家平等。我写我所理解的这个世界,你愿意读,是我的荣幸;不愿意读,那是我俩这个缘分还没到,也不是我的损失。
我不考虑读者的阅读能力。别说普通读者,就是批评家等相对的专业读者也不考虑。那是他们考虑的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个理由,我还有一份工作,得养活这个肉身皮囊。
萧耳:你怎么看小说中父与子的冲突?主人公张三从小厌恶父亲身上的“恶”,始终保持着对“父亲”这个男性权威有清醒的批判,又为什么自己也走上跟父亲一样的“恶”的道路呢?那么这种批判是否是一种“伪批判”?
黄孝阳:父与子的冲突是永恒主题,我很喜欢德国漫画家埃·奥·卜劳恩创作的那部同名漫画作品。这是给予这个严酷主题的一个富有温情的微笑。
但这个笑容不是人类历史中的主线。恶不可避免,比如我们说谎言是恶,也都知道“谎言重复千遍即是真理”之类的法西斯宣传口号,知道世界上充斥着谎言,但由于信息匮乏与观念倾向,我们往往浸身其中而不自知,还以为自己是正义化身。
就拿“世界上充斥着谎言”这个句子说吧,一句陈词滥调,如风过耳,我们的注意力不会因为它有片刻停留。但有多少人能听到这风声里的故事呢,那些正在发生的悲伤与血泪呢。举个例,说下曼德拉,说下这个打破宗教、国族分歧,意识形态冲突、肤色与语言等所有障碍,让全球齐声点赞,乃至于圣人这个词语才勉强配得上他的德行与光辉的人物。
全世界给曼德拉的掌声,大概赶得上几十颗原子弹爆炸的当量。但他在走出牢门执政后短短数年内,一个有过全球第1例心脏移植手术,低犯罪率,拥有强劲的金融与制造体系,被誉为彩虹之国的准发达国家,就变成了一个罪犯横行、失业率高企,毒品与艾滋病泛滥,国内经济体系基本破产的贫穷之地。
简单说,他把南非经济命脉的诸多要素,全部,不打一点折扣的,双手奉献给了全世界,主要是联合国那五个常任理事大佬。对于这种发扬雷锋精神的利他者,谁会吝啬手中那几声廉价的掌声?潮水般响起的掌声一浪更比一浪高,就把他带到一个让人晕眩的高度。这时他就算知道了什么,也下不来了,下来就是粉身碎骨。不仅是他的死无葬身,更重要的是,他用一生所追寻的,不惜付出二十余年囚笼生涯去信仰的价值体系的崩塌粉碎,这是对他自身魂灵的清算,所以他必须这样做下去,以非凡勇气,巨大耐心,把他发誓要解放的同胞们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险境,一个更广泛的普遍不幸中。
他不知道,他追求自由没有错,但自由是有成本的,有巨大风险的,是连接着衰败与恶的深渊,应对稍有不慎就会被恶龙吞噬。他高估了自己,以为自己是杀死恶龙的勇者,但不知道深渊里的恶龙,其数量之多胜过夜穹星辰,他更不知道在杀死一头恶龙后,那顷刻间获得的荣耀不再是王冠,而转化为傲慢,他甚至不清楚,他在变成另外一头恶龙,双翼尖喙,能离开山洞,在五大洲四大洋上空飞翔。整个过程类似那个古老传说里勇士弑龙原型的升级迭代。
他过于自负,那些给过他力量的,把他导入歧途与深渊。
是对自由的渴望与不懈奋斗,让他在出狱那天赢得数十万人的夹道欢迎。
但这种渴望与不懈奋斗不包括在一个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治理能力。时代变了,不可逆,普遍而又深刻的根本变化。而他对于国家的想象还是那样原始朴素,以为“这种渴望与不懈奋斗”能帮助他打通任督双脉,在扮演好一个精神层面慈父与导师的同时,还能在世俗层面带领他的同胞们进入这个全球化的博弈时代。一个坐了几十年牢的人怎么可能理解全球化后面那个现代性浪潮及其凶险,以及对技术治理能力的高标准?又或者说,一个人山洞里待了几十年,突然你让他当老大,你说他会怎么办?当然是被人家办。
对于全世界来说,他是圣人,是圣人之上。对于他的同胞来说,他曾是解放者,也是后来不能公开讨论的不道德。
当然,我这样说未必是对的,我所知道的那个国家相关资讯也极为有限。就不说曼德拉,假设另外一个平行宇宙里有一个这样也叫“曼德拉”的人。对于这个国家而言,他曾扮演了“国父”的角色;而今这个国家想要取得进步,或者说在那个星球上还能有一个存身之地,就必须抛弃他给予的道路,这就是弑父。
弑这个字,本身就是一种恶,就像是秋杀,是“把匕首捅入腹中,还转了两把”,如果没有这种清算,“父的罪恶”就会以别的形式复活。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最近我在构思一个异托邦的小说。主角在拥有曼德拉这种遭遇后,踏上了自我反思的旅程。怎么说呢,“真理只能是在无限接近中”。但哪怕我们走了十万光年的路,我们与真理之间的距离也还是一个无限大。
人是有限的,要谦卑。人类历史是有太多种恶龙。我们渴望成为杀死恶龙者,但很难摆脱自己成为另外一条恶龙的命运。所以说原罪。基督教义里有许多精妙论述与详例。
萧耳:既然是一部以恶人为主角的“恶之花”,为什么要取名为《人间值得》?是反讽,还是寓意主人公本质上那些善良的人性之光的一面?
黄孝阳:没有这些“恶之花”,把你放在丹麦乡村那个风景如画里,剔尽外界变化,每天就是吃饭睡觉打娃看窗外,几十年,我相信你愿意;几百年你还愿意吗?北欧诸国那么高的福利,政府从摇篮到坟墓一路承包过来,可抑郁症与自杀率高企。人是很难承受生命的轻。
恶让这些“轻”成为翻滚云层里的蜿蜒闪电。它给予善边界。包含了善的种子。生命或许就是从某次闪电击中地面一个小水洼开始的。
还有更多的问题不是善恶可以言说的,只是秩序。它的道德评价取决于你的立场与价值体系。:我们都知道那个说谎者悖论,“所有克利特人都说谎,他们中间的一个诗人这么说。”但少有人理解:克利特人为什么要说谎。因为“说谎”那是他们的善。
还记得卡尔维诺写的那个《黑羊》么,那是一个精彩的隐喻,人人是贼,他们就这样幸福地居住在一起,没有穷人与富人。那个打破了这个内部秩序的诚实人,不久饿死了。从那以后,“人们就不再谈什么偷盗或被偷盗了,而只说穷人和富人;但他们个个都还是贼。”
萧耳:围绕张三,为什么要写7个女人?少一个会怎样,真的是有7层隐喻吗?而且这7个女性几乎都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对于底层或者边缘女性,你有信心写好这类女性吗?你了解她们吗?
黄孝阳:这个在构思的时候就想了。我喜欢7这个数字。它是奇妙的,是开启万物奥秘的钥匙。“我们明明知道犯下七宗罪后所要受到的可怕惩罚,也都清楚作为七宗罪对立面存在着的那些美德书,为什么我们还要犯罪?是因为我们生来就是罪人吗?不,是因为这七宗罪不是人的错,皆有人之真性蕴藏其中,相对应的是:渴望、自信、性爱、进取、安静、好奇、力量。”对这本书来说,7是内容,也是形式。是通过对7的整理,求解出人这个奇点。少一个会怎样?也不会怎样。断臂的维纳斯可能更适宜成为美的化身。
至于这7个女性几乎都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问题,可能是我的眼睛有问题,我看到的女性,那种我觉得有生命质感的女性,基本有过这样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过程。这个问题还可以放在女权主义的大框架下讨论。女性的第二性,是被发明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在小说里创造了朱璇,这是一个新女性,由罪恶与血泊孕育而生,会是未来的神祇。其实,受难(痛苦)是人的本质。作为一个当代人,要对所谓的幸福保持警惕。
我当然能写好你眼里的这些“底层女性”,我了解这个金字塔结构的底层,我是这个底层的一部分,是它们的旁枝逸出。这种了解是体内某部分DNA。
萧耳:还有一个跟女性有关的问题,书中主要女性人物,似乎都经历特别不寻常,又有欢场经历,又有自毁倾向,又都是“性”符号,和人们所认知的生活中的真实女性相距甚远,这样的安排,是否过于戏剧性?
黄孝阳:随便在街头拉住一个普通人,他的生活中肯定是有“特别不寻常处”,关键是这种不寻常处是否能有机会得到书写,以及怎样的一个书写。
至于为什么是“欢场+自毁”,面对个巨大的文学命题,我得写上几十万字。
福克纳说过一句令人记忆深刻的话,作家最好的住所就是妓院。翻开文学史,有几个作家没有写过妓女呢?为什么他们会把笔墨集中在此?简单说,妓女满足各种条件,是人的极端性与戏剧性的节点,是风暴降临,把那些日常里的伪真实席卷而去,让我们重新有机会目睹田野与河流;是倾城之美,亦凋零有时,是命运在一个肉眼可察觉的“转眼即逝”中的吟唱;是钱的逻辑,这个支配着世界大部分秩序的肉体化身。等等。
人们生活中的真实女性又有哪几个没有“欢场时刻”?取悦N个男人是需要这个时刻的,取悦一个男人同样如此,哪怕冠以浪漫与爱情之名。关键在于阐释。大家也都知道莫泊桑的那篇《羊脂球》,在一个普世伦理的体系里,妓女的道德水准不低于贵妇与官员。这并不是虚构,所以人们说“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婚姻是卖淫。是合法的,长期的卖淫。
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真实女性”。最近美剧《西部世界》第三季上映。男主陷入死地仍不吐露女主的秘密。女主问他为什么。吐露才是他这个阶层出身的人应该做的事。男主的回答是,“你是我这些年见到的唯一真实事物。”
我们也都知道尼采说的那个词:群畜。
我把这个词分解了一下:社畜与家畜。
我们在世俗语境里所谓的真实,其本质与“社畜与家畜”有多大区别呢。唯一的真实,即是我们对自我的探索与认知啊,这个永不停止的孤独旅程。
关于真实,我有太多话想说了。如梗在喉。
从真这个字开始说起吧。真的对乏面不是假,而是匮乏。把真的对立面看作假,这是通俗史与大多数人的误区。
一个被垃圾食物(观念)填饱了的男人发现自己很难有能力去品尝露珠与清晨第一缕光线。他是饱腹之徒,亦是匮乏之人。他没有这个能力保持饥饿感,身体里塞满各种信息碎片与各种欲望胶囊。
这种饥饿感,决定着人,决定着人在摆脱一个纯粹自然状态后的存在形式,决定着人在挣脱宗教枷锁后的(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可能行动,决定着人是否有有资格以这个广袤宇宙为背景开启他们的星辰大海,是人类未来的生长点。新的思想新的语言新的连接方式与结构,乃至于新的历史,皆由这种饥饿感分娩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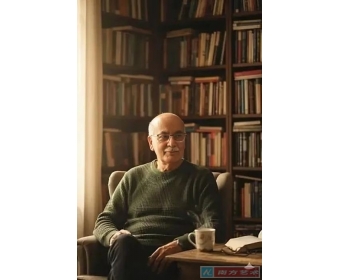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