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离:莎士比亚说过:世界之大,比你能想象到的更多。我们总能够想起神话时代对自然界神秘力量的信奉,或者是航海时代时充满了对新世界的冒险的幻想,那都表明了想象力对于我们所具有的重要性。诗歌同样是其中重要的一员,从《荷马史诗》到李杜诗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诗歌勾画了我们这个世界所到达的边界。但是不幸的是我们的世界正变得越来越狭隘,这是个想象力缺乏的时代,铺天盖地的财经新闻和雷同乏味的娱乐积节目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点,它的原因也许在于我们对世界的基本态度中,以正确性取代了真实性,我们把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的责任完全地推给了科学家,同时,其他人的理解即使不被认为是无稽之谈,也起码是无足轻重的,正确的态度就是我们对待日常生活采取的态度,无论是神奇还是敬畏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诗歌所处的边缘化位置由此也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一个诗人,你写作的动力来自哪里?诗歌可以为你带来什么不同的东西吗?
泉子:莎翁说出了一种悖论,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辽阔。而在同时,又正是这种局限性成为了激发我们认识世界、探索真理的热情的那最初原动力。这同样是诗歌那最初的原动力。诗歌,包括所有的艺术都是探求真理的一种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艺术与科学是殊途同归的。如果我们把真理比作一颗星辰,那么诗歌(艺术)则是它的光,是我们逆着光的方向探索星辰的过程。星辰真实地存在着,但我们永远无法抵达。过去十年的写作使我离真理接近了一厘米。是的,我愿意用剩余的时间去换取另一个一厘米。如果真的能够如愿,那么我一定是受到祝福的那个人。而这样的一厘米可能重过一个时代,甚至可以说,多少世代的徒劳将在这微小的尺度中得到全部的补偿。
江离:对你的诗歌来说,2001年似乎是一个分界线,在这之前你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雨夜的写作》,在那些以短诗为主的诗集中,风格清新,隽永,比如《多么孤独啊》。从2001之后到2004年,在第二本诗集中,有了很大的变化,完全超出了自我为中心的经验,在这些作品中时间构成了真正的考验,无论是死亡、消逝、虚无还是永恒,你就像西西弗斯那样在不断的推动着时间这块大石,诗歌变得更加开阔和有力,另外就是其中个人信仰的部分变得很重要了。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一种变化?
泉子:我们笔下的河流的任何一次拐弯都对应于我们对生活的新的认知。出版诗集对我来说,是想和自己的某个阶段作一个了结,并以此为新的起点。我的两个诗歌集的出版完成了两次告别。《雨夜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些练习之作。这些练习使我懂得了诗歌只能从这个最微小的我出发,从自身出发,再也没有别的起点了。如果说我在《雨夜的写作》中找到了诗歌的起点,那么那条追随内心流淌的河床在《一只鸟分享的时辰》中才得以呈现。对我来说,刚刚过去的2005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在诗歌中完成了一次拓宽的努力,诗歌改变了往日的幽深,这不是对深度的放弃,就像一条向下生长的路,洞穴的幽微沿着道路在加深,但随着洞穴的拓宽,深度依然得以保持,而幽暗已经不再了。而这种变化是与我对这个我们置身的世界最新的认识相对应的。它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一个由时间和空间构筑而成的容器。所有的事物不会也没有消失,任何一个微小的事件都会在这个坐标系里,在这个容器中找到一个独立而永恒的点。时间如一道光柱,一些事物在呈现,更多的被隐藏。就像我写下米沃什(1911--2004)时,米沃什并没有消失,他依然活着,他依然活在1911—2004年这狭长的地带中。他与我们的故乡、与我们身后的这个岛屿一样真实而确凿。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勇气与激情,只要我们的一个转身,我们便能与它们一一重逢。我们将与米沃什重逢在1911—2004年之间任何一个可能的时辰。
江离: 回忆就是去重新发现,以一种不在场的方式重新经验所经验过的一切,你的作品中写道不少童年时代的事情,那里它们不再是平凡的瞬间,而充满了神奇和光辉,比如《掷骰子的母亲》。巴什拉说在童年之中拥有以后生活的所有原动力,在那里我们生活的核心已经构成了,那么对你而言,童年意味着什么?它对你的生活和诗歌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泉子: 童年就像是一个核或者是一枚种子。它储藏着我们一生的秘密。我感激于命运与我的父母带给我的一个近乎完美的童年。那是置身于中国乡村背景中的,作为辽阔与自由的代名词。我想我今天的写作正是我重回人生这最初阶段的努力。我还要感谢我的亡兄,这个以他的疾病与死亡换得我的生命的人,他与我一同见证与描绘了另一个童年。他并没有死去,他依然在我的身体中,或者说,我们在同一个身体中延续着那共同的生命。这另一个童年依然是命运的馈赠,正是在对疾病与死亡的逼视中,它为我揭开了那通往生命本质的道路。
江离:你的作品数量颇丰,并且持续稳定,你平时在什么时候写作诗歌,或者是在高兴的时候还是不愉快的时候?
泉子:我只有在“出神”的状态中才能写作。这是一种极度的宁静。或者说当所有的神思都汇聚于一个点,以致于我们以为这是无依无凭、无羁无绊的漂浮之物。而在极度的宁静与极度的癫狂(这一定是一种狂欢的状态)之间一定形成了一个交合的地带。这里将作为艺术最为肥沃的土壤。
事实上,我的许多诗歌都完成于西湖南线一个湖畔的小茶馆,茶馆的主体建在湖面之上,我几乎都在这里度过了我的每一个周末。这是一些《神示的午后》,它给予我一个完全不同的西湖,并最终使我懂得“向一面湖水学习辽阔是必要的”。
江离:国内外诗人以及其他作家之中,你受到哪些人的影响?你说过,写作一首诗歌的时候应当向经典看齐,那是否意味着要将古代的那些大诗人和当代优秀诗人构成了当代每个诗人对自己写作的参考坐标?
泉子:我曾受惠欲于无数的诗人,我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庄子、李白、杜甫、苏轼、博尔赫斯、艾米莉·狄金森、保罗·策兰、阿米亥、曼德尔斯塔姆、帕斯、米沃什、叶芝……还有许多无名的诗人,他们中一些人在我今天的书写中已经不再重要了,但他们依然是我感恩的部分。
我在写作一首诗歌时更愿意追随它自身的流淌。但当一首诗歌完成,在我们重新审视时,它就必须置身在这样的坐标系中。因为我们的诗歌也将接受末日的审判。在那里,所有的诗歌都是平等的,审判的尺度也是统一的。这末日审判,不会因博尔赫斯、米沃什、杜甫的文本而将标准提高,也不会因为一个普通的写作者而将标准降低。就像博而赫斯表述的,在时间的深处,“所有的诗歌都是匿名的。”
江离:我是最早读到你关于诗歌的随笔《诗之思》的人,这是些充满思想闪光的作品,就如题目所表明的,它们确实构成了诗和思的完美的结合,这在年轻一代的诗人当中是十分罕见的。诗人被柏拉图从认识世界的任务中驱逐出去,因为他认为,诗歌仅仅是对世界的再模仿,事实上思考并非仅仅是哲学家的问题,而且面对他所处的时代恰恰构成了极大的挑战,比如面对伊拉克战争、面对海啸、以及不断的矿难,那么用菏尔德林的话来说“诗人何为”呢?他是否应该对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
泉子:《诗之思》的写作直到完成了近200个章节后,我才意识到它的重要性,特别是它对我个人写作的重要性。它使许多纠缠的事物变得清晰,并在它自身的延伸中把我引向了那从未抵达的地方。
柏拉图对诗人的理解只是他的一家之言,显然他并没有对照与他几乎同一个时代的一位来自东方的旷古奇才—庄子的文本,以及他之后的李白、苏轼、莎士比亚、米沃什、叶芝们的文本来发言。柏拉图显然没有认识到诗歌作为我们认识感知世界的一种方式,诗人同样肩负着探索真理的使命。
我是在这两年才渐渐理解歌德提出的诗歌“使世界重回一个整体”的命题。伊拉克战争、海啸以及不断的矿难都作为这个分崩离析的世界的症状,而你在第一个问题中多少描述出了我们这个充满焦虑的时代的症结所在。科学与艺术是文明得以前进的一对翅膀,它们之间任何一侧的偏废都会埋下致命的种子。我们的时代显然对科学是过于倚重了,我们甚至以为通过科学可以凌驾于万物之上。我们不是在寻求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之道,与自我的和谐,而是在寻求征服自然的道路。如果我们还不警醒,那么巴别塔的警示与惩罚迟早有一天会再一次落到我们的头上。这让我联想到鲧与大禹这对父子的不同的治水方式。
江离:请谈谈想象力、节制和诗歌自由的关系。
泉子:诗歌是一种克制的激情。但激情在诗歌中没有因克制而丝毫地被损伤,甚至因克制而形成了悬崖,进而将一种流于泛滥的动能转换成静止的势能。所以说,诗歌与其说是一种自由的艺术,不如说我们在语言中寻求克制之术。
另外,我希望将想象与记忆作一种对应。想象是遗忘的记忆,是修补记忆,使“世界成为一个整体”的力。
江离:身体是具有开源性的,因为我们的可靠经验都来自身体的直观感受,我们是依赖于我们的眼睛、手、味觉、嗅觉以及身体的每一部分来参与理解和领悟我们的世界,它们是真正的基础,正是因为身体,事物才逐次呈现在我们面前,前几年国内很多人尝试“身体写作”,剔除媒体造就的哗众取宠的成分,实际上他们的写作关注了身体中和性欲相关的部分,对纠正过分抽象的理念化的,就人当成非人的写作有积极作用,但是身体的各个部分似乎还需要诗人进一步加以开发,加强自己的直观感受力,因为丝毫没有新鲜感的语句在现在的诗歌中实在太多了。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如何?
泉子:我愿意用性感一词来代替你对“身体写作”的描述。一个性感的女人能一再并持续地激发我们的热情,而完美的女人却不能,甚至会有一种甜食过量后的腻味。这样的经验同样成为我们写作阅读诗歌的经验。
我们身体的每一部分作为我们感知世界的触角,它们在我们与我置身的世界之间建立起了广泛的联系,它们丰富了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的同时,而又仅仅作为一种手段。“身体写作”作为对“理念化”写作的反拨,它本身依然是一种过渡中的写作。我想强调的是,诗歌首先是“求同”,寻求一种共鸣的体验,然后才是“求异”。而对独创性的追求,确保并加强了共鸣的有效性。同时,这种“独创性”又是以抵达或切近真理的难度来做保证的。
江离: 现代社会就像米兰·昆德拉描写的那个在公路上骑着摩托车的人那样处于一种对速度的“出神状态”,全神贯注于速度,而丝毫没有发现两边的景象,那么作为一种慢的诗歌(臧棣语)不正应当对充满了焦虑感的生活起一种中和调节作用吗?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诗歌只为少数人而存在,也许这说得对,不期望喜欢花边新闻的人来阅读诗歌,但是为什么阅读诗歌的人在逐渐减少,作家马原的看法更加悲观,认为文学有它开始、兴盛的一天,就也有它消失的一天,因为文学的手法相比电视、电影显得过于单一了。当然也一些人觉得随着生活水准的提高,网络空间的普及会给诗歌带来新的契机,你怎么看待诗歌的前景?
泉子:我在第2和第6个问题中已经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每一种事物在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承担起它的命运。即使在盛唐,诗歌的那些最伟大的传承者,依然是孤独的。但孤独最终在这些最伟大的传承者的身体中孕育出一可颗颗的珍珠,并因此最终通往了一种祝福。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得以从越来越广阔的视野中来审视我们自身,现代诗歌在完成了一次重要而深刻的转向后,依然延续着这样的命运。它不会消失。
诗歌究竟是作为一种审美,还是我们探索真理,认识世界的方式?这两者在更多的时候是同时抵达的,但对两者细微处的厘清在我们今天的谈论中却尤为重要。在中西方都有着两个并存在传统,就像汉语诗歌中李白、杜甫、苏轼的传统,以及李贺、姜夔、吴文英的传统。但愿意这样来表述,诗歌本质上是我们探索真理、认识世界的方式,而在相对的层面上,诗歌才是一种审美。回到莎翁的话:世界之大,比你能想象到的更多。
200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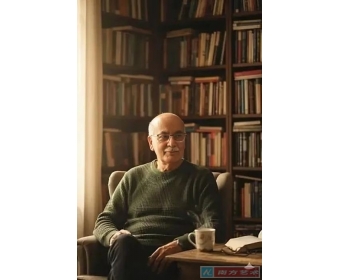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