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救赎,我们必须病得更深?”
谷禾/ 霍俊明

谷禾,1967年端午节出生于河南农村。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写诗并发表作,著有诗集《飘雪的阳光》《纪事诗》《大海不这么想》《鲜花宁静》和小说集《爱到尽头》等多种。策划出版了《中国诗典》《新世纪中国诗典》(群众出版社)等当代汉语重要诗歌选本。部分作品被译介到美、英、澳、新等国家和、港澳地区。曾获“华文青年诗人奖”“《诗选刊》最佳诗人奖”“全国报刊最佳诗歌编辑奖”等奖项,现供职于《十月》杂志社。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霍俊明:谷禾兄你好!一直想就兄的诗歌写作以及当下相关的诗歌问题进行对话。我想这不只是一次关于你个人诗歌的简单对话,这其中必然会涉及一些重要现象以及当下的诗学问题。在这个愈益让人不可思议的时代,在寒冷的冬天我们的这次对话应该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和象征性。此时我远在呼和浩特的一个狭小巷子里的一个宾馆,窗外的雪并未散尽,而你此刻正在北运河的一隅或者正赶在“回家”或“出游”的路上。此时,我想起了你今年冬天刚刚完成的一首诗《诗片段:初冬之诗》:“从一个陌生的城市,到另一个 / 更陌生的城市 / 浮生若梦,星空浩渺,人世近于虚幻 / 当你出现在我的视野—— / 这个恍惚的初冬充满了变数”。能否先说说北运河、通州以及北京(京郊)与你的生存以及诗歌写作之间是否存在着不言自明的关系(例如“北京记”、“地名学词典”)?我曾注意到,你诗歌中不断出现的这些城乡结合部场域和城市(地铁、车站、桥、天桥、码头、街道、市场、广场……)以及乡村的地理坐标。这更为复杂的“过渡”地带是否给你考察和反思乡村和城市提供了更为恰切的视角?
谷禾:俊明兄好!接到你的邀请,我正在广东东莞的一家宾馆里。房间里没有开暖气,但温度仍足够高。我们原本在一个城市里生活,对话却被分置于了南疆和北国,我觉得场在和气候这种变异本身可能就是诗歌的一部分。它如此荒诞,却又真实无比。就像诗歌(文学),让能它的写作者有一颗大心灵,让它的写作者聆听到“钟的秘密心脏”,同时也让我们变得漂浮。这里如何扎根(自我和写作的扎根)肯定是一个认真的地写作者必须面对的。到今天我来北京正好12年,其中前5年我在朝阳的管庄地区居住,后7年搬来了通州的运河边。相同的是,两者都是城乡结合部,聚集了最多从乡村赶来城市的寻梦者。居家的时候,我去运河周边走动,也去他们中间寻访。上班的日子,需要我换乘不同的交通工具,穿越半个北京城。可以说,你提问涉及的地理坐标不是源于诗歌的想象,而是每天扑入我视野的现实,它们几乎构成了我生活的大部分存在,去面对它们,洞悉它们,并呈现其中的诗意,在我即是写作的自我要求,也是本能。我在不同的场合说过,我是一个没有什么诗歌理想的家伙。但如此并不是说我没有关于诗歌的想法——我想尽我所能,写出作为个体生命面对过去和现在的疼痛——这种疼痛首先是真实的,关乎我的生存环境的——又是从个人视角所引起的——当然它的呈现必须是诗性的。用希尼的话说:“我写诗 / 是为了凝视自己 / 并让黑暗发出回声”。这样表达可能更准确一些吧。
霍俊明:由你的诗歌我愈益感受到“现实性”或“现实感”之于诗人的重要性。诚如你所说,在这个时代谈论诗歌理想多少有些令人生疑,或者起码有些矫情。但是我在你的诗歌中看到了当下中国诗人普遍缺乏的质素,即写作的诚意。在你的诗歌中我不仅看到了一个生命的历史以及想象,我更感受到了一个人的血肉、骨架、呼吸和灵魂。很多诗人和研究者对你诗歌的印象一个最重要关键词就是“乡村”,甚至干脆称之为“乡村诗人”(乡土诗人)。我知道你对此并不认同或并不完全认同。甚至在你编选自己新世纪以来的诗集《大海不这么想》时有意回避和过滤了关于乡村题材的抒写,但是我仍在你的诗歌中看到一个再也不能返回“故乡”的人在城市中有意或不自觉的一种身份焦虑和惶恐。记忆(历史)或现实中的乡村的物、人、事仍然在你诗歌写作中不时出现,甚至它们一起携带了黑暗质地的“挽歌”表征。我非常认同你说的“我一直对那种虚幻的乡村镜像保持着足够的警惕”,确实,在当下诗坛甚至小说界我看到了那么多虚假的乡村写作和底层写作。就你长时期的乡村生活以及对诗歌化的“乡村现实”的特异抒写,谈谈你对诗歌写作和“乡村”之间的关系和体认吧!或者视野再推进一步,在一个愈益复杂、分化以及去地方化和去乡村化的时代,诗人该如何以诗歌的方式予以介入或者担当?就近年来流行的乡土诗写作和新农村写作你觉得需要特别反思甚至警惕的是哪些方面?
谷禾:我的诗歌写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最后一年,那是海子卧轨之后,“麦子”开始从田野向整个中国诗坛铺天盖地。我生于乡村,长于乡村,工作在乡村,诗歌写作从乡村这个主题起步并不出人意外。直到前两年我还分别在《诗刊》《散文》用“以前我在乡下”为题分别发过两大组不同体裁的东西。那时我还在河南一所乡村中学教书,从我家的窗户望出去尽是一望无际的村庄和绿树掩映的村庄,课余我几乎天天在田野里转悠。周末还经常回到村里帮父母耕地收割。我熟悉田野上的一草一本,熟悉村里人的喜怒哀乐,至少能从声音分辨出几十种鸟叫,我写的就是我最熟悉的人和事,我认为自己还算是一个诚实的写作者。称我为“乡村诗人”或者“乡土诗人”,我并不觉得丢份儿。
对一个写作者来说,诗歌首先是一种情怀,你用它去观察世界、认识世界、发现世界,抒发自我,写得好与差是能力问题,但从一开始就必须有一种真诚地态度——真诚的面对世界和自我,如果这个你做不到,至少我是怀疑写作的意义的。当写作和现实发生联系以后,诗歌当然不能是飘在天空的浮云,它必须扎根于大地,接通地气方有生命,有生机,有活力。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改变自己的这一理念。1999年,我一个人来到了北京,后来家人也都跟了来。12年的光阴就这么不知不觉地流逝了,尽管我每年都要抽时间回去我出生的村里几天,但每次回去都很匆忙,很难细细地看一些东西,静静地想一些东西。说一个细节吧,小时候在村子里,无论多黑的夜晚,你从灯影里走进去,只需要几分钟,黑夜里的东西便清晰可见,你现在再去试试,就是一个睁眼瞎,真的什么都看不见了。我觉得这种脱离让你的感觉也迟钝和麻木了,包括村子里的人情世事,你很难再深入下去,你怎么去反映它呢?所以说,我真的不是“不屑一顾”了,而是我的笔和文字已经没有了那一片乡土的呼吸,我是不敢再去触碰它了。
诗人伊沙在他的《新世纪诗典》推荐我一首《亲人们》时这样说:“有一段时间,我认为谷禾是中国最好的乡土诗人。今年他光临长安诗歌节,却念了一首不怎么样的社会批判诗,模糊的印象中,他似乎对乡土诗已经不屑一顾。诗歌的现代化真是一个复杂微妙而又极其内在的东西,不是简单的‘进城’,不是在题材上入时,不是政治正确。乡土诗的现代化可以在其内部完成,你看这首,写得多好,接了地气,又不显土。”但我知道自己没那么好。我在阅读杂志的诗歌来稿时,也读到很多乡土题材的诗歌,但认同的极少,因为我有足够的乡村经验,这些所谓的“乡土诗”,你看它是隔了一层的,有的甚至仅仅是想象的乡村,其中呈现的苦难和幸福,都太假了。我想与其这样,不如不写。“乡土诗”的现代化不是命名一个“新乡土”,或者添加几个现代农具和通讯设备的名词就完成了。写什么和怎样写,值得、也需要有心人深入探讨。从我自己说,我写城市或者底层的很多诗歌,主人公涉及有集贸市场的小贩、装修工、送奶员、黑车司机、废品收购者等。他们本身也是乡村的一部分,或者说他们把各自乡村背到了城市里,经常和他们聊一聊,你能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和认识眼下的这个城市和远方的乡村。和过去的写作相比,我的更多了些怒气,多了些尖锐的批判。其中如《宋红丽》等受到了几乎众口一词的表扬,也有些东西引起了朋友们的非议。这一点我很冷静,如果仅仅想用诗歌去进行社会批判,不如去写时评,那样更有战斗力。所以重要的是你表达的东西一定要有诗意,你要能发现残酷现实里的诗意,又要做得恰到好处,这比之过去对乡土(自然)的表达有更高地难度。
多年以前,我曾有过编一本乡村诗选的冲动。我心中的乡村既不代表悲苦,也不是被人为放大的欢乐和自足,而是自然本身,是几千年积淀形成并延续的自然的伦理和秩序。美国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说:“认识故乡的办法就是离开它;寻找故乡的办法,是到自己的心中,自己的记忆中,自己的精神中以及到一个异乡去寻找它。”所以衡量乡土或者其他任何题材(如果可以这样划分)的诗歌写得好与不好的标准应该是它是不是写出了某种存在的真实和事物内部的真实,而非题材本身。波兰诗人米沃什认为“诗歌是对真实的热情追求。”这是迄今为止我最认可的诗歌观点。那么你的写作首先是不是走在这条道路上?其次这条道路上有哪些景象甚至气息?万物生灵有着怎样的生死疲劳和内心的秘密?它们既是物质的,又是写作者个人的,诗能把这些写出来就足够了,至于先锋啊后卫啊什么的,缺失了这个最基本的东西,都不过是唬人的玩意儿。我们不妨去读一读托尔斯特、普鲁斯特、卡夫卡,去读一读艾略特、米沃什、布罗茨基等人,可以说无不如此。其实所有的艺术形式所通达的最高境界就是真实,也许我们穷尽一生也不能写出其几百分之一,但我们可以通过自我的努力去无限接近这种真实。
这里我也接受伊沙的批评,因为我知道自己还差得远。对一个时代来说,诗歌既非“不朽之盛事”,更非“经国之大业”,也许只是人们(写作者和阅读者)内心残存的那一点点柔软。从文学的社会学功能来讲,诗歌似乎已经变得越来越无用,但无用之用,恰恰是诗歌的大用,我因此更敬畏诗歌,更热爱诗歌。
霍俊明:我觉得确实当下很多诗歌都没有“接地气”,功利、虚假、浮泛,贩卖和利用“疼痛”和“眼泪”,更不用谈论那些命题写作和征文写作了。我一直觉得长诗写作在很多诗人那里仍然是一个集体的焦虑,很多所谓的长诗成了短诗的拼凑品或者变相的组诗。我注意到1960年代出生的一批诗人已经写出了优异的长诗文本,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考量这些诗作仍然是凤毛麟角。你在2009年和2010年分别完成了《庆典记》和《少年史》两个长诗文本。也许把它们和你的短诗放到一起来考察你近年的诗歌写作,能够更为深入和全面。对这两个文本,你自己有什么必要的补充和说明吗?尤其读完《少年史》,我沉浸良久,这已不能用语言来形容的一种感受。我曾经写过组诗《一个人的编年史》。可以说,这印证了布罗茨基所说的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我觉得“人类”这个词太大了,诗歌就是一种记忆方式——时间、命运、现实、历史。
谷禾:当下的诗歌写作者,被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大体上每10年划分为一代,这就有了所谓的50后、60后、70后、80后等概念。其实也许以每个10年中的逢5这个年份划分我觉得更科学一些。如果你有留意,会发现,1966——1975年出生的这一拨诗人,很多人都在尝试那种500——1000行之间的小长诗创作,我把它看做是这一拨诗人在写作上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经过这么多年的积淀,他们已经完全有了结构长诗的能力,而且和短诗相比,长诗更有足够的文化的、历史的、思想的含量,也值得人们给予更高的阅读期待。
回到这两个文本的谈论上来。《庆典记》共45节,有700多行吧,这首诗写于2009年国庆节期间,用了不到半个月时间。为什么写这样一个东西,到现在我自己都说不清楚。我记得那些天到处锣鼓喧天,旗帜招展,花团锦簇、歌舞升平,头顶不时有拉出彩烟的飞机驶过,老头老太们戴上了安保标识的红袖章,分立在小区门口盘查路人,红光满面的,仿佛刚打了鸡血。然后阅兵,烟火,等等,不一而足。就像我在诗中所写“又一次彩排圆满成功 / 人去场空,仿佛一个器官抽离另一个器官 / 留下凛冽的空气,垃圾,剪纸的月亮 / 留下空虚之海 / 这样的夜晚,适于长睡不醒 // 更适于,醉生梦死”。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缺少的恰恰不是这种醉生梦死式的庆典。往大的说,逢五逢十必列队检阅,往小的讲,春节元旦必火树银花,再小的说,升学得奖也要摆个宴席,却唯独缺少对历史的反思。我们老念叨要日本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其实我们自己才最善于“遗忘”和“背叛”,我在极度的沮丧和愤懑中陆续写下了这些诗行,尽管在诗中对现实的批判多有苛刻,但我觉得它是诗的,有足够的思想含量。不瞒你说,对这首诗,我是有一点小小的骄傲的。如果说,《庆典记》是批判现实的,那么《少年史》则是反省历史的。这首诗在心中构思了5年,写出来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后来分别在《中西诗歌》、《河南诗人》和《青年文学》刊发了出来,引起了一些读者和批评家的兴趣。有人问我究竟写了什么?我说“我只写了一个少年成长过程中的孤独”,并且顺便把带来这种孤独的时代的、家庭的、个人的因子给真实的呈现了出来。《少年史》写了文革,写了一个村子里的农民对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和“四人帮”认知,写了八九之夏,以及这些大事件在一个少年心中激起的小回声,因为接近了真实,它才有了锋芒和疼痛,有了对那一段荒诞历史的反思和批判,有了力量。也许再过几年,我会再去写一首关于未来的东西,这样和《少年史》《庆典记》构成一个三部曲。我有这样的想法,但现在还不成熟。
我也曾在另一篇关于诗歌的文字里提出了自己的疑惑,我这样写道:面对“在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的提问,荷尔德林的回答是:“诗人是酒神的祭司,在茫茫黑夜中走遍大地,察寻神的踪迹,吁请神的出现。”但我们所处的是不是“贫乏的时代”?在这个十年里,我在号称首善之区的钢筋水泥的森林里,目睹蔓延横流的物欲让无数的写诗者迷失了心性,见惯太多的所谓诗人甚至“著名诗人”津津乐道于制造事件和事端,沉迷于发表和获奖,醉心于在各种以诗歌为名的聚会上指点江山,他还有作为“酒神的祭司”的资格吗?在这个十年里,我越来越成了一个不断后退的先锋主义者,力图从浮泛的抒情回到坚实的述说,梦想着用诗歌见证这个喧嚣的时代和一日千里的人心。尽管我也写出了属于自己的《少年史》《庆典记》《宋红丽》,但它们仍然如此微不足道,因为在铜墙铁壁的现实面前,我越来越发现,诗歌是如此的渺小和无助,势单和力孤。当千沟万壑猝然崩塌,当轰隆隆的铲车滚滚碾过阻挡者的头,当高速列车不期相撞,谁能告诉我,诗歌真的能抚慰一下幸存者伤痕累累的心灵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诗有何用?
我没有办法回答自己。这是不是有点儿操蛋?
霍俊明:哈哈!这是个问题。更多的中国诗人成了旅游见闻者、红包写作者、流行吹鼓手、新闻报道者、娱乐花边偷窥者、自我抚慰者和犬儒主义者。当你仍然追问诗歌是什么以及诗歌具有什么作用时,足以表明了一个忧心忡忡甚至有点矛盾和分裂的诗人在这个时代的可贵和稀缺。话说回来,我们的诗人学会了抱怨,也学会了撒娇,就是没有学会抱负“诗人”的“良知”。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甚至国际的、全球的诗歌奖把诗人们惯坏了。说句心里话,我向那些仍然彷徨、仍然分裂、仍然有些愤青的诗人们致敬!《庆典记》和《少年史》正好是两个互相印证和倚靠的维度,现实的、历史的,而这两者又是如此胶着的纠缠在一起。在这两个“小长诗”中我领受了我在评论中一直赞许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能力,这实际上就是诗人的“去魅”和发现的能力。
我认为当下中国诗歌一定程度上带有“时代病”和“精神疾病”的雅罗米尔气息。在你的诗歌中我看到了“中年”、“身体”在诗歌写作中的精神征候。同时,这个迅速“前进”和“拆迁队”的时代,你的诗歌也呈现出了反讽、“焦虑”甚至疑问——“为了救赎,我们必须病得更深”。显然,你不能成为一个“飞上天空”的诗人,你的眼界更多是扎根向下的。那么,当你以诗人的身份来面对时间、生存、身体甚至更为庞大的“时代”和“现实”时,你觉得诗歌应该如何予以“真实”的回答?诗歌是否具备面对“身体”、“疾病”和“时代”的“返真”能力?
谷禾:我也补认为浪漫和小资都是什么坏东西。坐在咖啡馆里,喝着各种凉热饮品,一边谈论诗歌或风月,的确是个惬意的事情。但它的确也不属于我这样的人。我们这一代人(60后中后期)见识过发生在文革里的种种荒诞和那种体制对人性的摧残,尽管那时我们属少年(我以此为主题写过一篇叫《1976年的黑白电视》的中篇小说可参看),但今天想起来(每一个集体的建制无不是一个精神的屠宰场)仍恐怖得心惊肉跳。“文革”后我们曾经“为振兴中华而读书”热血沸腾过,甚至走向过街头,再后来一盆凉水迎头浇了下来,醒来后发现我们为之热血沸腾的所有东西和“文革”时期的那些东西其实毫无二致。从那以后的这20年来,整个社会和人对物欲的追求都被无限放大,而对精神、理想和艺术追求几乎只呈现于纸面和口头上。社会各阶层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都可以置社会公理和人类的普世价值于不屑。有一段时间,我怀疑这个时代是不是疯了?对一个诗人来说,这是多么杞人忧天,但没有办法,我的出身、经历、信仰等让不可能做一个超脱者,只能陷入类似于“如果爱和健康都是疾病 / 为了救赎 / 我们必须病得更深”的自我诘问和焦虑,而不可能沉湎在浪漫和小资情调里。“中年”也好,“身体”等征候,都不过是精神镜像在写作者内心的投影,或者自我的模糊替代物罢了,它仍不是写作者所看到的自我真实的全部,而只是被时代粉碎的自我的一个碎片而已。
我的朋友铁夫有诗写道:“父亲就是村庄/母亲就是故乡”。也许他是不经意间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但在我却愣了很久——发现了一个真理。是的,我们从出生哪一天就再也回不去故乡了,我们记忆中的故乡也在疾速消逝。我在前边反复说起了诗歌的无用和现实的强大。在此局面下,诗歌和诗人的声音有着越来越暗弱的危险——不管这样的声音多么真实!我们试图通过对“乡村”的回忆和美化来抵抗和消解强大的现实,因为一个人的童年决定了他的现在和未来(这个是谁也难以改变的)。但没有用,在这个基点上,我终于理解了叶赛宁当年的痛不欲生。
不好意思,这样的谈论有些离开了诗歌。诗歌当然不是现实本身,但诗歌必须根植于现实,并且必是现实的回声,而不是诗歌中所呈现的形形色色的“伪现实”。
这里我想顺便再一次说及“灾难诗歌”(包括地震诗、动车事故诗、校车诗)。我注意到在它们铺天盖地占领微博的时候,有人站出来指责伊沙等知名诗人的沉默并酿成争论(当然,也有人以此断言诗歌的“有用”和“堪大用”,并回击另一些人对“当代诗歌远离现实”的批评)。我觉得两者不是以偏概全,就是不无意气用事。诗歌指涉现实不是匆匆忙忙地去写突发性事件——不管你是去赞美、抚慰还是追思、批判。优秀的诗人会自觉地从这样的现实里悄然退出来,冷静的观察反复思考并经历时间的足够沉淀后,方去提笔书写其中的诗意。这样写出的诗歌才有可能是我们所熟悉的陌生,才有可能产生震撼人心的穿透力。
“不要刻意去做事件性的诗人!”这是我我反复对自己说的。也是对朋友们的善意提醒。
霍俊明:你说一个人的“童年”(少年)决定了现实和未来,甚至也决定了一个诗人的精神征候。我想这是对的。精神成长史以及更为具体的童年显然具有不言自明的重要性。我在关于“70后”的那本书《尴尬的一代》里也反复强调了一代人的成长和写作之间的重要关系。你应该是当下中国直面现实的重要诗人之一,底层写作也亦成为重要的现象。我注意到你更多是从叙述和精神的角度来面对社会分层严重的现实。你诗歌中很多的场景、人物、细节都带有这个时代的“景观”和寓言性质。你的诗歌中不断出现关于“疼”、“痛”和各种各样的“死亡”场景和记忆。就此说一说吧——
谷禾:现实每天呈现在我们面前,你怎么能够避开?你不要想着我退到屋子里去,因为现实的红色铲车已经把钢铁的牙齿咬进你并不坚实的墙壁,即使变成一只卡夫卡的甲虫吧,你也要做好有朝一日被你最亲的人踩死并丢入垃圾桶的准备。这也是现实。你说是吧?刚才我去宾馆的公共洗手间,看到墙壁上写了这样一句话:“请把垃圾放进垃圾桶。”——它瞬间触动了我。我觉得往深处想,它说的似乎有那么一点点禅意。
好吧,我来仿造一个:“请把诗人放进诗歌里——”
“请把诗歌放进现实里……”
我再说说“底层写作”吧。这个概念好像已经在诗歌内外流行了很久——当然比它更流行的是对各种写作的命名。仅就诗歌写作来说,就有“知识分子”“中年”“口语”“中间代”“七零后”“八零后”“第三条道路”“草根”“新红颜”“打工诗歌”等等。被一个命名都圈进了一批人,甚至连李白杜甫白居易都被划入了不同的阵营。我觉得这有点搞(其实大家都知道,只是不说破而已)。不客气地说,它反映了命名者和被命名者的双重焦虑,其微妙之处不言自明。我们不去讨论这个。
“底层写作”被作为一个类型化写作方式被提出来最早是源于小说,其涵指是说,小说的主人公大多为社会底层人群,写得也多是他们所经历的苦难,这几年似乎势微,不再打开一本纯文学杂志,到处都是倾诉苦难的人。我不怀疑大多数人所经历的苦难和正在经历苦难,我怀疑的是:当对底层和苦难的书写成为一种潮流,它的制造者把多大程度的诚实放进了自己的作品里?无论什么形式和类型的文学,说到底还是人学,衡量一个作品的分量和价值的最重要的标准就是这个作品在多深的程度上反映了人类身外和内心的真实。明白了这一点,你就不会沉溺于词语的游戏和修辞的圈套,不会得意于抖包袱式的小聪明,不会满足于把读者的廉价的泪水哄出来,而是用你勇敢的心去尝试撞击黑暗的世界,并倾听它发出怎样光明的回声。我最近在看三本书——菲利普•罗斯的《遗产》、哈金的《南京安魂曲》和熊培云的《一个村庄的中国》。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看一看这些诗歌以外的人是如何呈现那种噬心的触目惊心的真实的。
如果像俊明兄所说“你诗歌中很多的场景、人物、细节都带有这个时代的“景观”和寓言性质。”那也许是因为我也是希望去这样尝试一下的写作者,并碰巧在某一个部位窥见了这个世界的“时代病”。四十多年前,梁漱溟先生就曾发出“这个世界会好吗?”的诘问,我也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美好的世界”会不会根本就是贝克特的戈多?我真的无从回答。
我出生在淮河平原深处的一个村子里,记得我家门口就是一条很宽的河,因为很小的时候就每天帮着母亲烧饭,11岁那一年,因为整个夏天都在烧完饭后立刻跳入河水里去游泳,累积下来,就有了麻烦。高烧不退并且浑身疼痛不止,送到镇上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其中半个月完全处于昏迷状态,后来虽然捡回了一条命,但风湿痛从此想梦魇一样缠上了我,让我经常梦到自己以不同方式的死亡。我不是宗教信仰者,死亡对我来说不是天堂,而是活生生的梦魇。每次我从梦中逃出来,都会半夜睡不着。三十以前,我认定自己是活不过三十岁的,非常恐惧。直到今天,“疼”、“痛”和各种各样的“死亡”场景和记忆仍然时时刻刻缠着我,它让我更珍惜人间的小欢乐,每天以笑容示人,与世无争,而至把孤独感和宿命的悲伤留给自己,正如我在一首中所写:“但更多的时候,我的欢乐大不过一粒米 / 我就想办法把它爆成米花吧,蘸上甜,制成毒药 / 送给有缘人,击鼓相传。如果这样的想象失于天真 / 我就把它写成诗篇,对着天空和田野朗诵 / 这时候,我的心情蕴含着千万种心情 / 它是无法比喻和形容的,也是无法描述的,只供奉于 / 我辽阔而不安的内心——”
当然,从另一个方面看,这样的童年梦魇可能也让我无不自觉地放大了各种各样的“疼”、“痛”和死亡的场景和记忆,并且特别容易对各种社会性的“疼”、“痛”和死亡的场景和记忆产生敏感,生死乃天大事,诗歌呈现这些东西,可能比较容易感染读者,但反复书写也会陷入自我重复,俊明兄这里提出来,倒是给我提了个醒儿。
霍俊明:“辽阔而不安的内心”——这是对所有诗人的一个很好的提醒。你的诗歌在我看来呈现了一个旁观者、介入者和漫游者的形象。“他”在乡村和城市间散步、游走、漫步、奔波(还有“火车”的意象),这体现你怎样的精神状态和“观察”能力?这是否是中国化的资本市场时代(后社会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形象?
谷禾:人落草到一张床(世界)上,然后尝试摇摇晃晃学步——然后始能独立走各种各样的路,到最后再躺回到床上,平静或者不平静地接受死亡。所以你可以说人之一生就是走在路上,也可以说人之一生其实就在一张床上打转,都有道理,视角不同罢了。我生于乡村,父母如今还生活在村子里;我落脚在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妻儿也都在这里,无论在现实里和精神里,我都是在两地之间“散步、游走、漫步、奔波”,我是众生的一个,同时也非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我通过这样的旁观、介入和漫步,试图窥破和理解事物和人的内在的精神世界。无论采取哪种方式,都不过是想更深入更准确。其实即便不写作,我可能也会这么做。每一个人都有试图窥破他者的欲望,他者即世界。还有诗人自己的定位问题,诗人不是救世主,也不是精神导师,而只是他们中的一个——诗人在这样的位置去观察理解他者,也许会更接近于世界的本质。诗人不是先知,不是上帝,更不是救世主,他最大的可能是让自己发光,照亮世界的一个微小角落,谁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他就非常了不起了。
霍俊明:我一直关注着具有“乡土”经验诗人的家族叙述,你的诗歌中出现最多的是“父亲”形象,比如《劈柴的父亲》、《再写父亲》、《去年》、《我的父亲母亲》、《我在身体里……》、《落院》、《再次写给父亲,也写给母亲》、《我父亲的故事》、《回乡记》、《在屋檐下,和父亲论生死》、《深夜接听父亲的电话》等等(还有更多)。相反,写“母亲”的诗却相对较少,或者母亲形象是作为父亲的“陪伴物”出现在诗中的。说说你诗歌中的“父亲”形象以及你借此所要表达的精神维度或某种宿命性的“情结”。或者说这个“父亲”形象是否早已经“溢出”了个人和“血缘”的范畴,从而具有了象征性和寓言性,尽管其中的诸多细节和场景是来自和生发于实实在在的“现实”和“经历”。
谷禾:的确如此,“父亲”的形象在我诗里一直占据了非常核心的位置,相反母亲的形象却十分模糊,有一次我集中读自己的旧作,我突然发现自己竟然从来没有一首以“母亲”作为书写核心的诗,我在反复思考这一问题(如果它算一个问题),发现我还是要从源头说起。我在前边说的,一个人的童年决定了它的现在和未来,也许我们的写作就是为了不断回到童年。我在村子里出生并长到13岁,然后去异地求学、工作,然后越走越远。那时候还是生产队时代,和包产到户初期相比,农民的劳动强度其实并不高,但对血统的歧视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我的母亲出身三代农民,嫁给我父亲这个富裕中农的儿子后,受到了想不到的生活的歧视和人格的侮辱,这让她非常委屈(我倔强的大伯母干脆直接选择了我们家门前的一棵老桑树,用绳子了结了年轻的生命),我的母亲没有走极端,但她的性格渐渐变得非常不平和,尤其对我这样野小子,几乎动辄以掌相加,之后再用饥饿加以惩罚。以至于我对童年最刻骨的记忆就是饥饿和胖揍。我在前边提到的《亲人们》曾这样写:“四十年前,我还没有出生,只把母亲当亲人 / 三十年前,我九岁,把所有的饭当亲人 / 二十年前,我十九岁,只把青春当亲人 / 十年前,我的父母,妻子,儿子和女儿,是我的亲人 / 踩着四十岁的门槛,所有的敌人和亲人,你们都是我的亲人 / 当我八十岁,睡在坟墓里 / 所有的人都视我为亲人,但你们已经找不见我—— // ……这一撮新土,这大地最潮湿的部分——” 可以这么说,母爱在一定程度上丧失,让我过早体验了人生的孤独,这样的孤独反过来造成了我对母爱的忽视和熟视无睹。我生活中的父亲则是中国农民的典型,他性格隐忍,坚强、宽容,仁厚,耐劳,本分,与世无争,向亲人和身边的相邻释放着绵绵无尽的爱,我的诗歌如《劈柴的父亲》、《再写父亲》、《去年》、《我的父亲母亲》、《我在身体里……》、《落院》、《再次写给父亲,也写给母亲》、《我父亲的故事》、《回乡记》、《在屋檐下,和父亲论生死》、《深夜接听父亲的电话》等等(还有更多)里的父亲其实早已经超出了他的范畴,而逐渐成为一个中国乡村农民的典型形象,他身上渊源流淌着父爱的力量,我甚至曾用另一首诗完整地阐释了他:
一个熟睡的老人
就像一座空荡的房子,因为年久失修,
它的内部
黑暗,肃穆,荒凉,蛛网密布
如果一阵风吹过,
逝去的母亲,和母亲的母亲们回来,和他合而为一
它会变得
自然,亲切,带着桃树的端庄和垂柳的慈祥
噢——,一个熟睡的老人和空荡的房子
接着,河流与村庄诞生了
田野,羊群和炊烟,
女人抱着孩子,沿月光走来——
我想,这不是幻象
从一个熟睡的老人开始,当他和一座空荡的房子结合
我被允许经常回到屋檐下,成为
众多父亲中的一个
——《一个熟睡的老人》
每个人迟早都会回到屋檐下,成为众多父亲中的一个。
这就是命运,它不可逆转。
霍俊明:是啊,无论是从个人家族谱系还是从乡村中国最后的黄昏来说,“父亲”或者“母亲”已经成为了中国带有乡土经验或者想象的诗人的核心意象构造,尽管很多诗人处理地煽情而浮泛。由于写作小说的缘故以及对诗歌写作自身的认识和调整,你的诗歌叙事性是非常突出的。显然叙述在你这里已经不是简单的修辞,我当初印象最深的诗歌就是那首《宋红丽》。还是说说你对诗歌叙述的体认吧!反过来,1989年之后中国诗歌对“叙事”和“戏剧化”的强调以及对抒情的“矫正”是否存在着另一个向度的问题?或者说,我们这个时代是否还需要理想主义和高蹈的抒情者;抑或抒情方式在这个时代不可避免地相应发生了变化?记得你曾说过自己是一个“不断后退的先锋主义者”。
谷禾:当然记得。我说过自己是一个“不断后退的先锋主义者”,那是因为年轻时候人总有赶潮头的想法,你说谁先锋,我就去学习他,然后觉得自己也“先锋”了,慢慢的,你会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学习或者甘心做一个诚实的写作者——哪怕因此不断后退。这比什么都重要!
在当下的写作者群体里,我算是那种什么都能来两下子的家伙,小说、诗歌甚至评论杂文等都尝试过,其中2002和2003两年,我基本把诗歌写作停了下来,一门心思弄起小说来,如果仅仅从发表的角度说,我写下了1部长篇,6个中篇和10来个短篇,其中的大部分发在了国内有影响的《十月》《北京文学》《青年文学》《人民文学》等刊物上,成绩还算不丢份儿。2004年后突然停了下来,原因也很简单,写小说真的是个体力活,我的颈椎出了问题,而且我越来越认识到,一个人一生要能做好一件事情已经足够了,我很自然的回归了诗歌写作。但两年的小说写作训练仍然让我受益匪浅。首先是诗歌观念的更新,之前我的诗歌写作抒情意味比较浓厚,写得比较自我和纯粹,写过小说后我发现这种写作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世界万物的存在无不是冷静的,而且越持久的东西越是冷静的,你只有冷静下来才有可能触摸到事物的真实和事物瞬间消失的诗意,构建诗歌的基本元素,除了语言和想象,还有经验、经历、思想、发现,它们和前者有着相同重要价值和作用。无论诗歌或者小说,终极的价值都该是反映世界的真实和梦想,而要达到这一境界,你必须把激情冷却下来,在这种背景下,我的诗歌写作确实融入了更多的叙事元素,但它仅仅是对抒情的矫正,而绝非替代。其次还有语言——你要把曾经的高蹈转为一种可触摸的有温度的状态。小说家格非说到一个人死了以后,用了“像一首歌谣一样消失了”这样的句子。博尔赫斯也写到了一个人死了,他用了这么一句:“仿佛水消失在水中”。两相比较,博尔赫斯比喻的想象力和洞察力多么强大,而且保持了持续的冲击,你说高下立见吧?所以好的作家是能够把不同的艺术形式糅合在一起的,虽然他表达的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稍纵即逝的诗意。美国小说家福克纳在《我弥留之际》写一个医生骑马走过来,他看眼前的山路,就仿佛一条折断的胳膊。这些比喻无不结合了语言使用的现场,从而让读者生发出更多的想象,而不像当下很多诗歌中的比喻那样仅仅到语言为止,显得突兀、盲目和随意。即使在诗歌写作中,你的语言运用一定也好贴近现在时的场景。所以在我,叙述的介入是一种不自觉的主动转型。
去年我曾经写过一篇叫《叙述对当下诗歌的介入》的文章,详细探讨了叙述在诗歌中的运用(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到我的博客里去看一看)。叙述对当下诗歌的介入,让诗歌从云端之外结结实实地回到了尘埃里,但其过度的膨胀也让很多文本变得更加隐秘和难以把握,并增加了阅读的难度,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叙述几乎存在于当下最优秀的诗歌写作者的文本里,只不过运用的方法和量能控制不同而已,但与浮泛的抒情和抖包袱式的顿悟相比,我宁愿多一点智力和精力去投入到对这一类诗歌文本的解读中去。
在这个争相自视为诗歌的先锋派的时代,我愿意继续做一个“不断后退的先锋主义者”,无论是写作还是阅读。我觉得这蛮好。
另外,《宋红丽》问世后,得到了无数朋友的赞扬和嘉许。我觉得大家喜欢它更多不是因为我写得多好,而是感叹于宋红丽们多舛的命运。对我来说,它仅仅是一次尝试——把抒情藏起来的尝试,碰巧它取得了小小的成功。仅此而已。只要还写下去,我还想继续进行多方的尝试和探索,哪怕它遭遇失败。这是作为一个诗人的使命,也是一个出身于乡村的野孩子的倔强使然。
霍俊明:好像我们的对话才刚刚开始!说句题外话,我记得你是端午节出生的,这多少带有了某种预示性,尽管并不是这天出生的人都能够有幸或者不幸成为诗人。但愿更多的诗人如你所说能够抓到那些稍纵即逝的诗意,抓住那些诗意的闪电。在一个所谓不断加速度“前进”的时代,心存真诚和敬畏地做一个不断后退的先锋主义者。确实,有时候或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逆流而上和顶风前行。
谷禾:是啊,难得有这样的心情如此深入地谈论我们共同热爱的诗歌。这里也谢过俊明兄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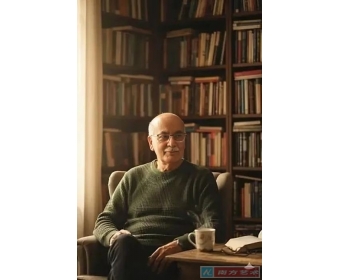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