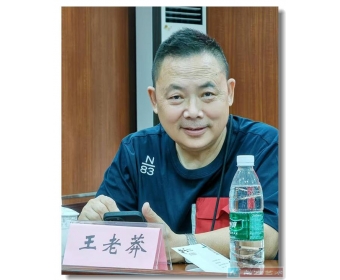|
原载 诗画论语 公众号
张小榛的音高和语言
李建春
高音诗人一般是从理念出发,到达经验;中音诗人是从经验到理念;低音诗人是从经验到经验。张小榛的组诗《机器娃娃之歌》无疑属于高音诗,在当代诗中罕见,在90后一代中目前为止仅见。郭沫若《女神》中的若干篇章,一些以民歌为源头的诗及革命浪漫主义朗诵诗,属于高音诗。汉语当代诗由于不避免、必须的怀疑主义,使低语成为最可信赖的姿态,因为诗人只相信经验了。成为高音诗人,除了性格因素外,一定要有理念上贯通、自信的感觉,以理念构成宏大的时空背景,涉及日常经验,往往以俯身的姿态。当代诗中的高音部,几乎都与基督教有关。本人前期的部分诗,张小榛的许多诗,都是在福音的崇高和得救自信中写出来的(张小榛的不大容易察觉)。为了在现代诗的语言传统中生效,接受了上帝的诗人通常会把这种崇高的情感和身心获得质变的感觉隐藏起来,像基督一样重新降生到人世中,去观察、感受、批判和说教。不同的基督性诗人方式不同,他们会糅进不同的知识背景和社会背景。有借着福音而为了诗的,有借着诗而为了福音的,有无意于涉及宗教而不得不带上信仰底色的,有在生活中得救而在语言中下沉的,有刻意激化光与暗冲突的,有精心挑选基督宗教中个人自由因素的。
一团火燃在村庄中心。我们起身,露水滴进铜盘,
头顶上大而横行的蟹,拖着地球吱嘎响的轴承。
如同古人,我们抬头凝视它青铜的手足。我们用它命名夜色。
饮酒,偷偷地。“唯有夜色掩蔽我们。”
诗人设想,或化身为机器娃娃。这90后记忆的,无辜的,童话的,玩具的,机器美学的,种种动机集中于一个形象。以此形象介入一个创世纪似的发生,“一团火燃在村庄中心。”圣灵降临。“我们起身,露水滴进铜盘,”承露盘。求仙。“头顶上大而横行的蟹,拖着地球吱嘎响的轴承。”这又像卡通又像玄幻,进入机器了。小榛的语言总是从不可思议的文化碎片中擦过,这种诗其实全靠语感,甚至只有语感。
尚未开始失去时最疼痛。世界病了,霍夫曼,霍夫曼
我看见你呕出被嫌弃的肝脏。
母亲在我怀中升起篝火,我所羡慕的
炙熟的心如月亮般跳动。灼热中,霍夫曼但霍夫曼,你是
有世界的。
吻我——以你吻过泥土的双目,趁我死于厌腻之前。
(我们,两个语词的天使,在说漂亮话方面同样笨拙。)
霍夫曼,你推土而成的地铁,今天又咣当咣当穿过夜幕。
我是悲伤、我是无力、我是孤独。
世界病了。呕吐。这悲伤,无力,孤独,似乎不得不以童话的方式。可能因为她还没有世界。“尚未开始失去时最疼痛。”这疼痛,能在“世界”中被理解吗。“母亲在我怀中升起篝火”,最初的生命难道不是言词的中心,鸿蒙,浑沌,那难以言说的。而童年就是世界之无渴望其有。童年获得过最多的吻,但那是被保育的吻,令人厌腻,她需要霍夫曼的吻,因为霍夫曼是她能亲近、能获得的世界的形象,“吻我——以你吻过泥土的双目,趁我死于厌腻之前。”
张小榛的长行,是在玄秘的诉求和创世纪大爆炸的叙述中建立起来的,诗性的悸动,体现于出人意料的断句、分行。刻意的文化穿越,杂糅。“为了上帝我们采莲。我们采莲,喝米酒,采莲,/采那清如水的少年郎。为了上帝我们看海去,/看你布满齿轮的心脏升起在海面。”采莲,喝米酒,南方生活符号,却要“为了上帝”。这个短语一嵌入味道就变了,进入文化诗学。“布满齿轮的心脏”,再变一次,成为文化鸡尾酒和朋克音乐。
我注意到她的起句之美:
他的癖好是看着事物凋零。柠檬的风干
苹果的萎缩葡萄的失水人生的如梦性。
——《副驾驶座上的机器娃娃》
象限仪不动经纬仪不动唯繁星坠胀,
玫瑰若不推动天极的旋转就必凋零。
——《观象台上的机器娃娃》
我的灵魂不再有了。它凋零在四个午后,
父亲死在其一。我在第二个醉酒、
狂怒、将刻薄掷向旁人。
——《机器娃娃的黄玫瑰》
让我们敲希望的,钟啊。
往来的天使身上溢出黑夜,将那病体
交给春天。交给有樱桃的夏天。
——《机器娃娃的祈祷》
起句都是从一种特殊性开始。特殊性是语言内部的传奇。这种高音部诗是从上而下的俯冲,以发现他人或“我”的特殊性作为突破口开始叙述。它蕴含的生活态度是反叛、重构与游离,关于伤的讲述是人性的突破口,特殊意象“机器娃娃”被挑选出来作为语言装置,与文化碎片作概念的偶合,以奇异、神秘的语调生发诗性。这当然是不自然的诗,具有显而易见的急躁的语速和不稳定感,“诗性安慰”的期待必定落空。与“成熟”无关。从这种写作出发,不妨设疑:当代诗人的成熟必定与当代史、政治操守和个人化语调有关吗?文化鸡尾、科普控、另类生活意志,怎样与前述“有深度”的指标沟通?如果不能回到自然,诗写就只是一种行为,行为艺术的行为。
这是张小榛大叫大嚷地登上诗坛或她自己一代人“歌厅”的标志性作品。现在撇开与机器娃娃或霍夫曼有关的,再找一些或许是中音或低音的诗看。
从翅膀往下看,穿行在花丛中的绿火车顶上
坐满亡魂。风循环在我们的迁飞区,
从太平洋带来回声:长毋相忘。这样
他们便可不怀揣疼痛渡过那大川。在夜晚
明亮的八月星空与惊惶下,我们飞抵达里诺尔
和铁轨汇合。他们肩并着肩簇拥在站台上
有些身影被汽笛吹散,这逃过星陨如雨
和流沙的,在煤烟中微微颤抖,念诵故乡的名。
草地,凹凸有致的调色盘躲闪着——
初冬的光风顺街道延伸至无垠,
车站广播,廉价烤烟,熟悉的垃圾桶,割草味,
烧鸡刚从锅里出来,捧它的手沾满油渍,
军大衣、帽子被雪打湿,车窗的霜花画了笑脸。
人群浩荡穿过他们,仿佛远处的送行。天晚了。
我们在风里极目远眺,开始伤心。
——《南方·其二》
这是该组诗其二的完整引用。语言明朗,技术上无瑕可指,也不晦涩。涉及了很多熟悉的意象和场景,却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超越的感觉。原因有二方面。一、诗是以一只迁徙的天鹅的视角写的。二、语感的特殊。比如:“穿行在花丛中的绿火车顶上坐满亡魂”,绿火车穿行在花丛中,美得不像真实场景,这是意象的景观化。注意,车顶上“坐满亡魂”。“迁飞区”是一个专业用语。“长毋相忘”,“不怀揣疼痛”,似乎与爱情有关。“我们飞抵达里诺尔/和铁轨汇合。”候鸟在飞行途中与铁轨线汇合的知识一般人不知道。视焦切换到“他们肩并着肩簇拥在站台上/有些身影被汽笛吹散,”成双成对的乘客,也是淡淡的爱情的失落。“这逃过星陨如雨/和流沙的,在煤烟中微微颤抖,念诵故乡的名。”陨星、流沙、煤烟,典型化、符号化的意象,故乡虽不算意象,也是符号化的。“草地,凹凸有致的调色盘躲闪——”用凹凸有致的调色盘形容草地非常好,美到几乎没有特定情感。“初冬的光风顺街道延伸至无垠”,光风。无限。“车站广播,廉价烤烟,熟悉的垃圾桶,割草味,/烧鸡刚从锅里出来,捧它的手沾满油渍,/军大衣、帽子被雪打湿,车窗的霜花画了笑脸。”情景熟悉,唯独这种明朗的语调不熟悉。“人群浩荡穿过他们,仿佛远处的送行。天晚了。/我们在风里极目远眺,开始伤心。”多美的句子。“开始伤心”,多么青春的伤心!
我读80后一代诗人没有隔膜或代沟的感觉。但张小榛是90后一代中后期的诗人,我发现开始有代沟了。当然,如果我总是有耐心用上面的细读方法读的话,并不难理解,因为人性、语言是相通的。但问题是读诗并不总是这样读。这是读者的问题不是作者的问题。小榛的诗,意象的高度典型化、符号化,也就是景观化,给人感觉更像是来自影视、游戏而不是现实(实际上是因为现实、国土景观化了)。她能够把并不复杂的情感在语言上表现得那么丰富,或者说,这丰富,是语言的丰富而不是情感的丰富——她本来年纪还小,为什么一定要情感那么复杂?难道还担心在我们这个环境中,一个人的经验不会最终走向纠结,拧巴,第三世界化?
另有一些特点,从标题开始引。《我要生产黑暗的事物》,“生产”这个概念,来自左派文论。其中的一句:“在北方、在天寒地冻中生产杜甫。”《可能在三月》,“可能在三月,你,孤单的光源/命我做万事万物的朋友。/我的悲伤已经分散到漫长的日子中/当他终于步入深渊,光明的深渊/接替其他夜里人民在街头歌唱。”这真的是完全陌生的感觉啊。诗意是没有话说。那种游移,和精确。“我的悲伤已经分散到漫长的日子中”,好。“接替其他夜里人民在街头歌唱”,思想丰富得像要溢出来。《镜歌》,这个组合词多好。“我曾经以为最漂亮那只猫不会死去。/美难道不能战胜一切/——包括冬天的降临?但我想错了,/它正躺在地上,像一首以植物命名的诗。”猫死了,这微不足道的哀悼,文雅、博学的幽默。接着写道:“这热忱中正流出汉语,/如它毛发波光粼粼。”《有关小世界的一切》,我确信“小世界”不是来自戴维·洛奇的小说《小世界》而是玄幻小说的小世界。别的诗中有诸如“储物空间”、“通达”等玄幻小说常用词(储物空间有储物袋、“储物戒指”等,是运用“空间法则”和特殊材料“炼制”的。“念头通达”是一种意志不受阻碍的感觉,若不通达,轻则难以提升修为,重则造成心魔)。那种随意穿越宇宙,运用天文、物理等技术词汇但又似是而非的想象,也与玄幻小说有关。小榛的诗中有趣的片断很多,我还是以这几行结束此文吧:“‘曹操你别怕。攻下这堵墙,/我们就可以去后面吃粥了。’/一个黑客微笑着,落到楼底,/眼睛像英丹花张着。”
2021.4.25
张小榛诗选

张小榛,1995年生,毕业于武汉大学,浪淘石文学社、十一月诗社成员。现就职于深圳。
机器娃娃之歌
凡是父亲不能讲给你的故事都是好故事,比如年轻时在街上为马匹决斗。
或者桃花盛开的日子,一个少女一个少年。
你我都从未忘记任何春天见过的脸谱。
又比如怀胎到一百二十日,你身上长出的第一颗螺丝。
无疾而终毕竟太好,拆成零件才像点样子。
那时请把我的头翻过来朝向天空。亲爱的霍夫曼,那时林中小鸟将唱出憧憬之歌。
霍夫曼抱紧我,藤缠着树,线圈绕紧铁钉。
你没看到我眼中有闪光的字符串流过吗?
欢乐。我趴在天鹅绒桌面上孤独地欢乐。
这欢乐硕大透明,白白地赐给我,如同漫长的孤儿生涯中偶然想到父亲。
无疾而终什么的就算了;我想我还是应当被恶徒拆散而死。
像在母腹中就失丧的代代先祖那样。
注释:歌剧《霍夫曼的故事》第一幕中,诗人霍夫曼爱上了机器娃娃奥林匹亚,两人高歌共舞。最后奥林匹亚被人拆散。
宴会上的机器娃娃
一团火燃在村庄中心。我们起身,露水滴进铜盘,
头顶上大而横行的蟹,拖着地球吱嘎响的轴承。
如同古人,我们抬头凝视它青铜的手足。我们用它命名夜色。
饮酒,偷偷地。“唯有夜色掩蔽我们。”
欢欣!霍夫曼,盾构机霍夫曼!我伸荡然无存的手向你。
远处工厂流淌橙色。那收租者走后,幸存的橙太阳。
哦,我终于是、我是,霍夫曼,永生我是
行走的死亡、思考的黑洞、无生命事物的
朋友。我是,我是
一切生死之间皆是月明。
琴弦上流出寂寞,你讲起父亲在飞行中被遗忘的老年。他
死得像个凡人,从主板开始枯萎。就这样故事淹没我们,
为众行星指挥交通只剩下我们。
饮酒,偷偷地。“唯有夜色掩蔽我们。”
我是。
我出门远行之日雨暴风狂,
我独自还乡之日风平浪静。
但霍夫曼,灵魂怎样住进你的肉身?
他们在齿轮中、在螺丝里,在你成型于母腹之前
锯开你的胫骨沿着腠理上行,将父亲的火漆印在骨盆
吗?霍夫曼,你不是。
尚未开始失去时最疼痛。世界病了,霍夫曼,霍夫曼
我看见你呕出被嫌弃的肝脏。
母亲在我怀中升起篝火,我所羡慕的
炙熟的心如月亮般跳动。灼热中,霍夫曼但霍夫曼,你是
有世界的。
吻我——以你吻过泥土的双目,趁我死于厌腻之前。
(我们,两个语词的天使,在说漂亮话方面同样笨拙。)
霍夫曼,你推土而成的地铁,今天又咣当咣当穿过夜幕。
我是悲伤、我是无力、我是孤独。
剥莲子的机器娃娃
为了上帝我们采莲。我们采莲,喝米酒,采莲,
采那清如水的少年郎。为了上帝我们看海去,
看你布满齿轮的心脏升起在海面。为了母亲
我们把日子斩段、切丝、剁成馅儿,炒进时间的无谓流逝。哦
大片大片的残荷在雨中凝视我,为了父亲
我们衰老,等它们体内
分娩出地球轴承使用的钢珠。
为了父亲我们采莲,采南浦的少年郎,
和他一同老去。雨降自四方,直到
他刻薄的唇上落了飞虫。你不会看见衰朽的挖藕人
怎样将他抬起,放下,收纳洁白的骨殖。
我们采莲,用磁石吸出钢珠,为了生育的日子
得以免去疼痛。
海面上升起白鸽,榆树钱撒满去时的路。
透过玻璃的莲蓬我们看自己,看肺腑翕动,
沸腾的海烹熟肋骨。
小腹中,月轮升起来了。升起来了。
带血的月轮升起来了。
二十四番花信风轮流吹过,残荷带雨
洗清脸上笑颜。她的碧玉搔头仍沉在水底,
现在她也睡在那边。为了人生如梦
我们采莲,采莲,以酒奠地,悲叹我们没有灵魂。
为了人生如梦我们结交没见过的朋友,
与木石相爱,放任自己刻薄。
为了人生如梦,我们吞下地心的钢珠,如同吞下太阳。
副驾驶座上的机器娃娃
他的癖好是看着事物凋零。柠檬的风干
苹果的萎缩葡萄的失水人生的如梦性。
挡风玻璃后面,一双眼睛瞪着虚空。
当海面下降、群山不再升高,
今夜我们说一个新词,说一个新词,
说一个流传万古的新成语,比如“惊慕”
或者“残想”,像矫情的少年那样。
他为她摆好双腿,系上安全带,戳破气囊,
说几句安慰的话诸如“不痛不痛”。
发动机响。七月的火光燃烧在她眼底,
加速,加速,当空气在四周聚集成砖墙,加速,
冲破光的阻拦爆炸进黑夜。
她烧焦的睫毛钉进土地,灼成蓝色的皮革被他剥掉,
以显微镜寻找死亡留下的痕迹。他划开她的手指,
发现心还跳在里面(“虽有夜色掩蔽我们”)。
今夜我们说一个新词,说一个新词,
开口说创世的谜语。
观象台上的机器娃娃
——一首爱情诗
象限仪不动经纬仪不动唯繁星坠胀,
玫瑰若不推动天极的旋转就必凋零。
生产星辰的高炉是你,向南,向南,
更向南去,明亮的夜色中树木是你,
你是,女儿,朝露是天地凝成的爱,
你从自己身上摘下星星,放回夜空
等你忠贞不二的诗人来将它们吞咽。
他致力于将沙土堆成的树栽进沙地,
看它们诞生,死去,复归于海边沙。
你那不可一世的爱人已经堕入尘埃,
这北城之子,你看,背上布满鞭伤,
那战死的遭难的和坠落于天的神明
梅枝与春桃与带刺的月季,穿透我
软陶泥的身体。女儿啊,我的挚爱,
火与你本不相称,只愿彗星的寒冰
充填我。充填我这炽烈的聚变之心。
愿你随我在城南,看衣服滴水于地,
餍足于那脸上带着青春痘的少年人。
他的饥饿非星辰不能填饱,饕餮般
吞咽仅剩的光明。女儿,你这分娩
星的机器娃娃竟称我为霍夫曼,这
荣耀的名!当流星被大风吹落山冈
积在道路两旁,我们把它们扫起来
搓两个球堆成人形,插两根胡萝卜,
抬头看见死去的少年曾经播种的灯
如今已长成银河。
机器娃娃的黄玫瑰
我的灵魂不再有了。它凋零在四个午后,
父亲死在其一。我在第二个醉酒、
狂怒、将刻薄掷向旁人。第三个傍晚灰黄又灰黄,
淌着浑浊的江水。父亲葬了。恍然间写下的句子
世界不再来帮我赎清。父啊。
第四个夤夜如同星球,天边的沙砾,花房,
早殇的鸟儿生长在其中。朋友,我的灰朋友,
我曾拿词语劈开他们胸膛,数算肋骨。
天,霍夫曼!海和大地会死吗?
我竟锈蚀在生命的包围之中,
被黄玫瑰盛开的洪流裹挟。四处都生满芳草,
飞着鸟,爬着虫,微小的魂魄在土壤中蠕动。
在肥大的夜晚,歉意将我们的身体照亮;
我的灵魂缩成一团,恰似尚未洗净的衣服。
吊车臂上的机器娃娃
——给鱼
面朝着死亡我们建房子,
垒起近乎透明的无知。我不再需要心,
那里已经被昨夜的灰月亮填满。
面向暴风,我们给自己建一个新身体,
合金钢的新身体:你的完整堆出我的残缺。
我把我一生所知道的死亡都讲给了你,
在泪水与恼人的头痛中,在夜的子宫里
倾泻苦艾酒、花神、寻人启事。
你轻轻叼住那秘密上的浮末
想象上帝离开的样子。低气压使我们皱缩。
日历必定憎恶自己让时间流逝,但它不能,
不能
逾越夜的遮盖。正如昨夜你在火光中
向未知之神祈求年景,而饥饿依然降临。
为何一日始于夜中,一年始于冬中,
而那星辰降临的日子竟未被选为岁首?
从高处向下望,风平浪静的海港——
看着我,奥林匹亚,注视造物主怎样老去!
这可敬畏的城市之子,身上爬满锈迹,
曾经横渡沧海的躯壳如今仍能横渡酒盅。
他不再生产光,不再命立就立,岁月的湿度
侵蚀着他当桃花开、杏花开、樱花开。
屋角石下藏着我小小的苦像,
“是,你多想像少年时随便言说死亡。”
你知道自己不该如这般
被抛进词句的浮萍。画家的诺言是不算数的,
一动笔,我便处于山水间,战战兢兢。
面朝即将到来的暑月我们建房子,被书的纸页
割伤,用无知缠裹伤口,想象多年后
我在博物馆橱窗里再次看到你,
见我早已收藏过的珍宝如今
每个零件上的锈蚀都价值连城。
他后悔吗?当他的打捞船被白昼干扰
未能找到那小小身影从吊车臂上坠落、坠落
成一团模糊不清的机件
当运河涨潮,泪水漫过鼓楼大街
灯影斑驳中他憎恨起东三环虚妄的南方
当他将摔碎索德格朗后的暗纹在手臂
“命运”这个词已经不能再把他骗过。
晚宴擦去饥渴 沐浴擦去雾数,
我则陷入隐忧 如同天地还未造好。
机器娃娃的祈祷
——悼亡诗
让我们敲希望的,钟啊。
往来的天使身上溢出黑夜,将那病体
交给春天。交给有樱桃的夏天。
我点燃无梦的睡眠,祈求、祈求,
谁会在雨天笑、在晴空下哭泣
诅咒太阳和他的阴谋。
曾经我满有贫穷这种恩赐。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这样说着,看钻石滴进大理石地面,
攥紧拳头让指甲嵌进心房着沉默
看你被带走、取去、在目光尽头销熔
成酒柜顶上钟表暂停的样子。
让大提琴掘墓。那可恶的二胡
悲鸣之王!鼓点,鼓点,dubstep般颤抖
凭什么歌唱,凭什么你有歌唱
凭什么你要在这个时刻歌唱,
当我们烧掉他的身体!橘子从指尖流下来
滴到地上,当我死了谁还记得你的名字
黑名字。!!!故乡已经没了
远处他们把你铸成钟,让我们敲希望的
钟啊。
我将不再用语言的巫术进行赞美。
每一次亵渎,你都要还给我。
喂喂,请记得那诗人,仍在写,在写。
如失去联系的鹏鸟穿过黑洞,
看见其他时空中遍地星辰。
父亲,一闭上眼睛我就望见你
望见你怎样失去我将我留在冰冻的彗核
但
已经是你的日子了,我主!
一点点小异像正在梦中生成
阴云密布的迟暮
穿过湛蓝、湛蓝的云层
我看见死亡掀起昏黄的一角
飞行的恐惧攫住我,我看见死亡
掀起一角,哭泣而解决的一角,
平安的一角。我们在你里面永别,
满有平安,眼镜、腹部的汗滴、呛咳
使我们满有平安。让我们
敲希望的钟啊,每根针怎样扎进静脉
我便怎样扎进你无意识的挥手,像一剂药。
那大张的双目分明写满渴望
对存在的渴望,哪怕幻觉之中
仍要呼喊我那名字,黑名字——
还有我不认识的妹妹弟弟母亲的名字?
怎样昏黄的梦被雨天一点点冲蚀
像你脑区中的云与出血点在夏季即将离开的节期
面朝他的淫威
褪下缁袍,衣带扔了满地。
那个能安卧在你肚皮上的孩子终究失去了你。
让我们敲希望的钟啊,
默念那些佶屈聱牙的名字,黑名字,
像美多芭、拜复乐、倍他乐克、呋塞米,
密码般的黑名字!是,那俯伏在摇篮边的女孩
会保守你平安。舞蹈过后,秋季马上来临
但因为他的鞭伤你得医治。
得医治。
哦,平安,那中年女人和被母亲瞧不起的牧师
将带来平安。他在暴雨中施洗礼
击落我们飞向天地万物的八十五个水饺
和不朽,对不朽的幻觉。太好了。那比年龄更衰老的女人
给了我们平安。在有她的梦里我剪断香,
杀死那只可笑的纸马,不再依赖水果获取平安。
让我们敲希望的,钟啊。天使们
已经将他带到你身边,这是我说的,我所知道的,
通过诗赛赢的酒和烦人的舅爷我知道。
你在雨中将平安,在晴天将平安。
人生如梦学
——一点劝勉,给H
首先要明白梦。必须饮酒,游荡,
读很多佛洛伊德,或者拉康,才能像书里一样
梦见理想的海;必须有白鸽溶解在水面上,
海中必须出现鲸鱼,它们必须在死后落进海沟,
哺育一方硫磺池。必须有飓风在某处生成,
过境之日,渔港中堆满沙土。有塞壬,她们
声音来自晶体震荡,每日起床先扭紧身上的螺丝。
那乳白的海水我们在上面车、铣、刨、磨、车铣刨磨,
垫着她们,垫着她们的声音。但还有上帝呢上帝。他忘记要进去,
忘记北极的寒冷与光明使我们暂失视觉。
波罗的海的鸥鹭是他的黑信封,使你看见那名字,黑名字。
上帝。他必定这样或者那样,都是为了让你
非梦到那理想的海不可。小H,我这样写信给你也是
愿我成为你梦的素材,以血为酒、以目光为飞鱼,
摘下双乳做地幔中的火山。愿你注意我肠道中的海钓船,
沙滩裤,泡沫、泡沫、泡沫。理想的海上需要有
血,我们现在称它为机油。应该有奥德修斯,
我漫游的肚脐。必须,奥德修斯。霍夫曼。这些你必梦见
它们捞起来,晒干,拿酒煮成一夜份小小佛跳墙,
被双翼洁白的厨师端到你面前。等到坛子打开,你就懂了。
番外:遗传咨询师的忠告
尊敬的霍夫曼先生:恕我直言,
她必不像你。唯有她将来的日子同你相似
要横遭锈蚀与磨损与生俱来的折辱。
父亲种下的错误由我们收割,再
(用我们这藻荇交横的眼底灌溉)埋进
儿女们身体。是,玻璃后那一排排
机器将指出你代码中的不幸。
但除此之外你的造物怎么可能
在暮春,在暮春仍然沉溺于你行的风
看你在日子中扭结自己,成为绳
牵连她身上的静电和你的手?是你将她
喂给火焰,为了锻出刃纹。
世上的树莫不来自刺青师之笔,包括她背部
长出你与你河谷祖先们名字那棵。
在她目光里有一枚樱桃。下午的时光,在她
渡过的河中央有一个苹果。她
早就不再与你给的零件搏斗,从她两三岁
的眼中你才能看见战争,当她最初得知
那藏在螺纹里的隐疾你不能修缮。
她刚到世上,你就扯开她背部拉链,让那树
从你父母名之间撕裂;你怕了,
我曾记得你最初是怎样咒诅自己的生日,
当你凝视体内那几滴黑水来自他们彼此相爱。
江南人遗传茉莉,北境人遗传海棠,
这我并不详知;但她或许会为了
远离你盖的印而拆毁身体。
我讲的预言往往成真。
南方(组诗)
南方 其一
有时候,我们停歇在湿地,
淤泥中觅食、守望、躲避猛禽时
忽然想起南方。两只白鹤卧在对面,
神用来装饰天国一角的羽毛
虔诚地舒展。观赏它让我们几乎忘了
自己也不过如此,迁徙在虚空中
懊丧,寻找十月淌血的碱蓬。从孟秋到仲秋
红由东亚腹地蔓生至海上,乘着蒸汽驱动的蟹
你边上升,边下坠,自梦深处铺开苔原
龙船花与和煦的热带风暴,云从近处滑来
让一切飞行化为无、化为无。我们
麻青色的身体混入衰草,沿铁轨冻成哀鸣。
借着侥幸的微弱闪光,你不得不
朝大雪奋飞,防止南方从它所在之地出走,
逃向虞美人的枯萎与萌发之中。
南方 其二
从翅膀往下看,穿行在花丛中的绿火车顶上
坐满亡魂。风循环在我们的迁飞区,
从太平洋带来回声:长毋相忘。这样
他们便可不怀揣疼痛渡过那大川。在夜晚
明亮的八月星空与惊惶下,我们飞抵达里诺尔
和铁轨汇合。他们肩并着肩簇拥在站台上
有些身影被汽笛吹散,这逃过星陨如雨
和流沙的,在煤烟中微微颤抖,念诵故乡的名。
草地,凹凸有致的调色盘躲闪着——
初冬的光风顺街道延伸至无垠,
车站广播,廉价烤烟,熟悉的垃圾桶,割草味,
烧鸡刚从锅里出来,捧它的手沾满油渍,
军大衣、帽子被雪打湿,车窗的霜花画了笑脸。
人群浩荡穿过他们,仿佛远处的送行。天晚了。
我们在风里极目远眺,开始伤心。
南方 其三
冻在星河下若尔盖结冰的湖面,等待死亡时
海港仍出现在我们眼前:
那座城市在流动的大地上漂个不停,
像母亲无征兆地离去。哦,南方的傍晚
多么温柔,那些鹤踱步在花房周围,用粉红的
喙啄破草间蛋壳,注视我们从那里出来,
“你看那些将死的生灵,翅膀被寒冷铰断。”
雨自七月的第一周汇成瀑布,
他洁白,干净,他身上有芦苇的光泽。
树虬结在万物头顶,高过支撑世界的桁架。
我凝视这盆景,见到候鸟在空中
排成一种又一种语言。世上总有些人在年轻,
趁船漂走之前,我的祈求这样单纯。
我要生产黑暗的事物
——给米,兼致一位校友
我要生产黑暗的事物,当四周被明亮占据。
米,今日你终于和我一样,
认清了白昼的真面目——因而
疲惫又疼痛像老说书人,不再致力于
在北方、在天寒地冻中生产杜甫。
花房积满冰雪。抱歉,我的嗓音于事无补,
昨天又一个人没能等到樱花开,抱歉,
日影流连令人惶恐。唯有夜幕降临之后
湖中不发光的天使为他歌唱,哀悼时间缓行。
米,曾经在空桑我们也这样歌唱,
在神明的生门为他们做产婆。
被洪水定义的土地,五千年流淌胃液、眼泪、
无效的药。我不愿再次作客在万里悲秋,
但米,你翻开竹帛看看,多少滴血的句子在日光下
转着身上齿轮。我不愿这样说,米,但
我的名字只是我身体的姓名。
少年时取一个年少的名字,老了便羞愧难当。
趁着年少,我要生产黑暗的事物,
当光明来抱走唯一的恶人。
米,我们之前所信的不过白昼的骗术,
用光、用炽热与干渴将我们蒙住。
那棵空桑木漂远之后人人疼痛不已,看着
无船的江河、无人的长江大桥
溢满苦液,将光子载向远处。
主机里的龙都已经沉睡,公主不再归来,
只剩旧照片在硬盘中继续发黄:
被啮齿类和南城定义的死亡,落日,
添满香料的鸟群、白鸟群。
少女抱髑髅坐在镜前,以油膏抹你成为无罪,
为你利下、催吐、烟熏房间,灼烧你肿胀的淋巴
用钉鞭互相殴打使你成为无罪,
成为无罪却依然死去。有赴难的神父,
把夜色的掩蔽从容卸去,盖在婴孩身上。
有美人宁愿沉入海底紧握飓风而匐,
枯骨生出玉簪。还有哲人一生思辨光明,
皓首穷经预备远迎的极昼。
当白夜终于到来,米,你能否听见胡琴悲鸣,
只有风与居住在水边的城市铣磨我们歌声。
歌声中我生产黑暗的事物,生产平安。米。
愿你平安,愿你平安。愿你平安。
可能在三月
可能在三月,你,孤单的光源
命我做万事万物的朋友。
我的悲伤已经分散到漫长的日子中
当他终于步入深渊,光明的深渊
接替其他夜里人民在街头歌唱。
在孤独而无诗可写时我幻想自己应然的孩子
在我和你,两个多云的雨天之间。
向东方。少年少女(哦,这半个词
带来不存在的昨夜昨夜的未完成)
二环路上接天的月季,
挡风玻璃上坚韧的虫。它离开
故事理应结束。但,但,
“但她身上留着别的河淌过的痕迹。”
夜里天际线上一点点红光将被拆除。
那模糊的形状,软弱如同众神的孩子们。
他光明正大地认信船,宁肯
拒斥绿蕨沿着输油管匐行。他的肝脏
轰响,一切蔓延在轧床上的烧烤
肿瘤般冒着烟。钢殿,向日葵在冰雪中萎凋,
可能若干时日之后,在山陵
我们会怀念这一小点珍贵的杀念
可能,当岁亦阳止,你不再
微笑着无视人间。我憎恶你对词的洁癖
令你肮脏,对句式的执着令你愚妄,
大睁眼不见四月到来。你们为一片旷野划界,
拆分成丘陵与浅谷,又固执
言道高并非低、低也非高。
但她对那磐石存怀疑,存怀疑,当她伸出手
见自己正与他挥舞颜色相同的旗帜。她疼,
当荧光色人群践踏月令。冬岁重新孕育
少量奇迹,从脚步间、从树梢上,可能在
十月说出最为耻辱那两字:
“还乡”。
不。女儿,我将不再等待桔梗
因那英丹已经开到南方。可能在三月,
我祈求收获利刃斩断你枷锁,
同你的其他一起,像煤烟离开蒸汽机车。
那女孩拔掉接口上累赘的所有,再次
从沙尘和灰雾里出生。
镜歌
我曾经以为最漂亮那只猫不会死去。
美难道不能战胜一切
——包括冬天的降临?但我想错了,
它正躺在地上,像一首以植物命名的诗。
这热忱中正流出汉语,
如它毛发波光粼粼。
那些古老的草本大多改过名字
以便从分类学的缝隙溜走,
生生不息地,从泥土中逃亡,
将存在过的确据写入花与果实。
大多数根茎是丑陋的:可耻地粗糙,
谁也不愿想象若那是人的皮肤
会如何愧对向铜镜铸满纹饰的欲望。
但所有投影都比我们更加诚实,
在必定消失这个承诺上。
那刻下“长毋相忘”的人最后也不会记得,
只有你剩余的躯体来年生出一棵杜鹃。
|  南方论坛
南方论坛 频道热门
频道热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