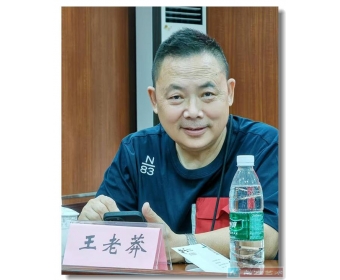廖伟棠 | 假装读懂一首诗,是诗歌最大的敌人
|
“诗歌”二字,仿佛离人们过于遥远,而当代诗人中,除了海子、北岛等已被大众认可的诗人,其他诗人的身份,在大众眼里有些陌生。 在诗人、作家廖伟棠看来,“爱读新诗的人觉得旧诗太陈腐,离我们太遥远;爱读古诗的人觉得新诗太新,无法沉淀出来诗意”。虽然其中存在对诗歌的误解,但不得不承认,阅读新诗会让人拓展想象力。 下文中,廖伟棠以诗人周梦蝶、西西以及保罗·策兰为例,为大家详细分析阅读现代诗歌时的愉悦性、想象力,以及现代诗歌与古典诗意中那种古今相通的美感。 下文摘自《我偏爱读诗的荒谬》,经出品方授权推送。 新诗与古诗水火不容吗? 心里有绿色,出门便是草 我想你肯定是基于一种对诗、对美的爱打开此书的,那我们就从爱说起。 有的爱令人宽大,有的爱令人狭隘,但很不幸,作为一个新诗写作者,我经常感受到一些人出于对古诗的爱,对新诗怀抱着质疑态度,甚至带有某种恨。因为他们觉得古诗已经是完美、至高无上的,一提到古诗就沉醉得一塌糊涂,恨不得背出《全唐诗》来。但一提到新诗,就一脸不屑,觉得多读几句都会玷污对诗的想象。 这扬古抑今的态度,不但在民间的诗词爱好者里常见,有时候在某些知识分子或者研究古典文学的教授所写的文章里,也常常流露。前两年我看到一篇文章《诗歌是个人朝圣,与集体无关》,按理说是一篇专业的文章,但里面也夹杂着一两句对新诗的偏见与误解。比如他说:“在我看来,首先,诗歌应当具有音乐性,要能背诵。现代诗大多是分行散文,只能看,不能读。”这两句话很能代表公众对新诗的偏见与误解。 新诗和古诗,尤其是好的新诗和好的古诗,真的这么水火不相容吗?其实归根到底,还是两种读者的爱所导致的误解:爱读新诗的人觉得旧诗太陈腐,离我们太遥远;爱读古诗的人觉得新诗太新,无法沉淀出来诗意,或是新诗缺乏音乐性,等等,双方都有误解。 其实,新古相通。我经常在一些古诗里读出强烈的实验性、先锋性,当然,也在很多新诗里读出它们和古诗的相通;除了相通,还为古诗“招魂”,让古诗翻出新意来。就拿公认最像古人的新诗诗人周梦蝶先生为例好了。
诗人周梦蝶(1921年2月6日—2014年5月1日) 周梦蝶是当代诗人,所有见过他的人都感觉他就是传说中的仙风道骨。他相貌奇古,举手投足像从桃花源里走出来的人物,当然,他的诗更是,他跟古代、古诗是亲密无间的。——不,我说错了,他是亲密,但不是无间。 这个“间”是什么?就是新诗特有的一种疏离。在新诗里面,疏离是一种技巧,它可能来自现代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是诗歌让人拓展想象力的途径。意象与意象之间,句子与句子之间,越是跳跃得大、疏离得狠,留给读者的想象空间就越大。这就是新诗的魅力所在。 周梦蝶先生恰恰读到了古诗里的疏离感,再以一个现代人在现代生活里所触碰到的疏离去呼应之。正是这种亲密中的间隙,让他接通了古诗当中的现代性,从而让古诗复活,而且是非常活泼地复活。 我很喜欢他的一首晚期诗作《善哉十行》。 善哉十行 周梦蝶
人远天涯远?若欲相见 这首诗那么打动我,确实跟古代有关系,里面出现好些古代诗词、戏曲中的场景,“流萤提灯”“蕉窗下久立”“前庭以玉钗敲砌竹”。但周梦蝶强调的是“不劳”“不须”,他要讲的是不用古典辞藻我们也能通古。 他通的“古”是什么?熟识古典的人,应该会从这首诗想到《论语》里的一段名言:“‘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意思是,唐棣树开的花在风中翩翩地飞舞着,我难道不想念你吗?只是我家离你太远了。但孔子幽默,他反将一军,好像在笑话这首诗的作者,他说:哪里远?明明是你没有真正地想念对方,你要是真想她,她马上就会出现在你眼前,在你脑海里,在你心里,哪里有什么远不远? 多么可爱的一个孔子,跟我们想象中的老夫子、孔圣人是两回事。周梦蝶也是这么可爱的人,不要看他仙风道骨,一个老人家,他的诗充满孩子气的天真和真诚。 但他难道只是用这首新诗去演绎孔子的这句名言吗?并不是。我们还要留意他某些很不符合旧诗习惯的细节。他说,“你心里有绿色/出门便是草”,这句非常特别。在古诗里常见的是“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这样的句子,是先有自然再有心像。所谓的意境,是先看到一个境,才生出心里的意。草地、青草、树木先存在了,诗人才说自己心里有绿色。 但周梦蝶老先生说,不一定,我心里有了绿色,看到哪里都是青草,哪里都是绿色。这简直可以令人想象一个动画般的场面:周梦蝶先生坐在家里,心里想到绿色,他一推门,绿色就哗啦啦从他的门口向四周蔓延,遍地遍野都是青草了。这就是新诗的主动性和旧诗的被动性之间的差异,新诗反而更加贴合孔子所需求的“之思”,你要主动去思念,然后才能逾越这种遥远的距离。 接下来很不旧诗的,就是音乐性。“心头一跳一热,微微/微微微微一热一跳一热”,这里含有一个节奏,可以说是简单的,也可以说是复杂的。简单在于,它模拟的就是心跳的节奏,复杂在于里面有一种婉曲——他心跳了,又想去压抑,但又压抑不住,所以才有中间的微微停顿,然后慢慢又跳动起来了。你可以说这是一种思念,一种爱,也可以说是老年人的一种克制。一个老年人,无论怎么克制,他还是心肠热的。 你能从里面听出那些否定新诗的人说的音乐性吗?读一首好的新诗,就能证明新诗的音乐性不是少了,而是多了。新诗没有格律,恰恰解放了它的音乐性,没有界限,就意味着无穷的可能性。过分强调格律诗和韵脚里机械的、表面的音乐性时,我们怎么能超越音乐本身呢?因为诗歌无论怎样追求音乐性,都无法跟音乐本身相提并论。正是因为对所谓音乐性的不满,才有了诗的发展。 你看,以上的解读已经存在大量需要调动你们想象力的情况,甚至你要想象自己在拍一部电影,把你看到的诗句,像看剧本一样,在脑海重现,才能够把这些跳跃的、巨大的句子透过蒙太奇手法,连成一部电影。读旧体诗,难道就不需要这种想象力吗?阅读杜甫、李商隐、吴文英这些以实验性著名的诗人,更加需要想象力,一种积极的想象力。阅读新诗不过是把这种想象力承接过来,更加调动起来。越是读挑战性大的诗,越能在读到它、读通它的妙处时,得到更大的阅读愉悦。 长大了,就做热水炉吧 有些新诗是以现代方式复活古意,譬如刚刚分享的周梦蝶的《善哉十行》,但新诗与古诗的关联还不止如此。在新诗里还有一类诗,是以散文化、口语化的形式,去处理在古诗里往往是任重道远的主题。 关于诗和散文之间的界限,有一位神人废名早就说过,古诗多数是散文的内容包装以诗的形式,而新诗,是用散文的形式去承载诗的内容。这两者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其实相当多的古诗,如果剔除表面华丽的辞藻、平仄押韵的讲究,就是日记和应酬诗,只不过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文字被雕琢得琳琅满目。 当然,真正的大诗人例外。但即使是真正的大诗人,就像杜甫、李白,也有的是这种拿手到擒来的诗的语言,去包装那些相当乏味的题材的诗。
废名(1901年11月9日—1967年10月7日),中国现代作家、诗人、小说家,在文学史上被视为“京派文学”的鼻祖。 为什么说新诗是用散文的形式去承载诗的内容?那是一种更高的要求,意味着我们对世界万物的洞察里,本身就应该包含着诗意,并且用散文的方式去书写那诗意。散文的形式,不但没有削弱诗意,反而能够让我们更好地亲近这种诗意,并且在貌似没有诗意的文字之中得到顿悟。 古诗有一个传统说法:“诗言志”。诗以言志,很难不沉重起来,尤其在我们的民族命运里。新诗则不然,新诗的形式比较灵活,言志的方式也就更加灵活。我们不妨看一个更极致的例子,跟周梦蝶相反的一种写作方式,西西写的《热水炉》。 热水炉 西西
妈妈问我
做了
做了
我希望
我并且要和别的
我们还要
如果冬天到了
妈妈很高兴 这首诗简直有点像是从麦兜动画里截取出来的,像是傻乎乎又热心帮人的麦兜小朋友跟妈妈麦太的对话。麦太已经困了,但又被这么可爱的孩子所感动,就说:那好吧好吧,你去做热水炉吧。 这首诗模仿的是我们小时候经常会被要求写的一篇作文——《我的理想》。老师期待你写“我要做科学家,我要做教育家,我要做这个家那个家”,最不济你也要说“我长大要当老师”。但是顽皮的西西小朋友,她说长大了要做一个热水器(热水炉就是香港对热水器的称呼),这样就能让一切都暖暖的。小时候我们可能真的会这么想,想做一辆汽车,想做一个机器人,想做一盏灯,甚至想做一个根本没有什么象征意义的事物。 当然,诗人毕竟是诗人,她像孩子一样随口说出要做一个热水炉的时候,并不真是随口说的。西西以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成名,一般的理解,她是很西化、很现代派的一位香港作家,但她写诗的时候却分外孩子气,也可以说这是一种赤子之心。 赤子之心,是古代儒家很强调的,只不过大人反反复复说赤子之心,其实早就把它不知抛到哪里去了。在这首诗里,我看到西西跟儒家的相同之处。那就好玩了,一首这么口语化甚至是活蹦乱跳的诗,怎么会跟想象中正襟危坐的儒家有相通之处呢? 这就是诗人的奇妙。她通过这首诗,让我们发现儒家是具有现代诗意的,也可以说现代诗当中的爱复活了儒家中的仁。仁者爱人,仁者强调爱,而且他是爱其他的人,他具有丰富的同理心。
西西,作家、诗人 受儒家影响的诗人陶渊明,在给他儿子的一封信里写过这么一句话:“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他送了一个仆人帮儿子干活,特意叮咛,这个仆人也是别人的儿子,就像你是我的儿子一样,你应该像我对你一样去好好地对他。其实这也是在阐释着孟子“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 不过我还是觉得遗憾,陶渊明仍旧板起面孔写什么“命子”“责子”“示儿”,多少还是一本正经地期待自己的儿子能够完成儒家使命,成为儒家所期待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至少是立德立言的人。 西西是纯粹从孩子的角度去写这样一种精神,这就是决定性的瞬间。她不像陶渊明那样,从成人的角度要求自己的孩子有赤子之心,她就是赤子之心本身。古诗里诗人板着面孔训人,新诗里诗人是自己;古诗里仁者要爱人,新诗里仁者先爱自己,然后才能推己及人。 西西是用孩子的童心去推己及人。整首诗看下来,她先从自己的妈妈延伸到别人家的孩子、别人家的妈妈,甚至延伸到地球万物。这又是一种超越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想法,她不是先立人,而后兼并天下,而是朴素地直接思索,人与河流、泥土、鸟兽,与万物都是平等的。这又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的生态主义思想是相呼应的。 这样的诗意拓展,我想就算读给小孩子听,他也能听懂。这难道不就是古代诗人期待和推崇的所谓诗教吗?而且西西可能比很多古代诗人做得还要成功。 除了这种诗歌内核的古今相通,还有很多从技术层面继承和转化古诗美的,比如我接下来要讲到的卞之琳、张枣。
诗人张枣 / 1986年成都 / 肖全摄影 新诗难懂,是否故弄玄虚? 有人曾经问我,诗人是不是语言骗子? 不知道这话是褒是贬,如果是褒义,他可能是觉得诗人把语言用得太花巧、太漂亮了,通过这样的方式把想要灌输给别人的思想暗度陈仓,用这些美好的辞藻骗取读者的心。这是善意的理解。 要是贬义,那他真是觉得诗人只是巧言令色,实际上空洞无物,甚至就是故弄玄虚,让大家看不懂,然后觉得高深莫测。其实后者才是问题所在,很多人对新诗的第一印象就是读不懂。 诗如何读懂,为什么非要读懂,读懂读不懂的标准在哪里,对诗为什么要追求一种懂,想清楚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够继续下去。 说新诗读不懂,有一个潜在原因是对新诗的质疑,读者对这些诗人未必信任。新诗跟已经经典化的古典诗歌毕竟不一样。对于经典,我们有一种心态,觉得它是高山仰止,读不懂,是自己的问题。 但是面对同代的新诗写作实验者,就有点看当代艺术的将信将疑,觉得也有可能这个诗人是故弄玄虚。确实有些诗人是故弄玄虚的,但这本书里推荐的诗人,是绝不故弄玄虚的。我写诗的一贯要求就是不打妄语。打妄语,是对诗歌的真诚的一种侮辱。那么,有些新诗为什么看起来还是那么玄虚呢?这就是这一章想探讨的问题。 其实诗歌也像冯唐说的,的确有一条所谓的“金线”的存在,这条线以上是诗,这条线以下是不是诗呢?这当然不由我们来决定,只是说诗歌的确是有好坏之分的,有更加认真的诗,跟人的心性更加相关的诗,和更加虚假的诗,用励志格言来营造销量的营销性的诗。 现在,我们因为把诗发表在公共网络,这就衍生出一个问题——它是好也是不好——你会碰到很多所谓的非专业读者。但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要求诗需要专业读者来读呢?唐诗、宋词估计是不会有这种要求的,但是随着诗歌的精致化,随着诗歌的门槛逐渐提高,对读者的要求也不能不提高。 说诗读不懂、写得不好倒无所谓,我最怕的是捧杀。这种捧杀还不是到位的捧杀,比如你写一首政治隐喻的诗,他就会说你像北岛;如果你写一首意象跳跃或者装疯扮傻的诗,他会说这不就是顾城吗?或者更糟糕地,他说这诗太诗情画意了,太浪漫了。这样的评语真的很伤新诗写作者、认真的实验者的心,这样简单化地捧杀,把诗人和诗都符号化了。
北岛(1949年8月2日—),当代诗人、作家,朦胧诗代表人物之一 这种误解,当然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归咎于诗教不力,或者说诗人脱离人民大众。这样说很容易,好像也立得住,但往更深处去想,还是因为在现在的语境里,日常语言和诗歌语言这两个语言体系之间的误会和冲突实在太大了。 这种语言的落差折射出来的,就是不同的文学观和意识形态的需要,导致不同的语言选择。而这些就决定了一首诗的命运或者一个诗人的命运,所以我也很希望这本书能够稍微纠正一些观念。 这个问题曾经发生在一个大诗人身上,犹太诗人保罗·策兰。他成长于德国,“二战”中全家被抓到集中营,父母都死在里头,他幸存下来,移居到法国,但最后仍不堪记忆的重负,也是深深地感到民族的命运和自己的诗歌不为世人所理解,终于以自杀来了结自己的生命。
保罗·策兰(Paul Celan 1920-1970),二战以来影响最大的德语诗人 保罗·策兰的诗震撼了世界诗坛,大家认为他是自里尔克以来最伟大的用德语写作的诗人。他最有名的一首诗叫《死亡赋格曲》,最广为人知的中文翻译版本由北岛所译,收在他的《时间的玫瑰》中。 赋格曲是一种古典音乐形式,通过不断地重复变奏展开,形成一个高度繁复而迷人的音乐结构,巴赫就是赋格的大师。这首《死亡赋格曲》收录在1952年出版的保罗·策兰的诗集《罂粟与记忆》中。以下是孟明翻译的版本。 死亡赋格曲 保罗·策兰 孟明 译
清晨的黑牛奶我们晚上喝
清晨的黑牛奶呀我们夜里喝你
清晨的黑牛奶呀我们夜里喝你 这首诗似乎有一种魔性的魅力,一方面来自它的音乐性,如我刚才所说,它在模仿赋格曲,一种循环往复的节奏。 诗人为什么要选择赋格呢?不只是音乐性的考量,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对德国文化的沉痛反思。赋格是由德国的音乐大师巴赫发扬光大的,很多人提到赋格会想到德国音乐。但是不要忘记,在纳粹德国时期,那些死于集中营毒气室的犹太人经历了什么样的命运。 有一部纪录片记录下来,当时的纳粹军官一方面让那些懂音乐的犹太人组成乐队为他们演奏巴赫、贝多芬、瓦格纳——这是德国音乐;一方面,他们听着音乐,然后把其他犹太人赶进毒气室。这些演奏音乐的犹太人也不会活太长,也会死得很悲惨,他们甚至还要为死难的同胞和自己挖掘坟墓。 这个史实,不但恐怖,更动摇了我们对文明的想象。为什么同样一群人,可以既喜爱那么高雅的音乐,同时又做出那么野蛮的屠杀自己同类的行为? 哲学家阿多诺从中得出一个结论,他说,奥斯维辛以后,写诗是野蛮的。经历了这样一种对人类文明的质疑,如果我们还从事艺术创作,是不是就成了凶手的帮凶? 作为诗人,我不认可这样一种质疑。诗歌正是在抵抗着文明的疯狂,就像策兰写下这首《死亡赋格曲》,成功地质疑了纳粹德国人所做的事情,同时还通过这首诗,把犹太民族曾经经历的命运戏剧性地推到了我们眼前。 这首诗用的是舞曲一样的节奏,写的却是极其可怕的事情。为什么牛奶是黑色的?为什么我们要晚上偷偷地喝,要喝了又喝,无时无刻不喝下这种像是我们命运一样的东西? 诗中写“德国的大师”,“大师”这两个字非常讽刺,一般我们用它来称呼贝多芬、瓦格纳这样的艺术大师,但这里的大师是一个杀人的大师。他善于杀人,一边叫受害者演奏音乐,一边挖掘坟墓。而且,他所造就的罪恶不但施加于灰发的书拉密(犹太人),也让金发的玛格丽特(雅利安人)负罪。 最后诗人说,“我们在空中掘个坟墓”,这意味着毒气室。犹太人进去以后,毒气也好,他们的灵魂也好,甚至他们被焚烧之后产生的烟雾也好,都飘往天空,所以坟墓是在空中的。 他说“躺下不拥挤”,这是指也许死去比活着还要舒服一点。因为在集中营里过着那种非人的生活,犹太人巴不得早点离开残酷的人世。 这样一首悲惨的诗,但同时又强烈地质疑着所谓的来自德国的大师,质疑着所谓的艺术准确性。准确性不只体现在音乐的对位和对艺术的要求,同时他们用子弹打人也是很准确的。 这首诗发表以后,得到了德语批评界莫大的重视,但是也有相当多的解读,令策兰从哭笑不得到深受伤害。对于犹太人——一个集中营的幸存者来说,这种来自德语的解读,注定是一种误读。 策兰说过,他最大的悲哀,就是要用杀害他父母的凶手的语言去写诗。因为他是一个受德语教育、用德语写作的诗人,这造成他一生最大的痛苦。 那些严谨挑剔、艺术品位非常高,但是又在潜意识里抗拒承认自己曾经犯下罪行的德国人,他们都把眼光集中在《死亡赋格曲》里那些超现实主义的意象,那些反复而迷人的节奏。有人甚至说,他们在诗中对立的残暴与温柔里,得到一种像禅师开悟一样的体验。 著名的诗人批评家霍尔特胡森甚至说,策兰通过大师级的技巧,制服了一个恐怖的主题,使他能够逃离历史中血腥的恐怖之室,上升到纯净诗歌的苍穹。这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大师”这两个字正是策兰诗里谴责的对象,用大师来形容受害者策兰,这相当于在伤口上撒盐,完全违背了策兰写诗的初衷。这位德国评论家认为,诗能够逃离历史的血腥去到一种沉思的境界。这种说法意味着对现实的逃避,甚至纵容。有的德国人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回避历史的审判。 诗歌里的现实被这些高雅的读者美化成令人赞叹的诗歌的隐喻艺术。这个犹太人策兰,这个幸存者策兰,被忘记了。被记住的,是一个优秀的德语诗人策兰。这对他构成了最大的伤害。策兰很多年以后都忘不了这种伤害,最终选择自杀。 我讲这样一个沉重的故事,想说的是,假装读懂一首诗,甚至故意误读一首诗,是诗歌最大的敌人。所以问一首诗是否故弄玄虚的时候,其实还算是一个公正的诚实的读者。从这里出发,而不是假装自己读懂一首诗,其实更有发展下去的可能。 策兰对今天的诗人至少有两点启示。第一,一个诗人要反叛地具有宗教情感,那是一种像《圣经》里的约伯那样不断质问神和终极价值的努力;第二,诗人要时刻保持对语言难度的挑战,在语言上设置很高的自我目标,以期望得到更大的超越。 人人都可以写诗,参与诗人的队伍,但是只要你选择了写诗,就一定要努力精进,让你的母语在诗中得到一种新的面目,得到一种新生。新生不可能是容易的,我们都知道语言的新生决定了一种文化的新生。战后策兰的写作可以说给德语换了一次血,我们的汉语也期待这样一个诗人。最后我想再分享一首策兰的短诗《法国之忆》。 法国之忆 保罗·策兰 孟明 译
跟我回忆吧,巴黎的天空,大秋水仙...... 这首短诗可以理解为爱情诗,也可以理解为政治诗,当然归根到底它是关于我们的存在的。我不打算做更多的解释,因为我确定策兰不是一个故弄玄虚的诗人,你一定能够感受到这首诗里的“我们”真真正正就是指的我们,我和在读这首诗的你。 当你能够感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能领悟到里面的超现实场景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邻居莱松先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难道不存在吗? 诗当然是没有门槛的,但诗又是有很高门槛的。日常语言在频繁地使用之中,让母语变得越来越熟悉,但是也越来越麻木,越来越失去诗意,失去光彩。诗歌语言就是在不断地擦亮母语,让它重新焕发出光彩。它是在追溯语言的源头和破坏语言的承袭。日常都这样用语言,已经用熟用烂,我偏不这样用,我要挖掘语言的潜能。 当然这些都给诗歌、给写诗和读诗带来了难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读诗会有惊喜感、会有新鲜感的原因。我想这就是日常语言和诗歌语言最重要的不同。 本文节选自
《我偏爱读诗的荒谬》 |
 南方论坛
南方论坛
 频道热门
频道热门
-
鬼金的小说与绘画
它们以慢的形式推进着,就像刀子,在某一个虚构的想象中,在推进,推进,直到划开皮肤,呈现出白色的茬,然后才是肉,才是红色,破裂的...[详情] -
刘川 译 | 弗兰克·比达特:夜的第四时辰(长诗)
弗兰克·比达特,1970年代出版的首部诗集《黄金州》与《身体之书》虽获评论界关注,但其作为不妥协的原创诗人之声誉真正确立于1983年问...[详情] -
清静 | 深入解读王老莽诗作《三元塔》
这种深度并非老莽刻意为之的深奥,而是源自诗人对生活的敏锐感知和对人性的深刻理解,让读者在阅读中能够获得启示和感悟。其洞察犹如一...[详情] -
美国当代诗人弗朗兹·赖特诗选
美国诗人弗朗兹·赖特,1953年生于维也纳,2015年因肺癌去世,2004年诗集《走向葡萄园岛》获得普利策诗歌奖。他父亲是著名诗人詹姆斯·...[详情] -
马嘶诗选:不与他人同巾器
马嘶,生于四川巴中,现居成都。著有诗集《万古与浮力》《热爱》《春山可望》《莫须有》。曾参加《诗刊》第三十三届青春诗会,获人民文...[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