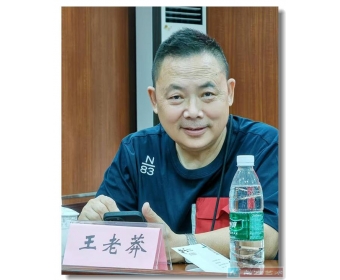|

宇秀(Yu Xiu),祖籍苏州,现居温哥华。文学、电影双学历。文学公号《Meet域外典藏》主持人,《南方周末》、加拿大《高度周刊》专栏作者。出版散文集《一个上海女人的下午茶》、《一个上海女人的温哥华》、诗集《我不能握住风》、《忙红忙绿》等,作品被收入六十余种文集。曾获中国电视奖、第40届中国时报文学奖新诗首奖、2018年度十佳诗集、2018年度十佳华语诗集、2019年度十佳华语诗人称号等。
道义
这条路对所有的脚步都表示沉默
它唯有以躺着的方式抵抗
不说,什么也不说
凡在它身上发出的声音
肯定是强加的被迫
它喜欢松鼠和落叶的访问,胜过
人的踏足
尤其不懂为什么
人们常常在它身上开膛破肚大动干戈
然后……再打破,再缝合
它能做的无非是忍耐,再忍耐
在地震前,每一条路都预备了岔道
让人走错
当人们争论道义的时候,路
躺在天空底下,想念它自己长草的岁月
想念那些草结子,又被风吹落
想念果子在夜晚悄悄落地
人类的眼睛
把明亮收藏进来
把黑暗关在外面
假如这两扇窗户从不曾打开
世界可有黑白的分别?
假如世上所有的窗户都贴上了封条
光明也是可怜的流浪儿
假如这窗户只能开在夜晚
那么,我们的心里必须有团火焰
我们在黑暗里跳舞、脱衣服
我们在黑暗里躺下来,呢喃、做爱
我们在黑暗里深入黑暗
最荒谬的事情莫过于
我们在黑暗里辩白
静下心吧,在火焰里铸剑
把真理挑在剑锋之上
道路闪电,穿过鹰在远方的翅膀
雨中疾驰
马路上的雨水,被疾速的车轮
碾出奔腾的沙飞翔的雾
风夹着雨,被行进中的车窗削成一把把
湿淋淋的快刀
追杀路人。流浪汉
胸口挂着饥饿的牌子穿梭于快刀之间
其实,雨并不急
它知道自己——从天上掉到地上的宿命
急的是车
更急的是车里的人,他们
总是比雨中的流浪汉更多焦虑
所有地上的奔波
无论朝着哪一个方向,都免不了急切
一只臭鼬窜出来,试图穿过马路
觅食,却在轮下倒毙
它垂死前因恐惧发布的恶臭
躲过湿淋淋的乱刀,搭上我的车
令我不得不
把死亡的气息带到远方
秋色
叶落草黄
这没什么好担忧,无非春去秋来
年年岁岁的周而复始
如果发白了呢,凋谢从头开始
这也没什么好紧张,无非人老珠黄
谁也逃不脱的暮年
如果小腹下幽暗处那片迷你三角洲
不再葱郁而如烧荒之后呢
我便说不出无非
如此秋色只能深藏
那是一种难以启齿的荒凉
你是我的虚构
没有你,我就是一栋空置的房屋
门已成虚拟,开也好关也好
皆无意义,反正无关进出
夜深时,墙壁的剥落声盖过风雨呼啸
这间房屋也曾热闹过,有过笑语有过呻吟
幸福眩晕的一刻,非人前的欢愉
而是发丝般纤细的呻吟撑着你
一浪高过一浪的雄风
我的房屋在你的雄风浩荡中无限延伸
延伸到连着天际的草原
羊群在我的山峦纵情奔跑
你,是我的牧羊人
没有你的房屋,蜘蛛网罗天下
杂草封锁窗门。我在封锁里虚构火焰
和火焰里的羊群,和前世在今生里的狂奔
你,是我的纵火者
向日葵的记忆
关于向日葵的记忆
与蓝天下的金色有着密切关系
是在拐了几道弯儿的队伍末尾盯着遥远的
旗帜,紧紧跟着不离不弃
那张幼稚的脸庞总是转动着细细的脖子
向着太阳。这样的画面
令我蜡笔盒里的黄色和橘色往往最先耗尽
我用它们合成老师指导下的金色
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当那脸盘日渐成熟
它就默默低下了头
向日葵也有背叛太阳的时候?
我没敢发问,小心守住一个疑惑
就如守住一个私生子的秘密
我知道那熟透的脸庞里的一颗颗种子
到了明年又将是一批跟着太阳转动脖子的
天真笑颜。如果这时谁要锁住眉头
必定不合时宜,众叛亲离
遗忘进行时
正是腊月,已暖若阳春
雪在雨中背叛了初心
后巷的道路没人管它平与不平
一脚踩到水坑,恰好搭配一柄破伞支在头顶
如今的伞招架不住几场雨就折骨断筋
撑着寂寂冷雨,仿佛招供一个潦倒的人生
想起追着我打伞的那人
洗得发白的蓝卡其布中山装左上袋
总是别一支钢笔,还有白框镜片后面笑眯眯的眼睛
我曾躲在宿舍里看他在楼下,一场场空等
最近,他不停地回来
一如从前,毫无岁月之痕
我却死活想不起他的名字,甚至他的姓
其实,我想不起来的何止一个男人
我常常刷信用卡忘记密码是谁的生日
想到一个故事,却怎么也想不起作者和书名
想不起旅行过的地名
想不起散过步的街名
想不起每天放学后
给爷爷打外卖的苏州老字号面馆的店名
甚至想不起刚才碰到的新邻居
是马克还是麦克先生,他一分钟前才握过我的手
种种的想不起,困扰着我
半夜到谷歌里查找
幼年背得烂熟的一首唐诗或宋词
一本丢了封皮的小说
可类似雨中打伞的那人已毫无线索
而曾经放在胸口的某一只手
至今还有温度,只是我遗忘了相关的姓名
一月的路边已绽放早春的紫丁香
季节弄错了时间
我在种种的遗忘里像一间被搬空的房子
徒有四壁。外面的雨越下越急
想到一生丢掉和遗落的伞不计其数
天空并不因此停止下雨,我开始试着
把惊恐轻轻落实到空气里,试着习惯生命之色
和头发一起渐渐白稀
偏偏一些疼痛不肯失忆
它们从每一处关节爬向胸口,结成余生的顽疾
与所有的遗忘为敌
西晒
西边的太阳在午后和傍晚,不让人睁眼
世界茫茫然裸露在巨大的探照灯下
这样的光明霸道而衰败
我不得不质疑照亮的前程未必似锦
其实太阳并不都是暖人的,此刻
它被一圈光芒箍紧,像磨得又薄又亮的
洋铁皮锅底,随时有被烧穿的危险
我用墨镜过滤堕入黑暗前的光芒
看它在柏油路上制造着显而易见的枯燥和无聊
专门撵着那些蹒跚的步子
追到山墙、追到露台、追到半幅倾斜的风景里
父亲驮着一片光像驮着一柄寒光闪闪的大刀
背对世界。他背后哗啦啦刺眼的白,貌似壮观气象
却是千古洪荒涌到眼前的万般忧伤
背脊上的光芒和背脊一起下沉,沉到风景以外
天空展开父亲洗得发白的蓝布衣裳
父亲
你亲手栽培的蔷薇,突然
在某一个早上探出你的臂腕
绽开,开得你瞠目结舌
你经年呵护的花蕊,突然
在某一个傍晚把心掏出来
给了一个让你猝不及防的陌生
你其实曾经准备了许多遍的叮咛
却一下子来不及赶来送行
你厚厚的嘴唇就变成了沉默的渡口
你转身的瞬间,被风放慢成高速电影
在流年似水的银幕上无限放映
时光深处的眼帘轻轻掀起,目送你
缓缓地朝向忽明忽暗的母亲走去……
失守的花茎在你身后
潸然泪下
在一个以你名字命名的节日里
你被称为高山被誉为大海
其实你没有那么伟岸也没有那么辽阔
你只是一个无怨的花匠一介无悔的挑夫
当花朵无需你的看护,你原本板刷一样
坚硬的黑发就在阵阵秋风里渐次荒凉
当肩头已无重负,你却承受不起一片落叶
你原本牦牛一样壮实的肩头
在一场场冷雨中消瘦成
危险的悬崖
你悄悄把心底的祝福立成一个路标
竖在身后的道旁,不管有没有脚步经过
你留在荒原里的一如峭壁的背影
被谁一遍遍阅读啊?即使岁月
卷了刃的目光依然毫不含糊地读出
一个狂风吹不走的名字
磐石 一样沉重啊
——父亲!
我忙着绿花菜的绿西红柿的红
绿花菜昨夜还绿得很沉着
今天午时就黄了
一如我在母亲怀里的照片失去鲜明
那色衰的照片像一张老去的脸
诉说着日子和那日子里的不可诉说
我问母亲我是怎么离开她怀抱的
她说她正忙着洗尿布
和尿布以外的许多有意思没意思的事情
一回头,她的孩子就自己去了菜市
就买了绿花菜、西红柿还有其它
对了,西红柿昨夜还红得很美艳
和绿花菜一起躺在一个篮子里
今天午时那红红的美艳就溃疡了
我顾不得思考那一夜的红那一夜的绿
如何这般速朽,我只是在心疼
贵到七块加币一颗的绿花菜
就这样扔掉吗?然后我就像医生
切掉一处发炎的脓包一样
切掉西红柿溃烂的部分
接着开始盘算是去大统华
买两元一磅可能摘掉一半的菠菜
还是去沃尔玛
买三元一磅的可以做六盘沙拉
顺便看一下婴儿的尿片和成人的纸尿裤
哪个正在打折
在不知菜价也无需了解尿片的时候
我常常像哈姆雷特
延宕在夜空之下思考是生还是死
此刻,我就只顾忙着
绿花菜的绿西红柿的红
却怎么也挡不住日子跟着绿花菜泛黄
跟着西红柿溃疡
偶尔激动的事情像菠菜一样没有常性
转眼就流出腐烂的汁液
所有的新鲜不过是另一种说法的时间
母亲在时间的左边洗完尿布
就到时间的右边被穿上成人纸尿裤
好像仅仅隔了个夜
那一夜,篮子里并排躺着
沉着的绿花菜和美艳的西红柿
它们不知道第二天让我的心
有多疼
马王堆丞相夫人
两千年前的肌肤仍被今天的手指按出弹性
她曾被如何宠爱过啊,居然可以柔软到现在
当年封存她的人可曾想到未来的某一天
多少无关的手来翻弄和他有关的身体
翻弄她的人戴着口罩戴着手套
在她身体上一厘米一厘米地行进,当然也不会放过
那处最私密的风景
考古学在因痉挛猝死的心脏和被瓜子窒息的气管之间
各执一端,而谁是痉挛的诱因?谁是致命的瓜子?
则是一部野史小说倒叙的开端
小说家让狄仁杰、福尔摩斯,还有活在当下的李昌钰
相互穿越,他们各自从陪葬的珠宝中选取一颗
然后沿着三条细如发丝而富含蛋白质的线索进入历史
宋朝的天空还在今天的天上
今天的云踱着宋朝的步子
在邻家屋顶上踯躅
但我肯定屋檐下不是宋朝的后裔
像小时候的棉花糖可以抓一把
塞到嘴里,也像集合在一起的羊群
令人幻想去天上放牧
今天的云,离宝石蓝的天幕有点远
离后花园荡在秋千上的风比较近,风里的人儿
不知去向。空空的秋千
晃悠着几许轻叹几许怅然
高脚杯里的红酒,青花瓷碗里的绿茶
欢喜着各自的欢喜
孤独着各自的孤独
同一朵云下开着不同的花
风信子甜蜜的香气令人陷入紫色的忧郁
曼陀铃妖冶的媚态让人忘记她的毒性
那邻家屋顶上的云
在遛狗女人的墨镜上忽快忽慢地走着
阳台上烧烤的浓烟
混合着鸡翅的焦味和最新的地产信息
给云抹上一层烟灰色的眼影
傍晚的风把城里的新闻和烧烤的烟味混在一起
扩散。那些新闻总是翻炒着旧闻
一如死亡不停止死亡,新生不停止新生
然而,没有一片云重复过往的云
就像没有一滴泪是曾经流过的泪
北美六月里的风
不是汴京的燥热,也不是西湖的熏醉
它携着海洋的肚量
宽敞得像件尺寸过大的披风
谁都可以披一下,却于谁都不那么合身
而宋朝的云总是骑在风的背上
看秋千上荡来荡去的女子荡出一行行
瘦瘦的宋词。那些骨感的词啊
从北方流亡到江南,从江南流亡到北美
侧身于烧烤的烟熏和密集的广告里
也流连在风信子和曼陀铃之间
在香气与毒性中自我解构
秋千上的人儿,早已不在此刻的云朵下
宋朝的天空还在今天的天上
|  南方论坛
南方论坛 频道热门
频道热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