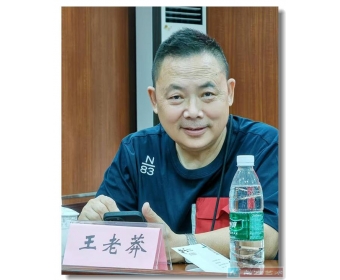纪念王元化先生逝世十二周年
|
我心目中的他,从不是一副青灯苦读的老儒生模样,他的形象总是与春天的青草地,与夜色背景中的白T恤、白球鞋联系在一起,总是不断走动着的同时不断地思索着的样子。他的步子硬朗,且总比一般的散步者更显得有些急促有力。 ——胡晓明 今天(5月9日)是王元化先生逝世十二周年,今年也是先生诞辰百年。在这个漫长的春天终于远去,夏日将至之时,他的道德文章依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并愈来愈彰显出独特的思想魅力与精神风范。或许如其弟子胡晓明教授所描述,读王元化的文字,仿佛“跟他见面,陪他一起散步,看着身边的楼影消融于温柔的夜,看着脚下的青青草,渐渐发黄,又渐渐转绿……”今天,我们一起重温王先生的《自述》,怀念这位沉潜自在、暧暧含光的思想者,感受他不懈反思、探索的生命历程。
自述
学不干时身更贵, 我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写作,到目前已有五十六年了。但认真算起来,我从事研究和写作的时间并不多。生活环境的变化使我有好几次不得不放下笔来。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到一九四九年,我只写了几篇短文。一九五五年反胡风到一九七九年末平反,在这二十多年中,由于偶然的机缘,我才鼓起勇气记下当时的感受。我并不奢望这些文字将来可以发表,只是为了排遣生活的空虚,想在流逝的岁月中留下一点痕迹。这期间我两次患病,一次在三年灾害时期,因营养不良得了肝炎。一次在“文革”前两年,正是我写作《文心雕龙创作论》进入高潮的时候,突然少年时期所患的静脉周围炎(眼底回血管出血症)复发了。一天早上醒来,我的右眼一片黑暗,完全看不见了。我对这意外的打击感到恐惧。那时写作是我的惟一寄托,我不能想象眼睛完了我将怎么办。在这愁苦的日子里,我的亲人为我去找上海最好的眼科医生。我接受了何章岑医生直接在我眼球上的注射,每周一次,一共打了九针。由于疗效不大,剩下的一针就停止不打了。当我从消沉中渐渐振作起来,我还不能使用目力,只有请求父亲帮助。那时他已八十出头了,早已从北方交通大学退休回来,和母亲住在一起。每天他步行到我家,以极大耐心为我阅读资料,作我口述的笔录。现在我还保存着他为我誊写的八大本手稿。我的眼病刚刚有所好转,持续十年之久的“文革”发生了。 我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青少年时期是在战争烽火中度过的,接踵而来的则是运动频仍的严酷岁月。从事研究工作,需要摆脱世事的困扰,无拘无束地进行潜心思考。黑格尔于一八一八年荣膺柏林大学的讲席,他一登上讲台就在开讲词中说:“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骛于外界,而不遑回到内心,转回自身,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现在现实潮流的重负已渐减轻,使得几乎已经很消沉的哲学也许可以重新发出它的呼声。”(大意)黑格尔说的使精神返回自身那种内心的宁静,不是生活在动荡环境中的人所能享有的。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艰难岁月也使人有可能将环境施加在自己身上的痛楚,转化为平时所不容易获得的洞察力。没有经受这种痛苦,没有经受环境施加给人的无从逃避的刺激,就不可能产生这种深沉的思考。这是在远离尘寰的书斋中苦思冥想所不能得到的。大概神秘主义者雅科布·伯麦(Jakob B hme)把“苦闷”(qual)作为能动的本原就含有这种意思吧。为什么有不少人一旦离开养育他的土地,在尚不熟悉的新生活中过着很少变化的平静日子,思想反而逐渐枯窘起来呢?恐怕那些曾经使他感到不安的刺激因素的全然消失,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应该把环境施加给我们的影响,作为我们丧失宁静生活的某种补偿,虽然这并不是我们所追求、所愿意的。相反,我们却要为命运所作的这种安排付出重大的代价。 忧患意识长期以来促成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升华。太史公所谓“西伯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著《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可以说是对一部中国思想史所作的钩玄提要的说明。我以为不能单单列举“五四”时代那些把学术当成实现某种意图工具的学人,作为维持“救亡压启蒙”这一观点正确性的惟一依据。我们应该从他们的思想本身去找寻问题的答案,纵使当时没有救亡的压力,他们也不会做出其他的选择。直到今天还有人把这一时期和他们不同的另一些人,如王国维、陈寅恪等,看作只是一些从事纯学术研究的冬烘学者,殊不知他们对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的追求,并不比前面所说的那些人逊色。他们以为学术而学术的观点,弘扬传统,重建中国文化,未始不含有救亡图存的动机,但这并没有损害他们的学术研究。 一位友人曾从我的书中摘出这样一些句子:“人的尊严愈是遭到凌辱,人的人格意识就愈会变得坚强起来。这是施加暴虐的人所不能理解的。”——“心灵的相契有时比观点上的分歧更为重要。”——“思想是古怪的东西。思想不能强迫别人接受,思想也不是暴力可以摧毁的。”……他认为这些见解不是来源于读书,而是直接来自阅历。这话是不错的。生活经历激发了思考。这些年我所写的谈龚自珍、谈韩非、谈公意、谈激进主义、谈杜亚泉,以及对于黑格尔、对于“五四”等等的反思……也都是在同样情况下进行的理论探讨。在历史和现在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克罗齐(Bendetto Croce)说的“史家对已往史实的兴趣永远是和他对当前生活的兴趣连成一体”这句话最为透彻。但它也包含了一条界限,史家一旦越出这条界限,把对当前生活的关怀变成用历史去影射现在,那么也就使历史失去了它的独立自主性。这种现代关怀是隐含在历史研究之中的,史家本人往往是不自觉的、无意识的。 我希望读者从这本论学集中可以看出我的思想历程。我的早期文字,在一九四五年编第一本集子时,大部分就未收入。这些文字多半是抄袭苏联的理论模式,很少有自己的看法和感受。我从这种模仿中挣扎出来,已是孤岛时期结束以后。日伪直接统治下的上海成了一个恐怖世界,我的许多藏书都自行销毁了,自然更谈不到发表文章。但幽居生活却使我可以沉静地思考。我对教条主义感到了厌倦。浸透着人文主义精神的西方十九世纪文学,几乎成了我当时的惟一读物,引发了我的浓厚兴趣。也许这是由于小时在家庭受到邻人爱的基督教义的影响,使我对这些文学作品产生一种认同感吧。抗战初,我结识了满涛,他刚从美国经欧洲返国。由于共同的爱好,他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我们都是鲁迅的崇拜者,喜欢他的小说的沉郁,也欣赏他的杂文的犀利。我们对鲁迅精神作了自以为深刻其实不无偏差的理解,以为在论战中愈是写得刻骨镂心、淋漓尽致,也就愈是好文章。偏激情绪对于未经世事磨炼、思想不够成熟、血气方刚的青年来说,并不是什么好的征兆。一九五五年,我受到胡风案件的株连,引发心灵上的大震荡,接着陷入一场精神危机之中。在隔离审查的最后一年,我被允许阅读书籍。这时我完全被黑格尔哲学所吸引。我认真地读了可能找到的他的著作,其中《小逻辑》、《美学》、《哲学史讲演录》三种,成了我十分喜爱的书。仅仅《小逻辑》这部著作,我就读过四次,每次不止读一遍,现还保留两次写的笔记,共有十来本练习簿。我沉潜于思辨的海洋,不再像过去那样迷恋于令人心醉的激情世界了。 这以后有许多年,我只读那些不容易读懂的书,以为只有这种著作才蕴含深刻的哲理。幸而那时以艰深文浅陋的赝鼎之作,尚不像今天这样弥漫于理论界,而我对它们也有了一定的识别能力。我深深服膺德国古典哲学自康德以来所倡导的批判精神。这里说的批判精神,就是对过去各个哲学范畴重新衡量与估价,也就是对那些未经过追究的范畴进行考核,探讨这些范畴在什么限度内具有价值与效用。批判是不接受未经考察过的前提的。它具有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提倡独立思考的意义。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者开启了批判精神的先河。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权威,不管这权威是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这种批判精神给予了我很大的影响。直到这两年,当我对黑格尔哲学进行反思时,我还是以它去清理由惰性和习惯所形成的偏见和谬误。这不仅限于对黑格尔本身的再认识,而且也是对“五四”以来在进化论思潮下所形成的新与旧、激进与保守、进步与反动等等既定观念的重新估价。这些观念至今仍作为知人论事的标准,牢牢支配着思想界,成了遮蔽历史真象难以破除的偏见。 我感到,自己没有充分掌握材料并对材料作出仔细的鉴别和考察,是造成误差的原因之一。这就很自然地联系到传统的训诂考据问题上去。这方面的思考使我发觉,过去所深信的所谓逻辑和历史一致性的说法其实只是理性主义的过分自信。在历史的进程中虽然也可以发现某种规律性,但历史和逻辑毕竟不是同一的。逻辑推理不能代替对历史的实际考察,史家的史识必须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的实证上。清人钱大昕说训诂考据乃“义理所由出”,也就是阐明此义。可是长期以来,只有观点才是最重要的这种看法始终占据上风,而训诂考据则多遭藐视。据说一位论者准备批《四书》中的儒家思想,竟以为用不着去读原著,只要请人把《四书》中的有关观点罗列出来供他使用就行了。这可以作为上述那种看法的一个实际例子。不必讳言,过去不少训诂考据文章,往往流于琐碎,有的甚至变成了言不及义的文字游戏。但不能因此断言训诂考据是无用的,正如不能因为曾出现过大量“假、大、空”的理论,就断言观点义理是无用的一样。我不同意把观点义理置于训诂考据之上,作出高低上下之分。这个问题不能抽象对待。对于庄稼来说,下雨好还是晴天好?要根据具体情况才能判定。对于研究工作来说,观点重要还是考据重要?也属于同类性质的问题。马克思曾经嘲笑莎剧《科里奥兰纳斯》(Coriolanus)中的美尼涅斯·哀格利巴(Menenius Agrippa)荒唐地把人比作他自己身体的一个断片,由一个个体供给其他所有个体以营养。他认为各司不同职能的人是像珊瑚一样,每个个体都供给全体以养料。我觉得,学术工作所采取的各种研究手段,其作用虽有大小,但也应作同样的理解。庄生所谓“泰山非大,秋毫非小”,也即阐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之理。这句话隐隐含有平等与自由的意蕴,是值得细细玩味的。 一九九四年八月记于沪上清园 * 本文初刊于《收获》“人生采访”专栏,后作为“序言”收入《清园论学集》。现选自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2019年版《九十年代反思录》。 王元化作品系列 《读文心雕龙》 定价:38元 《读黑格尔》 定价:48元 《莎剧解读》 定价:56元 《思辨随笔》 定价:58元 《九十年代日记》 定价:75元 《九十年代反思录》 定价:58元 《清园书简选》 定价:78元 来源:上海人民出版社 |
 南方论坛
南方论坛
 频道热门
频道热门
-
鬼金的小说与绘画
它们以慢的形式推进着,就像刀子,在某一个虚构的想象中,在推进,推进,直到划开皮肤,呈现出白色的茬,然后才是肉,才是红色,破裂的...[详情] -
刘川 译 | 弗兰克·比达特:夜的第四时辰(长诗)
弗兰克·比达特,1970年代出版的首部诗集《黄金州》与《身体之书》虽获评论界关注,但其作为不妥协的原创诗人之声誉真正确立于1983年问...[详情] -
清静 | 深入解读王老莽诗作《三元塔》
这种深度并非老莽刻意为之的深奥,而是源自诗人对生活的敏锐感知和对人性的深刻理解,让读者在阅读中能够获得启示和感悟。其洞察犹如一...[详情] -
美国当代诗人弗朗兹·赖特诗选
美国诗人弗朗兹·赖特,1953年生于维也纳,2015年因肺癌去世,2004年诗集《走向葡萄园岛》获得普利策诗歌奖。他父亲是著名诗人詹姆斯·...[详情] -
马嘶诗选:不与他人同巾器
马嘶,生于四川巴中,现居成都。著有诗集《万古与浮力》《热爱》《春山可望》《莫须有》。曾参加《诗刊》第三十三届青春诗会,获人民文...[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