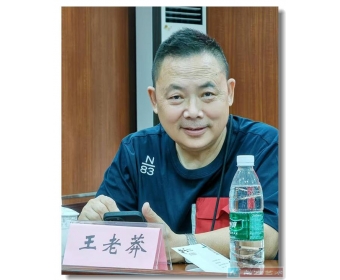傅雷:最敢说真话的中国人
|
近日,某报总编批评电影《江湖儿女》太“负能量”。导演贾樟柯发文回应说:真话才是最大的正能量。 说到讲真话,我想起了翻译家傅雷:一个被誉为“最敢说真话的中国人”。
唐代诗人崔颢写过一首《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此诗境界开阔、自然宏丽,被誉为唐人七律第一。数年后,诗仙李白游历至此。据说兴之所至,也欲赋诗一首。但读罢崔诗后,李白搁笔而去:“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1300年后,一群翻译家,读罢傅雷译作《约翰·克利斯朵夫》后,发出了和李白一样的慨叹:“再也没人能译出这样的文章了。”《约翰·克利斯朵夫》开篇第一句,许聪这样翻译:江流滚滚,震动了房屋后墙。韩沪麟这样翻译:屋后江河咆哮,向上涌动。而傅雷这样翻译:江声浩荡,自屋后升起。哪种译文更有格局气魄,不言自明。傅雷这翻译,简直可以把纸钉在墙上。 傅雷一生,翻译过33本名著。他的译本,除了人名有点洋味外,文章本身几乎看不出翻译痕迹。“既展现了原作之神,又展现了中文之美。”傅雷有本《国语大辞典》,译到外文成语或俗话时,他一定会在辞典中寻找妥帖的成语俗话来匹配。他还给自己订了规矩:每日进度不超过千字。“这样的一千字,不说字字珠玑,至少每个字都站得住。”译完之后,他还要逐字逐句细细爬梳。“一句话翻得不好,十年都会耿耿于怀。”以至于法国人说:“再也没人能把我们的名著翻译得如此传神了。”因为这么“顶真”,傅雷成了一代翻译巨匠。也因为这么“顶真”,傅雷58岁就自杀而亡。
1908年4月7日,傅雷出生了。这一年,正赶上末代皇帝溥仪登基。是巧合,也像宿命。傅雷4岁那年,父亲被乡绅陷害入狱,含冤未得昭雪,抑郁而死。其母为营救丈夫而四处奔走。以致无暇照料孩子,四死其三,只有傅雷一人侥幸生存下来。巨大的悲痛从心理上摧毁了母亲,致使她对傅雷存着一种病态期望:“希望他出人头地,为父亲沉冤昭雪。”她以一种极端方式督促傅雷学习。 小时候,傅雷有一天逃了学。那天晚上,傅雷已经睡沉了。母亲在亡夫灵前哭了一阵后,用包裹布将傅雷缠捆起来拖出门外,她想把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扔进池塘。傅雷大喊,引来邻居,才得以获救。自那以后,傅雷再不敢逃学。有一次,傅雷念书时睡着了。忽然,他从烧灼的疼痛中惊醒,低头一看,母亲竟拿着蜡烛,将蜡泪正往自己肚子上倾倒。“我的童年只见愁容,不闻笑声。”在这种残酷方式下磨炼出来的傅雷,养成了为人做事极端刚烈认真的性格。
▲ 傅雷和妻子朱梅馥 傅雷的刚烈认真在亲朋圈无人不晓。从巴黎留学归来后,傅雷常与友人打桥牌,原本纯属娱乐,傅雷却极其认真。绝不以“技巧”欺瞒别人,以致他的牌别人都猜得一清二楚,结果往往就是十有九输。傅雷为此大发雷霆,认为自己愚蠢。但他又拒绝使用所谓的“技巧”,最后弄得牌局常常不欢而散。别人知他脾气,总不愿同他搭档,傅雷只好和妻子朱梅馥搭档。但几轮下来,傅雷就会气得“牌扔一地”。朱梅馥只好赔着笑脸给朋友道歉。久而久之,大家都不跟傅雷打牌了。 “他这个人做事,极其顶真。”钢琴家傅聪如此评说父亲傅雷。家里热水瓶把手必须一律朝右摆放,倒光了水的空瓶必须放置排尾,灌开水时,也必须从排尾灌起;日历每天由保姆撕去一页,不许别人撕。偶尔夫人撕了一张,傅雷就用糨糊粘好:“等会保姆再来撕一张,日期就不对了。”这种认真,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程度。他规定几点工作、几点休息、几点吃饭,“都是准时的,不能更改的。”在他工作时,谁也不能去惊动他。与人交谈也有时间限制,到点便请人家回去。对自己如此难近常情的“顶真”,傅雷还有绝妙诠释:“一个艺术家若能很科学地处理日常生活,他对他人的贡献一定很大。”大倒未见得,得罪了不少人才是真。
1931,刘海粟与傅雷留学归来。刘海粟担任上海美专校长后,立即邀请傅雷担任校办公室主任。一位北平画家受刘之邀来校任教,为树立威信,将自己的画挂在长廊上。傅雷见了,一瞪眼:“这些画不行,收掉!”刘海粟赶紧将画家介绍给傅雷认识,好个傅雷,一言未发就走开了。事后,刘海粟说傅雷:你怎么这样狂?傅雷一脸不屑:“此公没本领,只会抄书。” 同傅雷和刘海粟一起回国的还有张弦,张弦回来后担任上海美专西画科主任。张弦专心艺术,而刘海粟则忙于交际。学者荣宏君撰文谈过一次见闻:“刘一次周日叫张弦到家吃饭,却安排他临摹一幅画,自己却打麻将去了,中午回来,在张作品上署了自己的名字。第二天又让张弦临了一幅,又署了自己名字。”张弦工作繁忙,还得为刘海粟代笔。傅雷看不惯,常为张弦打抱不平。1933年,借母丧之机,傅雷提出辞职。后来傅雷在《傅雷自述》中说:“刘海粟待我个人极好,但待别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我非常看不惯,故母亲一死即辞职。” 1936年8月,傅雷收到刘抗来信,得知张弦积劳成疾,不治而去。傅雷立即致信刘海粟:“把死讯在报上登一登,让其桃李得悉;筹备遗作展览会,设法替他卖掉些作品,所得款作为他遗孤的教育费……”信去后,石沉大海,傅雷火了。随后,他在张弦老同学筹办展会上,拍案大骂:“永不和刘海粟来往。”1939年2月,滕固担任国立艺专校长,“时北京与杭州二校合并,迁在昆明。”滕固倾慕傅雷之才,邀其担任教务主任。傅雷到后向他建议,若要办好学校:“一测试学生,二甄别教师,不合格者一律淘汰。”但因种种原因,滕固没有接受。作家施蛰存回忆,在雕塑家江小鹣新居,“他和滕固吵翻了。一怒之下,回了上海。”这就是刚直顶真的傅雷。 “过分的认真,在他性格里构成一种强烈色彩。因此带来的就是执拗,大家觉得他太桀骜不驯了。”至交柯灵这样评述傅雷的狷介。傅雷也承认自己“过于严苛”:“提到学术、艺术,我只认识真理,心目中从来没有朋友或家人亲属的地位。”这一点,朋友杨绛十分明了。杨绛译了一篇散文,傅雷称赞了几句,杨绛以为这是客套话,照例一番谦辞,傅雷强忍了一会,最后还是沉脸发作了:“杨绛,你知道吗?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杨绛在怀念傅雷的文章中讲过一事:1954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讨论翻译问题,傅雷提了份书面意见。他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但他似乎忘了,这些例句都是有主人的。因此触怒了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一位老翻译家,被气得当场大哭。 “平心说,把西方文字译成中文,是极繁琐的工作,译得尽管认真仔细,也不免挂一漏万,译文里的谬误,好比猫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净尽。”事后,钱锺书写信“责备”傅雷,说假如你打头先挑自己的错作引子,或挑自己几个错作陪,人家也许会心悦诚服。当时,傅雷经常和钱锺书书信往来。读罢钱锺书之信,傅雷生气了。杨绛回忆说:“气呼呼地对我们沉默了一段时间。”过了一段时间后,傅雷闭门思过,越想越觉得自己这事是做得欠妥当,于是又给钱锺书去信,“承认错误”。傅雷就是这样可爱:认事不认人。即便与刘海粟绝交,但涉及他之事依然公允。1957年在院系调整座谈会上,他因支持刘海粟反对华东艺专迁往西安,而被牵连打成右派。数年后摘掉帽子时,面对歉疚的刘海粟,傅雷却放声大笑,以一句“算了”相应。这便是率真刚直的傅雷!
从国立艺专辞职后,傅雷回到上海。那时的上海,已被日本军队占领。抗战期间,傅雷给自己定下规矩:“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这是为了避免向日本宪兵点头行礼。从此,傅雷闭门不出,埋首于翻译。新中国成立后,吴晗钱锺书当说客,邀请傅雷到清华大学教法语,傅雷拒绝了,他只想干他的翻译工作。傅雷内兄朱人秀说过这样一段话:“傅雷性格刚直,看不入眼的事,就要讲。看不惯的人,就不想往来。他选择闭门译书为职业,恐怕就是这个原因。”好友杨绛也说:“傅雷满头棱角、脾气急躁,动不动会触犯人,止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于在世途上圆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书斋。”但正因如此,中国才有了一位伟大的翻译家。 在家闭门不出的傅雷,一边专注于翻译,一边专注于教育孩子。对两个儿子的教育,傅雷严苛之极。规定孩子应该怎样说话,怎样行动,做什么,吃什么,不能有所逾越。比方每天吃饭,就注意孩子坐得是否端正,手肘靠在桌边的姿势,是否妨碍了同席人,饭菜咀嚼,是否发出丧失礼貌的咀嚼声。站着跟长辈说话时,要身体站直两手下垂,说话时决不能将手抄在衣服的口袋里。有一次,傅聪一事做得不对,傅雷抡起蚊香盘就猛地砸了过去。击中傅聪的鼻梁,顿时血流如注。傅聪鼻梁上,从此留下一道疤痕。两孩子在父亲面前,总是小心翼翼。只有当父亲出门后,才敢大声笑闹。 “我是你的舵工,责任最大。”傅雷曾对儿子傅聪这样说。如此严苛,是希望子有所成就。傅雷本想让儿子学画,但傅聪没兴趣。“傅聪3岁至4岁之间,站在小凳上,头刚好伸到和我的书桌一样高的时候,只要收音机或唱机上放送西洋乐曲,他就安安静静地听着,久了也不会吵闹。”傅雷两口子就卖掉首饰,买回一台钢琴。“他7岁半,让他开始学钢琴的。”练琴枯燥,傅聪时不时就会偷懒,比如,一边弹奏一边偷看《水浒传》。因此而屡遭傅雷修理:“爸爸打得我真痛啊。”1955年,傅聪参加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夺得了唯一的“玛祖卡”最佳奖。一举震惊世界乐坛,被誉为“钢琴诗人”。 这次比赛后,傅聪留学波兰。临行前,傅雷给他的叮嘱是:“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从此,父子俩开始了漫长的书信交流。与儿子的通信,是从“认错”开始的。“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跟着你痛苦的童年一齐过去的,是我不懂做爸爸的艺术的壮年……”随后,傅雷便在信中教导傅聪为人做事。“人一辈子都在高潮——低潮中浮沉,唯有庸碌的人,生活才如死水一般;或者要有极高的修养,方能廓然无累,真正的解脱……”“凡是一天到晚闹技巧的,就是艺术工匠而不是艺术家。一个人跳不出这一关,一辈子也休想梦见艺术……” 1958年,傅雷划为右派。政府接二连三催促傅聪回国,傅聪知道一回就必然难有宁日,一番思索后,从波兰逃去了英国。从此,父子俩再未谋面。1978年,傅雷夫妇自杀12年后,傅聪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邓小平在傅聪的信上批示:“傅回国探亲或回国工作都可以同意,由文化部办理。”80年代初,傅聪才得以回国,并在中央音乐学院做了兼职教授。傅聪把父亲教导自己的信整理出版,这便是后来风行中国的《傅雷家书》。金庸这样评价《傅雷家书》:“是一位中国君子教他的孩子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中国君子。”一语道破傅雷教育儿子的基本精神。那天晚上,傅聪拿到《傅雷家书》后,无法入睡,他不酗酒,可那晚,他喝了整整一瓶。
1957年,风云突变。傅雷被指为亲美反苏急先锋、“中间路线”代言人。一位领导来沪后,示意上海右派太少。为填充名额,傅雷被加进了这个名单。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周而复想保傅雷“过关”,暗示傅雷,检讨不妨将调子定高点。但傅雷却回答得斩钉截铁:“没有廉价的检讨。”见傅雷不肯低头,周又让其好友柯灵前去说服。但傅雷的回答依然斩钉截铁:“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1958年,傅雷被戴上了“右派”帽子。 当时,在全国文化界,只有傅雷和巴金不拿国家工资,而靠稿费生活。但被划为右派后,傅雷不能出书了。但傅雷的翻译实在是太牛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不舍,只有去请示中宣部。中宣部回复:可以让傅雷继续译书,但必须改名。出版社总编室主任郑效洵,便去函跟傅雷商量。但被傅雷一口拒绝:“译著署个什么名字,本来无所谓。可是,因为我成了右派,要我改名,我不干!”出版社没辙,只好内部商定,一面请傅雷译书,支付稿酬。一面把译稿压下,待他“摘帽”后出版。1961年9月,傅雷“被摘帽”。有关部门告诉他这个喜讯,让他有个承认错误的表态,一向顶真的傅雷竟不予理睬:“摘帽子是你们的事,和我没关系。”次子傅敏介绍当时的情状:“有些事,他(傅雷)非常讲逻辑,不光是骨气,是讲逻辑。因为如果去摘帽,就承认戴帽是对的,这是个原则问题,所以他说和我没关系。”傅雷就这么执拗得可爱。自此之后,傅雷更加闭门不出,除了翻译,他开始研习书法、收藏字画。并爱上了养花,在后院花园,他竟然培育出了50多种月季。
不问世事,只求偏安一隅的傅雷,终究还是无法安然置身事外。1966年,“文革”来袭。8月30日,一群红卫兵冲进傅家。一番搜索后,在傅家阁楼找到一箱子。箱里有一面嵌有蒋介石头像的小镜子,还有一页登有宋美龄相片的褪色画报。这便成了傅雷夫妇“反革命”的罪证。傅雷说:“这箱子是姑妈多年前托我保管的。别人寄存的东西,我家从来不动。”但红卫兵们哪会容你辩解。傅雷夫妇被拖跪在地上,然后就是4天3夜的连续批斗。1966年9月3日上午,保姆周菊娣发现,每天都会准时起床的傅雷,今天竟没起。等了一阵后,周菊娣去敲门,无人应。她推开门,发现傅雷夫妇已自缢而亡。 9月2日白天,朱梅馥对菊娣说:“衣物箱柜都被查封了,我没有替换的衣服,麻烦你到老周(熙良)家给我借身干净的来。”她是希望自己死得干净体面一点。那天晚上,她还嘱咐菊娣:“明天小菜少买一点。”那天晚上,傅雷留下了最后一封家书。这封信是写给朱梅馥哥哥朱人秀的。“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 委托数事如下: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三、故老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儿媳,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傅雷 梅馥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在即将了断自己生命的前夕,竟然还能如此地沉着冷静,一笔一画,事无巨细,为他人而想。即使这个社会亏欠了他们,他们也不愿亏欠任何人。人心之温厚,莫过于此了吧!那晚,夫妇俩将土布床单撕成长条,然后搓成绞索,挂到落地窗钢架上。临行前,他俩还在地板上铺了一床棉被,惟恐木凳倒地会影响楼下保姆的睡眠。所谓优雅,有时不过是一床棉被的厚度。真人的自毁,好像揉碎了花朵,震撼的同时,还能嗅到色香。
9月4日,在北京的傅敏收到父母死讯电报,他只是发愣捏着信,竟然没哭:“我发现人很奇怪。悲到极点时,欲哭无泪,欲喊无声。” 傅聪知道父母死讯后,与弟弟反应近似,他似乎早已预料到了这个结局:“我父亲一开始就是烈士的典型,这就是他的命运。”那晚,演奏时,他对观众说:“今晚我演奏的节目,都是我父母所喜爱的。”80年代中期,傅聪回京表演。有晚没演出,他坐在宾馆看电视。他看到戏里,一个孩子在四处寻找爸爸。突然悲从中来,嚎啕大哭。 事后,很多人问傅雷为何会自杀。 傅敏说了一段话:“傅雷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不能违背自己的心灵,同样不能违反自己的逻辑,不能忍受自己的思想被霸占,更不能让自己的灵魂被否定,所以他选择了死。”1935年12月9日,为反抗日寇侵华,蒋南翔执笔撰写了《告全国民众书》:“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文革”十年,也是如此吧!一心只求偏安一隅的傅雷,竟也寻不到“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在那个年代里,一向以民主著称的作家舒芜开始“忏悔”,哲学大师冯友兰低着头选择了“投机”,五四闯将周作人写下了肉麻吹捧的日记,就连敢大硬汉梁漱溟也选择了委曲求全。但是,傅雷做不到。他性格之刚直,容不得说违心话。如同作家狄马所说:“傅雷是他自己精神世界的王。”后来,钱锺书这样评价说:“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两个人很重要,一个是‘不宽恕’的鲁迅先生,一个就是‘大爱’的傅雷先生。”这个大爱,就是爱真实、爱真理。傅雷死后,他翻译上“一生的对手”施蛰存说:“只愿他的刚劲,永远弥漫于知识分子中间。” 1955年1月26日,傅雷在家书中告诉傅聪:“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2013年10月27日,傅聪傅敏将父母骨灰取出合葬,也在墓碑之上刻下了这句话:“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来源:拾遗 |
 南方论坛
南方论坛
 频道热门
频道热门
-
鬼金的小说与绘画
它们以慢的形式推进着,就像刀子,在某一个虚构的想象中,在推进,推进,直到划开皮肤,呈现出白色的茬,然后才是肉,才是红色,破裂的...[详情] -
刘川 译 | 弗兰克·比达特:夜的第四时辰(长诗)
弗兰克·比达特,1970年代出版的首部诗集《黄金州》与《身体之书》虽获评论界关注,但其作为不妥协的原创诗人之声誉真正确立于1983年问...[详情] -
清静 | 深入解读王老莽诗作《三元塔》
这种深度并非老莽刻意为之的深奥,而是源自诗人对生活的敏锐感知和对人性的深刻理解,让读者在阅读中能够获得启示和感悟。其洞察犹如一...[详情] -
美国当代诗人弗朗兹·赖特诗选
美国诗人弗朗兹·赖特,1953年生于维也纳,2015年因肺癌去世,2004年诗集《走向葡萄园岛》获得普利策诗歌奖。他父亲是著名诗人詹姆斯·...[详情] -
马嘶诗选:不与他人同巾器
马嘶,生于四川巴中,现居成都。著有诗集《万古与浮力》《热爱》《春山可望》《莫须有》。曾参加《诗刊》第三十三届青春诗会,获人民文...[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