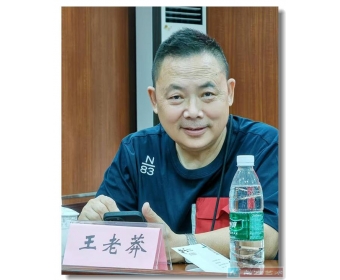|
??边缘时代的诗思(1995)
??这是一个由我们自己的个人良心的相互影响来治理的没有父亲的社会。
??——卡尔·波普尔
??
??越往艺术的深处走,就必须越来越艰巨,而且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正是艺术的恐怖之处。
??——里尔克
??
??一、
??
??马丁·布伯说:当一个人把无生命之物引入他关于对话的充满感激的渴望之中,借给他独立,就像一个心灵,那么在他身上或许会出现一个世界范围内对话的预感,这乃是一场与世界事件之间的对话,世界事件部分由众事物构成,甚至在他的环境中走向他。这时的他不是作为戴着人类假面具的一群人,而是作为一个人,在这时他中践行对话的责任。①而康德说:“人有一种使自己社会化的倾向,因为他在这种状态感觉自己不止是一个,也就是说发展他的自然素质。但是他有一个巨大的斜坡,即使自己个体化(孤立起来),因为他同时在自身遇到了不合群的特性:仅仅想按照他的意象安排一切,并且由此处处预料到反抗,正如他对自己本身所知道的那样:他自己方面倾向于反抗他人。” ②我之所以要在文章开篇引述马丁·布伯和康德的哲语,即因他们的哲语能较好地映证和比较,我在《神话、悲剧和存在的诗歌》一文中所坚持的思辨态度。
??
??诗人先知:一个边缘时代的来临。他沉静而理智地思考自己的心灵历程和一些相关的事件和物质,乃至“他们”的幸福、斗争、死亡和命运等与一个时代的亲缘。于是诗人企图通过哲学、政治、艺术和宗教来营救一个时代趋向泯灭的诗歌理想。诗人这种企图是一种文化精神的殉难。其实也是在寻求一种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和自我超脱:对生活的远观、沉沦和抵抗,对真善美的坚守和审定,以及再创造和质疑。拉斐尔的画和活的模特儿是一个同义语,那就是因为拉斐尔选择了真的(艺术)道路,质朴无华,对于造化始终是臣服的。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哲学家都未曾停止过对艺术的善的思考和探求。雅克·马里坦说:“艺术存在于灵魂之中,它是灵魂的某种完善。……一种习性,一种内质或一种使人的主体及其自然力达到生命结构和活力较高的稳定的并且是根深蒂固的气质——或使人具有自身特别的力量:假如你愿意,当一种习性,一种占有状态或控制性,它成为我们最有价值的好事,成为我们最不屈服的力量,因为在人性和人的尊严中的真正王国中,它是一种升华。” ③马里坦还告诉我们,拥有艺术的善的人在他的作品中,并不是确实可靠的,因为在行动中,他并不总在运用他的善。但艺术的善自身绝对没有错,它是一种实践的智性崇高,尚待我们去发现和引领。美,之闯入形而上学中,是通过柏拉图。柏拉图之前的希腊思想家几乎是不关心美的,关心美和揭露美都是艺术家的事。
??
??文学(包括诗歌)经常作为一种独立的形式与整个“艺术”相对比,于是便出现了“文学艺术”的并列。文学和其它艺术的区别,首先是媒介材料上的区别:“词不像雕塑那样去使用一种石头、青铜之类的惰性材料,词比起声音来还要显得‘透明’些,也就是说词所传的符号不再需要思想,它本身就是思想。” ④词是语言的基本元素和符号,“是语言中固有的精神力量得以从中被理解的第一种形式”(卡西尔语),甚至是来自神话和现实中的历史和生活的存在隐喻。赫尔德在论述语言起源的文章中写道:“当人类达到了他所独有的反思状态时,并且这种反思首次获得了自由的游戏时,人便言语”,这是启蒙运动时期语言理论的余音。
??
??近代语言科学在努力说明语言“起源”问题时常回返到乔治·哈曼的那句格言:“诗是人类的母语”。语言学家一直强调,言语并非植根于生活的散文性,而是植根于生活的诗性上;因此必须在主观感受的原始能力中,而不是在对事物的客观的观照中或者按某些属性类分事物的过程中去寻找言语的终极基础。⑤卡西尔说尽管这种演说初看上去似乎避开了“逻辑表达说”,但它终究不能在言语的纯指功能与纯表现功能之间的鸿沟上架起桥梁。在这种理论中,言语的抒情性发声变形为指称性发声的解脱过程。⑥我为何要在此详尽地引述关于“词”与“语言”的言论呢?作为一个诗人,必须要深刻地认识到语言与诗的关系,要深刻地认识到语言的魔力和隐喻力量,语言与神话的亲缘。普罗斯在尤多多印第安人那里搜集到的文献中,有一篇他认为与《约翰福音》的起首一段相似,他的译文也与之完全吻合:“天之初,语词给予天父以其初”。在一份埃及神学的最早记载里,“心与舌”(心智与说话)这首要的力量就被归结为创世神塔的属性⑦,普塔凭借这一力量创造并辖治所有的神和人,所有的动物,以至所有的有生命的东西。的确,远在基督教纪元数千年以前,人们全有了这样一种观念:上帝是一种精神的“存在”,他先思想世界而后创造世界,而语词则是他用来表达思想的手段和创造世界的工具。卡西尔说:“人类的心智不得不经过漫长的演化过程,不能从原来那种信仰蕴含在语词(逻各斯)中的物理——魔法力量的处境达于认识其精神力量的境界”:
??
??正是语词,正是语言,才真正向人揭示出较之任何自然客体的世界更接近于他的这个世界;正是语词,正是语言,才真正比物理本性更直接地触动了他的幸福与悲哀。因为,正是语言使得人在社团中的存在成为可能;而只有在社会中,在与“你”的关系之中,人的主体性才能称自己为“我”。
二
??
??人是什么?生理学把他作为生死机体来研究,心理学把作为灵魂来研究,社会学把他作为社会和文化、精神来研究,人类学则把作为尚未被确定的动物和已确定的自我塑造的对象来研究;我们再看看这些伟大的哲人是如何面对人的: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设想人是一种理发存在物;德国的雅斯贝尔斯重申人作为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经验的存在,他不是一个可知的对象;美国的L·A·怀特定义,人是一种终极可能的理想符号;法国的笛卡尔坦言,人是神秘地寄存于某个机械的、有广延的,肉体中的无形的心灵;丹麦的克尔凯戈尔意识到人总是处于上帝的手中,并接受上帝的引导——判断的或命令的真理性;英国的阿诺德·汤因比则把人寄予宗教和历史,那么人的一生就是祛除人类自我中心的原罪的一生,高扬宽容、博爱与和平主义的理想人生。总之,这些优秀的思想者和言说者对人的思考和探究以及质疑均是深刻无比的,尽管存在偏颇和谬误。正如米夏埃尔·兰德曼所言,人不是一个定义能确定的,他具有一种不可确定性。如果借用尼采的一个警句:人是尚未被确定的动物,那也是算是对人的定义的一个让步。
??
??关于人的定义太多太复杂了,我们无法绝对倾向,但我们也不能折衷地对人的定义妄加论断,这样将会陷入机械的形而上学中去。诗人的思想在某种不可言说的哲学意义上是孤独的,是不合群的。康德说,“没有那种虽然本身不值得喜爱的不合群的特性——从中产生任何人其自私自利的傲慢情况下必然碰到的反抗——就会处于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牧羊人生活,这种生活尽管多么地和瞌、知足和相互亲爱,但是一切天赋将会永恒隐藏于其萌芽状态之中:人温顺得像他放牧的羊那样,而他的生存将不会比他的家畜所具有更大的价值;他不会填补造物主——鉴于他的目的是作为理性的自然——的空白。因为,应当感谢天性,这种不可容忍性、忌妒地进行竞争的虚荣心,对于财富的不满足的欲望,或者还有对统治的欲望!”⑧康德如此强调不合群性,必须引起诗人的重视和反思。在康德看来,这种不合群性是一种对社会的病态地渗入的协调,他甚至也期望达成一个道德上的整体认同。他还说,自然的推动力促使不合群性和普遍反抗的根源(……)去更多地发展自然素质,也就是说透露了智慧的造物主的安排,而不是什么恶魔的手,这种恶魔干扰造物主的庄严殿堂或者心怀忌妒地破坏它。
??
??康德的论语强调人的不合群性,在我看来尤其暗示了诗人的不合群性:他的精神特质,生活面貌,思想状态,人生境遇,乃至他的人格,前不见病态的或迷狂的理想。这些不合群性的征象进一步地在他的诗歌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和渲泄,同时也表明了诗人的社会地位是无法被其他的语言使者或艺术创造者所代替。我揭示诗人的不合群性,也是想引渡诗人们对“人”的独特理解和关注的同时,也应关注自身。诗人理解和关注人,传统地带有宗教意义和忧患意识,甚至对人类自身存在的卑俗和劣根性文化、精神表现出歧视和愤怒。诗人总是伫立在一个时代的边缘地带,或者说他总是挺立在时代的悬崖上,时刻有跳下去的壮烈景象,这种事实存在三点可能性因素:
??
??第一、 诗人具有强烈的不合群性。
??
??第二、 诗人是作为精神性存在的而主体存在,而不是以物质性的人主体存在,这就决定诗人在物质感官的世界中以隐形者的身份和灵魂的持有者的双重形象出现;或者说诗人就是人类被隐喻的精神,就是灵魂的重要持有者。
??
??第三、 诗人同历史学家的哲学家一样,习惯于把自己隐秘在时间和物质的背后,让时间和事物出来说话,诗歌不过是一种精神与灵魂的载体。
??
??不难看出,一个诗人从传统时间的意义上讲就是时代的一个片断,一段历史,一种征象和见证。我一直认为时代不仅仅是针对人而言存在,普遍的动物也应该有它的时代,包括植物和一些无生命的物质景象及群落,这从犀牛的头角、树干上的年轮以及地脉的岩层中都可以发现它们的时代的存在、历史的继承。
??人的可疑性是尼采毕生从事的真正的伟大课题。尼采说:我们不再从“精神”指导出人,我们把他放回到动物中去。尼采以人之脱离动力界及乖离其本身的事实所要解释的正是这种可疑性。他说人是一种过分雕饰的动物,是地球的隐患,因而人是有问题的;他是把人的问题视为一种边缘状态的总是,人已从自然内部走到其最外缘,走到自然物的危险的尽头,在那里出现的不是康德的精神天空而是可怕的虚无的深渊。⑨海德格尔在《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一书中写道:“没有哪个时代像我们时代这样对人了解如此众多,知道如此众多的不同的问题”。尽管如此,他说人们仍然不知道人是什么,只知道人的边缘是什么,即人在边缘是什么——已达到存在边缘的人是什么。马丁·布伯年轻时读克尔凯戈尔,就认为克尔凯戈尔的人是处于边缘的人,而海德格尔的人又从克尔凯戈尔朝着面临虚无有边缘向前迈出了巨大的至关重要的一步。在卡西尔看来,“人”是一种特殊的动物,它具有一种别的动物所绝对没有的功能——运用符号的功能,符号不是事实性的,而是思想性的,因而不是实体性的,而是功能性的。由于有了这个特殊功能,人才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世界所给予的影响作出事实上的反应,而且能对世界作出主动的“解释”;用包括艺术在内的不同符号形式对世界作出各种解释,就形成了人类的文化体系:人类学。⑩卡西尔发挥苏格拉底、柏拉图“认识你自己”的思想,强调人的本性就像一本难读的大书,要哲学来释义。叶秀山由此意义意识到,包括艺术在内的整个人类文化,从符合哲学的眼光看,与整个物质世界的关系不是事实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思想性的意义关系,无论艺术、神话‘历史、宗教、科学等都像一本本大书,要哲学来释其意义;就在这个释义的进程中始终贯穿着人类的可疑性:
??
??1、 我能认识什么?(康德)
??——人能够认识:因而他就能是自由的。(卡尔·波普尔)
??
??2、 上帝存在吗?(克尔凯戈尔)
??——上帝根本不存在,上帝的观念是一种虚构物。(霍尔巴赫)
??——上帝死了。(尼采)⑾
??
??3、 在无限中人是什么?(帕斯卡尔)
??——他是一个存在,上帝在他身上爱他自己。(马丁·布伯)
三
??
??诗人无疑是生活在历史与时代的可疑问性中。在时间的放逐中,他是自觉的;在社会的尘埃中,他是纯粹的。他始终坚持的不仅仅是理念,更重要的都是对人类和生命的情感体验。为了获得这种崇高的情感和理念,他可以放弃和牺牲:一个世俗者的幸福和理想。“诗人是一个异己者,他放弃集体主义的荣光。诗人在一个不和谐的不存在自由和隐伏民族危机、文化危机的时代里,他情愿选择流亡和隐遁,或成为物质的清贫者,一个白痴,一个被时代被确诊的精神病患者。”⑿
??
??诗人生活在模仿者的时代。机器模仿人类(功能);人类模仿兽物(本能),模仿神灵(力量)和上帝(极权);上帝模仿谁?他自己——那无异于臆淫。上帝为何物?一面人工的镜子,形而上的镜子。人制造了它,并且不断地修饰它,使它趋向完满和虚无的神圣,然后用它来如何禁锢和诱引自己的欲望和行为。一些现代人依旧需要和渴望这面镜子,一旦离开,也就看不到自己存在的面目。透过这面镜子,我看到了一副副“模仿者的面孔”:在芸芸众生之中,也夹杂着模仿死者的表态——那就是人们理想生活的真实。诗人、思想者和艺术表现者卷入了这个模仿者的时代。诗人模仿什么?模仿个性和自我,模仿现代和后现代,模仿人格和精神,乃至模仿天才和大师,模仿死亡和博爱……。然而一些东西是不可模仿的,只能创造和修行。模仿时代的继续只会使诗人逐渐世俗化,功利化和平庸化,最终时间将使他成为一个午夜街头的匆匆过客,消失在时间之外,消失在茫茫的灰暗和尘埃之中,沉溺于琐碎的睡眠和生活,从而失去存在于诗人生命底蕴中的诗性直觉的理想和言词,走向惰性和习俗的死亡境地。当然,走向死亡,并非意味着生命意义的终结,只能说是人生的终结,或者说从死亡本身来看,人生结构是消逝性的。
??
??诗人沉浸其中的时代,是一个怀疑与被怀疑的时代。虽然诗人自身充满了可疑问性,可是诗人的死亡仍是值得质问和怀疑的。正如我在《神话·悲剧和存在的诗歌》一文中所说,拜伦的死拯救了他的诗歌,兰坡的死埋没了他的诗歌,普希金的死正直了他的诗歌,海子的诗张扬了他的诗歌,⒀女诗人中普拉斯的死应验和补充了她的诗歌,萨福的死隐秘和激荡了她的诗歌。主宰死亡的主人不是上帝,不是人的思想,而是人的意志和时间。人所拥有的意志和时间是相互斗争的妥协的。诗人的死亡不管是自杀、他杀或者自然之心声,依然是意志与时间达成谅解的产物。在这一章即将结束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叔本华,他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不管人们曾经怎么去理解他,攻击他,他还是曾经深深地影响了我的哲学生活和诗性写作:
??
??绝大部分的死亡恐惧不外是基于“自我已消灭,而世界依然存在”的错误幻觉所致,这实在是一种很可笑的心理。世界的伴随意志,原如影之附身一般,世界唯有在这个主体的表象中才能存在,这个世界的真正主人是意志赋予了一切生物的生存,它是无所不在的。正确的答案是:“世界虽消灭,而自我的内在核心却永远长存。”如果能够善用机会的话,“死亡”实是意志的一大转机。因为在生存中的人类意志并不是自由的,一个人的行为是以性格为基础,而性格是不会改变的,故其行为完全隶属于必然性。如其继续生存的话,只有反复相同的行为,而目的记忆中必定存留着若干的不满。所以,他必须舍弃现在的一切,然后再从本质之芽萌生新的东西。因此,死亡就是意志挣脱原有的羁绊和重获自由的时候。⒁
??
??1995年3月26日海子祭日写于黄瑰堡
??
??注释:
??
??①:参见马丁·布伯《人与人》卷一《对话》,作家版。
??②:参见康德:《世界公民意图中通史观》,《著作》第11卷
??③:参见雅克·马里坦:《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三联版,46页。
??④:参见朱狄:《当代西方美学》,92年人民版,467页。
??⑤:参见卡西尔:《语言与神话》,88年三联版,51页。
??⑥:参见同上。
??⑦:普塔:古埃及神话中的创世之神,又译“普塔赫”,原为盂斐斯的守护神,第三王朝(约公元前3000年)时期,王都迁至盂斐斯,普逐擢升为创世与造物之神,也被视为技世庇护神。智慧之神托特为其舌,神牛阿庇斯为其灵,太阳神阿图姆为其齿,大地之神塔泰奈恩为其化身。“心与舌”即由此而来。
??⑧:同(2)
??⑨:同(1)《人与人》卷五《人是什么》第一章。
??⑩:参见叶秀山:《思、史、诗——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研究》,人民版43页。
??⑾:尼采说“上帝死了”的潜台词是:上帝存在过。
??⑿:摘自作者1995年1月19日的日记。
??⒀:参见作者的长篇诗论《神话、悲剧与存在的诗歌》第二章,“张扬”一词原为“夸张”。
??⒁:参见叔本华:《爱与生的苦恼》,中国和平86版。
|  南方论坛
南方论坛 频道热门
频道热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