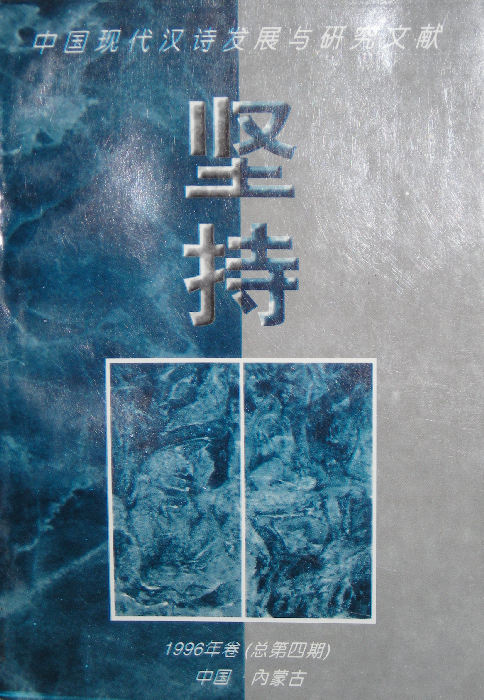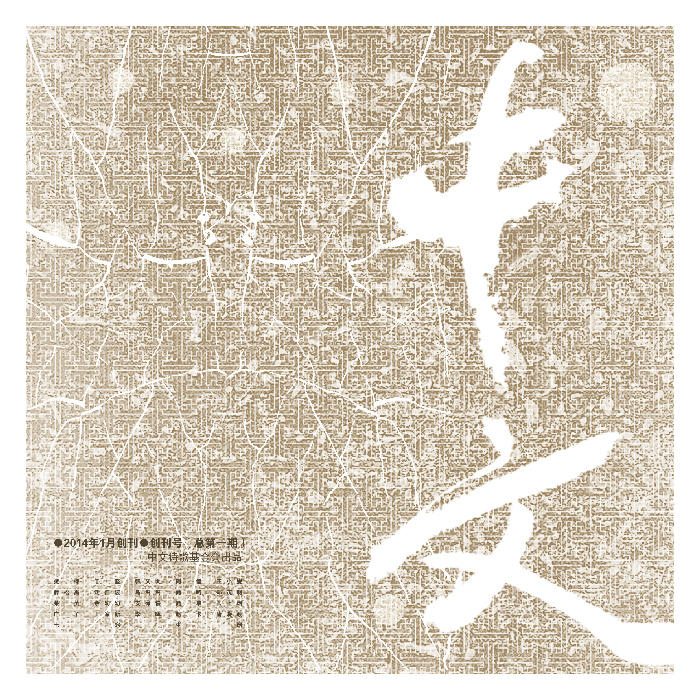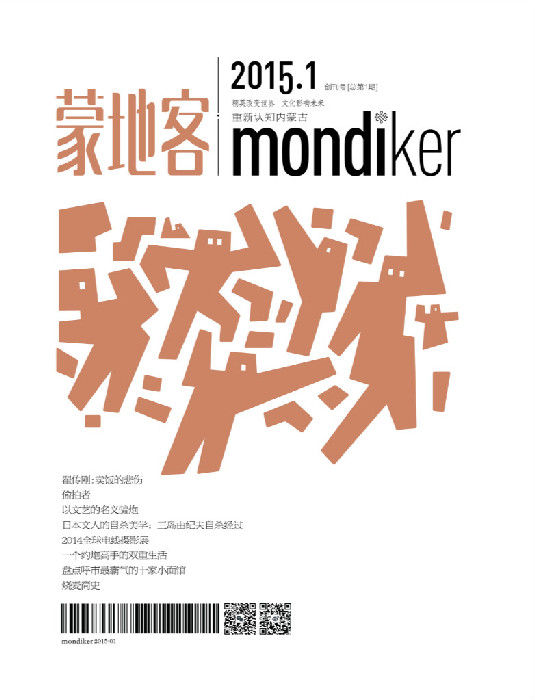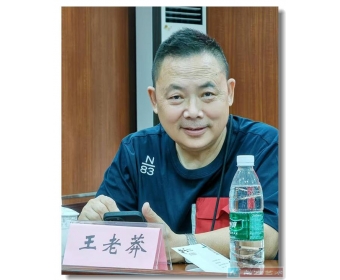李悦:论广子
|
《坚持》(1996年卷) 诗人广子而立之年写出诗名,再从而立之年写到不惑之年,诗作走向成熟。及至知天命之年诗歌达到顶峰,取得优异成绩,进入当代知名诗人序列。本文主要评论广子这十多年的诗歌创作,此际正逢内蒙古文学艺术兴盛的十年,也是广子写作生涯的黄金期。 广子的系列诗组《蒙地诗篇》是他这十年诗歌创作中最优秀的作品。这个系列诗组的第一部分首发2013年《草原》杂志,《十月》2014年第六期刊发的组诗于2015年获内蒙古文学创作索龙嘎奖。 《蒙地诗篇》从题材上讲,属于边塞诗。内蒙古的多数诗人一直在创作边塞诗,广子的这组诗写的是边塞景物:阴山、召庙、哈素海、乌拉山、羊群、草原、岩画、乌兰木伦河、四合木……这些元件是多数诗人用来组装赞美塞外的宣传车,车上的喇叭还不时地高声发出有关环保生态的慨叹。而广子知道诗并没有实际效益,仅仅是停留在言说之中,所以他剔除了意识形态的成分,避开了世俗的功利目的,以语言为筑料,无拘无束地构建了一个意象的世界并沉溺其中。在这个世界里,我们看到:“石头不认识山,羊不认识青草,你不认识我,我们不认识阴山”;在这个世界,“我们就可以加入祖先的生活,男人出门狩猎,女人在篝火旁跳舞,在日落时分支起一架野猪头”;在这个世界,“幸运的诗人也许会撞见画像上,走下来的女人,宛如生前一样美丽”;在这个世界,“暮色里苜蓿像一盏盏幽暗的灯笼,为迟归的奶牛带路,给灌浆的麦苗送去芬芳的晚安。” 广子创建的这个世界,敕勒川不再是川,美岱召不只是可拆的庙,哈素海其实并不是海,乌拉山弄不清山上住过的神灵,召烧沟最后一幅岩画“等待着风剥雨蚀”,人在“和苜蓿一起来跳舞”,四合木唱起了寂寞的歌……我更喜欢那首《乌兰木伦河》,广子写道:“我们的祖先取暖时烧过的/他们祖先的骨头/每当我在河床,捡起一块石头/俯身敲打另一块石头/乌兰木伦,我就能听到你/在高原上哗哗流淌”。 广子认清了诗的本质,认为写诗是一种创造性活动,以语言为材料去创建诗人自己的世界。当更多写诗的人还在把语言当成传达信息的手段,广子已经认清了语言的本质。他深知语言才使人得以从诸存物中突现出来,存在必须打开,在者才能显露。在这个意义上,诗的本质是创建永恒,并使得永恒得以确定。而诗人的任务是使转瞬即逝的神圣之物永恒留存。广子创建的世界,不再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反映论是席慕蓉吐露真情的理论依据,是汪国真写诗的指导思想,是以往边塞诗的衣钵。广子写的是新边塞诗,存在通过他的诗句被确立。以上我引用的《多兰木伦河》写的就是生命存在的本质,原来生命就是一个过程:下一代人烧前一代人的骨殖。广子在《美岱召,与爱情有关的一座庙》一诗的结尾处写道:“一具遗骨所佩戴过的,肉体也曾佩戴过,如今依然在我们爱人身上叮当作响”。当我们了解了诗的本质,认知了诗者何为,我们才能知道广子的这两句诗是真正的诗。因此可以说广子的诗开一代边塞诗新风,有着里程碑的意义,从此宣告旧边塞诗到此止步! 广子诗歌的成熟与他的诗歌理论认知分不开,但诗歌是一种审美对象,要运用形象思维。我也懂诗的本质与诗人的任务,但却写不出广子这样的诗,我认为广子在具备了理论意识之后,还有着他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那是他走向诗本质的内驱力。例如我在他这组诗中不时地发现人进入一种静的状态,人的变迁,景物的转化,历史的沿袭,都是那么安静、寂寥地进行,但并不是思维毫无活动,而是处于人的各种潜能和谐运动的那样一种无限的状态。这让我又一次从新的角度理解并认可荷尔德林所说的:人诗意地栖居在这个世界上。 写到这儿,我又想起荷尔德林的另一句诗:凡留存者,皆为诗人所确立。 诗人广子为诗坛确立的是新边塞诗,是对于他自身之外的留存。对于他自身也有所巨大的改变,那是诗歌整体立意的改变。过去他如同孩子,向往着诗与远方,他流浪,他闯荡,他漂泊,是向远方寻找着他的诗。他长途跋涉来到呼和浩特,来到北京,写下他一路的人生体验。他称这些诗为“蒙地诗篇”,文学圈称其为“地域诗歌”“新草原诗”“新边塞诗”,这已经是诗的设计与实践的成功,可以画个圆满的句号。然而他并没有就此止步,他是诗人,也是个思考者。对于他来说,写诗的过程不只是完成向往和预想的过程,还是个修正向往和预想的过程。诗艺正是在写作实践中提高的。2012年的12月,广子随同朋友、诗人西凉为他组织的越野车队,横穿乌兰布和沙漠。这是他的故乡鄂尔多斯身边的一座大漠,是鄂尔多斯沙尘的源头,曾经陪伴他度过充满诗情与幻想的青春。他头一次发现内蒙古家乡大漠的神奇与殊异之美,发现故乡是文化和历史遗产相当丰厚的土地,从来不缺乏滋养文学艺术的基因。他惊异自己二十多年几乎很少写过故乡内蒙古。这次意外的乌兰布和之旅,唤醒了他内心积蓄、储存太多的诗的冲动,激活了被他自己抑制的近乎迟钝的诗的神经。 诗神召他魂归故乡,他这才知道诗不在远方,就在故乡。他要写故乡内蒙古,回归内蒙古。他知道随着年龄增长、阅历反馈,对原乡故土的认知和情感积累、沉淀应该够了。可以写了。他从乌兰布和沙漠回来,开始了蒙地诗篇系列诗歌的写作,五六年间写下近三百首。这是广子的一次诗和命运的双重转身,是自觉的向后看向后退,一种回到原点的重新出发。
《仅仅是诗·广子十年诗选》(2006年) 广子曾经奋斗、向往、漂泊、受苦……但是他知道,一生注定要与诗为伍。这不是他给自己规定了这样一项任务,而是因为诗歌对他来说是世界上最壮丽的景象。 《蒙地诗篇》系列诗歌发表后,得到海内外众多知名诗人和评论家的好评。荷兰汉学家柯雷先生曾专程到呼和浩特访问广子。《蒙地诗篇》的成功,还对新世纪十年之后的内蒙古新草原诗歌审美和写作群体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了以《蒙地诗篇》为修辞摹本的诗歌潮流,被公认为内蒙古新草原诗歌写作的源头。近十来年在内蒙古诗坛流传着一句高度赞扬广子诗作的顺口溜:“开言不谈蒙地诗篇,读尽诗歌也枉然”。 广子对自己的诗作审视十分严格,不轻易发表作品。他呈现给读者的作品都是自己的满意之作,这反映出广子能够以真诚回报读者,从来不敷衍读者,他过于珍爱自己的羽毛了。尊重读者才能受到读者的尊重。由此诗人、诗歌评论家赵卡在《作为插入和需要附加说明的蒙地诗篇》一文中说“如果我们说内蒙古的诗歌需要一种尊严的话,应该是广子给我们挽回的。” 广子在《天赐礼物(献给LX)》一诗中写道:
广子在这首诗后特意注明写于“2016.7.9,阴历六月初六”。这一天是佛家的天赐节,求药祈福之节。他深刻体悟到这首短诗的灵感来自天赐。也只能是天赐。同样,我读到这首诗所唤起的诗评灵感仍是天赐,并能让我想到用艾青先生的诗论去评论这首天赐之诗。我把广子的这首诗视为他一生诗作的代表,对于这首诗的评价就是对他的诗的整体思想性与艺术性的评价。 诗的散文美理论是艾青先生美学思想的核心。它代表并凝聚着艾青一以贯之、毕生追求的诗学理想。也是他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创造性贡献。我以为广子近十年诗歌创作走向散文化,正是他诗歌叙述形式趋向成熟的表现。广子的这首《天赐礼物(献给LX)》并没有像他青年时代诗歌那样刻意追求韵脚和节奏,而是有意引入散文的自由活脱,清淡自然,不拘成法,如同饮茶间的闲话,却构成一道独特的诗学景观——散文美。 广子显然实现了艾青倡导的叙述方式,使诗歌从矫揉造作、华而不实做派中走出来,走向诗句的日常化,形式的自由化,意境的整体化,走向一种流转如弹丸的圆润之美。
《往事书》 广子著,2012年 罗丹说:“艺术上最大的困难和最高的境地,却是需要自然地、朴素地描绘和写作。”我国元代的房皞在《逸志堂诗话》中写道:“后学为诗务斗奇,诗家奇病最难医,欲知子美高人处,只把寻常话作诗。”这些都是反对语言的争奇斗艳,华而不实,而主张以朴素自然的“寻常话”为美。寻常话就是口语化,艾青认为,语言的口语化是“诗的散文美”理论的首要含义。广子的这首诗显然尽可能地运用口语写,尽可能做到深入浅出。但他的口语并非口水之类,恰是一种沃尔特翁指认的“书面口语”,他所运用的口语,新鲜纯净,富于自然性、简约明畅。他没有运用华丽的形容词,没有为押韵而拼凑诗句,全诗无定韵,无定节,无定句,无定字,这无定字是指一句诗中字数多少无定。以上所说的四个无定,并不是漫无边际随意为之,而是要为内容和主题服务。广子自觉地把散文创作中的“形散神不散”运用到诗歌中,形成他自己的诗歌风格。广子并不像有些诗人散去难受,而只是散在形式的表象上,其内在节奏、内在神韵、内在意境并不散,且刻意不散。且要凝聚。在这个意义上,赵卡称广子为“理性与感性完美结合的风格和修辞大师。” 惠特曼说:“我想说什么,就照它的本来面目说出来,让人家去高兴、吃惊、着迷或者宽心吧。我却有我的目的,正如健康、热度或白雪各有它的目的一样。”他想说就直接说出来,似乎是在讲“自由”,而“照它的本来面目”,“我的目的”却又强调了“集中”。这也是艾青所指出的“自由而自己成了约束”。 诗歌是文学艺术的一种载体,我国的古典文学起源民间诗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诗歌当然也是语言的艺术。艾青在他的诗论中强调诗是艺术的语言。广子的诗也如同这首《天赐礼物(献给LX)》一样,把语言的技巧放在首位,这是从形式上抓住了根本,抓住了诗歌技巧的本质。 广子这首诗的语言就是艾青强调的“艺术的语言”,是最高的语言,最纯粹的语言。艺术是情感凝铸的形式,广子的艺术语言则是饱含情绪的语言,是饱含思想的语言,是形象化的语言。 广子这首诗的旋律就是生活的旋律,这首诗的节奏就是生活的节奏。当读者阅读时能真切地体验到这一点,同时体验到诗的节奏与旋律的关联。这二者正如艾青在《诗论》中所说:节奏与旋律是感情与理性的调节,是一种奔放与约束之间的协同。 诗的技巧就在于处理好这二者的协同。过于奔放很容易造成主观单向引导,走入标语口号的迷途;过于约束则伤害读者的想象空间。所以契诃夫说:好和坏都不要喊出来。 广子没有喊出来。而是做得恰到好处。准确地把握了奔放与约束的关系。诗人赵卡看清了这一点,在《作为插入和需要附加说明的蒙地诗篇》一文中又写道:“这是一种伟大的局限,而局限这种特质并非每个诗人都有。” 正因为这种特质是广子具有的,不是他的同代诗人都能具有的,才能够确定广子独树一帜的位置。 艾青在《诗论》中曾指出:“诗人的行动的意义,把人群的愿望与意欲以及要求,化为语言。” 艾青在这里强调指出的是语言的内容,也就是在说诗人要用语言表达什么。艾青认为人群的愿望与意识以及要求的最基本的精神核心是真、善、美。真是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它给予我们对未来的信赖。善是社会的功利性,善的批判以人民的利益为准则。没有离开特定范畴的人性的美。美是依附于先进人类向上生活的外形。艾青认为诗歌对于真、善、美的歌颂,来自诗人的人文追求。诗人只有和人民在一起,喜怒哀乐和人民相一致,智慧和勇气都来自人民,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
《中文》创刊号(2014年) 广子是来自底层民众的诗人。他在青年时代就长期从事临时工、砖瓦工、矿工等多种体力劳动。生活在广大民工当中,深切地了解普通民众的生活和工作状况。他是人民中的一员,表达着人民的感受和愿望。人民也就喜欢他的诗。人民信任他,内蒙古文学界也信任他。近些年,内蒙古文学界、诗歌界信任他。许多艰苦的编著任务都请广子担纲。他曾主持编选了《中国70后诗选编》(长江文艺出版社,大16开本,上下卷),《内蒙古七十年诗选》(内蒙古教育出版社,上下卷),他执行主编的《内蒙古文学百年大系·诗歌卷》共七本,二百多万字,耗时两年,将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艾青在《诗论》中对于诗歌语言还有一个硬性指标:“语言里面必须有暗示性和启示性。”他以为能做到暗示和启示的语言,诗歌才能以他的“由衷之言去震撼人们的心。”广子的这首《天赐礼物(献给LX)》就在语言中有着暗示性和启示性,暗示的是人生短促,启示人们珍惜生命。这首诗看上去是闲聊,但是聊的是人生的生死大事,世界上再没有比此更重大的事了,当然能够震撼人们的心。 曾担任内蒙古文联主席的著名作家特·官布扎布曾经在2016年第三期《作品》的下半月刊中评价过广子的诗。他强调指出广子“文字背后有着比诗艺更可贵的见识与胸怀。”他其实是在指出广子诗歌语言中的震撼人心之处。 特·官布扎布的文学眼光越过广子的诗句,看到广子诗歌形而上的哲学品味,比诗艺还可贵的是对人存在的思考。米兰·昆德拉说“文学是对存在的勘测。”他在这里指出了文学的任务。 广子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是用诗歌去完成文学的任务。这首《天赐礼物(献给LX)》看上去是一首写给女友的情诗,男主人公在茶余饭后闲聊起来,话题又是世界又是尺子,但诗句下的意味却是生与死。 广子并不是直接用标语或口号去启示读者,而是用“拟陈述”的方式。我们身边用口号直接给塞外草原唱赞歌的诗人太多了,说明他们没找到高明的叙述方式。不在于叙述什么,而是在于怎样叙述。广子在许多诗歌中都熟练地运用了“拟陈述”。他《在夜行中巴车上》写道:“一辆中巴车/行驶在笔直的夜色中,歪斜的旅行者/睡姿各异,梦境不同。我是说/我和他们一样,临时来到世上/迷失了方向和目的。在同一辆中巴车上/成为肉体请来的客人……” 广子这首诗再度运用了“拟陈述”的叙述方式。所谓“拟陈述”是指看上去在叙述某个人、某件事、某个物、某个场景。其实其意不在表面叙述的东西,而在于语句下的意味,这正是艾青所说的“暗示”。以上这首诗,看起来在叙述一辆中巴车行驶在路上,车中乘客或睡或歪斜坐着,其实语句下的意味又涉及到生死,涉及到人活着的真相。原来我们每个人来到世界上,都如同中巴车上的乘客,虽然各自情况不同,各有特点。但是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肉体请来的”。言外之意是说当肉体消失就一切都消失了。这很像林黛玉的《葬花》诗,看上去是在葬花,诗句下的意味是葬人,“他年葬侬知是谁?”启发读者的是“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当语句下的意味是在勘测人活着的真相,这些语句正在完成文学的任务。 广子能够运用诗歌去完成文学的任务,是在内蒙古竖起一面纯诗之旗。我说的纯诗指“五四”之后中国白话诗中的纯诗。广子还在传承坚守,与纯诗相对立的是通俗诗,我们身边的通俗诗过多了。这也确定了广子诗歌的风骨,艾青认为诗的风骨是诗人的风骨。竖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我高兴地看到蒙地诗派的形成及其产生的影响。 这十年广子从不惑走向知天命之年,诗歌越写越好。不只是因为他不断地写诗,还因为他不断地阅读和行走。在漂泊无定的时日里,在穷愁潦倒的忧虑中,他总不忘读书,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文学、历史、哲学、美学等方面的书。他边阅读边修正自己的诗路,逐步走上坦途。从青春期到中年,三十年的写作生涯中,广子写下诸多名篇。除了《蒙地诗篇》中的某些篇什不胫而走,在网络流传甚广的《回家》被北岛赞为“佳作”。他的另一个系列诗组《礼物》中的“祭南岳忠烈祠”享誉诗坛,成为当代诗歌的抵鼎之作。 这里需要特别谈论一下广子的“礼物系列诗歌”,这个系列诗组写作大约始于2007年,但真正形成规模性书写实则与《蒙地诗篇》同构而成,大概也有几百首。广子的“礼物系列诗歌”可谓中国当代持续写作时间最久的系列组诗之一。其写作视野小到个人精神史,如心灵经验、情绪观照、应景唱和;大到人类命运、现实图景、生存情境、全球性事件等,全景式记录了诗人的生命体验、精神思索与美学观照。诗是另一个世界,广子的礼物诗歌系列即是以诗的形式传达人类的存在感。世间万物,人生况遇,一切都是上苍赐予的礼物。 这么说的另一层意欲在于,广子之所以将“礼物系列诗歌”的写作与《蒙地诗篇》同步进行,理应是有意为之。我理解这无疑是诗人的一种“修辞”行为或抱负,将两种语言或修辞风格迥异的书写并行推进,类同于左右手之间的默契与异图,一种写作上的自我制衡和博弈,一种诗人预设的写作上的自我防范,以避免造成写作的自我同质化、模式化,即所谓风格化,甚至滑入写作的致命桎梏,走向僵化。 此外还需要提及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广子曾创办以内蒙古诗群为主、在中国诗歌民刊史上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坚持》,持续出刊周期长达十八年;2000年后遂又创办倾向个性化写作的《中文》诗歌民刊;期间还创办了基于地域性的大型人文精英读物《蒙地客》,这些都已成为内蒙古文学文化事业的另类符号。尤其在诗歌层面,2017年由他牵头发起的“蒙地客诗群”及其后与诗人西凉、李建军创立的“荒野诗派”再度引发内蒙古的诗歌现象。
《蒙地客》创刊号(2015年) 广子的一些有着经典意义的诗作,让我们在阅读时产生了许多联想,不禁想到他曾受到现代主义某个流派的影响。例如美国意象派诗人埃兹拉·庞德写过一首诗,名为《在一个地铁车站》。诗的初稿长达30多行。经过修改,最后压缩到15行,仍不满意,最后改成我们迄今所读到的两行:
人群中这些幻影般闪现的面庞; 埃兹拉·庞德对中国及东方文化颇感兴趣,曾经翻译、改写过许多中国古典诗歌,也仿照日本俳句的形式写过一些短诗。东方特色的诗歌以其“意象和技法的新鲜气息”为美国的意象派诗歌注入了活力,使美国诗坛“大为改观”。正是西方与东方文化交融的结果,才使得《在一个地铁车站》成为意象派诗歌的压卷之作。原来经典是这样产生的。 广子或许也像埃兹拉·庞德一样,通过借鉴西方意象派的理论与创作,写出一首好诗《八问丁香》:
看到这个丁香的意象,我联想到埃兹拉·庞德《在一个地铁车站》中的意象。谁能说“花瓣从树上飘下来”并不是来自那地铁车站的“花瓣片片”?谁能说那“寂寞的暗香”不是在“幻影般闪现”?谁能说这八问丁香不是来自林黛玉的《葬花》? 丁香。没有牡丹的艳丽,没有梅花的俏枝,没有荷花的高洁,没有兰花的典雅,没有杏花的朴实,没有桃花的灼热……却有着沁人心脾的幽香。读着广子这首诗,我不禁想到唐朝诗人张谓的“不知近水花先发,疑是经冬雪未销。”我还自然想到宋代诗人王安石的《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这些意象传导出丁香的意象,表达出丁香的风骨。广子问丁香,实则是问自己,他的风骨的形成和丁香很有相似之处。丁香坚实的根和柔韧的枝条,在北国冬季严寒中隐忍着,坚强地隐忍着,等待着春天。当百花争奇吐艳地在春日里开放,丁香细碎的小花也默默地开放了,看上去不但不夺目,甚至有些平庸和卑微,然而却发散出一股独有的幽香。正如经历过艰苦奋斗,漫长隐忍的广子在诗坛上大放光彩一样,香自隐忍!丁香是呼和浩特的市花,准确真切地表达了青城和青城人的风骨。广子这首诗的成功充分显示出他从古今中外文化和文学艺术中汲取了营养。也正如著名文学评论家兴安在《繁华在天边怒放》一文中对广子诗歌的评价:“他的诗冷眼望去。外貌豪放粗粝,读后却发现其内里的细腻和阴柔,充满了莫名的感伤和孤独气息。”总结广子的成功经验,对青年诗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内蒙古的新诗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地域特色,经历了漫长的生长蔓延和起伏嬗变,确立了其在中国诗坛中的重要位置,形成系统的草原诗歌流派。这个草原诗歌流派,在每个时代都产生出优秀的诗人群体及其代表人物。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上世纪50年代,纳·赛音朝克图是代表人物。这位穿越旧时代、拥抱新生活的诗人,率先领头唱出了歌颂祖国、歌颂党、歌颂内蒙古的赞歌。到了上世纪60年代,内蒙古涌现出一大批诗人,他们热情地赞颂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团结,进行着诗歌艺术的探索。这一时期的领军人物是巴·布林贝赫。 改革开放之后,贾漫、安谧等老诗人回归,陈广斌、贾勋、火华等中年诗人成为诗歌的中坚力量。到了80年代后期,内蒙古探索与全新风貌的诗歌涌动,与新一代诗人登上诗坛密不可分。他们是张廓、赵健雄、雁北、白涛、张天男等众多诗人,这些诗人带动了20世纪后期二十年内蒙古诗歌的发展。这一阶段的领军人物为贾漫。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温古等年轻诗人应运而生,壮大了内蒙古诗人队伍。他们在21世纪初期的二十多年中,为内蒙古诗坛做出了可喜的贡献。这个时期广子的诗歌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创作成果。在《繁华在天边怒放》一文中,兴安直言:“在我心目中,广子依然是当下内蒙古最重要的诗人之一。” 我认为广子开塞外一代诗风,努力地完成着诗歌的任务,他是内蒙古诗歌的新一代领军人物。
《蒙地诗篇》 广子著,2022年 希望他今后能够创造出更多更好的诗篇,为内蒙古诗歌的发展贡献力量。 写到这篇长文的结尾处,又想起广子的诗《大雁飞过》:
此刻,我感到一阵孤单。我从来没有写过这样的论诗长文,我不知道能否落下好名声。由他去吧,好在我完成了内蒙古文联《书写新时代——内蒙古十年文学成就研讨会》约稿函的任务。 2022年8月17日晨 |
 南方论坛
南方论坛
 频道热门
频道热门
-
鬼金的小说与绘画
它们以慢的形式推进着,就像刀子,在某一个虚构的想象中,在推进,推进,直到划开皮肤,呈现出白色的茬,然后才是肉,才是红色,破裂的...[详情] -
刘川 译 | 弗兰克·比达特:夜的第四时辰(长诗)
弗兰克·比达特,1970年代出版的首部诗集《黄金州》与《身体之书》虽获评论界关注,但其作为不妥协的原创诗人之声誉真正确立于1983年问...[详情] -
清静 | 深入解读王老莽诗作《三元塔》
这种深度并非老莽刻意为之的深奥,而是源自诗人对生活的敏锐感知和对人性的深刻理解,让读者在阅读中能够获得启示和感悟。其洞察犹如一...[详情] -
美国当代诗人弗朗兹·赖特诗选
美国诗人弗朗兹·赖特,1953年生于维也纳,2015年因肺癌去世,2004年诗集《走向葡萄园岛》获得普利策诗歌奖。他父亲是著名诗人詹姆斯·...[详情] -
马嘶诗选:不与他人同巾器
马嘶,生于四川巴中,现居成都。著有诗集《万古与浮力》《热爱》《春山可望》《莫须有》。曾参加《诗刊》第三十三届青春诗会,获人民文...[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