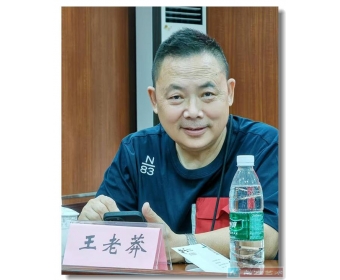严复《天演论》序
|
严复【1854-1921】 天演论序 严子几道,既译英人赫胥黎所著《天演论》以示汝纶,曰:“为我序之。” 天演者,西国格物家言也。其学以天择物竞二义综万汇之本原,考动植之蕃耗。言治者取焉,因物变递嬗,深研乎质力取散之几,推极乎古今万国盛衰兴坏之由,而大归以任天为治。赫胥氏起而尽变故说,以为天下不可独任,要贵以人持天。以人持天,必穷极乎天赋之能,使人治日即乎新,而后其国永存,而种族赖以不坠。是之谓与天争胜。而人之争天而胜天者,又皆天事之所苞。是故天行人治,同归天演。是为书奥賾纵横,博涉乎希腊、竺乾、斯多噶、婆罗门、释迦诸学,审同析异而取其衷,吾国之所创闻也。凡赫胥氏之道具如此,斯以信美矣。 抑汝纶之深有取于是书,则又以严子之雄于文,以为赫胥氏之指趣得严子乃益明。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凡吾圣贤之教,上者道胜而文至,其次道稍卑矣,而文犹足以久。独文之不足,斯其道不能以徒存。六艺尚已,晚周以来,诸子各自名家,其文多可喜,其大要有集录之书,有自著之言。集录者,篇各为义,不相统贯,原于《诗》、《书》者也。自著者,建立一干,枝叶扶疏,原于《易》、《春秋》者也。 汉之士争以撰著相高,其尤者,太史公书继《春秋》而作。人治已著;扬子《太玄》拟《易》为之,天行以阐。是皆所为一干而枝叶扶疏也。及唐中叶,而韩退之氏出,源本《诗》、《书》,一变而为集录之体,宋以来宗之。是故汉氏多撰著之编,唐宋多集录之文,其大略也。集录既多,而向之所为撰著之体,不复多见。间一有之,其文采不足以自发,知言者摈焉弗列也。独近世所传西人书,率皆一干而众枝,有合于汉氏之撰著。又惜吾国之译言者,大抵弇陋不文,不足传载其义。夫撰著之与集录,其体虽变,其要于文之能工,一而已。 今议者谓西人之学,多吾所未闻,欲瀹民智,莫善于译书。吾则以谓今西书之流入吾国,适当吾文学靡敝之时,士大夫相矜尚以为学者,时文耳、公牍耳、说部耳。舍此三者,几无所为书。而是三者,固不足与于文学之事。今西书虽多新学,顾吾之士以其时文、公牍、说部之词译而传之,有识者方鄙夷而不之顾,民智之瀹何由?此无他,文不足焉故也。 文如几道,可与言译书矣。往者释氏之入中国,中学未衰也,能者笔受,前后相望,顾其自为一类,不与中国同。今赫胥氏之道,未知释氏何如,然欲侪其书于太史氏、扬氏之列,吾知其难也;即欲侪之唐宋作者,吾亦知其难也。严子一文之,而其书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然则文顾不重耶? 抑严子之译是书,不惟自传其文而已。盖谓赫胥氏以人持天,以人治之日卫其种族之说,其义富,其辞危,使读焉者怵然知变,于国论殆有助乎?是旨也,予又惑焉。凡为书,必与其时之学者相入,而后其效明。今学者方以时文、公牍、说部为学,而严子乃欲进之以可久之词,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之书,吾惧其舛驰而不相入也。虽然,严子之意盖将有待也。待而得其人,则吾民之智瀹矣。是又赫胥氏以人治归天演之一义也欤? 光绪戊戌孟夏桐城吴汝纶叙。 自序 英国名学家穆勒约翰有言:“欲考一国之文字语言而能见其理极,非谙晓数国之言语文字者不能也。”斯言也,吾始疑之,乃今深喻笃信,而叹其说之无以易也。岂徒言语文字之散者而已,即至大义微言,古之人殚毕生之精力,以从事于一学,当其有得,藏之一心则为理,动之口舌、著之简策则为词。固皆有其所以得此理之由,亦有其所以载焉以传之故。呜呼,岂偶然哉!自后人读古人之书,而未尝为古人之学,则于古人所得以为理者,已有切肤精怃之异矣。又况历时久远,简牍沿讹。声音代变,则通假难明;风俗殊沿,则事意参差。夫如是,则虽有故训疏义之勤,而于古人诏示来学之旨,愈益晦矣。故曰,读古书难。虽然,彼所以托焉而传之理,固自若也。使其理诚精,其事诚信,则年代国俗无以隔之。是故不传于兹,或见于彼,事不谋而各有合。考道之士,以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证诸吾古人之所传,乃澄湛精莹,如寐初觉。其亲切有味,较之觇毕为学者万万有加焉。此真治异国语言文字者之至乐也。 今夫六艺之于中国也,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者尔。而仲尼之于六艺也,《易》、《春秋》最严。司马迁曰:“《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谓本隐之显者,观象系辞以定吉凶而已,推见至隐者,诛意褒贬而已。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乃推卷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其言若诏之矣。二者即物穷理之最要涂术也。而后人不知广而用之者,未尝事其事,则亦未尝咨其术而已矣。 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其所得以为名理、公例者,在在见极,不可复摇。顾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此非傅会扬己之言也。吾将试举其灼然不诬者,以质天下。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是已。而吾《易》则名、数以为经,质、力经为纬,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凡力皆乾也,凡质皆坤也。奈端动之例三,其一曰:“静者不自动,动者不自止;动路心直,速率必均。”此所谓旷古之虑。自其例出而后天学明,人事利者也。而《易》则曰:“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后二百年,有斯宾塞尔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书造论,贯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绝作也。其为天演界说曰:“翕以合质,辟以出力,始简易而终杂糅。”而《易》则曰:“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至于全力不增减之说,则有自强不息为之先,凡动必复之说,则有消息之义居其始。而“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之旨,尤为“热力平均,天地乃毁”之言相发明也。此岂可悉谓之偶合也耶!虽然,由斯之说,必谓彼之所明,皆吾中土所前者,甚者可谓其学皆得于东来,则又不关事实,适用自蔽之说也。夫古人发其端,而后人莫能竟其绪,古人拟其大,而后人未能议其精,则犹之不学无术未化之民而已。祖父虽圣,何救子孙之童昏也哉! 大抵古书难读,中国为尤。二千年来,士徇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是以生今日者,乃转于西学,得识古字用焉。此可与知者道,难与不知者言也。风气渐通,士知弇陋为耻。西学之事,问涂日多,然亦有一二臣子,訑然谓彼之所精,不外象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讨论国闻、审敌自镜之道,又断断乎不如是也。赫胥黎氏此书之恉,本以救斯宾寒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夏日如年,聊为迻译。有以多符空言无裨实政相稽者,则固不佞所不恤也。 光绪丙申重九严复序。 |
 南方论坛
南方论坛
 频道热门
频道热门
-
鬼金的小说与绘画
它们以慢的形式推进着,就像刀子,在某一个虚构的想象中,在推进,推进,直到划开皮肤,呈现出白色的茬,然后才是肉,才是红色,破裂的...[详情] -
刘川 译 | 弗兰克·比达特:夜的第四时辰(长诗)
弗兰克·比达特,1970年代出版的首部诗集《黄金州》与《身体之书》虽获评论界关注,但其作为不妥协的原创诗人之声誉真正确立于1983年问...[详情] -
清静 | 深入解读王老莽诗作《三元塔》
这种深度并非老莽刻意为之的深奥,而是源自诗人对生活的敏锐感知和对人性的深刻理解,让读者在阅读中能够获得启示和感悟。其洞察犹如一...[详情] -
美国当代诗人弗朗兹·赖特诗选
美国诗人弗朗兹·赖特,1953年生于维也纳,2015年因肺癌去世,2004年诗集《走向葡萄园岛》获得普利策诗歌奖。他父亲是著名诗人詹姆斯·...[详情] -
马嘶诗选:不与他人同巾器
马嘶,生于四川巴中,现居成都。著有诗集《万古与浮力》《热爱》《春山可望》《莫须有》。曾参加《诗刊》第三十三届青春诗会,获人民文...[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