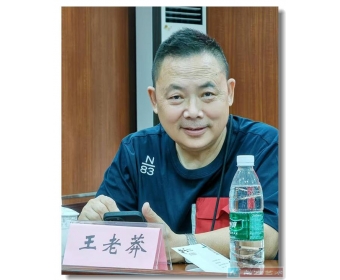新晋诺奖得主托卡尔丘克演说:谁能讲故事编故事,谁就有掌控权
|
今年10月10日,瑞典文学院宣布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获得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称托卡尔丘克“有着百科全书般的叙述想象力,把横跨界限作为生命的一种形式”。 托卡尔丘克在今年3月接受新京报专访之时提到“自然”,那在她看来是一种更高形式的“自我”,是叙事想象力的一种来源。 于人而言,“我”的生长,在表达上最直观地体现为“第一人称”的出现。在本月7日的获奖演说“温柔的叙述者”里,托卡尔丘克也讲到“第一人称”,一方面这种个性化的观点“来自自我的声音,是最自然的、最人性的、最诚实的”,虽然另一方面它不可避免地“放弃了更广阔的视野”。 以下正文即为此次演说全文。 01 我有意识经验的第一张照片是我母亲生我之前拍的。可惜照片是黑白的,也就是说好多细节都失去了,只留下灰的形状。光线柔和、湿润,像春天时节,显然是从窗户渗进来的那种光线,刚好能照亮屋子。我妈妈坐在老收音机旁,收音机带绿眼睛和两个调钮——一个调节音量,另一个调台。这个收音机往后会是我童年难得的伙伴;从它那里我知道了宇宙的存在。旋转乌木旋钮调节天线脆弱的触角,在其所及的范围里有各种不同的电台——华沙、伦敦、卢森堡、巴黎。有时候,声音会变弱,好像在布拉格和纽约,或莫斯科和马德里之间,天线的触角掉在了黑洞里。一旦声音变弱,颤抖就会顺着我的脊柱往下。我深信不同的太阳系和星系通过天线在跟我说话,噼啪噼啪地给我发送重要信息,而我无法解码。
生活中的托卡尔丘克 当我是个小女孩时,我会看向那张照片,我确定地感到妈妈转动收音机的旋钮时,曾寻找过我。像敏锐的雷达那样,她刺透宇宙无尽的领域,试图找出我什么时候、从哪里到达。她的发型和着装(船领)显示出照片拍摄的时间,是六十年代初。注视着画面外的某个地方,背带点拱着的她看到了一些东西,后来看照片的人感觉不到。作为孩子,我想象那是她在朝着时间注视。其实照片里没发生什么——照片拍的是一个场景,而非一个过程。里面的女性有点悲伤,好像陷入了沉思——好像有点迷失。 后来当我向她问起那悲伤——我在无数场合问起过,总是得到同一个反应——我母亲会说,她悲伤是因为我还没出生,可是她已经想我了。 “你怎么会想我,在我还没生下来的时候?”我会问。 我知道你想念的是你失去的某个人,那种渴望是失落感。 “不过换种方式也行得通,”她回答。“想念一个人意味着他们在那里。” 六十年代末,在波兰西部农村的某个地方,我母亲和我,也就是她的小孩,进行了一次短暂的交流,这种交流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给了我一生的力量。因为它使我的存在超越了一般的物质世界,超越了偶然,超越了因果和概率法则。她把我放在时间之外,放在永恒的甜蜜附近。在我孩子的脑海里,我明白了我有比我以前想象的更多的东西。即使我说“我迷路了”,我还是会从“我是”开始——这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奇怪的一组词。 因此,一位从不信教的年轻女子——我的母亲——给了我一个曾经被称为灵魂的东西,从而为我提供了世界上最伟大、最温柔的叙述者。 02 世界是我们每天在信息、讨论、电影、书籍、流言蜚语和小轶事的织布机上编织的织物。今天,这些织布机的范围是巨大的——感谢互联网,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这个过程,或承责任或不,或带着爱意或满怀恨感,或好或坏。当故事改变了,世界也就改变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是由文字构成的。 因此,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也许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叙述这个世界,因此就有巨大的意义。一件事发生了,如故没人讲述那这件事就停止存在并消亡。这不仅是历史学家都知道的事实,而且(也许是最重要的)是每一个政客和暴君都知道。谁能讲故事编故事,谁就有掌控权。 今天,我们的问题在于——似乎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不仅没有准备好讲述未来,甚至讲述具体的当下、讲述当今世界的超高速转变也没准备好。我们缺乏语言、缺乏视角、缺乏隐喻、缺乏神话和新的寓言。然而,我们确实经常看到有人试图利用陈旧过时的叙述,这些叙述无法将未来融入对未来的想象,毫无疑问这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旧的某个什么总比新的什么也没有强,要不就试图以这种方式来应对我们自身视野的局限。总之,我们缺乏讲述世界故事的新方法。 我们生活在众声喧哗的第一人称叙述的现实中,我们从四面八方听到多音杂音。我说到第一人称,指的是那种狭隘地围绕着讲述者自我的故事,讲述者或多或少直接地写她自己,或通过她自己而写。我们已经确定,这种个性化的观点,这种来自自我的声音,是最自然的、最人性的、最诚实的,即使它放弃了更广阔的视野。照此理解,以第一人称叙述是编织一个绝对独特的模式,是唯一的;它有一种作为个体的自主,意识到你自己和你的命运。然而,这也意味着在自我和世界之间建立一种对立,这种对立有时会让人感到疏离。 我认为第一人称叙事是当代光谱上的一大特色,个体在其中扮演着世界主观中心的角色。西方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自我发现的基础上的,而自我发现正是我们衡量现实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在这里,人是主角,他的判断——尽管是众多判断之一——总是被认真对待。以第一人称编织的故事似乎是人类文明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满怀信心地读着。这类故事,当我们通过某个不同于其他的自我的视角看世界时,与叙述者建立了一种特殊的联系,叙述者要求他的听众把自己放在他独特的位置上。 第一人称叙事对文学,普遍来说对人类文明所做贡献怎么高估也不为过——它完全改写了世界的故事,所以,世界不再是英雄和神明(他们对我们没有影响)行动的地方,而是为我们这样的人(带着各自的历史)准备的。我们很容易认同和我们一样的人,这就在故事的叙述者和读者或听众之间产生了一种基于同理心的情感理解。而这,就其本质而言,汇集并消除了边界;在一部小说中,叙述者的自我和读者的自我之间的界限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引人入胜的小说”实际上依赖于模糊边界——读者通过移情作用,暂时成为叙述者。因此,文学变成了一个交流经验的场所,一个人人都能讲述自己命运或表达自己的地方。因此,这是一个民主的空间——任何人都可以畅所欲言,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发出声音。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成为作家和讲故事的人。我们只要看看统计数据就知道这是真的。 每次我去书展,我都能看到当今世界上出版的书有多少与作者本人有关。表达本能或许和其他保护我们生命的本能——它在艺术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一样强烈。我们想要被关注,我们想要与众不同。“我要告诉你我的故事”,或“我要告诉你我的家庭故事”,甚至简单地说,“我要告诉你我去过哪里”,构成了当今最流行的文学体裁。这是一个大范围的现象,也因为现在我们普遍能够获得写作,许多人获得了用文字和故事表达自己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以前只有少数人拥有。 然而矛盾的是,这种情况类似于由独唱者组成的唱诗班,每个声音都在争抢注意力,都走着相似的路线,淹没了彼此。我们知道关于他们的一切,我们能够认同他们,体验他们的生活,就好像他们是我们自己的一样。 然而,引人注目的是,读者的体验往往是不完整和令人失望的,因为事实证明,表达作者的“自我”很难保证具有普遍性。我们所缺失的——似乎是——故事的维度,也就是寓言。因为寓言的主人公是他自己,一个生活在特定历史和地理条件下的人,但同时他也远远超出了这些具体的细节,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普通人”。当一个读者读到一个人写在小说里的故事时,他可以认同这个人物的命运,并把人物的处境当作自己的处境来考虑,而在一个寓言故事里,他必须完全放弃他的独特性,成为一个“普通人”。在这个要求很高的心理操作中,寓言概括了我们的经验,为迥然不同的命运找到了一个共同点。我们很大程度上在观点中失掉了寓言,证明我们目前的无助。 也许为了不被纷繁复杂的头衔和姓名所淹没,我们开始把文学这个庞然大物划分成不同的类别,我们把它当作各种不同类型的运动,把作家当作经过特殊训练的运动员。 文学市场的普遍商业化导致了文学作品的分门别类——现在有这种或那种文学的集市和节日,各不相关,这就形成了一群渴望阅读犯罪小说、幻想小说或科幻小说的读者。这种情况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要做的仅仅是帮助书商和图书馆员摆放书架上数量巨大的出版物,给读者在浩瀚的作品提供指引,不仅现有的作品被归入抽象类别中,而且好多作家也据此开始写作。越来越多地,体裁作品就像蛋糕模子,生产极度相似的产品,它们的可预见性被视为一种美德,它们的平庸被视为一种成就。读者知道会发生什么,并确切地得到了他想要的。 我一直本能地反对这样的命令,因为这会限制作者的自由,会使我不愿实验或越界,一般来说这实际是创造的本质。而且他们完全将创作过程中的特立独行全部排除在外,没有这些怪癖,艺术便迷失了。一本好书并不需要捍卫其类属关系。把文学划分为不同类型是文学整体商业化的结果,也是把文学作为产品来销售的结果(还用上了销售、推广、目标等全套哲学),这种分类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类似产物。 今天我们心满意足地见证了一种世界性故事的新叙述方式的诞生,这种叙述方式正是由银幕上的系列片提供的,其中的隐藏任务便是引导我们进入一种忘我之境。当然,这种讲故事的方式早已存在于神话和荷马史诗中,毫无疑问,赫拉克勒斯、阿喀琉斯或奥德修斯是这系列故事中的第一批英雄。但在此之前,这种模式从未覆盖如此大的空间,也未对集体想象产生过如此强大的影响。二十一世纪的前二十年是这一系列故事不容质疑的财产。它们对于讲述世界故事的模式(以及对我们了解这些故事的方式)是革命性的。 在今日版本中,系列故事不仅扩大了我们对时间领域叙事的参与,产生了多样化的节奏、分支和角度,而且还引入了自己的新秩序。因为在很多情况下,系列故事的任务是尽可能长时间地吸引观众的注意力——系列故事增加了叙事线索,并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以至于陷入迷局的时候,它甚至回到了古老的叙事技巧上,这种技巧曾在经典歌剧中被妥协采用,也就是所谓的“天降神兵”(Deus ex machina )。新剧集的创作往往需要对人物的心理状态进行特别的全面修改,以便他们能更好地适应剧情中的事件发展。一个刚开始温和而保守的角色最后变得充满暴力和仇恨,配角摇身一变为主角;而我们原本渐生好感的主角,失去了意义或者实际上完全消失了,真是让人万分沮丧。 新一季的可能实施将开放式结局变得尤为必要,在这种开放结局中,所谓神秘的情感净化(catharsis)毫无发生或充分回应的可能——情感净化,以前是内部心理转变的经验,参与到故事行动中的充实感与满足感。这种情感实现,而不是结论——情感宣泄的持续性延迟——使观众产生依赖,催眠了她。成名于一千零一夜的契约中断型故事在很久以前就被发明了,如今在系列故事中大大胆回归,改变了我们的主观性,施以奇异的心理影响,它将我们从自己的生活中撕裂出来,像兴奋剂一样催眠着我们。同时,这种系列故事将自己投入到新的、旷日持久且无序的世界节奏中,投入到它混乱的交流、不稳定性和流动性中。这种讲故事的方式或许是当今最具创造性的寻找新公式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系列故事中包含着关于未来叙事的严肃探讨,包含着重新编排故事以其适应我们新现实的努力。 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太多矛盾、事实相互排斥的世界里,一切事物都咬牙切齿地争锋相对。 我们的祖先相信,获得知识不仅会给人们带来幸福、福祉、健康和财富,而且还会创造一个平等和公正的社会。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缺少的是来自知识的普遍智慧。 约翰·阿摩司·康米纽斯(John Amos Comenius)是十七世纪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创造了“pansophism”一词,以之表示可能达到的全知理念和普遍知识,这种知识包含了所有可能获得的认识。最重要的是,这也是一种所有人都能获得知识的梦想。如果不是接触到关于世界的事实,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怎么会转变成一个对世界和自身具有反思的个体呢?唾手可得的知识是否意味着人们将会变得明智,将会沉着而智慧地指导他们自己的生活呢?当互联网刚出现时,这样的理念似乎将最终被完全实现。也许,像许多志同道合的思想家们一样,我赞赏和支持的维基百科,对康米纽斯来说亦是人类梦想的实现——如今,我们能够创造和接收大量事实,它们民主地到达地球上的几乎每个地方,并不断被补充和更新。 梦想成真往往令人失望。事实证明,我们没有能力承受如此巨大的信息,这种信息不是团结,归纳和释放,而是分化,分裂,被包围在单个小气泡中,创造出许多彼此不相容甚至公开敌对,互相对立的故事。 此外,互联网彻底且毫无反思性地服从于市场流程,并为垄断者们所掌握。互联网控制着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并不是为了扩大信息访问范围而被用于广泛求知,相反,它主要是用来对用户的行为进行编程,正如我们在“Cambridge Analytica”事件之后所认识到的。我们没有听到世界和谐的声音,而是听到了刺耳的声音,这是一种难以忍受的静电,我们在绝望中尝试着捕捉一些安静的旋律,甚至是最微弱的节奏。这句著名的莎士比亚名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符合于现在这刺耳的现实:互联网越来越像痴人说梦,充满了喧哗与骚动。 不幸的是,政治学家的研究也与约翰·阿摩司·康米纽斯的直觉相矛盾,他的直觉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即关于世界的信息越普及,则政治家越能发挥理性并做出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但是,事情似乎根本不是那么简单。信息可能是压倒性的,其复杂性和模糊性导致了各种各样的防御机制——从拒绝到压制,甚至逃脱到简单化的,意识形态的和党派思维的简单原则中。 其中,虚假消息引出了关于虚构是什么的新问题。反复被欺骗,误传或误导的读者已开始慢慢获得特定的神经质特质。对虚构感到疲惫的反应可能是非虚构的巨大成功,在这种巨大的信息混乱中,我们的头顶充满了尖叫:“我会告诉你真相,只有真相”,以及“我的故事基于真实事件!” 自从撒谎已经成为一种危险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来,虚构就失去了读者的信任,即使它仍然是一种原始工具。我经常被问到这个难以置信的问题:“你写的这句话是真的吗?”而每当此时,我都感到这个问题预示着文学的终结。 从读者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是无害的,但在作者的耳中,它听起来却是世界末日。我该怎么说?我该如何解释汉斯·卡斯托普,安娜·卡列尼娜或小熊维尼的本体论地位? 我认为读者的这种好奇心是文明的退化。它损害了我们的多维能力(具体的,历史的,也是象征的,神话的),我们以之参与到那称为生活的一系列事件中。生命是由事件创造的,但是只有当我们能够解释它们,尝试理解它们并给它们增添意义,才意味着它们已转化为经验。事件是事实,但经验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区别。是经验,而非事件,构成了我们的生活素材。经验是已经被解释并存在于记忆中的事实。它也指我们脑海中的某种基础,指含义的深层结构,在此之上,我们可以展开自己的生活,并对其进行充分而仔细的检查。我认为神话履行了这种结构的功能。每个人都知道神话从未真正发生过,但一直在发生。现在,它们不仅继续在古代英雄的冒险中发生,而且也进入了当代电影,游戏和文学中,成为了无处不在且最受欢迎的故事。奥林匹斯山居民的生活已转移至《王朝》(Dynasty),而英雄的英勇事迹则得到了劳拉·克罗夫特(Lara Croft)的支持。 在对真理与谎言的坚定划分中,文学创造了我们的经验,这些经验所形成的故事具有其自身的维度。 我从未对任何关于虚构和非虚构的明确区分感到特别激动,或许我们没能意识到这种区分是宣判性和自我解释的。在虚构定义的海洋中,我最喜欢的一种也是最古老的一种,它来自亚里斯多德。虚构总是某种真理。 作家、散文家E.M.福斯特(E.M. Forster)对真实故事和情节的区分也使我信服。他说,当我们说“国王死了,不久王后也死了”时,这是一个故事。但是当我们说“国王死了,不久王后因伤心而死”时,那就是情节。每种虚构都涉及这样的过渡:从“接下来发生了什么?”的疑问到尝试根据我们的人类经验来理解它:“为什么会这样发生?” 文学以“为什么”开始,即使我们要用普通的“我不知道”来一遍又一遍地回答这个问题。 因此,文学提出了无法借助维基百科回答的问题,因为它不仅限于信息和事件,还直接涉及我们的经验。 但是,与其他形式的叙事相比,小说和文学可能总体上在我们眼前确实已经变得有些边缘化了。图像以及直接传递体验的新形式(电影,摄影,虚拟现实)的影响力意味着它们可以替代传统阅读形式。阅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心理和知觉过程。简而言之:首先将最难以捉摸的内容概念化和口头化,转变为符号和象征,然后将其从语言“解码”回为体验。那需要一定的智力。最重要的是,它需要集中精力和注意力,而在当今这个极度分散注意力的世界中,这种能力变得越来越罕见。 从口头表达,依靠鲜活的文字和人类记忆到古登堡(Gutenberg)革命,人类在交流和分享自己的经验交流和分享自己的经验方面已经有悠久的历史,当时故事开始通过写作广泛传播,并以此方式固定和编纂,尽可能地复制而无需更改。这一变化的主要成就是,我们开始用语言和写作来辨别思维。 今天,我们正面对同样重大的革命,无需依靠印刷文字就可以直接传播经验。 当你只需拍照并立即通过社交网站直接将照片发送到世界上时,便不再有任何写旅行日记的需要。不需要写字,因为打电话更方便。当你可以直接进入电视连续剧时,为什么还要写厚厚的小说?与其和朋友一起出去玩,不如去玩游戏。写一部自传?没有意义,因为我在Instagram上关注着名人们的生活而且可以了解他们的一切。 正如我们在二十世纪回想着电视和电影的影响一样,今天,图像甚至不是文字最大的对手。这是一种体验世界的完全不同的维度——直接作用于我们的感官。 03 我不想就讲述关于世界的故事遇到的危机描绘出一幅全景图。但我时常被一种世界有所空洞的感觉困扰。当透过玻璃屏幕与APP感受这一切时,这世界不知怎得变得虚幻,遥远,两极,奇怪地不可描述,即使在这里想找到任何一段信息都令人惊奇地容易。在这个时代,这些令人担忧的词,“有些人”,“有些事”,“有些地方”,“有些时候”,变得比那些极为具体,确切,用十足的肯定说出的话——诸如“地球是平的”,“接种会致死”,“气候变化是胡扯”,“民主在地球的任何一处都没有受到威胁”,显得更危险。“有些地方”有些人在试图越过海洋时溺水身亡。“有些地方”,在“有些”时候,战争正在“某种程度”地发生。在信息的洪流中,个体的声音纷纷失去了轮廓,很快在我们的记忆中被瓦解,变得不真实,然后消失。 愚蠢,残忍,憎恨言论,暴力影像的潮流被各种各样的“好消息”抵消了,但我无法用言语表达它未能掩盖的痛苦,察觉到这世界有地方不对头的痛苦。如今这曾仅为神经质诗人独占的感觉,像是一种无法被定义的瘟疫,焦虑从四面八方渗出。 文学是极少数可能让我们贴近世界确凿事实的领域之一,由于它的本质涵盖了心灵的哲学,也因为它始终关注人物内在的合理性与动机,揭示出他们难以用其他方式向他人展开的体验。唯有文学能够让我们深入其他存在的生命,理解他们的逻辑,分享他们的感情,体验他们的命运。 故事永远在意义周围游荡。即使它并不直接地将道理表达出来,甚至有时它形成,故意拒绝寻求意义而专注于形式或实验来寻求新的表达方式。当我们阅读哪怕是最行为主义,我们也情不自禁地会问:“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事?”,“这有什么含义?”,“它想说明什么”,“它要将我们引向何处?”我们的思维很有可能在不断地给予百万个围绕着我们的刺激解释时,以一种故事的方式进化了,以至于我们入睡时,仍在无休止地修改它们的叙述。因此,故事是一种在时间中编织起无限量信息,打开它们向过去,现在,未来的通路,把握住它们的每一次再现,并将它们安放在因果类别中的一种方式。理智与情感都参与其中。 这也难怪,故事最早的发现之一是除了总是以恐怖与非人化的面目出现在人类面前,却也在每日的现实中引入了秩序与永恒的“命运”。 |
 南方论坛
南方论坛
 频道热门
频道热门
-
鬼金的小说与绘画
它们以慢的形式推进着,就像刀子,在某一个虚构的想象中,在推进,推进,直到划开皮肤,呈现出白色的茬,然后才是肉,才是红色,破裂的...[详情] -
刘川 译 | 弗兰克·比达特:夜的第四时辰(长诗)
弗兰克·比达特,1970年代出版的首部诗集《黄金州》与《身体之书》虽获评论界关注,但其作为不妥协的原创诗人之声誉真正确立于1983年问...[详情] -
清静 | 深入解读王老莽诗作《三元塔》
这种深度并非老莽刻意为之的深奥,而是源自诗人对生活的敏锐感知和对人性的深刻理解,让读者在阅读中能够获得启示和感悟。其洞察犹如一...[详情] -
美国当代诗人弗朗兹·赖特诗选
美国诗人弗朗兹·赖特,1953年生于维也纳,2015年因肺癌去世,2004年诗集《走向葡萄园岛》获得普利策诗歌奖。他父亲是著名诗人詹姆斯·...[详情] -
马嘶诗选:不与他人同巾器
马嘶,生于四川巴中,现居成都。著有诗集《万古与浮力》《热爱》《春山可望》《莫须有》。曾参加《诗刊》第三十三届青春诗会,获人民文...[详情]